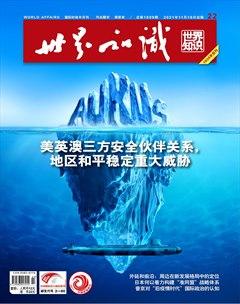中日青年對彼此國家的認知何以重要
師艷榮
2021年10月25日,在第17屆“北京—東京論壇”開幕式致辭中,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表示,中日雙方應著眼長遠,持之以恒地推進青少年交流,培養中日友好事業的接班人。
不久前由中國外文局和日本言論NPO共同實施的第17屆“中日關系輿論調查”顯示,對華無好感的日本民眾達90.9%,同時中國民眾對日無好感比例也升至66.1%。
但相較于中日兩國民眾相互好感度整體下滑,青年人對彼此國家的好感度要樂觀得多。2021年2月,日本內閣府公布的外交輿論調查顯示,超三成的日本青年對華有好感。
中日青年對彼此國家的好感高于整體水平,為兩國民眾間的彼此認知注入了一股暖流。
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持續下降
輿論調查是判斷民意的重要指標,中日兩國民眾對于對方國家的好感度認識存在明顯差異。自2013年以來,中國民眾對日好感度一直保持回暖態勢。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卻持續下降。特別是疫情爆發的2020年,中日民間相互好感度“一升一降”反差明顯。2020年11月的第16屆“中日關系輿論調查”顯示,與中國民眾45.2%的對日好感度相比,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則創下10%的新低,而對華無好感的日本民眾比例高達89.7%。
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持續下降,原因是多方面是:一是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國際形勢下,作為美國同盟國的日本緊跟美國步伐,加入圍堵中國陣營,宣傳“中國威脅論”等,嚴重貶損中國形象。二是中國國力的迅速提升,2010年即反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力的反差令日本民眾的心態也越發不平衡,甚至于產生仇視心理。而日本媒體也投其所好,大肆報道有關中國的負面新聞,抹黑中國形象。本次輿論調查中,只有19.6%的日本受訪者肯定本國媒體對改善兩國關系、促進兩國民眾相互理解的貢獻。可見,日本媒體的偏頗報道在惡化中日關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三是日本政治生態中右傾化傾向增強,對華友好的青年政治家不斷減少,民間交流中能夠推動中日友好的青年人才十分短缺。

2019年12月8日,“中日青年友好使者沙龍”活動在北京舉行,數百名中日青年學子參加。
超三成日本青年對華有好感
但本次調查顯示,與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整體下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日兩國青年對彼此國家的好感度明顯高于中老年受訪者。日本外交輿論調查也表明日本青年對華好感度明顯高于其他年齡段。
日本內閣府開展的外交輿論調查是日本各項有關外交問題的民意測驗中最具權威性的調查。2021年2月,日本內閣府公布的第45次外交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在受訪的3000名日本人(18歲以上男女)中,對中國“不抱親近感”及“較無親近感”的人,合計占比為77.3%;對中國“抱有親近感”和“較有親近感”合計為22%。認為中日關系“良好”的比例為17.1%,而認為中日關系“不太好”的比例為81.8%。
從各年齡段看,18~29歲、30~39歲、40~49歲、50~59歲、60~69歲及70歲以上各年齡段人群對中國“有好感”的占比分別為34.3%、25.0%、25.3%、19.9%、14.7%和19.2%。很明顯,18~29歲青年人對中國的好感度領先于其他年齡段。
后疫情時代的中日青年交流
本次輿論調查顯示,70%的中國公眾受訪者、50.9%的日本公眾受訪者認為民間交流對促進中日關系重要。但新冠疫情下中日民間交流受阻。66.6%的中國受訪者、50.3%的日本受訪者認為過去一年兩國民間交流不夠活躍。
中日民間交流受阻主要體現在現場式的、面對面交流活動因疫情而“停擺”,但實際上利用新媒體的線上交流卻越來越活躍。這一點在青年人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一是新媒體成為日本青年人獲取對華認知的重要媒介。雖然日本媒體在對華報道上存在很大的導向型,以負面為主,這對于以傳統媒體為信息主要來源的中老年人來說影響較大。但對廣大的青年人來說,他們接收信息的渠道已不局限于報紙、電視、廣播等傳統的新聞媒介,抖音、嗶哩嗶哩(B站)等新媒體成為他們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和渠道。二是中日青年之間有共同的文化需求。日本的二次元文化、動漫文化、電競文化在中國流行文化中占有很大市場,同時,中國年輕人喜歡的抖音、直播帶貨、美妝文化等也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人。因此,后疫情時代,以日本青年為主體的對日民間交流更契合當前的形勢。
因此,在后疫情時代,中日雙方更應從交流的廣度、方式、內容等方面不斷創新雙方青年交流新途徑,推動兩國關系向好發展。
例如積極承辦國際性的青年交流項目,努力將中日青年交流納入到多邊區域交流框架中。自2013年以來,中日韓三國已聯合舉辦七屆“東亞文化之都”評選活動,中國泉州、青島、寧波、西安、揚州、紹興、濟南與日本橫濱、新潟、奈良、東京都豐島區、北九州市、大分縣等相繼入選。不妨以這些“東亞文化之都”為平臺,積極開展中日韓青年文化交流活動。另外,還可以不斷擴大作為“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項目”(GYLD)長期活動之一的“國際青年中國行”活動規模,吸納更多的日本青年人才參與到活動中來。
再如探索中日青年交流新模式,利用在線視頻等方式延續因疫情限制而“停擺”的中日青年交流活動。可充分發揮新媒體在中日青年交流中的橋梁作用。抖音、B站等新媒體成為中日青年相互交流與了解對方國家的重要媒介,這種更貼近生活的民間交流渠道值得鼓勵。還可為在華日本留學生和在華日本青年搭建文化交流平臺,組織他們參加各種青少年交流或參觀等活動,使其對中國有更深的感知。
又如以流行文化為媒介,拓寬交流領域,突破語言、武術、書法、茶道等傳統文化交流的界限,將新一代年輕人崇尚的二次元文化、電競文化、漢服文化等納入到交流范疇中,政府助推以青年為載體的流行文化產品“走出去”。
中日青年的相互認知將影響著未來兩國關系發展的方向。在中日關系的困境中,從青年民間交流中尋找突破口,改變日本青年對華認知,是改善兩國關系并促使其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