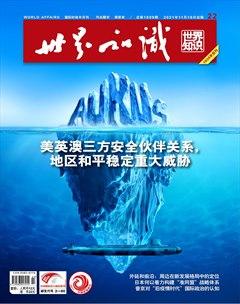美英澳核潛艇協(xié)議可能導(dǎo)致國際核不擴(kuò)散體制潰堤
羅曦
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guān)系(AUKUS)的首要任務(wù)是幫助澳大利亞建造核潛艇,從而開創(chuàng)了核武器國家與非核武器國家合作制造核動(dòng)力潛艇的先例,也將使澳成為世界上首個(gè)擁有核潛艇的非核武器國家。三國在9月15日首腦會(huì)晤后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稱,“將長期致力于維護(hù)印太地區(qū)的和平與穩(wěn)定”。然而,審視三邊核潛艇協(xié)議之后的國際核不擴(kuò)散進(jìn)程和“印太”地區(qū)安全形勢,卻是與和平穩(wěn)定漸行漸遠(yuǎn)了。
凸顯《不擴(kuò)散核武器條約》漏洞
國際核不擴(kuò)散機(jī)制以1970年生效的《不擴(kuò)散核武器條約》(NPT)為基石,旨在以禁止核試驗(yàn)、限制核軍備、防止核武器擴(kuò)散為手段,以實(shí)現(xiàn)降低核風(fēng)險(xiǎn)并最終實(shí)現(xiàn)徹底廢除核武器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然而,鑒于NPT締結(jié)時(shí)的時(shí)代背景與國際形勢,以NPT為基石的國際核不擴(kuò)散體制在公平、地位和責(zé)任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和漏洞,例如條約只約束締約國,對締約國之外的國家沒有約束力;退約機(jī)制模糊不清,締約國享有事實(shí)上單方面退約的自由權(quán)利;沒有規(guī)定對違約國的制裁舉措;國際原子能機(jī)構(gòu)(IAEA)在執(zhí)行監(jiān)督保障職能時(shí)受到多重制約,等等。
三邊核潛艇協(xié)議的達(dá)成暴露出此前被國際社會(huì)忽略的NPT一個(gè)重要漏洞,即,沒有禁止、也沒有監(jiān)督非核武器國家制造或運(yùn)作核動(dòng)力設(shè)施的行為,這在某種程度上為無核武器國家將核燃料轉(zhuǎn)化為核武裝提供了空間,為核燃料或核技術(shù)在“常規(guī)用途”與“軍事用途”之間切換提供了可能性。
為了防止非核武器國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時(shí)對核材料、核技術(shù)進(jìn)行“非法”擴(kuò)散,NPT第三條規(guī)定,“國際原子能機(jī)構(gòu)制定并執(zhí)行安全保障措施,以確保特種裂變材料及其他,不致用于推進(jìn)任何軍事目的。”為實(shí)施核保障監(jiān)督職能防止核武器擴(kuò)散,IAEA于1997年通過了《附加議定書》范本,旨在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保障監(jiān)督系統(tǒng)。三邊核潛艇協(xié)議的達(dá)成,同樣預(yù)示著這套保障監(jiān)督系統(tǒng)并不“完整”,即缺少對核反應(yīng)堆尤其是海上核反應(yīng)堆的監(jiān)督保障職能,缺少對無核武器國家將核材料用于“非條約限制下的軍事用途”的監(jiān)督保障職能。在《不擴(kuò)散核武器條約》這一重要漏洞的庇護(hù)下,美英兩國對澳進(jìn)行核武裝的戰(zhàn)略企圖一覽無遺。
在美英兩國提供敏感性核援助之后,澳大利亞的擁核前景究竟如何?通常來說,國家實(shí)現(xiàn)核武裝需要同時(shí)滿足四個(gè)前提條件:高濃縮钚或鈾、工藝技術(shù)流程、搭載核彈頭的運(yùn)載工具,以及政治意愿。澳是全球第三大鈾礦出口國和全球鈾資源探明儲(chǔ)量第一大國,也是核供應(yīng)集團(tuán)的核心國家之一。冷戰(zhàn)時(shí)期美英法均在澳進(jìn)行過數(shù)次核武器試驗(yàn)與反應(yīng)堆掩埋。在澳新(西蘭)美同盟的軍事承諾下,澳一直在追求美國的核保護(hù)傘。此次美英兩國將直接向澳方提供高濃縮鈾用于核潛艇上的核燃料反應(yīng)堆,雖然按照協(xié)議,澳方需保證核潛艇30年服役期滿后將其核燃料反應(yīng)堆返還供應(yīng)國,但鑒于IAEA在該領(lǐng)域監(jiān)督保障職能的缺失,澳要想突破從“用核”到“擁核”的臨界點(diǎn),已非技術(shù)或燃料問題,而只是“機(jī)會(huì)窗口”和政治借口的問題。
美國有選擇的核不擴(kuò)散政策
當(dāng)今世界的國際核不擴(kuò)散機(jī)制,是美國主導(dǎo)下的國際安全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受美國“絕對優(yōu)先”和“實(shí)用主義”理念影響,本應(yīng)凸顯公平、價(jià)值和道義原則的國際核不擴(kuò)散機(jī)制正逐步顯現(xiàn)出工具化、片面化、策略化的弊端。出于確保盟友安全、制衡地區(qū)對手的目的,美推行的地區(qū)核不擴(kuò)散政策分為“選擇性”擴(kuò)散和“歧視性”不擴(kuò)散這樣的“雙標(biāo)”做法,預(yù)示著“美國治下”的國際和地區(qū)核不擴(kuò)散形勢始終逃脫不掉反復(fù)性、多變性、復(fù)雜性的特點(diǎn)。
針對對手或者“不友好”國家,美常以“核不擴(kuò)散”為名,對其濫施政治孤立、經(jīng)濟(jì)制裁和軍事威懾。但美國強(qiáng)制性的不擴(kuò)散政策往往導(dǎo)致對手國家突破重重阻力“以核謀安全”,朝鮮半島、伊朗核問題的演變就是結(jié)果。而對于盟友或者伙伴國家,美往往采取“選擇性”支持政策,以政治承諾、前沿部署、核材料與核技術(shù)分享以及核磋商等手段,向它們提供延伸威懾保護(hù)。在美庇護(hù)之下,英國、法國、聯(lián)邦德國、意大利、日本、韓國、以色列等都已發(fā)展或曾經(jīng)試圖發(fā)展核武器。其中,英、法成為聯(lián)合國承認(rèn)的核大國,印、以成為事實(shí)核國家,韓擁有武器級(jí)鈾濃縮能力,意擁有核燃料后處理能力,德、日均擁有武器級(jí)鈾濃縮能力和核燃料后處理能力。
美針對印度的核不擴(kuò)散政策最具代表性。2006年美印正式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xié)議》,規(guī)定IAEA對其民用核設(shè)施進(jìn)行全面保障監(jiān)督,但選擇性地保留八座反應(yīng)堆、兩座塊增殖堆以及三座研究堆,不進(jìn)行全面保障監(jiān)督,使印成為世界上唯一不加入NPT卻可突破核封鎖的國家。
美英澳此次達(dá)成三邊核潛艇協(xié)議,既是美借助澳地緣特點(diǎn)遏制中國海上力量發(fā)展的結(jié)果,也是澳“依美靠美”借機(jī)實(shí)現(xiàn)本國核潛艇野心的結(jié)果,同樣還是美“選擇性”核不擴(kuò)散政策的結(jié)果。近年來,美國對外戰(zhàn)略重心由大國合作邁向大國競爭,其核政策議題重心由核安全向核武現(xiàn)代化轉(zhuǎn)移,核軍控外交政策更多呈現(xiàn)“工具主義”“實(shí)用主義”傾向。在“任性”退出《中導(dǎo)條約》《開放天空條約》《武器貿(mào)易條約》等國際多邊軍控條約的同時(shí),以“選擇性”支持和“歧視性”打壓為鮮明特征的地區(qū)不擴(kuò)散政策,成為美制衡地區(qū)對手、維護(hù)地區(qū)主導(dǎo)權(quán)的有力手段。
引發(fā)地區(qū)軍備競賽升級(jí)風(fēng)險(xiǎn)
國際多邊核軍控進(jìn)程存在著諸多結(jié)構(gòu)性難題,諸如五核國如何盡快達(dá)成“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諾,如何在NPT框架下協(xié)調(diào)推進(jìn)核裁軍與防擴(kuò)散進(jìn)程,等等。國際社會(huì)對既存的多邊核裁軍行動(dòng)(如《禁止生產(chǎn)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條約》談判、《全面禁止核試驗(yàn)條約》生效等)存在巨大爭議。受新冠疫情影響,五年一度的NPT全球?qū)徸h大會(huì)推遲舉辦,大量重要的國際軍控活動(dòng)及會(huì)議改以線上方式進(jìn)行。2021年1月22日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條約》進(jìn)一步凸顯無核國家與有核國家之間的結(jié)構(gòu)性矛盾。三邊核潛艇協(xié)議的達(dá)成則進(jìn)一步加劇了地區(qū)海上核軍備競賽與危機(jī)升級(jí)風(fēng)險(xiǎn),嚴(yán)重威脅地區(qū)安全形勢,沖擊既有國際核不擴(kuò)散進(jìn)程。
一是地區(qū)國家恐將陷入核潛艇軍備競賽。2020年11月巴西開始在法國的援助下建造核潛艇,并計(jì)劃于2034年服役。2020年8月韓國發(fā)布“2021~2025年國防計(jì)劃”,表示有可能建造三艘4000噸級(jí)核動(dòng)力潛艇。2021年9月韓國首次成功試射潛射彈道導(dǎo)彈,成為首個(gè)具有海基戰(zhàn)略遠(yuǎn)程打擊能力的無核武器國家。三邊核潛艇協(xié)議的達(dá)成為那些已簽署NPT但依然有“核野心”的國家開啟了“先例”,即通過制造或購進(jìn)核潛艇來借機(jī)實(shí)現(xiàn)“核武裝”并免遭國際社會(huì)譴責(zé)和制裁。韓國已向美明確表示,希望美能向其提供類似技術(shù),日本國內(nèi)也重新掀起自制核潛艇的呼聲。
二是海基中程導(dǎo)彈擴(kuò)散引發(fā)該地區(qū)危機(jī)升級(jí)風(fēng)險(xiǎn)。美國自退出《中導(dǎo)條約》后,一直在“印太”地區(qū)謀求研發(fā)和部署陸基中程彈道導(dǎo)彈和巡航導(dǎo)彈,其中包含改裝海基“戰(zhàn)斧”的備選方案。在美英援助下,澳大利亞的核潛艇部隊(duì)將仿照英國潛艇配置,搭載“戰(zhàn)斧”潛射對陸攻擊式巡航導(dǎo)彈(TLAM),從而實(shí)現(xiàn)在“印太”地區(qū)部署海基中導(dǎo)的戰(zhàn)略構(gòu)想。盡管澳方宣稱該型導(dǎo)彈將搭載常規(guī)彈頭,但由于其射程短、易突防且可攜載核常兩用彈頭,極易造成對手國家的情報(bào)失誤和戰(zhàn)略誤判。為防止遭受海上核突襲,對手國家可能發(fā)動(dòng)先發(fā)制人攻擊,從而引發(fā)由常規(guī)沖突升級(jí)為核沖突的風(fēng)險(xiǎn)。

2021年10月18日,美國國務(wù)卿布林肯在華盛頓與國際原子能機(jī)構(gòu)總干事格羅西舉行會(huì)晤。
三是對幾近停滯的國際核不擴(kuò)散進(jìn)程造成新的沖擊。首先是加劇了五核國之間的內(nèi)部矛盾,削弱了五核國機(jī)制的合作基礎(chǔ)。澳方在未與法國提前溝通的情況下,取消了之前與法總價(jià)值約為560億歐元的潛艇合同,導(dǎo)致法澳關(guān)系與美英法關(guān)系受影響。其次是海基“戰(zhàn)斧”巡航導(dǎo)彈的可能性擴(kuò)散,將嚴(yán)重削弱“導(dǎo)彈及其技術(shù)控制機(jī)制”(MTCR)。該機(jī)制的目標(biāo)是限制成員國向其他國家轉(zhuǎn)讓射程300公里、荷載500公斤以上的投送系統(tǒng)及其相關(guān)技術(shù)。美國向澳方提供“戰(zhàn)斧”巡航導(dǎo)彈以及“聯(lián)合增程防區(qū)外導(dǎo)彈”(JASSM-ER),實(shí)際上是對“導(dǎo)彈及其技術(shù)控制機(jī)制”的破壞。再就是對南太平洋無核區(qū)的負(fù)面影響。作為《南太平洋無核武器區(qū)條約》的締約國,澳曾為推動(dòng)南太平洋地區(qū)無核化進(jìn)程、反對英法等國在南太地區(qū)的核試驗(yàn)發(fā)揮巨大作用。美英澳三邊核潛艇協(xié)議,已然顛覆了澳方曾經(jīng)在地區(qū)無核化進(jìn)程中的歷史貢獻(xiàn),也進(jìn)一步損害了東盟國家建立東南亞無核區(qū)的長期努力。
- 世界知識(shí)的其它文章
- 美英澳軍事同盟與美國戰(zhàn)略轉(zhuǎn)向
- 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關(guān)系,地區(qū)和平穩(wěn)定重大威脅
- 習(xí)近平在第四屆中國國際進(jìn)口博覽會(huì)開幕式上發(fā)表主旨演講
- 20國集團(tuán)領(lǐng)導(dǎo)人峰會(huì)閉幕,承諾應(yīng)對最緊迫全球挑戰(zhàn)
- 習(xí)近平以視頻方式出席20國集團(tuán)領(lǐng)導(dǎo)人第16次峰會(huì)
- 中國社科院-俄羅斯遠(yuǎn)東聯(lián)邦大學(xué)中國研究中心舉辦線上國際研討會(huì)“‘印太戰(zhàn)略’背景下的中俄戰(zhàn)略協(xi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