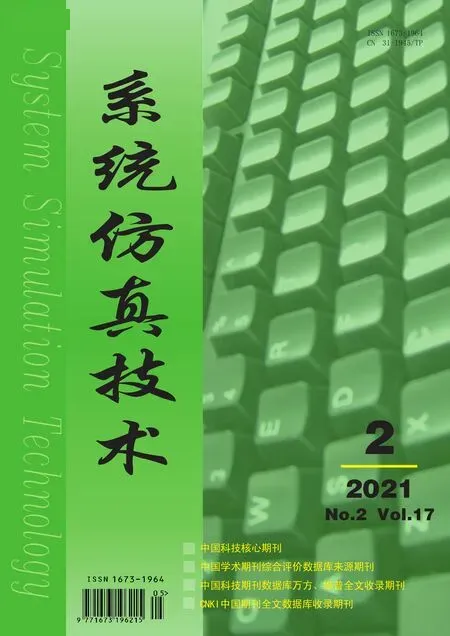艦載激光武器毀傷能力的建模與仿真
徐東翔
(解放軍91404部隊,河北秦皇島 066001)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超高速導彈、隱身導彈、低空突防導彈等反艦武器不斷出現,特別是現如今的戰場電磁環境復雜,環境信號密度較高,極大地壓縮了傳統的雷達探測與雷達偵察的反應時間。相比于以往的防空武器,激光武器具有攻擊速度快、殺傷威力大、使用成本低廉、殺傷概率高等優點。因此,各國都不約而同地在激光武器的研發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例如,美國1976年在亞拉巴馬州使用100千瓦功率的激光防空炮擊落了兩架靶機,1982年用激光武器摧毀了“陶”式導彈,1983年使用機載500千瓦激光炮摧毀了“響尾蛇”空對空導彈。2018年,美國陸軍提交的國會報告中提到了一種新型系統,能夠對導彈、無人機、各類炮彈進行有效防御[1-3]。雖然艦載激光武器相較于傳統防御手段擁有諸多優點,但是艦載激光武器也面臨許多考驗。首先,海浪與艦體機械振動會影響激光武器的跟蹤精度,尤其是在高海況條件下,會使跟蹤精度大幅度下降,甚至無法跟蹤;其次,海洋大氣環境的突出特點是濕度大,使大氣對激光的散射和吸收效果更加明顯,這就使得激光的毀傷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為了節約武器研發成本、制定有效的作戰策略,建立一種比較可行的仿真模型就顯得尤為重要。目前,國內學者針對激光武器的毀傷效果建立了不同的仿真模型,如彭聰等分析了艦炮間隔和艦船升沉運動的影響[4],李奇分析了激光大氣傳輸對毀傷效果的影響[5],宋乃秋等基于激光武器破壞機理,建立了毀傷評估模型[6]。雖然以上這些模型分析了影響激光毀傷效果的一些因素,但是都沒有考慮到在實際工程應用中存在的現實影響因素,如火控系統的跟瞄精度。本文從跟蹤瞄準精度入手,分析實際應用中,火控系統跟蹤精度對激光武器毀傷效果的影響。
1 激光武器系統相關介紹
1.1 激光武器系統的應用原理
激光武器系統一般由光電跟蹤設備、大功率激光器、火控設備組成。光電跟蹤設備主要負責目標的捕捉與識別,由于激光器產生的光斑較小,在防御低空快速小目標時,對光電跟蹤設備的跟蹤精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對不同導彈的破壞閾值見表1。

表1 對不同導彈的破壞閾值Tab.1 Damage threshold for different missiles
由表1可知,在防御反艦導彈時,只有激光功率密度達到毀傷閾值和能量閾值后,才能起到破壞作用。達到能量密度的閾值后,通過時間積累,往往能夠達到能量閾值的要求。從兩者比較來看,達到能量密度就顯得更為重要,因此評估激光的毀傷能力就轉化為對激光能量密度的計算。激光武器根據不同類型的攻擊目標,需要的功率密度有所不同,特別是燒穿金屬外殼所需的能量密度要大于彈體的其他部分。結合激光器功率與艦載的加裝條件,通過燒毀導流罩和傳感器的方式進行防御較為可行[7]。
1.2 反艦導彈攻擊特點
反艦導彈在攻擊過程中,一般會經過初始階段、自控階段和自導階段。根據導彈導引頭的制導方式,可將其分為主動制導、被動制導和復合制導。反艦導彈攻擊末端的航路,一般采取蛇形機動、高空俯沖、超低空掠海等方式。攻擊目標艦艦艏水平方向時,反艦導彈會優先選取正面、正側面或斜面打擊,因此無論采取哪種方式,相較于反艦導彈其他部位,彈體頭部整流罩是最容易攻擊到的部分。另外,擊穿并燒毀燃料艙的能量閾值一般為500~1000 W/cm2,擊穿并燒毀戰斗部的能量閾值更高。綜上所述,激光武器一般會選擇攻擊來襲導彈的整流罩部分以達到防空反導的目的。
2 激光武器功率密度模型
2.1 激光武器發射參數
在不考慮激光武器光學透鏡透過率的情況下,激光的束散角可以表示為

式(1)中,β表示光束質量,D表示發射透鏡直徑,λ表示激光波長。
因此光斑直徑可以表示為

2.2 激光衰減特性
激光在大氣傳輸過程中主要受到大氣折射、氣溶膠的吸收和散射、大氣湍流、受激拉曼散射、熱暈等現象影響。
根據朗伯-比爾定律,激光透過率可以表示為

式(3)中,I(λ)表示距離為R處的光強;I0(λ)表示激光發射窗口的光強;k(λ)表示衰減系數,可表示為

式(4)中,αm表示大氣分子吸收系數,αA表示大氣氣溶膠吸收系數,βm表示瑞利散射系數、βA表示大氣氣溶膠散射系數。
大氣的吸收效應會嚴重干擾特定波段激光的傳輸,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特別是在高度較低的情況下,會選擇某些特定的散射吸收影響較小的譜段,如波長為1~2.5μm的近紅外譜段、2.9~5.0μm的中紅外譜段、波長為8~14μm的遠紅外譜段[8]。從表2的數據中,不難發現當選擇波長為1.06μm的激光時,散射系數要遠大于吸收系數,所以仿真過程中只需要關注大氣散射系數即可。

表2 大氣吸收、散射系數Tab.2 Atmospheric absorption and scattering coefficient
2.3 正態分布
正態分布又稱高斯分布,是一種在工程應用中十分重要的概率分布。其概率密度函數可以表示為

式(5)中,μ表示隨機變量x服從的數學期望值,σ表示隨機變量的標準差。
根據多年試驗經驗發現,跟蹤系統的跟蹤誤差近似服從正態分布,所以在忽略激光光斑發生畸變的情況下,到達導流罩的激光能量分布情況可近似認為服從正態分布。
3 Matlab仿真分析
仿真參數設定為激光發射功率=50 kW,光束質量β=3,發射透鏡直徑D=0.7 m,激光波長λ=1.06μm。假定目標導彈為低空掠海飛行,此時其飛行高度與激光武器架設高度差可忽略不計,即認為目標導彈與激光武器處于同一水平面。
因為導彈正面來襲,使用形心跟蹤的光電跟蹤設備一般會穩定跟蹤導彈整流罩的中心,但是會因為機械振動或海浪等原因產生輕微偏離,因此假定跟蹤誤差的均值為零,但是誤差的標準差不為零。
通過仿真,假定距離為10 km,計算得出在σ等于0.25、0.5、1.0和2.0時,對應的激光峰值功率密度分別 為68.87 W/cm2、64.04 W/cm2、34.35 W/cm2和11.04 W/cm2。在此仿真條件下,從圖1中可以看出,σ的變化對功率密度的影響較大,即使跟蹤精度的誤差均值為零,跟蹤穩定性較差時,激光武器的功率密度依然會出現巨大差別。因此,跟蹤系統在整個激光武器系統中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強跟蹤系統伺服模塊的穩定性是提高激光武器工作效率的一種重要手段。

圖1 不同標準差的功率密度分布情況Fig.1 Power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tandard deviations
只改變跟蹤誤差的標準差,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通過仿真計算得到激光功率密度與照射距離的關系,如圖2所示。從仿真結果來看,在5~15 km范圍內,隨著距離的增加,激光的功率密度會不同程度地下降,而且跟蹤穩定性越高,功率密度下降越明顯。這主要是因為隨著距離增加,一方面大氣的吸收效應影響了激光能量的傳輸,另一方面激光武器形成的光斑會明顯增大,導致功率密度下降。但是穩定性較差的系統因為光斑晃動較大,光束能量的“匯聚”性能較差,這種情況對功率密度的影響更為突出,所以距離變化引起的毀傷效果變化就不如穩定性較好的系統明顯。

圖2 攻擊距離對功率密度的影響Fig.2 Influence of attack distance on power density
如果改變跟蹤誤差的均值,水平跟蹤誤差與俯仰跟蹤誤差的標準差都等于1,距離為10 km時,得到仿真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3可以看出,跟蹤誤差的均值對激光武器的毀傷效果影響也比較明顯。跟蹤誤差的均值由0.5μrad變化到2.0μrad只是增加了三倍,但是目標指示點的功率密度卻只有原來的二十分之一。由此可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有效提高火控系統的跟蹤精度也可以提高激光武器瞄準點的激光功率密度,從而大幅提高毀傷效果,進一步提高毀傷效率。

表3 跟蹤誤差均值對功率密度的影響Tab.3 Infuence of tracking mean error on power density
4 結 語
由于激光武器系統的仿真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現有的仿真模型缺乏一定的實用價值,而且近幾年隨著激光武器在軍事領域的應用越加廣泛,對建立一個真實有效的仿真模型的需求也越加強烈。本文通過分析激光武器在工程應用中存在的一些不確定因素,結合正態分布建立了激光武器功率密度的仿真模型,分析跟蹤誤差帶來的不同影響,為今后制定激光武器的使用策略提供一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