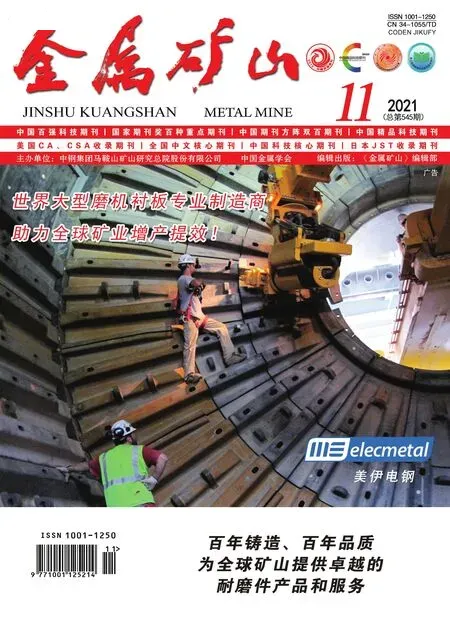Fe3+作用下煤矸石中黃鐵礦的氧化速率和化學計量學特征
金 韜 孟慶俊,3 鳳 陽 胡振琪 崔雅紅 馮啟言,31
(1.江蘇省老工業基地資源利用與生態修復協同創新中心,江蘇 徐州 221116;2.中國礦業大學環境與測繪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3.中國礦業大學礦山生態修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江蘇 徐州 221116)
黃鐵礦是礦區環境中常見的金屬硫化物,易被氧化形成酸性礦山廢水(AMD),進而引發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因此,黃鐵礦氧化的機理及其動力學影響因素研究一直是礦區污染環境治理領域的研究熱點。一般認為Fe3+與O2的含量越高,黃鐵礦電化學氧化速率越快[1-2]。KANZAKI等[3]研究發現,在低氧、酸性(pH=3)條件下,黃鐵礦與水、O2反應生成HO2·、H2O2和·OH等中間產物,氧化速率高于預期值。機理分析結果顯示,反應過程中溶出的Fe3+對黃鐵礦的氧化起到了促進作用;中性或堿性條件下,盡管Fe3+的活度降低,但Fe3+依然是黃鐵礦氧化過程的主要氧化劑,氧化速率甚至比O2高出3~4個數量級[4]。
煤矸石中伴生有黃鐵礦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目前,研究者普遍認為黃鐵礦是煤矸石產酸的主要礦物成分。中高硫煤矸石堆場在自然風化、降雨淋濾及水體浸泡等綜合作用下,煤矸石中黃鐵礦等含硫礦物易與水、空氣及微生物等發生氧化反應,產生酸性礦山廢水,促進重金屬離子的釋放[5-6]。與純黃鐵礦不同的是,煤矸石中除含有酸性礦物成分外,隨風化程度不同,還含有對酸起中和作用的碳酸鹽等堿性礦物成分。梁冰等[7]研究發現,當煤矸石具有產酸潛力但凈產酸量不高時,產生酸性礦井水的可能性較小;HESKETH等[8]研究認為,煤矸石中碳酸鹽溶解速率及黃鐵礦氧化速率共同控制著酸性礦井水的形成。
因此,研究不同類型煤矸石在Fe3+作用下的氧化特征對于全面了解煤矸石產酸規律并掌握其內在機理,從而從源頭控制煤矸石場地AMD具有重要意義。本試驗以高風化中高硫、低風化中高硫以及高風化低硫等3種不同類型的煤矸石為研究對象,對比黃鐵礦樣品,研究酸性條件、Fe3+作用下煤矸石樣品的氧化速率和化學計量學特征,為總結煤矸石實際產酸規律提供理論支持。
1 試樣采集與處理
低風化中高硫煤矸石采自山西古交東曲2號井排矸區煤矸石堆場,高風化低硫煤矸石采自德州邱集煤矸石堆場,高風化中高硫煤矸石采自凱里平路河旁煤矸石堆場,分別標記為SX、DZ和KL。樣品自然風干7 d后進行XRD分析、產酸潛力測試及產酸特征試驗。各煤矸石試樣特征見表1,主要化學成分分析結果見表2。

注:凈產酸量以H2SO4計。
試驗用黃鐵礦購自銅陵威特礦業公司,經手工錘碎、瑪瑙研缽研磨,干燥后篩取45~74 μm粒級,于乙醇中超聲洗滌,再置于濃度為10%的HCl溶液中浸泡2 h,接著用蒸餾水清洗至中性,然后真空干燥備用。化學分析結果表明,該試樣S和Fe合計含量為89.43%,S與Fe原子計量比為1.99,與理論值基本一致,可視為純黃鐵礦樣。

?
圖1為黃鐵礦、KL、SX、DZ試樣的XRD圖譜,結果表明,黃鐵礦試樣中除黃鐵礦外,僅有極少量石英;3種煤矸石試樣的主要礦物成分為石英,并含有一定量的黃鐵礦。

2 試驗方案、測試儀器及方法
2.1 試驗方案
設計 3個 Fe3+初始濃度(0、5.35×10-3mol/L、8.92×10-3mol/L),定量稱取黃鐵礦和各煤矸石試樣置于以上反應體系中,各試驗組設置3個平行試驗。試驗在250 mL錐形瓶中進行,控制反應固液比5%、反應溫度25±1℃,鹽酸調節pH=2±0.2,溶解氧濃度與大氣氧平衡。試驗時將反應容器置于SHZ-82數顯恒溫振蕩器內,振蕩速度為120 r/min。于第0 d、1 d、3 d、5 d、7 d、10 d、15 d、30 d取樣,對過0.45 μm玻璃纖維濾膜后的水樣進行分析。
凈產酸量w(kg/t,以H2SO4計)測試:將2.5 g煤矸石試樣置于500 mL的錐形瓶中,加入250 mL濃度為15%的H2O2溶液,當反應進行至瓶內無氣泡產生時放在電熱板上90℃低溫加熱至錐形瓶中無氣泡產生,冷卻至室溫后用0.1 mol/L的NaOH溶液進行中和滴定反應,根據NaOH的滴定用量計算試樣的凈產酸量w。
2.2 測試儀器與方法
本研究中黃鐵礦和煤矸石礦物相分析和化學成分分析分別由X射線衍射分析儀(SHIMADZU XRD-6100)和X射線熒光光譜儀(德國布魯克AXS有限公司,S8 TIGER)測定;pH通過pH計(上海精科雷磁有限公司,PXSJ-216F)進行測定;Fe2+和Fetotal用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恒平722)測定;SO42-使用離子色譜儀(瑞士萬通有限公司,ECO IC)進行測定;微觀形貌特征通過掃描電子顯微鏡(SEM,美國FEI Quanta 250)進行觀察。
煤矸石產酸能力的測定參照文獻[12-14]的方法,Fe2+表觀反應速率參考文獻[15]中的公式。
3 試驗結果與討論
3.1 Fe3+氧化黃鐵礦、煤矸石的動態特征
在前人有關黃鐵礦氧化速率的研究計算中,反應進程變量通常為SO42?或 Fe2+的產生量,又或是 Fe3+的消耗量[16-19]。由于硫在氧化過程中有多種氧化途徑可形成多種中間過渡性產物,如單質硫、硫代硫酸鹽和亞硫酸鹽等,所以基于SO42?釋放量計算的硫化物氧化速率常小于實際反應速率[20]。而黃鐵礦結構中硫原子對形成了非鍵合的軌道[21],所以這類金屬硫化物的價鍵只由金屬原子提供而不能與H+相互作用[22],試驗設計的酸性條件中H+不會使Fe2+從礦物中溶出,故選擇Fe2+的產生量為考察指標。
3.1.1 Fe3+氧化黃鐵礦、煤矸石的動態過程
圖2為黃鐵礦和3種煤矸石在不同Fe3+初始濃度下體系中Fe2+濃度的變化趨勢。
由圖2可知:①對于黃鐵礦試樣,Fe3+初始濃度為0時,Fe2+產生量較少,反應體系中Fe2+一直維持較低濃度;Fe3+初始濃度為5.35×10-3mol/L或8.92×10-3mol/L時,前5 d體系中Fe2+濃度快速升高,之后基本穩定;Fe3+初始濃度越高,反應體系中Fe2+濃度越高。②對于3個煤矸石試樣,0~1 d內Fe2+濃度快速升高,1~7 d內Fe2+仍然較快速產生,但升高速度減緩,7 d后體系內Fe2+濃度基本穩定;Fe3+初始濃度越高,反應體系中Fe2+濃度越高,KL試樣體系中Fe2+濃度平衡濃度最高。
3.1.2 Fe3+氧化黃鐵礦與煤矸石的氧化速率
根據圖2中各試樣不同Fe3+初始濃度下反應1 d后體系中Fe2+濃度計算表觀氧化速率RFe2+,結果見表3。


?
由表3可知:①對于黃鐵礦試樣,當Fe3+初始濃度由0上升至5.35×10-3mol/L時,表觀氧化速率RFe2+提升了20.38倍;Fe3+初始濃度由5.35×10-3mol/L升至8.92×10-3mol/L時,表觀氧化速率RFe2+提升了1.56倍。②對于3個煤矸石試樣,KL試驗組與此對應的表觀氧化速率RFe2+分別提升5.81倍、0.05倍;DZ試驗組與此對應的表觀氧化速率RFe2+分別提升1.11倍、0.09倍;SX試驗組與此對應的表觀氧化速率RFe2+分別提升3.36倍、0.59倍。
這一階段,可看作由表面反應控制的FeS2以及FeS2的少量氧化產物溶出過程[23-24]。對比不同試樣試驗組的數據發現:黃鐵礦試樣溶出濃度達到10-3mol/L水平,煤矸石試樣中KL組的Fe2+溶出量與黃鐵礦組數值相當,然而硫、鐵含量最高的SX試樣中Fe2+溶出量卻低于KL樣品,煤矸石DZ是所有試樣中Fe2+溶出量最低的,與相同初始條件下其他煤矸石試樣存在1~2個數量級的差別。結合煤矸石試樣特征可以初步判斷,硫鐵含量相當的情況下,風化程度越高的煤矸石在反應初期具有越快的反應速率。
1~7 d,體系中的Fe2+穩定快速的產生,用試差法對所測得數據進行分析,發現Fe2+濃度與反應時間t存在良好的線性關系,通過線性回歸方程擬合得到的試樣不同Fe3+初始濃度下的動力學參數,結果見表4。
由表4可知,試樣不同Fe3+初始濃度下體系中Fe2+濃度-時間基本符合線性規律,相關系數R2均大于0.9。需要說明的是,對于黃鐵礦試樣,Fe3+初始濃度為8.92×10-3mol/L時,相關系數R2為0.796 1,不符合線性規律。這是由于Fe3+初始濃度較高的情況下,黃鐵礦體系中Fe2+穩定快速產生期到第3 d就基本結束,此后進入緩慢產酸反應期,因此通過1~7 d的數據進行線性擬合結果不理想。
將Fe3+的初始濃度與對應氧化反應速率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對于黃鐵礦、KL和DZ試驗組,二者具有正相關關系(黃鐵礦組相關系數0.945,KL組相關系數0.996,DZ組相關系數0.803),而SX試驗組相關系數為-0.746,可見Fe3+初始濃度的上升并不對所有煤矸石1~7 d穩定產生期的氧化反應都具有促進作用。

?
本試驗反應過程屬于多相反應過程,礦物的溶解發生在固相和液相的界面。按照核收縮模型,這類反應需經歷5個步驟:浸出劑(Fe3+)在邊界層的外擴散和內擴散、浸出劑與礦物發生化學反應、可溶性產物在邊界層的內擴散和外擴散,當反應物通過邊界層的阻礙較小時則浸出過程受化學反應控制[25-26]。相對恒定體系下礦物顆粒浸出受化學反應控制時,符合浸出反應控制方程。將該反應期各試樣鐵浸出率與時間進行擬合,結果顯示較好的線性關系,說明在這一階段體系內發生的反應主要受化學反應控制。
表5為第1~7 d試樣不同Fe3+初始濃度下總鐵溶出量與參與反應固相鐵量的比值。

?
由表5可知,快速反應期階段(第1~7 d)產酸礦物的反應量(以液相中的總鐵溶出量占參與反應固相鐵含量計)基本都大于0.9,說明本試驗體系中黃鐵礦及含黃鐵礦煤矸石的大量氧化反應發生在1~7 d;KL在Fe3+初始濃度為0的條件下發生氧化反應,快速反應期階段內產酸礦物的反應量較其他試驗組低,這可能是因為KL作為高風化程度中高硫型煤矸石,在Fe3+初始濃度為0的條件下,其氧化速率在進入緩慢穩定期后仍然相對較快(經計算為4.65×10-7mol/(L·h)),說明風化程度高的高硫煤矸石其酸化污染期也會更長。
7 d后,各組Fe2+的快速產生期結束,Fe2+濃度緩慢增加直至在各體系內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測定7~20 d內各反應體系的pH值發現,黃鐵礦組pH值略微降低,而煤矸石中DZ組pH值出現上升現象,其3個Fe3+初始濃度下的pH值由2.49、2.71、2.52分別上升至3.97、5.26、4.36。這是因為煤矸石中可能存在碳酸鹽或硅酸鹽礦物,這些伴生礦物在液相條件中可以穩定、持續地中和酸度[27],影響整個體系的表觀酸堿度。
3.1.3 Fe3+氧化煤矸石的微觀機制
試驗測定的pH值是在發生在體系中的酸堿中和反應后的表觀測量值,煤矸石在硫化礦物氧化產酸的同時,伴生礦物也會發生氧化、溶解等反應,因此,僅以pH的變化作為產酸結果的表征是不夠的。為進一步探究Fe3+氧化煤矸石的微觀機制,對2種凈產酸潛力差距最大的KL(92.21 kg/t,以H2SO4計)和DZ(22.89 kg/t,以H2SO4計)進行了SEM分析,結果見圖3。
圖3(b)顯示:KL中,Si、Al、S、Fe、O等元素有重合的較集中分布區域,再次驗證KL煤矸石伴生有黃鐵礦(FeS2)等硫鐵礦物以及高嶺土(Al4[SiO10](OH)8)、莫來石(3Al2O3·2SiO2)等鋁硅酸鹽類礦物。圖3(d)顯示:DZ中除了以上礦物外,具有突出的K、Ca、Mg元素集中分布,這說明方解石(CaCO3)、白云石(CaMg(CO3)2)等碳酸鹽類礦物的存在;另外還可能含有少量菱鐵礦(FeCO3)和石膏(CaSO4)等。這些碳酸鹽、硅酸鹽礦物會消耗H+,與H2O反應發生溶解,中和黃鐵礦等硫化礦物氧化產生的酸度。此外,K、Na、Ca、Mg等煤矸石常見構成元素以離子態溶解后會在煤矸石顆粒表面與H+發生離子交換作用,造成反應體系pH的變化。因此,KL(92.21 kg/t,以H2SO4計)和DZ(22.89 kg/t,以 H2SO4計)具有較大的產酸潛力差異,在氧化產酸過程中由于以上礦物的溶解速率和中和能力的強弱,表現出不同的氧化速率。

3.2 化學計量學特征分析

當Fe3+為反應體系的氧化劑時,化學方程式為

由表6可知,①對于黃鐵礦,Fe3+初始濃度為0時,/[Fe2+]化學計量比范圍為1.18~2.62,基本符合O2為氧化劑的氧化反應化學計量規律;Fe3+初始濃度為5.35×10-3mol/L或8.92×10-3mol/L時,/[Fe2+]化學計量比范圍為0.15~0.46,Fe3+初始濃度的增加對化學計量比的影響不大,基本符合Fe3+為氧化劑的氧化反應化學計量規律,據此進行氧化速率的計算符合實際。②對于KL,Fe3+初始濃度為0時,化學計量比與黃鐵礦相似,較為穩定;Fe3+初始濃
度為5.35×10-3mol/L或8.92×10-3mol/L時,/[Fe2+]化學計量比大于0.13,均高于0.5。③對于DZ和SX,Fe3+初始濃度為0時,/[Fe2+]化學計量比遠大于2;對于SX,Fe3+初始濃度為5.35×10-3mol/L時,/[Fe2+]化學計量比范圍為8.88~10.38,較為穩定,Fe3+初始濃度為 8.92×10-3mol/L 時,/[Fe2+]化學計量比變化較大,整體呈升高趨勢;對于DZ,Fe3+初始濃度為 5.35×10-3mol/L 或 8.92×10-3mol/L時,/[Fe2+]化學計量比隨時間呈現較大幅度的無規則變化,對應的計量比在0.61~17.46和6.35~16.64波動,但整體低于Fe3+初始濃度為0的試驗組。

?
4 結論
(1)煤矸石在液相環境中Fe3+作用下產酸的過程可以劃分為0~1 d溶解期、1~7 d快速產酸期、7~30 d緩慢穩定期3個階段,其中快速產酸期受化學反應控制,該階段煤矸石被氧化大幅提高環境酸度,基本代表了該類煤矸石產酸量。結果表明:在實際煤矸石堆場環境中,當矸石遇到持續降水等液相反應條件后,酸性污染會很快產生并持續。
(2)在外加Fe3+的模擬酸性液體環境中,煤矸石的氧化速率隨液相中Fe3+初始濃度的增加而增加,為Fe3+濃度的一級反應。Fe3+初始濃度由5.35×10-3mol/L上升至8.92×10-3mol/L時,黃鐵礦的氧化速率由4.80×10-5mol/(L·h)升至5.23×10-5mol/(L·h);KL煤矸石的氧化速率由1.07×10-5mol/(L·h)升至1.91×10-5mol/(L·h);DZ煤矸石的氧化速率由0.9×10-7mol/(L·h)升至1.1×10-7mol/(L·h);SX煤矸石的氧化速率由1.39×10-6mol/(L·h)升至1.5×10-6mol/(L·h)。
(3)對于煤矸石這樣的復雜礦物混合體系,其氧化產酸過程不能簡單地類比黃鐵礦氧化理論,煤矸石的風化程度、礦物伴生情況極大地影響煤矸石的氧化產酸過程。風化程度高、有大量硫鐵礦物成分的這類煤矸石(如KL)氧化產酸規律接近黃鐵礦,更容易被氧化產生酸化效應;DZ這類風化程度高、硫鐵礦物含量相對較少而伴生有更多碳酸鹽、硅酸鹽礦物的煤矸石本身的產酸潛力就比較低,伴隨其硫鐵礦物氧化反應的是復雜而不可忽視的產堿成分的溶出;對于SX這類風化程度小的新鮮煤矸石而言,即使酸性來源物質硫鐵礦物含量高具有相當大的產酸潛力,其硫鐵礦物的氧化并不會像高風化矸石一樣快而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