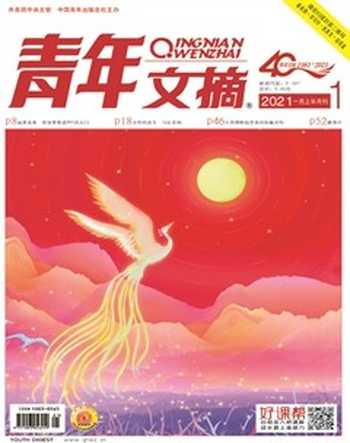好一個多情的和尚
潘向黎
一柄普通的東土扇子,能讓玄奘生病;一枚“小瑪德萊娜”蛋糕,能引出普魯斯特對似水年華的無窮追憶……從來“真情”最動人,中外皆然。好文章也是,必得有真情實感,先感動了自己,方可動人。本文作者認為,文字不佳,要從情感“源頭”上找原因。這一洞見,對我們讀書與作文,都有啟發。
一
在顧隨《蘇辛詞說》中讀到這樣一段逸事:玄奘法師在西天時,看見一柄東土扇子,就生病了。另一個僧人聽說了,贊嘆道:“好一個多情的和尚。”
見東土扇子而生病,如果玄奘在那時寫詩,當是一首千古絕唱;如果他給長安故舊修書,也會是一封感人的書信。但他什么都沒有寫,而用一場病對內心的情感做了最好的抒發。
至情之人就是這樣,感情到了這步田地,還是克制住,該寫也不寫;現實中許多人卻正相反,不該寫的猛寫。
讀一些作品的感覺很奇怪。不能說作者寫得不好,他明明該單刀直入處便單刀直入,該平穩時平穩,該峰回路轉處便峰回路轉,抒情的修辭也嫻熟,結尾還可以體會到振聾發聵的努力或者余音繞梁的預設,但還是讓人厭倦。它們起初讓我想起皮很厚而餡很小的包子,后來漸漸體會到,它們比包子更乏味,更像許多食堂的飯菜,雖然無毒無害,但也沒有色香味。
我忍不住產生一個疑問:這個作者為什么要寫呢?明明沒有感情的內驅力。抒情者,必須有了“情”才“抒”,他是為了“抒”而作“有情”狀。顧隨在《宋詩說略》中說:“詩應為自己內心真正感生出來,雖與古人合亦無關。不然雖不同亦非真詩。”既然詩有“真詩”與“非真詩”之分,散文也有“真散文”與“假散文”之別了。
對一些談論寫作技巧的文章有些疑惑,因為他們不關心水源和水流量,而專談如何挖水渠。如果一個作品不好,他們總是質疑水渠挖得不對,而不看看水渠準備迎接的水流量是否充沛。經常是源頭幾乎干涸,水流細弱,談技巧的人卻還在專心教人挖水渠。即使細弱的水流按照既定的水渠流了過去,是“真詩”“真散文”嗎?
不要說大江大河,許多小溪都能在“萬山不許”的情況下曲折奔出。水到哪里,哪里就是水的路徑,“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蘇軾語)那才是真詩、真文章、真文學。
杜甫《夢李白二首》,擔憂李白處境,浩浩渺渺,一片悲涼,令人“同聲一哭”,更留下“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諸名句。清《唐宋詩醇》評這兩首說:“情之至者文亦至。”
有人還進了一步說得更絕對——清代陳祚明評潘岳《悼亡詩》曰:“夫詩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語不佳者。”潘岳,西晉時期文人,他的另一個名字可能更加為人所知:潘安。他和妻子楊氏感情很好,琴瑟相和二十多年。妻子去世后他一再寫詩作賦悲悼懷念,開了悼亡詩的先河。
那種悲傷、無奈、恍惚、無助、哀痛,綿綿不絕地寫來,非常真實,深情傾注,因此也打動了無數人。
二
“未有情深而語不佳者”,看似偏激,其實有理。
有情,就是水已經天然在;情深,則水量豐沛。況且人還往往因各種原因而忍耐克制,或者一時之間無力訴說,則感情成了水庫,但“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水位越積越高,有朝一日終于堤壩潰決,豐沛的感情之水從高處奔涌而下,還需要什么水渠呢?這種表達是生命的必需,泣血一聲便是天下同哭,無語凝噎足令四海凄涼。情深,則流暢是澎湃,冷澀是沉郁,凌亂是頓挫,半含半露成了若悲若諷,戛然而止自有無限余味。情深,則表達就不成問題。
反過來說:那些文不至、語不佳的作品,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因為情不至、情不深。
顧隨講課,花雨紛紛,但他有一節說到老杜錘煉而能令人感動,山谷(黃庭堅)、誠齋(楊萬里)則不動人,“蓋其出發點即理智,乃壓下感情寫的”,葉嘉瑩當場在聽課筆記上寫下不同意見:“瑩以為是感情根本不足。”
許多作品之所以不成功、不感人,恰恰病在“無情”。顧隨在《太白古體詩散論》中比較了李白與杜甫,舉了李白的《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為例。李白經過了下邳圯橋,想起了西漢開國的謀臣張良,顯然感情上沒有什么波瀾,但作為大詩人到了這么一個強烈提示寫懷古詩的地方,少不得來一首。顧隨說此詩敘事而未能詩化,因為沒有動感情。而杜甫,欣賞公孫大娘弟子劍器舞,回憶起了自己童年看過公孫大娘的舞蹈,“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這開頭十分俊俏,“啪”的一聲,一個特寫鏡頭,一個身著戎裝、英氣逼人的美貌女子,手持劍器渾脫,剛健颯爽的舞姿一起,好得沒法說了,但杜甫說了——“動四方”。寫公孫大娘劍器舞的魅力,“動四方”,必得這三個字,只能這三個字。
為什么能這么完美?因為“動”的,首先是詩人的心,然后,才是四方,才是天地,再然后才是讀者。杜甫自己被震撼了,被感動了,被照亮了,所以隨手一寫,自然有力有情,讀之想不被感動都不成。而且還愿意重讀,生怕錯過了什么。絕不會像對李白這首,他隨便一寫,我們隨便一讀,彼此敷衍。
傳說李白到黃鶴樓,本來想題詩,但看到崔顥的《黃鶴樓》,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而去。這種傳說中的作派和詩的風格,都不像李白。不過如果詩人到了一個江山佳處或古跡名勝,卻并不喜歡,甚至不相容,那么不假裝感動地寫,甚至不寫,絕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正不必管有沒有“崔顥題詩在上頭”。
說到這里,想起了一向愛讀的汪曾祺。汪曾祺有篇散文叫《泰山片石》,里面這樣寫道:
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十年間兩登泰山,可謂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進入我的內部,我也不能外化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達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是強者之山,我自以為這個提法很合適,我不是強者,不論是登山還是處世。我是生長在水邊的人,一個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經過了七十歲,對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個安于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以慣寫小橋流水之筆而寫高大雄奇之山,殆矣。
……
但是,又一次登了泰山……在亂云密霧中坐下來,冷靜地想想,我的心態比較透亮了。我承認泰山很雄偉……承認偉大的人物確實是偉大的,盡管他們所做的許多事不近人情。他們是人里頭的強者,這是毫無辦法的事。在山上待了七天,我對名山大川、偉大人物的偏激情緒有所平息。
同時我也更清楚地認識到我的微小、我的平常,更進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
汪曾祺很誠實,而且自持,他對泰山,就是有點排斥,山與人差異太大,以至于不能相互融合,當然更談不上感動。汪曾祺這篇本來可以不寫,但是因為他對泰山是不認同的,真實、真切,于是就值得寫了。
說回李白與杜甫,杜甫是個老實人,他活得認真,感情強烈而真摯;李白大多數時刻比較關注自己,活得飄飄蕩蕩的,有點像一直被太多的愛與關注寵壞了的人。李白當然也有真動感情的時候,如名句“長相思,摧心肝”。總體而言,唐人比宋人感情豐富多了。唐詩之所以比宋詩高,就因為唐人多情。顧隨認為“唐人情濃而感覺銳敏”,宋人重觀察而偏理智,“宋人作詩一味講道理”,但宋人寫詞便有感覺和感情,所以“大晏、歐陽修、蘇東坡詞皆好,如詩之盛唐”。這里顧隨大概是隨意說說的,因為漏掉了他極愛的辛棄疾。
顧隨這樣說辛棄疾:“稼軒最多情,什么都是真格的。”胡適評辛棄疾:“才氣縱橫,見解超脫,情感濃摯。無論長調小令,都是他的人格的涌現。”
一柄普通的東土扇子居然能讓玄奘生病,玄奘和那個為他發出贊嘆的僧人,他們的感情多么強烈。這種細致精微的感覺,這種瞬間抵達無限廣袤的聯想,這種內心豐富的程度,真的是后天可以習得的嗎?“多情”是一種天性,還是一種能力?或者是天賦和后天習得各有占比?這個問題,似乎很難斷然給出答案。
周止庵說:“稼軒固是才大,然情至處,后人萬不能及。”這句話,評價辛棄疾說得極是,同時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如果不是“情至”,僅僅“才大”,也是無法寫出不朽杰作的。大才、至情,才能帶來“動四方”的作品。
真實感情的水源和流量,遠遠比水渠重要。沒有水源,就不必挖水渠,先去找水。感情不足,等于枯水期,就讀書,就靜默,讓文字和紙也歇歇吧。
(摘自《山》2020年第5期,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