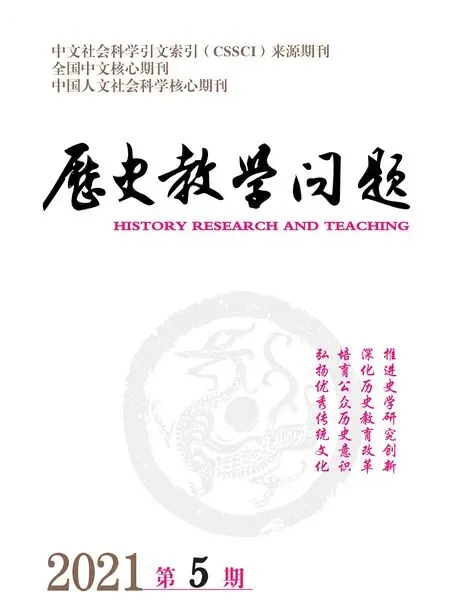論1848 年革命前拉馬丁政治實踐和政治理念的轉向
沐 越
拉馬丁(Lamartine,1790—1869)是近代法國著名詩人,其詩集《沉思集》在1820 年一經發表便獲得了上流社會的熱烈歡迎,被譽為19 世紀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前驅和巨擘。①同時,拉馬丁也是近代法國一位杰出的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1848 年二月革命后因為其較高的聲望和人氣、革命中做出的卓越貢獻、良好的口才和演講能力,而被起義群眾擁護為法國臨時政府的實際首腦,從2 月24 日至5 月11 日出任外交部長。5 月10 日臨時政府被執行委員會取代后,成為五人執行委員之一,隨著六月起義被鎮壓,卡芬雅克成為政府主席,保守派全面掌控政府,拉馬丁被迫辭職。最終在12 月的總統選舉中慘敗于拿破侖三世后(只獲得0.26%的選票),他退出政壇,開始潛心文學和史學創作。②Wright. Gordon,“A Poet in Politics: Lamartine and the Revolution of 1848”.

毫無疑問,拉馬丁在二月革命后的法國政壇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對于他的政治實踐和政治思想,國內相關研究一直著墨甚少,只有郭華榕的《法國政治制度史》③郭華榕:《法國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和《法國政治思想史》④郭華榕:《法國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較為籠統地介紹了拉馬丁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思想,相關文章也只有孫嫻的《拉馬丁對大革命的反思和他的革命實踐》⑤孫嫻:《拉馬丁對大革命的反思和他的革命實踐》,《世界歷史》,1988年第2期。和韓承文教授的《巴黎二月革命對歐洲國際關系的影響》⑥韓承文:《巴黎二月革命對歐洲國際關系的影響》,《世界歷史》,1989年第5期。等寥寥數篇。相較于國內研究的貧瘠,國外的拉馬丁研究一直是顯學,相關文章、著述不勝累舉,但研究重心也是偏向文學方面,系統性研究這一時期拉馬丁國內、外政策的只有皮埃爾一人,其《二月革命中的拉馬丁和其外交政策(2月24 日—6 月24 日)》①和《政治家:拉馬丁——國內政策》②兩本書全面介紹了拉馬丁國內外政策的方方面面,基本梳理了從二月革命開始到六月革命這段時間拉馬丁本人具體的政治外交活動以及相關事件。相關研究還有威廉的《拉馬丁的政治傳記》、③喬治·凱利的突出拉馬丁詩歌中自由主義思想的《拉馬丁:政壇上的詩人》④以及賴特·戈登的《政壇上的詩人:拉馬丁和1848 年革命》⑤等等。進入新世紀以來,不少法國歷史和文學研究工作者開始不再單純的從政治史或是文學史角度來研究拉馬丁,而是將兩者結合一起,通過其文學作品和政治演講中的民主抒情來研究拉馬丁的政治思想,其代表作品是巴黎大學多米尼克教授的《拉馬丁的民主抒情:1834年到1848 年的政治演講研究》。⑥
和拉馬丁革命時期政治活動的豐富研究相比,他在革命之前政治思想的形成、變化以及相關的政治活動,國內外都鮮有人研究,因此筆者在此通過搜集來的諸如法國外交檔案館整理出版的《法國臨時政府外交檔案》、⑦《拉馬丁通信集1830—1867》,⑧拉馬丁自己的著述《掌權三個月》⑨和《1848 年革命史》⑩等相關一手史料,來嘗試還原1848 年革命前拉馬丁的政治實踐和政治思想的變化。
一、初入政壇
拉馬丁早年的政治生活和其祖輩的生活環境和政治背景密切相關。他的父母都是貴族,不過和當時很多同階層的人一樣,并沒有正式的貴族頭銜,他們的貴族身份來源于1651 年拉馬丁的高祖父買下了王室秘書之職,從而獲得了世襲貴族的地位。?到1790 年10 月21 日拉馬丁出生時,拉馬丁家族已經扎根于馬孔-勃艮第地區(后來成為索恩-盧瓦爾省)將近200 年,擁有大量土地。作為這一代的獨子,拉馬丁成為了其家族大部分地產的假定繼承人,這使他成為這一地區最富有的地主之一,未來會有非常豐厚的家產繼承。?此外,拉馬丁家族和波旁王朝、奧爾良王室都有著不錯的關系,這使他們在政治上具備了天然的保王黨背景。
早期的家庭宗教教育對拉馬丁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其中包括了費奈隆、荷馬、塔西陀和拉封丹等的作品。之后因為不成功的學校生活,拉馬丁接受了貝萊耶穌會士的再教育,其側重宗教、文學哲學和修辭等教育內容對他日后寫作和演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長期的宗教教育并沒有讓他養成良好的個人習慣,拉馬丁的個人生活反而十分奢靡,健康狀態也非常糟糕,甚至因為放浪的私生活而和女仆有了私生子,?這些直接影響了拉馬丁日后的個人和政治生活。在17 歲離校后,因為對波旁王室忠誠和對拿破侖王朝抵制的家庭背景,拉馬丁難以找到政府工作,在無聊和抑郁的生活中,他開始注重閱讀古希臘羅馬的經典和盧梭、夏多布里昂的作品,?他的浪漫主義詩風便由此而來。1811 年拉馬丁前往意大利,之前養成的紈绔習慣讓他在意大利因為賭博和召妓花光了錢財,回國后依然風流成性,甚至有了第二個私生子。①和同時代人一樣,青年時期的拉馬丁認為女人不過是供人獵艷的對象,而抑郁、缺錢、疾病和無實際工作不斷困擾著他,但拿破侖王朝的毀滅改變了這一切。

1814 年復辟王朝成立后,其父因為忠誠于波旁王室而受到表彰,拉馬丁也獲準進入皇家衛隊,但他本人對此并不滿意,在謀求地區行政長官未果后便回鄉等待。百日維新時期,他繼續忠誠于王室,重回皇家衛隊并隨波旁逃亡,在衛隊解散后流亡瑞士。復辟王朝回歸后,他因病退役,奉母之命謀取洛漢思地區長官之職未果。拉馬丁迫于經濟壓力、父母期望、自身急于工作的期許,轉而寄希望于在外交使團或內政部門工作,但依然失敗。盡管屢遭挫折,但拉馬丁仍自命不凡,在來往書信中將自己比作卡珊德拉,對復辟王朝的不滿亦日漸增長。②
1816 年拉馬丁的政治生涯終于迎來了轉折,他在艾克斯養病時和一位有夫之婦熱戀,他的著名詩作《湖》便因這段戀情而誕生,回到馬孔后依然找時間去巴黎與她偷情,并通過她認識了幾位貴婦,以及包括她丈夫在內的數位政府人士,③借此被引薦入巴黎的貴族沙龍,并利用自己天主教、保王黨人和貴族的身份,開始建立社交人際網,為之后自己詩集的出版、獲得外交職務和進入法蘭西學院提供了幫助,他的個人詩集也在小規模的貴族范圍內傳播開來。1820 年2 月13 日貝里公爵刺殺案引發政治危機,秉持自由主義的首相被迫辭職,法國政治局勢重新右轉,這使得拉馬丁的數位正統主義支持者影響力大增。最終在他們的大力幫助下,拉馬丁得以擔任法國駐那不勒斯的大使,借此機會拉馬丁敲定了婚事,詩集《沉思集》也在3 月11 日出版。④這部詩集在巴黎天主教、王室、貴族圈子和沙龍中都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并引起轟動,短時間內再版十幾次。文學上的成功不僅給拉馬丁帶來政治上的聲譽,也推動了個人婚事的進程以及經濟收入的提高。5 月6 日婚禮后,拉馬丁便前往那不勒斯上任,恰逢意大利燒炭黨起義和兵變,它加深了拉馬丁對專制獨裁的厭惡和對自由主義的接觸,這種轉變在拉馬丁為貝里公爵遺腹子所做的詩中已有端倪,其后在陸陸續續創作的詩歌中也不斷歌頌自由。⑤1825 年7 月3日,拉馬丁終于得到覬覦許久的駐佛羅倫薩大使第二秘書之職。他在佛羅倫薩積極參與當地的社會活動,結交來此的法國貴族和政府要員,交好托斯卡納王國的上層人士。⑥但實際上這種偽善、四下迎合的社交活動加劇了拉馬丁對貴族的厭惡。他贊賞托斯卡納開明的統治,傾向于在意大利地區開展溫和務實的自由主義憲政改革和更大范圍的獨立運動,但他十分反感通過秘密陰謀和革命來實現這一切。盡管他對佛羅倫薩的生活比較滿意,但他對社交活動日益的厭倦、職位低微的不滿和晉升的野心,導致了他在1828 年七月底的離職,⑦并隨后在巴黎獲得了駐倫敦大使第一秘書職位的承諾。

雖然巴黎的外交職務還未確定,拉馬丁的政治野心已然膨脹,他期望能成為一名知名政客而不單單是文學家。1829 年1 月拉馬丁首次參與到地方政治中,負責起草復辟王朝時期葡萄酒行業請愿活動的請愿書,其內容是請求降低關稅,尤其是針對葡萄酒的間接稅,支持自由貿易。該活動造成的政治影響良好,受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報紙媒體的一致贊揚,⑧這讓拉馬丁樂觀地估計自己可以加入議會候選人的行列。1829 年8 月8 日法國政局發生了變化,為了壓制力量日益增強的自由反對派,查理十世任命極端保王派波利尼亞克擔任外交部長和政府首腦,波利尼亞克對拉馬丁十分欣賞,認為他會是一位有能力并站在保王派立場上的外交官,他的文學聲譽和沙龍人氣也有助于改善政府糟糕的公共形象,于是邀請拉馬丁前往巴黎協助他重組外交部。⑨但拉馬丁拒絕了邀請,因為他反對波利尼亞克的反動主張,不愿意服務于一個日益保守反動的政權而損害他的政治前程。在政治立場上,拉馬丁想脫離政黨保持政治上的身份獨立,避免黨派身份帶來的偏見、盲從和派系斗爭,在傾向自由派的同時反對革命的血腥暴力和獨裁統治,因此他支持君主立憲派,認為這是理性自由主義的實用選擇。
在1830 年4 月1 日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后的演講中,拉馬丁進一步闡釋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從基督教宗教道德觀念出發,說明君主維護憲章和立法的合法性,反對專制和無政府主義。①而在1830年革命爆發后,拉馬丁表示對革命的迅速成功并不驚訝,他只關心無政府主義的危險,只求君主制、自由、宗教和社會穩定,因此他迅速接受了新政府,但辭去了外交職務來表達對故主復辟王朝的尊重,并發表詩歌《人民》,表達對王室大臣的報復和審判持反對意見,②這是拉馬丁利用詩歌來進入國家政治領域的一次嘗試。因為對公眾來說,此時的拉馬丁還是創作《沉思集》的浪漫主義詩人,貴族女性的偶像,以多愁善感和家庭傳承的虔誠天主教和保守主義而聞名。但在1830 年,拉馬丁顯然已不滿足于文學家的身份,而是希望能更積極嚴肅地參與政治。在社會和政治問題上,擔馬丁開始基于對基督教道德的解讀和1789 年的革命理念來塑造自由主義,而他身上眾多矛盾沖突的理念決定他的政治未來是獨特而孤獨的。
二、迎合七月王朝
1830 年七月革命后,盡管拉馬丁在口頭上表示不會為七月王朝效力并辭去既有的外交職務,可是他的政治野心和逐漸左轉的政治傾向,再加上個人消除暴力、維持政權穩定和法制的愿望使其很快復出,參與貝爾格地區議員競選。拉馬丁依靠良好的詩歌聲望、廣泛的社會關系和中立自由的政治立場吸引選票,在競選綱領中強調自由是“人類未來命運之母”,并將自由分為個人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教育獨立于教會);信仰自由(政教分離);政府自由(中央權力下放);國家自由(統治政府需代表國家所有階級之利益),支持啟蒙思想和捍衛個人利益。③這些觀念與七月王朝強調個人、政治自由和政教分離的政治風氣相合,可見此時的拉馬丁意識到自由主義已成為未來法國的政治主導力量。但拉馬丁在書信通訊中依然強調自己的無黨派屬性,希望同時獲得自由派、保守派和溫和保王黨的支持,尤其是他的支持者中有大量的保守派和正統派。盡管最終選舉失敗,但他獲得了相當多的選票支持和未來的政治資本。
1831 年9 月拉馬丁發表《理性政治》一文,較為系統地闡述自己富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社會政治思想,認為法國當前正處于社會變革中,在肯定七月王朝取代復辟王朝合理合法性的同時,鼓勵一切促進自由、民主、平等的政府形式,推行政教分離和按財產劃分投票權,提倡英明君主領導下的行政集權,支持宗教的教化和私人財產權。④此外,拉馬丁在字里行間也流露出一種隱約的宗教狂熱觀念,認為世俗事物中具有神圣存在,基督教道德可以解決目前變革時期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人類的理性與上帝的意愿是一致的,但他也反對分權和任何形式的宗教神權統治,⑤這種觀念毫無疑問受到了這一時期基督教自由主義化的影響。

1833 年,拉馬丁終于得償所愿被選為貝爾格地區議員。因為部分政府人士視他為正統主義者,對他抱以敵視態度,為了避開來自政府的反對,拉馬丁公開強調自己溫和的政治觀點,并且與左派和正統主義者都保持距離,力求獨立于政府和各政黨。⑥當選議員之后,拉馬丁積極地參與到法國的政治生活中,不斷發表對東方問題的看法,要求確立歐洲對中東的保護原則,禁止任何一個歐洲列強對土耳其帝國的單方干預。而在國家內政上,拉馬丁主張在重大問題上基于道德原則和國家利益來喚起國家和人民的良知,對人民“非法結社”問題拉馬丁的態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支持政府的結社禁令但同時要求相關部門謹慎處理,避免直接鎮壓并采取補救措施。對于19 世紀上半葉逐漸顯現的工人問題,拉馬丁在情感上同情里昂工人起義,但反對陰謀煽動罷工等革命活動,支持政府維持秩序的自衛行動,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暴亂。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拉馬丁提議進行全面的改革,在教育中強調道德和啟蒙,延伸議會權力,持續調查工業問題,公平分配財富,通過直接提供工作或是在國內外提供土地資本建立新的農業社區來援助失業者,強調“愛人民”“關心群眾福祉”“慈善立法”。①而對于伴隨而來的財產權問題,拉馬丁在肯定財產和資本對人類幸福重要性的同時,認為城市工人沒有財富,極度依賴工作,容易遭受意外和不幸,因此他主張各個區縣成立儲蓄銀行,提供利息。通過定期儲蓄,工人可以預防疾病、事故和失業問題,并獲得防止懶散、墮落和放蕩的道德保障。②拉馬丁相信私有財產作為文明的根基,可以實現財產基礎上的民主,從根本上解決工人的困境。
1834 年6 月大選后,拉馬丁再次當選貝爾格地區議員。長期在詩人與政治家、思想家與實業家之間的身份切換和矛盾,再加上每年需要生活在外省六個月,讓拉馬丁開始對政治生活產生厭倦,他聲稱對政治生活十分猶豫,甚至是“帶著內心的厭惡”進入議會。③在新議會中,拉馬丁繼續支持人道主義事業,贊成政治特赦包括保王黨和罷工工人,推廣儲蓄銀行和懲罰決斗,加入廢奴協會。在政治理念上拉馬丁提出了七月王朝的“雙重使命”概念,即完成1830 年革命的同時阻止進一步的激進革命來實現1789 年的理想,將政治權力和社會福利擴大到盡可能多的人,擴大選舉權,減輕窮人稅負,廢除奴隸制,鼓勵海外移民,為被遺棄的兒童提供國家援助并改革死刑,實現基督教的慈善原則來促進社會和平與和諧。④
三、政治立場的左轉
1837 年11 月4 日的議會選舉中,拉馬丁堅稱自己“不是一個政黨的人,不是政府部長,也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反對派”,而是“一個社會人士,不關心一時的偏見、激情、王朝仇恨或是忠誠,而是關心正義、真理和國家的永久利益”,⑤最終他在三個選區獲勝,但在選舉中因為持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而與之前的正統主義支持者逐漸疏離。1838 年底,面對梯也爾、基佐和巴羅組成的反莫羅政府聯盟,拉馬丁支持對外采取和平外交政策的莫羅,反對聯盟支持比利時保留林堡和盧森堡領土的主張,因為他擔心如此會讓法國卷入嚴重的國際沖突。⑥除了外交政策,拉馬丁與基佐在工人問題上的觀點完全相左,這也是他選擇支持莫羅的一大原因,他宣稱七月王朝的使命是在社會領域取得1789 年在政治領域取得的目標,并在4 月23 日的演講中反對基佐重視中產階級的論調。⑦相較而言,他對“被從工廠中扔到大街上”的“悲慘的工人大眾”報以同情。⑧但拉馬丁的這些觀點被議會多數排斥,他支持的莫羅也在1839 年5 月14 日的議會主席投票中失敗而下臺。
1840 年3 月1 日梯也爾上臺后,拉馬丁和梯也爾在轉葬拿破侖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沖突,5 月26日他在一次議會演講中嚴厲批評了拿破侖,認為他破壞了法國的自由,建立了個人獨裁和新的等級制度,他對歐洲各國侵略戰爭使得革命理想難以受到他國人民的歡迎。⑨此外,梯也爾支持阿里反抗土耳其以增加法國在埃及和敘利亞的影響,這導致1840年7 月14 日俄、奧、英、普、土五國對阿里發布最后通牒。梯也爾對阿里的支持使得法國可能卷入一場全歐范圍的戰爭,拉馬丁為此四次發文抨擊梯也爾政府的這一危險舉動,法國對阿里的支持會破壞英法關系,進而鼓動歐洲列強建立新的聯盟來對抗法國,最終導致一場全歐范圍的戰爭。⑩盡管10 月21日梯也爾最終下臺,但接替他的依然是保守派蘇爾特和基佐,拉馬丁因為不愿做基佐(時任外交部長)下屬而拒絕了所有外交職務,對七月王朝的態度也就此轉向負面。到了1841 年1 月21 日,盡管菲利普國王在九天前勸說拉馬丁不要反對在巴黎周圍建防御設施,但他依然在議會演講中攻擊了這一計劃,巧合的是他對巴黎防御和被包圍的結局預測最后應驗在了巴黎公社身上。?而在議會主席選舉中失利后,拉馬丁與政府(王朝)反對派的聯系日益密切,甚至在回應因為王子意外身亡而出現的王朝繼承人問題時,拉馬丁更是放言“你失去了一個兒子,法國失去了統治”,“君主制僅剩的一切都與這個優秀的年輕人一起隕落了,這個國家必須擁有管理自己的權力”。①在之后有關繼承人問題的攝政法案中,拉馬丁與政府和保守派多數決裂,轉而與左翼反對派結盟,同年9 月1 日的《世界報》對此評論:“拉馬丁先生向左轉了。”②

總的來說,拉馬丁認為七月王朝對人民福利日益忽視,它已墮落為寡頭政治,法國正向腐敗的專制主義前進,③他對掌權政治家的不滿也加劇了拉馬丁對七月王朝的敵意。④1843 年1 月27 日,拉馬丁在一次議會演講中公開宣布他加入了左翼反對派,并自詡自己為“革命的希望”,⑤將建立與左派的新關系,從孤立的自由主義者轉變為左翼反對派的同時,闡發了新的個人政治理念:“將對大眾暴力的恐懼與革命理想主義結合,社會經濟保守主義和基督教的人道主義相結合。”⑥
四、正式加入左翼
盡管拉馬丁的政治思想中依然保留著保守主義和宗教元素,但他日益激進的思想逐漸獲得了左派的支持。1843 年1 月27 日,拉馬丁公開宣布加入左翼反對派的議會演講,奠定了他在左派中的政治基礎,此后他開始參與到之前他曾嗤之以鼻的宴會運動中,⑦他在1843 年6 月4 日宴會的演講中說,法國的政治形勢已經改變,政府忽視了對民主日益高漲的基礎要求。⑧為了進一步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拉馬丁創辦了一份名為《公益事業》的報紙,他在標題上追求社會的普遍福利并模糊政治屬性,目標是為缺乏閱讀材料的工人階級提供服務,從而潛移默化地推動一場變革。拉馬丁通過《公益事業》報獲得了一個可靠的輿論陣地和相當大的知名度,并由此組成一個由他領導的政治團體(為他服務的私人政黨組織)。他在這份報紙上的政治觀點可以概括為:反對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和自由放任,政府通過向富人征稅,阻止大型工業壟斷,從而承擔起公共教育、扶貧和醫療保健的責任,促進國家財富的公正、公平分配。⑨這是一種混合了基督教道德和革命理想主義的政治理念,強調家庭和宗教、財產和國家的關系。拉馬丁自認為復興了1789 年革命初期的政治理想,而從1791 年以后一直是反對派支持這種革命理想,從米拉波、吉倫特派、斯塔爾夫人到夏多布里昂等等,他自認是這一長列革命事業真正捍衛者中的最后一員:“(他們所做的是為了)法國大革命的真正理念,通過立法實現人民主權。”⑩雖然這一觀點過于夸大了拉馬丁個人作用,但左翼反對派認為,“人們可能發現自己的觀點與拉馬丁并不一致,但人們在挑戰他的同時喜歡他,在反駁他的同時崇拜他。”?

1845 年,拉馬丁開始致力于《吉倫特派史》的寫作,希望借助此書實現“為人民而寫”“暴力殺死了革命”和“恢復公眾對革命的信心”等目標。?此外該書也隱藏著他個人的政治野心和抱負,他在本書中更公開地為革命暴力辯護,接受共和主義,甚至為共和英雄羅伯斯比爾作辯護,放棄了他以往對雅各賓派全盤譴責的觀點。人們普遍認為《吉倫特派史》是1848 年2 月革命的起因之一,甚至影響到了巴黎公社,①因此該書對革命精神傳播和拉馬丁本人政治地位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1847 年7 月18 日在馬孔為慶祝該書出版的宴會,都變為了一場帶有宣揚革命色彩的政治活動。10 月21 日拉馬丁又在《公共利益》上發表文章,宣揚他當時的政治原則,“他最關心的是人民,如果七月君主制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就會接受它,但只有在七月君主制實現一系列目標的情況下才會發生。”②他在《吉倫特派史》中概述了這些目標:要實現人民的主權,必須進行重大的憲法改革,這些改革將導致一個單一的國民議會取代現有的上議院和下議院,議會成員由全體公民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政府部長的任命和罷免并非由國王決定,而是由國民大會的多數投票決定。此外,法國要通過政教分離恢復宗教自由;通過廢除1835 年9 月的新聞法獲得新聞自由;以及通過放松國家限制實現教育和結社的自由。法國要進行兩項重大改革,一是盡可能廣泛地提供免費教育,二是在所有法國領土上廢除奴隸制。③在社會和經濟問題上,拉馬丁仍然相對保守,他希望減少食品稅,采用新的稅收為窮人提供資金,由國家收養被遺棄的兒童,以及建立更全面的國家和私人慈善制度。
顯然,日漸保守的七月王朝根本無法實現這一系列目標,拉馬丁在政治上已經站在了七月王朝的對立面,并提出建設新的政治制度來取代七月王朝,建立一個以男子選舉權為基礎的單一議院立法機構,并要求君主是憲法的名義首腦而不是國家的行政首腦。這種比較溫和的觀點是他多次被共和黨和社會主義者,甚至還包括保守派廣泛支持的原因,他的社會和經濟計劃的相對保守讓他保持了與激進左派意識形態的差異,反映了他仍然不愿意考慮任何明顯威脅家庭和私人財產制度的社會主義政策。1847 年,法國相對較好的收成和農產品價格的下跌也促使拉馬丁像許多其他著名人士一樣,相信經濟危機最糟糕的時期已經過去,但實際上城市工人的失業率正在上升,他們將成為新一輪革命的力量來源。總之拉馬丁所做的一切讓《國民報》成員相信他愿意加入溫和共和黨,④而《國民報》正是決定日后臨時政府成員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

五、參與革命
1847 年10 月底,拉馬丁連發三篇文章展開對基佐的批評,在對法國協助意大利民主運動失敗表示遺憾的同時,針對瑞士內戰中基佐支持天主教聯盟而非瑞士聯邦政府表示了嚴厲批評。⑤但是,拉馬丁也并不希望人民將他視作為激進左派,他批駁了別的報紙宣稱《公共利益》是激進主義報紙的指控,堅稱自己從未提倡暴力革命,而是一直希望和平并積極捍衛社會的三大支柱:國家、家庭和私人財產。對于正如火如荼開展的宴會運動,拉馬丁也表現出類似的矛盾心理,表示將繼續支持但盡可能不親自參與宴會運動。他拒絕參加一個在里昂的改革派宴會的邀請,并給晚宴的組織者寫信,宣稱他的信念是迫切需要民主化憲法以及發揮公眾輿論對政府的壓力。他很樂意參加宴會,但是由于情況所迫,不得不拒絕參加任何針對現有政府而舉行的宴會邀請,盡管他完全支持宴會運動,但他不可能在冒犯他人的情況下接受里昂的邀請,因為他已經拒絕類似的邀請多達18 次。⑥可見拉馬丁在政治上依然試圖保持獨立的地位,他認為自己雖然政治上孤立但實際上廣受包括保守派、改革派和底層人民在內的法國各階層的歡迎,他反對人為的政治聯盟,但對激進派賴德律·羅蘭給予特別的支持,對改革派的宴會運動持保留態度的同時卻不希望這種保守態度為公眾所知。⑦
1848 年1 月2 日,拉馬丁強烈批評了路易菲利普的王座演講,認為路易菲利普將宴會運動的起因歸咎于盲目和敵對激情的觀點是錯誤的,這場運動是通過舉行有秩序的示威和公開討論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來行使人民的政治權利。⑧1 月29 日,他在議會發表的一次持續近兩個小時的講話中繼續嚴厲譴責基佐反動的外交政策。①在2 月11 日的第二次演講中,他指責政府試圖扼殺公眾輿論,并重申了他對宴會運動的支持。宴會組織計劃在第十二區進行大規模集會來把運動推向高潮,但被警察局禁止。2月13 日,他參加了在馬德琳廣場杜蘭德飯店舉行的一次約有一百名代表參加的會議,右翼和左翼的反政府團體都有代表出席,拉馬丁支持成立宴會委員會,但他本人沒有加入這個委員會。②可見直到這時拉馬丁對宴會運動的態度依然矛盾,他不想參加非法事務與政府徹底決裂。委員會將宴會時間延期到20 日,后來又推遲到22 日,但警察總監于21 日簽署法令禁止舉行宴會和其他任何政治活動,此時的拉馬丁卻一反常態堅持支持宴會活動,聲稱“如果有必要,他會孤身一人,與影子為伴參加宴會”。③面對可能因此產生的暴力沖突風險,反對派在會議表決后最終決定放棄舉行22 日的宴會活動,盡管宴會沒有成功進行,但拉馬丁最后的表態大大提高了他在反對派中的聲望。④
2 月23 日晚,一位名叫黑澤爾的出版商受《國家報》的編輯巴斯蒂德和前編輯馬拉斯特之委托拜訪拉馬丁,征詢他對可能爆發革命的態度,拉馬丁告訴黑澤爾,建立新的共和國是不可避免的。通過與拉馬丁交流,黑澤爾認為如果要維護國家團結,共和黨人需要拉馬丁的支持,于是安排拉馬丁第二天早晨在波旁宮與巴斯蒂德和馬拉斯特會面。⑤2 月24日革命全面爆發后,路易菲利普傳位給巴黎伯爵,當時的問題是同意為巴黎伯爵建立攝政,還是建立可能成為共和國的臨時政府。24 日上午,在《國家報》編輯部舉行的會議上,共和派決定建立臨時政府,并擬定了政府成員名單,阿拉戈、瑪麗、巴斯蒂德和馬拉斯特都在名單上,其他被提到的還有奧迪隆·巴羅和賴德律·羅蘭等,出人意料的是拉馬丁也進入了這份名單中。⑥這要歸因于拉馬丁在2 月24 日進入下議院之前在波旁宮同巴斯蒂德、黑澤爾和馬拉斯特的會面時,拉馬丁向他們保證,他將發表反對攝政王統治并支持臨時政府的講話,以換取自己名字進入到臨時政府的名單中。⑦
在2月24日下午的下議院會議上,溫和派領袖奧迪隆·巴羅建議宣布巴黎伯爵的母親為法國攝政王,但在隨后的議會辯論中,拉馬丁要求組建臨時政府,反對建立新的攝政王朝。如今主要的歷史著作例如拉波特的《1848革命之年》都認為對攝政王朝的拒絕和臨時政府的建立,主要是因為之后革命示威者入侵議事廳所導致的,⑧但拉馬丁對這場辯論的干預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保證了他在之后臨時政府中的領導地位。拉馬丁對攝政的干預可能是在最后一刻才做的決定,在此之前他一直猶豫不決是做人民的保民者還是逃亡君主制的捍衛者,奧迪隆·巴羅為攝政所做的辯護可能最終促使他站出來反對并捍衛共和制。⑨即便如此在當日晚些時候拉馬丁依然在向圍住市政廳的民眾詢問:“你們想攝政嗎?”⑩這也反映了他一貫模棱兩可的政治立場,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最終促使他拒絕了攝政,堅持要求建立一個臨時政府。除了當時對七月君主制的敵意、長期以來越來越愿意接受共和政體以及政治上徹底導向左派等因素外,拉馬丁無疑準確地預估了24日下午議會辯論的結果,尤其是革命群眾沖入議會讓他站在了勝利者的一方。而拉馬丁本人醉心于自己的聲望,雄心勃勃地想在危機時刻成為國家的救星,避免暴力并促進國家團結,因此當有成為臨時政府領導者的機會擺在他面前時,他是一定不會放棄的。
結 語

總的來說,很少有人預料到拉馬丁會出現在當初的法國臨時政府名單中,因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拉馬丁和改革派共和黨成員之間達成了一致意見,而且24 日上午產生名單時并沒有考慮拉馬丁在之后議會中所做的關鍵干預。①但到了2 月24 日晚上拉馬丁已成為兩個主要共和集團的必不可少之人,正如謝奧爾頓所言,“有一個人,他的雄辯、堅定和勇氣使他贏得了大眾的欽佩,有一個人的支持足以扭轉局勢,這個人就是拉馬丁。”②從結果上看拉馬丁被納入到臨時政府中并不奇怪,不光是因為他在議會中的關鍵干預,一方面他在法國各地的聲望將確保地方和中產階級支持新政府,另一方面至少到1845 年他已經成為少數同情左派的議員之一,并且可能會支持左派的國家領導和民眾支持。最后左翼媒體廣泛地報道了他的演講和文章,拉馬丁也追求這種左翼的宣傳和認可,并逐漸采取了一種更加激進的政治立場,當然法國左翼的個別成員依然對他持懷疑態度。③這是因為拉馬丁仍然公開反對激進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直到二月革命之后他才提倡直接男子選舉權,對改革派宴會運動的態度也充滿了矛盾。然而由于拉馬丁的演講、文章和《吉倫特派史》,他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和影響力,成了第十二區宴會最堅決的支持者之一。在2 月24 日至關重要的議會辯論中,拉馬丁最終否決攝政王并支持建立臨時政府的做法,為他最后謀得了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之職,并成為了臨時政府實際的領導者。但是,拉馬丁政治立場中仍然充斥著模棱兩可和左右逢源,這在作為反對派時并不致命,但作為革命后臨時政府的首腦,他的地位將因此變得難以維持。
拉馬丁的政府領導身份最終只維持了4 個月,就在拿破侖三世掌權后便黯然退出政壇,其晚年生活也因為債務纏身而窮困交加。④可以說作為一名政治家拉馬丁難言成功。但在19 世紀上半葉政治意識形態不斷變化的法國,拉馬丁政治思想的變化和轉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這一時期法國部分進步貴族的觀念轉變。拉馬丁早年深受自身家庭、教育背景影響,在擔任駐外大使后開始接觸自由主義思想,政治思想由此開始第一次轉變。在復辟王朝后期拉馬丁積極參與政治,政治思想逐漸自由主義化,但同時摻雜了不少基督教道德觀念。1830 年革命后他支持七月王朝,堅持自由主義化的君主立憲,但同時也強調自己無黨派、非左非右的政治屬性,在被選為議員后更多地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到了七月王朝的統治后期,拉馬丁的政治思想發生了第二次轉變,主要表現為政治理念的進一步左轉,尤其是在梯也爾、基佐等保守派上臺后與政府的執政理念嚴重沖突,他逐漸轉向左翼的王朝反對派。最終他在《吉倫特派史》中接受共和主義,甚至對暴力革命也不再全盤摒棄,正式宣布加入左翼反對派。⑤這條由右向左轉變的政治路線,不僅同樣發生在法國眾多同時代出生上層社會的政治家身上,也暗合了19 世紀上半葉法國由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制再到共和制的制度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