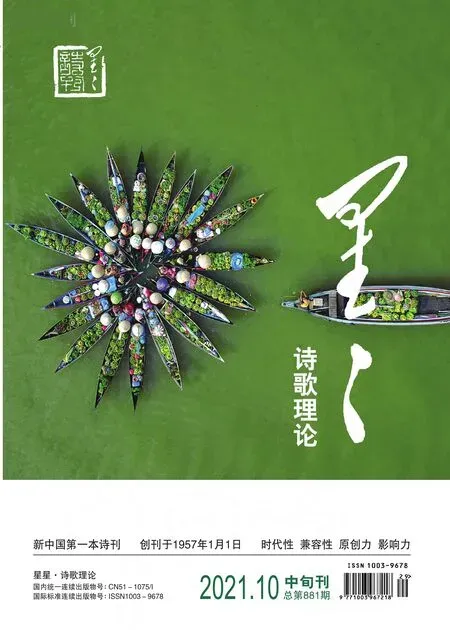新的詩美形態的生成
——第36屆青春詩會觀察
>>> 程繼龍
新詩的發展處在長期的裂變狀態中,當下的新詩有什么新動向,有沒有生成某些帶有普遍性的美學特征,這是很多熱愛新詩、與新詩同行的人熱切關心的問題。每年一屆的“青春詩會”是《詩刊》社推出新人的最重要的形式,發揮著引領新詩潮流、塑造詩歌形態的重大作用。入選第36屆青春詩會,分別是李松山、一度、王二冬、陳小蝦、徐蕭、蘇笑嫣、王家銘、吳小蟲、韋廷信、樸耳、葉丹、蔣在、芒原、瓊瑛卓瑪、亮子。閱讀這一屆參會詩人的詩作,可以得到一些直觀的感受,獲得一些有益的啟發。
有限度的想象
首先是想象的限度問題。當代新詩的寫作越來越傾向于將想象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以內。詩思的展開、文本的完成不再完全依靠想象的威力。這些詩人普遍與拉金、希尼、米沃什、辛波斯卡保持更多的認同感,而不是與屈原和雪萊。米沃什稱“詩是對真實的熱情追求”,他“反對現代詩歌里完全朝向主觀化的某些傾向”。王家銘自述“我的詩歌大體上是從自己的生活出發”“一個詞,曾代表過那么多具體的事物或動作”。徐蕭自述“我希望在增加寫作上的難度的同時,在情緒上更為克制”。這些說法都出于對想象泛濫造成的后果的憂慮,和對真實性的堅守。
對想象的審慎帶來的效果,是寫出了“自帶情境”的詩。這個“自帶的”情境是他們生活的、現實的真實體驗和記憶。這些經驗不是虛構的,不是靠自我內在的臆想生發而來的。這些真實經驗的閥域,成為他們一個個詩歌文本展開的語境和內容的構成部分。李松山《我把羊群趕上山坡——給量山》,詩中“把羊群趕上岡坡”“用不標準的口號”教羊分辨雜草和莊稼,出自這位患過腦炎,以放羊為生的河南青年的真實生活經驗。詩中所對話、致意的那個“量山”也是詩人生活中的朋友,一位“在黑板上寫下善良和丑陋”的教師。他“孩子王”的生活和“我”“放羊娃”的生活之間形成一種有意味的對位關系。更深的關系是后面出現的“溪流”“玻璃”和“詩歌”的三位一體,這是詩人相互之間對職業、詩歌隱秘關聯的知音式體認。王二冬是一位快遞員,對一個群體關注,要為他們眾多的同行們畫像。徐蕭的寫作從“校園寫作”的博學多才延展開來,流露出記者“對時代的凝視和思考”。亮子常以一個西北鄉村教師的眼光和感情描述、記憶鄉鎮生活空間里的老人孩子、山水草木,等等。每個人的寫作都拖曳著一個寬闊的界面,那是他們詩意的世界。就像河流拖著它雜草叢生、鳶飛魚躍的長長的兩岸。這個詩意世界充滿了土氣息、泥滋味,帶著個人生活的愛恨、汗水乃至淚水。古人說“功夫在詩外”,他們做足了生活的功夫,將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盡可能地放入了詩歌。
想象并非萬能,虛構不能解決詩歌的所有問題。過多的虛構,會造成詩歌中經驗的虛脫。這些詩人,正是看到了想象的盲區,站在想象的邊緣,站在不同經驗的交界處推進他們的寫作。這就要求詩人在寫作中同時做到“精準想象”,做到想象、經驗之間的自由切換。吳小蟲《局部的蒼涼》,首節“再一次在詩里愛上每一個人/理解他們的偏執,更理解他們的/悲涼。理解從生到死的一瞬/我的內心留下許多夢幻的腳印”,以及末節“涼風吹來,吹在那滾燙的肉體/他感到無比輕松,任風將頭發吹亂/沒有比原諒更上升到星空/他站在河岸靜靜地哭泣起來”,由感嘆入,由感嘆出,帶有個人強烈的沉思氣息,流露出郁勃的蒼涼感。細細品味,詩意的情感從長久的生存體驗、瞬間的禪意化合而來,悲欣交集。
對于這一詩學特征的生發,源于當代詩歌主體精神的混雜。當代詩人生活在一個快速發展、多元的社會空間里,“一日大于一年”,尤其是精神、文化內部發生的裂變速度和規模都在加劇,比之于20世紀,詩人更難保持自我、身份的完整性,因此覺察到僅靠某種單一想象、經驗難以寫出有效的詩歌。同時,現實經驗日益凸顯出來,小說家余華常說現實比小說更荒誕、離奇,詩人也有同樣的體驗。不斷生出的現實經驗,形成言說的勢能,催逼著詩人調整姿態去進行新的命名、表達。詩人不約而同地開始向外轉,轉向與現實貼身摩擦,對那種迷離惝恍、高度內在化的“小情緒”式(張立群《“小情緒”的簡約、泛化及其他——當前新詩發展的困境與難題》)的寫作開始保持足夠的警惕。
低調的倫理態度
這樣就帶來一種獨特的詩性倫理。近年的詩歌,明顯地越來越注重倫理態度、倫理思考。詩歌在求真、求美的同時,越來越注重對善惡的探求和反思。對人之為人、人性的思考,深深地融入了繆斯的血液。這又是一種回歸,中國詩人向來習慣民胞物與,憂樂天下。亞里士多德特意在“理智德性”之外區分出“道德德性”,更看重個人精神、習慣中善良、節制、慷慨等品質的價值。當下的詩人,明顯比之前的詩人更迫切地感受到自覺擁抱道德感情的重要性。詩人們不約而同地認為“詩是一種修煉”。吳小蟲說“詩歌涉及技藝和審美,但內在的本質卻是終極關懷”。“修煉”什么呢?修煉對人間的敬畏與悲憫,對萬物的感同身受。
因此,他們自覺堅持一種更為“低調”的倫理態度。正如辛波斯卡在諾貝爾受獎辭中提到當代很多詩人對自己的詩人身份不自信,懷有一種強烈的“羞愧感”。詩人們懷著對自己詩人身份的“幾分羞愧”無端淚涌,悄悄地寫下詩行,把內心的愛恨、把血液變成墨水或屏幕光標后面的字跡。中國的詩人情同此理,他們很少“大聲說出自己的愛”。他們的感情是樸素的,他們的態度是謙和的,1980年代的詩歌倫理姿態是崇高、超邁的,和現在有很大不同。朦朧詩人在廣場上高聲宣布“我不相信”。就連稍后民間口語派詩人的調侃、戲謔也帶著超出流俗、玩世不恭的味道。1980年代的代表詩人海子、顧城則在極端、自閉的突圍中,進入了修遠、抽象的幻象世界,遠離了現實,最終結束于“精神世界的坍塌”。他們的詩性自我是大寫的,詩性倫理是悲壯的。
而今天,詩人日益感覺到這樣的帶有強烈浪漫色彩和悲劇精神的姿態需要調整。王家銘詩集開卷的“獻詩”準確地表達這一倫理姿態:“毫無疑問,這些詩/有著藝術上的瑕疵/如情感中的歉疚/面對著天性/和每一個具體的你。”詩人為自己“藝術上的瑕疵”和“情感上的歉疚”不安,于是從身邊的事物出發,推己及人,觀察、記錄、照亮周遭的草木蟲魚、親人鄰里,乃至“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魯迅語)。李松山《路燈下》,在“時間的線軸”中展開對自己和小伙伴成長情節的描述,他們跑著,“三十九盞路燈一排溜亮著,/仿若三十九個月亮依次被記憶的閥門打開”,他們甚至跑到了月亮背后的黑暗中。“三十九盞路燈”實際上是詩人三十九歲的象征。“有的跑進了水泥森林,/有的嫁給了叫風的遠方”,只有“我往回走”“父親在另一個世界看著我”。這一成長記憶的場景放進了“自我”“父親”“同時代人”,舉重若輕的關聯起了八〇后、九〇后的成長經歷乃至時代進程。其中隱而不彰的愛與苦楚有催人淚下的感染力。陳小蝦的《他》寫自己返鄉去看望一位在屋檐下曬太陽的老人,原諒了“他”年輕時用鞭子抽打母親的暴戾,而且“以和先逝父母講話的語氣/塞給他幾百塊錢,叫他少喝酒,冬日里多添衣”。是歲月的沖刷和人性的寬厚,寬恕了當時人性中的惡,綻放出天使般慈愛的光輝。王二冬說他的詩幾經變化,“詩意的種子從兒時就埋進了那片故鄉的土地”,早先他寫“以東河西營為中心的十余個村莊”的人事,后來進城當了快遞員后,他寫城市送快遞生活的歡樂和憂傷,“這是我一個人的高原快遞站/一個人攬收、一個人分揀、一個人投遞/一個人喊出幾萬個人的名字”(《一個人的高原》)。今天,這些詩人所秉持的倫理立場,更多地不是以惡抗惡,而是用心去愛、身體力行,甚至具有某種“自我承擔”精神的隱忍與悲憫。他們深深地領受了“凡人在世”的命運,不動聲色地盡著自己生而為人的責任,守持著道德的理想。他們常常是站在弱者的一邊。
也正因此,他們的倫理精神顯出了博大的氣象。“泛愛眾,而親仁”,自我的承擔和恪守具備了普遍性。“這里剛下過一場雪,/仿佛人間的愛都落到低處”(黃禮孩詩句),唯因其“落在低處”,才更真誠而動人。王二冬說他越來越不滿足于“基于懷念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書寫”,而嘗試轉向“以社會為中心的書寫”,他發現了更高遠的“天空”。由此超越了漢語詩歌寫作常見的“自我中心主義”傾向,恢復了詩的社會性,重新發現了大地,接通了時代精神。這是一種既古且新的“倫理的詩性”。
泛化的修辭
到了今天,觀念化寫作的能量被耗盡了,當代詩歌更需要重新想象,再出發,這既出于對“新”的宿命般的渴望,也出于對自身和世界、時代感性之關系的調整的意識,當代新詩這個“認識/言說裝置”必須保持自我改進的活力。對“觀念”的厭倦,帶來的是對修辭的重視。
這里說的“修辭”,不單指我們所熟悉的比喻、擬人、隱喻等修辭手法,而且指詩人在詩意的生發和實現程中,更自覺地看待詞與物的關系、更有效地選擇表達方式以實現表達效果的意識和手段。“物”,不僅指和語詞對應、被語詞標記了的事物,還指詩人對事物的感覺、情緒和思想以及那些更為內在化的事物。在詞與物之間有一個廣闊而混沌的暗區,詩人對它心生恐懼,又躁動不安地想挺進它,開疆辟土,有所作為。西方文化界二十世紀后半期發生的宏大的語言學轉向影響了中國當代詩人的語言觀,甚至刷新了他們對世界、自我、詩藝的看法。但是,今天的寫作,實際上又再一次發生了重大的變革,當下的青年詩人,已經很少有人再奉持韓東當年“詩到語言為止”的信條,那個充滿結構主義意味的、作為人的世界的本體而存在的“語言”不再能成為詩人的牢籠,詩人須要更清醒地對待語言,就像本維尼斯特說的那樣,重新啟用語詞的指稱性,再一次將語言輕量化,站在內心、語言、外物的臨界點上展開他的作業,以圖更好地展開他的表達,既忠于內心感受,又忠于世界的原初模樣。不再癡迷于寫“語言的詩”,或者讓語言代替人來寫詩,寫語言自己。
因此,作為一種超級觀念的語言,也變成了修辭。一同修辭化了的,還有智性、玄學、戲劇性、寓言,包括前面說到的擬人、比喻、象征這些修辭手段。正如詩人所言,寫詩是一種修辭訓練,寫詩固然離不開想象、經驗、愛、悲憫這些東西,但更離不開設法操控語言以達成自己想要的傳達效果的技術。這樣,修辭就被泛化了。詩歌寫作的實現,離不開修辭。可以有詩意,但不一定有詩歌,因為前者在內心,后者需要借助修辭來實現外在的形式化。因此詩人越來越變成修辭的高手,玩修辭如同耍雜技。這樣做是為了把對現實的復雜感受和內心幽微的感覺高效地傳達出來。
這樣就帶來兩個變化。第一個是修辭的細密。修辭格遍布文本中,就像鹽溶于水。徐蕭《應許之事法則》,“法則”這個詞綴,有臧棣“叢書”“簡史”寫作的意味,是一種刻意而為的形式。借助這種形式,徐蕭打破了現有的詩歌文體,詩中雖然有隱約的本事(一個年輕的父親寫詩給出生不久的女兒“攸米”)、情感線索可尋,但它不是長詩。其中單首詩以“1:1”“1:4.1”這樣的小標題標示。在這種特殊的文本里,詩意的展開將修辭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每一個文本單位負責引導、承擔一種感覺、一種情境、一種寫法。整體上猶似一段隨想曲,一幅拼貼/裝置畫。修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修辭啟動了詩思,帶來一個個意象、情境,也導引了詩思的轉折、交錯。但看不到哪一種具體的修辭格能上升到主導地位。修辭就像原子結構內部,一個個電子在各自的層級弧線上運動。
第二個變化,是貼著物寫。我們把沈從文“貼著人物寫”的說法稍微修改一下,用以描述這一詩學傾向。樸耳《海棠拳》:
軀干細直,花朵連成蓬松山丘
海棠的分歧,從根部已現端倪——
斜出的分枝制造了更多
粉色的緩坡,更多灼熱與柔和
它是那么妥當無爭又飽含委屈
我理解海棠發自肺腑的纏斗
它的骨和肉,持續推翻它深埋根部的心臟
正如這一秒的我正在推翻上一秒的我
上一秒的我
接連從山坡上滾下來
這首怪異的詩,題為“海棠拳”,以一系列動詞、動作摹寫海棠怒放的情形。不管是第1至5行的“無我之境”,還是第6至10行的“有我之境”,都體現了一種面對物事時的竭力的“物化”狀態。陌生化效果,來自詩人在面對海棠遣詞造句時的自我化入狀態,自我進入審美對象“海棠”中去,感覺、意念順著海棠綻放、爛漫的情態運行。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的目光先是落在枝干、樹冠、斜枝上,海棠不計后果的開放和生命力的張揚,使她一度潛入海棠的根部(心臟),最后像獲得了縮身功一樣進入了花朵,進入了色彩和芳香的世界,那個世界對她來說是無邊的。“自我”的分身、幻化形同“海棠發自肺腑的纏斗”,一個部分推翻另一分部分,一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文心雕龍》“物色篇”中說 “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體物為妙,功在密附”,這真是到了“隨物宛轉”“密附”的地步。米沃什注意到東方詩歌有一種可貴的對物的沉思態度,他特別指出松尾芭蕉的寫作箴言:“寫松樹,你必須向松樹學習”。樸耳就是在向海棠學習。這樣做,就將修辭深深地融進了主體的眼光、感受和語詞的發起、連綴和轉折的肌理之中,使其不再是外在的客觀形式了。
這一屆青春詩會15位詩人創作的詩意、詩藝所綜合呈現出來的風貌,能代表近十年來當代詩歌探索的傾向和特征。可以說,這一初步生成的詩歌美學形態是繼承和修正1980年代、1990年代和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各個階段詩學成就的結果。這一在巨變中艱難聚合成的詩美形態,大體上是低調、沉實、厚重的。這一時代的詩心,也有激越、飛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在中國大地上俯首生活,偶爾低空飛行。詩人的愛恨和想象,更有人間煙火氣。從一個大的方面看,詩人的沉潛努力,實現了“普遍感性”和社會生活的結合,人性內容和語言形式的結合。這批詩人以“樸素的形式”表現了“時代生活”“時代心靈”的方方面面。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塑造的新的詩美形態,具備了阿甘本所說的那種詩的“當代性”,把握住了當代的感覺,體現了當代生活的“歷史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