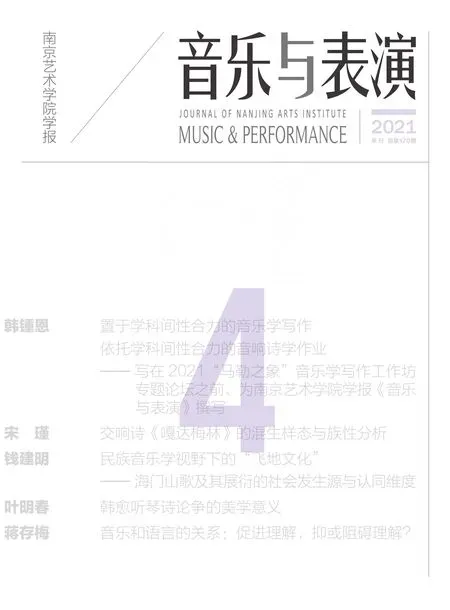相斥與合謀
—— 試論馬勒《c小調第二交響曲》的音響結構力并及意象生成
張瀟雪(上海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上海 200031)
引 言
馬勒《c小調第二交響曲》通常被冠以標題“復活”。目前雖沒有證據表明該標題是馬勒本人所加,不過他選用了詩人克洛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的詩歌《復活》作為第五樂章聲樂部分的唱詞①馬勒在創作《第二交響曲》第五樂章時,曾長期苦惱于找不到理想的文字用于聲樂合唱,后來在彪羅(Hans Von Bülow,1830-1894)的葬禮上聽到了這首圣詠。“我好像收到閃電的一擊,頓時,我心中的一切顯得清晰、明確!創造者等待的就是這一種閃現,這就是‘神圣的構思’。”(參見薩姆?摩根斯坦.作曲家論音樂[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6:171-172.),顯然是在作品中置入了較為明確的主題性內容。全曲的五個樂章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以獲得有機貫穿的整體性意義。內容上,第一樂章“英雄的葬禮”和第五樂章的“復活”前后呼應。同時他也在第一樂章中提出了一系列問題:接下來將是什么?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死亡?我們會永恒地活著嗎?并最終在末樂章中給出了回答。第二、三樂章類似“插曲”,分別是英雄對幸福時刻的回憶和對世界真實性的懷疑,第四樂章是在終曲樂章前的巨大引子,代表著對永恒生命的追尋。[1]結構上,首、末兩個樂章的篇幅大、分量重,中間三個樂章則相對短小,帶有過渡的性質。
目前國內學界對馬勒《c小調第二交響曲》的研究主要包括:任冰彬的碩士學位論文對該作品的歷史背景、音樂分析和精神內涵等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2];莫瑋嘉的碩士學位論文從指揮的角度著重分析了末樂章中的合唱部分[3];筆者也曾撰文探討過該作品的調性問題[4]。本文主要著眼在首、末兩個樂章,通過對音響結構的深入分析和音響結構力的描寫,尋找由聲音形象生成復活意象的可能性。為了能在龐大的篇幅和雜多的素材中厘清作品的行運邏輯以及局部和整體之間的內在聯系,筆者在研究中采取了第一樂章由“大結構”向“小結構”層層深入的方式,旨在提煉核心的結構因子;第五樂章反之,由“小結構”向“大結構”逐漸展開,旨在分析樂思的發展邏輯。這樣的研究思路又恰好與馬勒試圖在兩個樂章中建立問答呼應的意圖相合。
一、第一樂章:英雄的葬禮
第一樂章為奏鳴曲式,由四個大部分組成:呈示部、第一展開部、第二展開部、再現部。每個部分臨近結尾時都有一上一下兩股音流的對峙,并在隨后被下行音流鎮壓,這樣的四次音響行態轉折點分別在第97、196、291、441小節出現[5]。四個部分中,上下行音流對峙的強度各不相同,由對峙到下行的轉折方式也或含蓄或強硬,歸結起來四次分別是:強對峙—弱轉折、強對峙—強轉折、強對峙—強轉折、弱對峙—強轉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樂章末尾,兩股音流已經在葬禮節奏型的籠罩下殘喘呻吟,隨即在一個下行小二度的不祥宣告后,下行音瀑粗暴地闖入并一瀉千里。
然后將“鏡頭”推近到呈示部。四個主要主題中,兩個呈上行態勢,兩個呈下行態勢。兩個上行主題為:主部推進式“斗爭”主題(c小調)、副部升騰式“希望”主題(E大調);兩個下行主題為:連接部滑落式“呻吟”主題(c小調)、結束部-負重式“送葬”主題(c小調)。
再近一步看作品的“第一句話”。全曲第一個音是由小提琴和中提琴以震音奏出的c小調屬音,猶如死亡的陰影瞬間籠罩蒼穹,有著吞噬一切的力量,沒有人能逃脫。緊接著是在死亡陰影籠罩下“破土”而出的“疑問動機”(見譜例1),第一樂章的結構“種子”。馬勒借此提出了他對生死問題的巨大疑問:人固有一死,為何還要生?死后的世界究竟如何?
歸結起來,第一樂章的核心結構力就在于一上一下兩股音流所產生的斥力,它們經過幾番對峙之后,最終,下行音流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也正如馬勒所言,他親手將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送進了墳墓。

二、第五樂章:復活
與首樂章在死亡陰影籠罩下發出的“第一句話”截然不同,末樂章起始處就是一個以強力度向上疾速奏出的C大調音階,猶如火山爆發般噴涌而出,其能量來源是第四樂章長達五分鐘的慢板第四、五樂章通常連續演奏)。隨即由整個樂隊全奏出bb小三和弦音塊,就像是思索良久過后終得確證般酣暢淋漓。看來,對于第一樂章的疑問,馬勒在末樂章的第一句話就已給出了答案:死亡之后終將復活。
整個樂章的結構依然遵循了奏鳴曲式的框架,跟隨著主、副部主題的呈示與發展,可以理出如下線索。

(一)主線一:從“末日經”到“復活頌”(副部主題)
來源自天主教安魂彌撒的“末日經”①“末日經”(Die Lrae)又稱“最后的審判日”“憤怒的日子”,是羅馬天主教儀式安魂彌撒中的繼續詠部分。它源自基督教“最后審判說”,大意為現實世界在未來的某一天將會終結,彼時死者都將復活,與生者一同接受造物主的審判。對最后審判場景的描述使“末日經”逐漸成為死亡、死神以及末日的象征。此外,馬勒對自己的第二交響曲也曾做過類似描述,詳見(德)沃爾夫岡?施雷伯.羅沃爾特音樂家傳記叢書——馬勒[M].高中甫,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179.曲調以及接續出現的“復活頌”,在第五樂章中作為副部主題承擔著重要的敘事和結構性作用。起初是“末日經”曲調在木管聲部緩步托出,隨后平穩地銜接到銅管聲部,弱奏出“復活頌”。在這里木管到銅管的音色變化更多強調的是過渡性而非對比性,由此,“死亡”與“復活”就這樣自然而然地相接相生,向死而生,死而復生。
這個主題在整個樂章中一共出現 了 六 次(第62、142、289、472、512、618小 節)[5]142,148,168,186,190,195,每次出現時旋律輪廓基本不發生改變,而是在調性、速度、配器、音程關系等方面做出變化。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當它在再現部中再次出現時,便由最初的器樂搖身變成了莊嚴的合唱,音樂的主題也拋棄“末日經”只保留了“復活頌”的部分,唱道:“復活吧,我的身體!經過短暫休憩,你將復活!”[6]值得注意的是該主題六次呈示時調性的變化:由最初的f小調(末樂章起始調性),經由bG大調bD大調bG大調,最終在第六次呈現時落在了bE大調(末樂章終止調性)。這樣的寫作手法可稱之為“漸進調性”,往往具有音樂結構上的“遞延”和音樂表達上的“修辭”意義。②“漸進調性”概念來自美國音樂學家列昂?普蘭加特(Leon Plantinga),“遞延”概念來自武漢音樂學院教師符方澤,“調性修辭”范疇來自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陳鴻鐸的修辭分析。從f小調一路走到其關系大調bA大調的屬調——bE大調,調性色彩呈現先松弛再緊張的相對變化,一次次聚集能量,加深著對死而復生的渴望和期盼。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交響曲》不僅在末樂章的主題上有“漸進調性”現象,在樂章之間更大尺度的結構上也有著這樣的安排:第一樂章的主調性c小調,經由第二、三、四樂章的bA大調c小調bD大調,最后來到末樂章的終止調性bE大調,其中包含了關系大小調、屬調、重屬調等多重調關系,整體上趨向更加明亮而堅定熱烈的目的地前行(見圖示1)。對此我們可以進行合理的理論猜想:馬勒將具有英雄象征意味的bE大調作為調性行進的終點,正昭示著第一樂章死去的英雄在末日之后涅槃重生。

圖示1.第二交響曲五個樂章的“漸進調性”

(二)主線二:“永生”主題(主部主題)
如果說在“馬二”末樂章的“交響敘事”中,副部主題更多扮演的是“說話的敘述者”,那么主部主題(“永生”主題)就或許可以看作是“無言的見證者”。它并不像副部主題那樣多次穿插著出現,而是在開頭、中間和結尾這三個重要結構位置上穩穩地矗立。該主題建立在C大調上,其形態先是從屬音開始向下跳進到主音,緊接著通過上行音階再回到主音。不難發現它的輪廓與第一樂章開頭的“疑問動機”類似,都是先向下再向上彎折的句式。不過,與“疑問動機”圍繞著小三度蜷縮纏繞相比,“永生”主題(見譜例3)音高行進的幅度更大,時值拉伸的程度更寬,音色音質偏向溫和圓潤,使得主題的性格更加平和堅定,仿佛看透生死之后的淡然、無畏。
到了整個樂章的結尾,“永生”主題承載了全曲最壯麗絢爛的高潮。人聲與樂隊在這里完美融合,隨著“永生”主題的緩緩延展、層層推進,歌者們一齊高聲吶喊道:“我將死去,而后永生!復活吧,你將復活!”最后,莊嚴的鐘聲敲開了那扇通往永生世界的大門,追尋著神的召喚脫離肉體進入馬勒用聲音構想出的伊甸園,天國的光照亮了我們的存在,永生,永在。
(三)線索外的“意外性結構”
末樂章中,除了由主、副部主題貫穿出的兩條主線索之外,還有多處“意外性結構”。比如在“復活頌”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呈現中,當唱到“Leben”(生命、生存)和“Ernte”(收獲、成熟)時,bG大調調域內分別突然出現了E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它們就像是天外來音一般可以通達神境。再比如從遠處傳來的小號聲,吹響了末日的喇叭,以及再現部“復活頌”前凄婉的“鳥歌”,象征著世上最后一只夜鶯的悲鳴,等等。這些蒙太奇般豐富的音響容納了馬勒的各種奇思妙想,同時也從多個維度充盈了他對于往生世界的聲音想象。
最后,對整部作品的音響結構力加以提煉,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1)相斥,即一種局部相抗衡的斥力。第一層意思是指第一樂章一上一下兩股音流所產生的互相抗衡的斥力;第二層意思是指末樂章的“末日經”和“復活頌”主題,每次呈現都是起止分明、清晰可辨、互不干擾,因而同性相斥;第三層意思是指遙遠的小號、末日的鳥歌、E的大小三和弦等意外結構,彼此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同時又與主要的邏輯線索相斥相離。(2)合謀,即在某個共同意圖的引導下達到合一。在《第二交響曲》中,上述斥象的聲音都同時作為馬勒音響資源庫中可供挑選的素材,被他出于對“復活”這一意象的表現性目的 “天才”般隨心所欲地取用,或明示或暗喻地表明它們與“復活”意象之間或強或弱的聯系,最終合為那個獨一無二的有機聲音結構體。
余論:之所以是“小說交響曲”
馬勒在交響曲創作中始終踐行著他的宏大理想:“交響曲必須像世界一樣,它必須包羅萬象。”[7]因此,自然、愛情、生死、復活、神祇、天國、悲劇、夜晚……天地乃至宇宙間的百感萬象都被他納入了自己“建造”的交響曲世界。與如此廣博的理念相稱的是,交響曲體裁在馬勒筆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龐大規模和宏大敘事。與古典交響曲追求將凝練的樂思在奏鳴曲形式邏輯下進行“合力性”藝術表達所不同的是,馬勒的“交響敘事”是在強烈主觀意念下流淌出多彩的音樂元素和多重的發展線索,具有“混雜”“突變”的“散化性”特質。[8]
對于馬勒交響曲的這一特質,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1903-1969)用“小說”類比,指出:“從歷史哲學的角度來看,馬勒交響曲的形式接近小說的形式。就像小說一樣,他的每部交響曲都喚起了人們對某種特殊禮物的期待。”[9]阿多諾認為古典樂派創作的“戲劇性交響曲”(Dramatic-Classical Symphony),是通過主題核心因素的各種變化形成音樂的全面展開,整體的構思先于主題的構思。而在馬勒的交響曲中,主題材料的基本形態在音樂的進行中并未發生改變,改變的僅僅是時間的維度,例如整個主題時值的延長、縮短等。他所關注的是每個有特點的、單獨的部分(就像小說的角色或者事件一樣),而不是整體結構。阿多諾將之稱為“小說交響曲”(Novel-Symphony)。[10]
阿多諾的觀點引發了筆者的思考:為什么阿多諾用小說,而不是其他文學體裁,如戲劇、詩歌或散文與之類比呢?筆者以為,戲劇以矛盾的沖突與解決為內核,因此被阿多諾用來類比了古典交響曲。詩歌的語言凝練且講求韻律規則,顯然與馬勒龐雜豐富的交響曲不相及。界限相對難以劃分的是散文,散文的語言形式靈活,表述對象廣泛,似乎也能與交響曲形式在某種層面互通。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文學理論中,小說與散文也難有絕對的界限,再引申到音樂作品中便更加難以教條地一一對應。①耶魯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Seth Monahan在專著Mahler`s Symphonic Sonatas中也提到,阿多諾認為馬勒的交響曲更加類似于19世紀的散文小說“prose novel”(轉引自:孫絲絲.阿多諾的“馬勒觀”——評《馬勒:一份音樂心智分析》[J].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11(1).),或許也是出于這一考慮。筆者認為,相較于概念的辨析,更關鍵的問題在于:“小說結構”是怎樣的結構?這種結構在音樂作品中如何體現?以“小說結構”類比馬勒交響曲是否可能帶來理論增長點?受篇幅所限,在此僅以前文對《馬勒第二交響曲》的相關分析為基礎,淺談一些個人理解。
俄羅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認為,小說形成于語言和思想生活中分散、離心的軌道上,長篇小說意味著是雜語形象。[11]而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指出小說首先是建立在幾個根本性的主題上的,“主題就是對存在的一種探詢,實際上是對一些特別的詞、一些主題詞進行審視。”[12]這與《第二交響曲》中的“相斥”與“合謀”如出一轍,馬勒以“復活”為主題,隨心所欲地在他的音響資源庫中挑選聲音素材,在清晰可辨的主線結構之上,建構了諸多具有離心力的意外結構。就像是堂吉訶德騎士一路上遭遇的一個個人、事或物,充滿奇思妙想,活靈活現,隨心所欲,無法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