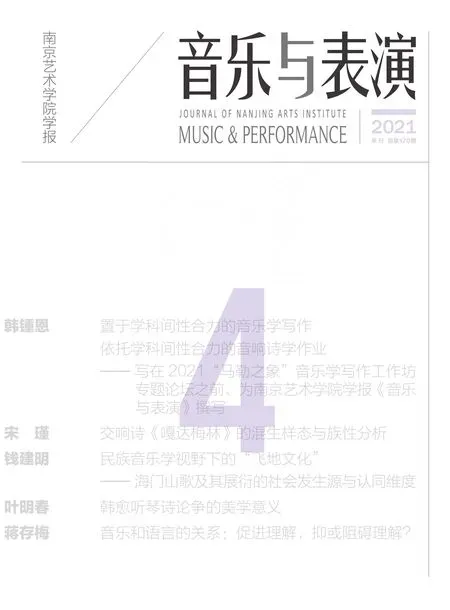相約南園
—— 母題學視域下的五河民歌《摘石榴》分析
施 詠(南京師范大學 音樂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0)
安徽五河縣(今屬蚌埠市)地處淮北平原和皖中丘陵的交界處,屬淮河中游下段,因境內流有淮河、漴河、沱河、澮河、潼河五條河而得此名。五河因地處淮北、淮南、蘇北交界之處,其語言、文化等方面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也受到吳文化和楚文化的浸潤,而體現了多元的交融性。
五河民間音樂亦十分豐富,尤以民歌極富特色,是淮河流域民間音樂文化典型代表之一。且由于五河自古水路通暢,南北文化交流頻繁,五河民歌在淮河中、下游十幾個縣市,江蘇(北)、山東部分縣、市都廣為流傳,影響深遠。五河民歌以其較高的藝術價值,于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五河民歌體裁多樣,其中以小調類的民歌數量最眾,頗具特色,在小調中則以《摘石榴》最為著名,民歌借助相關采摘勞動場景,表現青年男女之間的逗趣、戀愛、邀約幽會的主題。在20世紀50年代,《摘石榴》是以“三小戲”與民間小調這兩種形式并存流行。80年代經蚌埠市文工團的歌唱家馬留柱和曹新云①曹新云(1942—2018)安徽蚌埠人。1981年結業于中央音樂學院歌劇系。蚌埠市歌舞團歌隊隊長、獨唱演員。20世紀80年代和馬流柱一道曾以一首五河民歌《摘石榴》唱響全國,成為安徽民歌的代表人物。演唱,并由中央電視臺全國播放后紅遍大江南北。以朱逢博、吳瓊、魏金棟、閻維文、張也、孫國慶、張燕和阿寶等為代表的眾多歌唱家、歌手也都演唱(翻唱)過該歌。2010年祖海還在維也納金色大廳唱響《摘石榴》。作為安徽民歌乃至中國民歌中采摘題材類的經典之作,這首《摘石榴》與其他采摘題材的如山西民歌《打酸棗》、四川神歌《摘葡萄》、福建龍巖《采茶燈》等共同成為中國最為著名的“采摘”母題民歌系列。
從民歌的歌詞表現、題材分類來看,《摘石榴》應屬于采集、采摘文化母題下的口頭文學表述。眾所周知,不同文化背景下民歌的表現主題都有著其特定的文化烙印,由此構成其穩定的文化形態內涵。早在20世紀20年代,朱自清在其《中國歌謠》第四章“歌謠的分類”中就提出對民歌的表現題材進行類型化的主題學(theme)、母題學(motif)分類研究。[1]即由個案生發,擴及某特定的共同文學母題、或音樂主題相維系的民歌群研究,并探析相關母題、題材在不同時期的流變,以及在不同民族、地區的差異及其文化成因。
從“母題學”的逐層分類視角來看,《摘石榴》的表現題材分別與“采摘母題”“石榴母題”“摘石榴”母題的民歌群(或換言之“同宗民歌”)有著較為密切的關聯。
一、采摘母題
(一)采摘母題民歌的起源
首先,采摘母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淵源,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從人類的文明史來看,先于農耕文化的是漁獵采摘文化。而中國人早在漫長的舊石器時代,就主要是以采摘生活為主,漁獵為輔。彼時不是男耕女織,而是男獵女采的時代。而在以采摘農耕文化為特征的中國傳統文化中,“采摘”文化(意象)業已成為中國藝術創作中的一個重要的母題,與“采”“摘”等勞動方式相關聯的民歌(詩歌)也已成為一種十分重要題材類型。
從廣義上來說,采摘題材的民歌應肇始于《詩經》,其首篇《關雎》中便出現了該母題內容,在其“君子求淑女”的主題下,采“參差荇菜”的詩句先后出現了三次,并分別以“左右流(采、芼)之”三個動詞描述了采摘過程,暗喻了其與人生婚戀相關聯的意蘊。
《詩經》中涉及采摘類的共計26首。所關聯的采摘物種中則有薇、葛、桑、蕭、艾、苓、繁、蕨、蘋、芑、蘋、荼、菽、蓮、菱、卷耳、苤苢等具有藥用、食用、織染等價值,且與人情相通具有靈性的各類植物。從這個角度來看,“詩三百”中詠唱的是一個“采摘”的時代,通過對采摘活動及采摘意象的描述與詠嘆,給我們留下了一幅幅鮮活靈動的采摘畫面,也傳遞著先民們的喜悅、期盼、思念、憂傷……
譜例1.
(二)采摘母題民歌的種類
由于傳統(農耕采集)文化的延續性,這種源自三千年前“詩經”采摘時代的歌唱母題在后世的民歌中也得到了穩定的延續。在浩瀚的中國民歌的海洋中,以這種“采摘”為母題的民歌占有相當的比例,數量甚眾。
饒有趣味的是,由于民歌所依托之豐富的地域、鄉土性,而使得在這類“采摘”母題的民歌中,對于相關行為的動詞表達如“采、摘、撿、打、割、刨、薅、掐”等,也都體現了不同的民俗風貌、地域性格及方言特征。如“采”字系列就有《采蓮調》《采紅菱》《采檳榔》《采茶調》《采桑調》《采茶撲蝶》;“摘”字系列的《摘葡萄》《摘石榴》《摘黃瓜》《摘豆角》《摘花椒》《摘青梅》《姐在南園摘大桃》《摘菜調》《摘棉花》;“打”字系列的《打酸棗》《打仙桃》《打櫻桃》《姐在園里打香椿》,還有類似動作系列的《割莜麥》《刨洋芋》《姐在田里薅豆棵》等。此外,還有采摘農作物、果蔬后的下一勞動環節的《掐蒜苔》《洗菜心》等,也都是與“摘”“采”生產方式密切關聯的表現題材。
而且,在這些動賓結構的歌名中,其賓語的變化則是直接對應反映了不同地區農作果蔬的種類,并以動賓的搭配共同彰顯其不同的地域風土特征。所以,盛產大棗的北方才會出現著名的山西民歌《打酸棗》;同樣,類似莜麥、洋芋等作物,則也是交由山陜人民在“割”“刨”時所唱;而至于“紅菱”“蓮子”的采摘則是體現了一派江南水鄉的風土人情……
尚值一提的是,由于“采摘文化是一種以女性為主體的文化,以此文化為主要形態發展起來的中國文化,表現出最發達、完備的母性意識和女性智慧”[2],因而,在這類采摘題材的民歌中,還表現出多以女性為主體,展現其在采摘、農耕文化下勞作過程中的各種意趣之共性。
二、石榴母題
承前文,在上述采摘母題的民歌中,涉及了諸多種類的農作果蔬。其中,以“摘石榴”母題、或是以“石榴”為歌唱對象、起興對象的民歌也是其中饒有特色的一類,在全國大部分省份都可見此類的民歌。
(一)石榴母題的民俗背景
石榴成為中國民歌中高頻出現的歌唱對象,首先源于其自漢代西域引入后在南北都有栽培之悠久歷史,以陜西、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四川等地種植面積較大(也成為后文所提及這些相應地區以“石榴”為母題民歌眾多的原因)。在漫長的石榴栽培、觀賞、食(藥)用的過程中,也賦予了石榴特有的文化象征意義。石榴以其獨具特色的形態特征和內在品質,造就了富有中國特色的以吉祥團圓、和睦紅火為主題的石榴文化,并滲透到中國傳統藝術和重要節慶儀式活動中, 形成一種相沿成習的文化現象。
尤在中秋佳節,親朋好友“送榴傳誼”,合家團聚品嘗石榴月餅,以示吉祥。此外,由于石榴籽多且豐滿,象征多子多福、金玉滿堂;石榴的花、果還常常比喻夫妻恩愛或男女合歡。古時,定親的女孩要給自己的心上人繡石榴荷包,作為愛情的信物。并且,出于吉祥,還將很多孩子的小名稱之為“石榴娃”。
石榴在中國傳統藝術中也占有十分重要且獨特的地位。自古就成為詩人們詠頌的重要母題,以石榴花、石榴籽、石榴園等構成的石榴意象系統傳遞著人們離別、相思、孤獨、哀怨等豐富的情感。在傳統美術中還有石榴的門神、年畫、剪紙、窗花等;服飾類有石榴裙、石榴兜肚、荷包等。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為石榴在傳統民俗中的重要地位,因而石榴花還成為不少城市的市花。在安徽,除了五河被稱為“石榴之鄉”外,省會合肥也將石榴(另有桂花)列為市花。此外,河南的新鄉、駐馬店,陜西西安,山東棗莊,江蘇連云港,湖北黃石、十堰市、荊門,廣東的南澳等城市,也都將石榴花作為其市花,足可見石榴在中國文化中象征意義之廣泛與深遠。
(二)石榴母題民歌的敘事類型
在遍布全國的石榴母題民歌中,從其歌詞的敘事方式來看,又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以石榴為興起物,再唱及其他。如四川永川縣《石榴打花葉又青》(花燈調)[3]696、筠連縣《石榴打花葉又黃》(神歌)[3]125、攀枝花市《石榴開花一雙雙》[3]674等都是直接以歌名為第一句唱詞進行起興,再唱及其它的生活內容。其中,如合川縣的《石榴打花葉又青》(盤歌)中也是以歌名為首句起興后,再接唱問答式的歌詞:“唱一個盤歌問你們,啥子出來紅彤彤……”[3]66再如浙江龍游縣的《石榴開花》中“石榴早開花楊柳早青,東家阿嬤兩樣心……”[4]208與河南桐柏《石榴開花葉兒稀》(五句山歌)“石榴開花葉兒稀,你莫笑窮人穿破衣……”[5]則是以“石榴開花”起興后,再唱及同情舊社會的窮人之苦;而浙江衢州的《石榴花》“石榴花開百葉青,舊年想你到如今,舊時想你年紀少,今年想你正當齡。”[4]221則是由“石榴花開”再唱及情人相思。
第二類是唱及與石榴文化相關的民俗,如陜西商州市《看石榴》(花鼓子),唱的是自己的女兒“石榴娃”:“石榴娃命又苦,逢下女婿是二百五”[6]1381-1384,同類者還有陜西柞水縣《石榴娃燒火》[6]1380等。
第三類則為本文所主要探討的“摘石榴”為題材的民歌,這類民歌則都是以石榴園(南園)為故事發生的場景,歌中的男女主人公表達了彼此兩心默許,雖遭遇阻撓但大膽追求自由戀愛的勇氣和決心。
三、“摘石榴”母題
在全國范圍內“摘石榴”母題的民歌群中,尤以安徽五河的這首《摘石榴》最具代表性。
(一)“摘石榴”母題民歌的表現內容
首先,經歷了民間小調、三小戲發展而來的五河民歌《摘石榴》,在歌詞的表述上則更具敘事性與戲劇性。就其故事的梗概實意,可簡要概括為以下六句:
姐在南園摘石榴,哥從隔墻砸磚頭,約你去溜溜。為你挨罵又挨打,哥心難受如割肉,一起下揚州。
在這首《摘石榴》中,遭受父母阻撓的青年男女兩人最終是以相約“打起包袱、一起下揚州”完結全曲,其背景則源于:淮河常年水災泛濫造成該地區農田、房屋淹沒,村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而有著“淮左名都,竹西佳處”之稱的揚州作為周邊經濟繁榮之、交通便利之地,而成為令人慕仰之地。因而歌中的這對五河青年男女在遭父母反對后,有相約去揚州之意,亦是對周邊富饒之地向往,積極追求自由生活的態度。
在中國民歌中,這種將動詞置于地名前構成固定的動賓結構,以表達歌唱者將要去往之地的例子數量眾多,如《走絳州》《走西口》《跑四川》《過四川》《下四川》《上四川》等。在此動賓搭配中,其去往之地的“絳州、西口、四川”等地名具備的共性在于其多為物產豐富的富庶之地,“都是由于理想中的彼地在經濟生活方面高于本地而形成的歌唱對象”[7],是周邊地區向往的理想之地;而相關“動詞”(“走”“跑”“過”“下”“上”)之區分使用則在于地理地貌、勞作方式、表演形式、行為意義等方面的差異,體現了不同地理位置下去往目的地的不同方位的區分表述。如《下四川》《下江南》,以及這首《摘石榴》中所提及的“下揚州”之“下”則是出于揚州位于五河之東南方,而有南下之意,故為“下”揚州。
此外,歌中的女主人公將男主人公稱呼為“討債鬼”“小冤家”,則是表達了對心上人嗔怪的親密昵稱,也是江淮地區的方言表達。
值得重視的是,在諸多與采摘相關的民歌中,尤其是在《摘石榴》母題的系列民歌中,其意都并不在采摘勞動本身,而只是由此生發,并借助這些相關的采摘勞動場景,以歌唱青年男女之間的逗趣、戀愛為其第一要旨與主題。①此類民歌中大多數的歌名都為動賓結構,也有少數在歌名中就直接表達內容,如安徽肥東民歌《手采桑葉望情郎》。[8]236
類似于《摘石榴》這種男女在勞動場景中逗趣,打破封建禁錮,追求戀愛自由的情節模式并不少見。僅在《中國民歌集成?安徽卷》中的就有不少。如當涂民歌《姐在田里薅豆棵》中就以“姐在田里薅豆棵”起唱,再接以“一眼看見我情郎哥,田埂上來坐坐”;[8]411而在金寨民歌《姐在園里打香椿》中,則是以“姐在園里打香椿”起唱,再接“郎在高山放黃鷹,二人都有心。要吃香椿抓把去,采鮮要花萬不能,爹娘管得緊。”[8]517而在湖北鄂州市《摘黃瓜》[9]中則是“姐在園中摘黃瓜,郎在外面撒了一把砂,打落了黃瓜花……”
僅以這幾首表現內容相似的民歌為例,可見其事件情節的框架都以“姐在園中(田里)……”起唱,哥在外面則多以“砸磚頭”“撒砂石”等行為以引起對方注意。姐再抱怨爹娘“管得緊”,還多會交待“爹娘如何打罵”。如在滁州民歌《郎靠櫥柜妹靠箱》中就有與《摘石榴》中類似的訴苦挨打的情節:“郎靠櫥柜妹靠箱,眼淚汪汪告訴郎,昨天我為你挨頓打,今天我為你挨罵一場,小哥哥(呀),我渾身上下都是傷。”[8]457情哥聽后則勇敢地表達了沖破禁錮的決心,并相邀商量出路。
(二)“摘石榴”母題民歌的句式類型
以“摘石榴”為母題的民歌群在以安徽、江蘇、上海、山東、陜西為代表的全國范圍內都有流傳分布,歌名則以“摘、采、打”等不同的動詞變化出現。但由于受到所在流傳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在篇幅、句式等方面有著一定的區別。僅就句式而言,則體現為北方多兩句體,南方四句體,而中部多為三句體的句式特點。
如陜西紫陽縣的《摘石榴》(高腔山歌)[6]1152與洋縣的《打石榴》的句式都為北方山歌信天游式的上下句,歌詞“姐在后園摘石榴,郎在后面打石頭。你要石榴拿了去,莫在外面打石頭。”[6]1153分為兩段上下句進行陳述。而浙江嘉興的《采石榴》則為典型的南方山歌的四句體句式“妹在園中采石榴,郎在墻外丟磚頭。倷要吃石榴采只去,勿要丟到奴額角頭。”[4]159
而在中部地區的《摘石榴》,其句式則多為三句體。如這首五河的《摘石榴》,其句式結構即是主體為三句體,再加上一個襯句“咿兒喲,呀兒呀”和重復句。如譜例2所示,如將欄選的三行視為4+4+4的三個方整性樂句,兩上一下,且其概況其詞意后亦為方整的三句:“南園摘石榴,隔墻砸磚頭,砸在奴家頭。”而欄選之外,即第三句實際可視為2+4的兩個部分,前面兩小節“剛剛巧巧”則為情態描繪的狀語,體現表情夸張的戲劇性。而從樂句的結構來看,第三句中多出的兩小節“剛剛巧巧”,則可以視為是一種“前置性的擴充”結構。
無獨有偶,與安徽五河《摘石榴》相類似,蘇北鹽城的《打石榴》中“姐在南園內打石榴,忽聽得門外邊拋磚頭,(險險乎)拋到我小奴家頭”[10]833,以及睢寧的《摘石榴》“俺在南園摘石榴,巧遇情郎哥哥隔墻扳磚頭,(剛剛巧巧)扳在了為奴頭上”[10]833-834,其結構句式也是與五河《摘石榴》為一致的三句體。且都在第三句前綴有狀語“險險乎”或“剛剛巧巧”。(見譜例2)
此外,從篇幅來看,也體現為南方的《摘石榴》體例明顯大于北方,段落較多、情節復雜。如上海奉賢縣《姐在園中采石榴》[11]的歌詞就分為五段進行陳述,并在后三段中通過垛句對樂句進行了擴充。浙江嘉興四句體的《采石榴》則共有八段歌詞,主要著眼于青年男女之間反復表達對感情的忠貞,以及諸如“草雞怎好伴鳳凰、尖嘴鳥想吃天鵝肉”等較為復雜的情節。
譜例2.

(三)“摘石榴”母題民歌的同宗傳播
首先,就五河民歌的風格形成而言,其本身就是中國民歌在傳播場域的作用力下多元融合的一個典型個案。五河因地處淮北、淮南、蘇北交界之處,其語言、文化等方面受到中原文化與吳楚文化的共同影響,而體現其多元的交融性。當“淮河流域文化因素中融合了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文化的雙重因素,伴隨著人口流動、雜糅、聯結、融合,南北文化在這個特定地理環境中,自然過渡融合,吸納兼容,成為具有鮮明地域性特色的文化,這種鮮明的過渡與融合的文化特征淋漓盡致地體現于淮河流域的民間音樂文化中。”[12]
五河發達的水陸交通為文化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得本地區的民間音樂文化在南來北往的交流中逐漸融合并成為過渡性質的地帶。所以,在這樣文化環境下產生的以《摘石榴》為代表的五河民歌,其既浸吳越婉約之風,又吸魯楚豪爽之范。多元融合促成了其柔中有剛、剛柔兼濟的獨特風格。
從馮光鈺對同宗民歌六種分類的角度來看,“摘石榴”母題的民歌群中大多數應屬于“詞同曲異”的類型,只有少數為“詞曲都大同小異”者,這一“詞曲大同”的類型則多分布在皖北、蘇北、魯南以及河南南部等南北交界混融性較強的文化圈內,也是“摘石榴”母題民歌群同宗傳播的核心區,而具備了更多的共性。
其中以蘇北睢寧的《摘石榴》為例,將其與五河《摘石榴》進行比較,則可集中折射出雖地理位置相近,但分屬不同色彩區的這兩首民歌之間的異同及其成因。首先,不難發現,兩者在體例結構、句式襯詞、內容等方面都基本相同,如同為三句體,都為加變宮的六聲徵調式。而且,尚值一提的是,兩首《摘石榴》都采用了“變宮為角”往屬調的轉調,并再回到主調結束。并以宮和徵調式的交替。
五河《摘石榴》是由A宮—E宮調式,再回到A宮系統的E徵調式。而在睢寧的《摘石榴》[10]833-834中也出現同樣的調式轉換,為G宮—D宮,再回到G宮系統的徵調式。
另一方面,兩者之間在音樂形態上的差異也是較為明顯的,具體表現為:曲調進行中,相對于五河《摘石榴》中以二、三度為主的級進平穩流暢進行,睢寧的《摘石榴》則以其第二句中出現的5—7·、7·—3、6·—2這三處的六度和四度的大跳、以及第三句中出現的連續四度跳進而體現其明顯的變化,而彰顯其更往北方色彩區的變化趨向。從腔詞的關系來看,第三句中的“剛”字在普通話中調值為陰平5—5,而在五河及其以北的方言中都是調值近似為214的上聲,而相對于五河《摘石榴》中“剛”字對應的小二度音程的曲調進行,睢寧《摘石榴》中與“剛”字對應的則為2—7·的小三度,其更大幅度的字調變化亦無不表現更為豪爽的北方“侉”味方言風格。在《摘石榴》中,方言口語與曲調之間較為自然順應的腔詞關系,也無不成為其朗朗上口易于流傳的重要因素之一。
該差異首先是與兩者分屬不同色彩區有著密切的關聯,在苗晶、喬建中的漢族民歌色彩區的劃分中,是將蚌埠五河地區劃歸“江淮民歌近似色彩區”,同時指出,該區“與東北部平原區的聯系是相當密切的。江蘇徐州地區、安徽宿縣以北,實際上是兩區的紐帶”[13]。故而將蘇北的徐州劃歸為“東北部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區”,且進一步將其細化定位為該(東北)區的“南支區”①在王耀華的文化區劃理論中則是將蘇北徐州劃歸“齊魯燕趙支脈”。[14]。所以,江淮過渡色彩區的五河民歌《摘石榴》,雖然也采用了與東北平原區相聯系的(六聲)調式音階,但音樂的風格上更為細膩、委婉,而彰顯其吳頭楚尾的過渡性;而蘇北徐州睢寧的《摘石榴》則更顯其齊魯燕趙、東北平原的北方“侉”味。
關于對“摘石榴”在該同宗傳播核心圈及其構成原因的分析,王焰安在《<摘石榴>百年發展史簡論》一文中還在立足于對蘇北灌南縣、魯南棗莊、安徽臨泉、河南淮濱四個地區《摘石榴》歌詞進行對比后認為原因在于這四個地區“不僅同屬中原官話徐淮方言區,而且大多地方還曾是鳳陽府的轄地,數百年屬于同一管理轄地,政治、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因此,相同的方言、文化、心理、表達方式”[15]等諸多原因而使得五河《摘石榴》在這些地區得到更好的口頭傳播,并具有更多的同一相似性。
此外,還可以這首東北民歌《摘桃》[16]與五河《摘石榴》的比較,亦可說明 “江淮民歌近似色彩區”與“東北部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區”之間的密切關系。首先,從文學題材來看,這首《摘桃》與《摘石榴》同屬南園“采摘”母題的民歌,句式也為三句體,尤值重視的是,這首《摘桃》的曲調是五河《摘石榴》的簡化進行,可見這兩首“采摘母題”民歌之間較為親緣的“詞曲大同小異”的同宗傳播關系。
而從歌詞的層面來看,“詞曲大同”類的同宗民歌之間存有的“小異”則是受到不同流傳地區方言、民俗的影響所致。如在歌詞中對于女主人公的自稱,就有“姐、妹、俺、奴”等諸多的變化;作為動賓結構“×石榴”中的動詞就有“摘、采、打”等不同的表述;而關于“×磚頭”的動詞則有“砸、打、丟、扳、厾du(上海)”等帶有各地不同地域性格的方言表達,其中與五河方言最為接近的用法則是“砸”和“扳”。
四、結語
綜上,在本文中所論及的諸多與“(摘)石榴”母題相關的民歌中,無論是以石榴為興起,還是生發在全國各地石榴園(南園)中的石榴樹下發生的“砸磚(撒砂)約會下揚州”的故事事件,該母題意象產生的文化根源還是出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石榴意象所特有的文化意蘊,以及在長期采摘文化中對生活和愛情的歌唱。
作為該母題民歌群中典型代表的五河民歌《摘石榴》,作為淮河流域民歌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江淮大地一張鮮亮的文化名片,經歷了近百年來幾代人的傳唱,跨越時空,從淮河兩岸走向了全國,并遠傳海外,以石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特殊寓意實現了走出國門的“送榴傳誼”,向世界傳遞著中國人民對生活的美好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