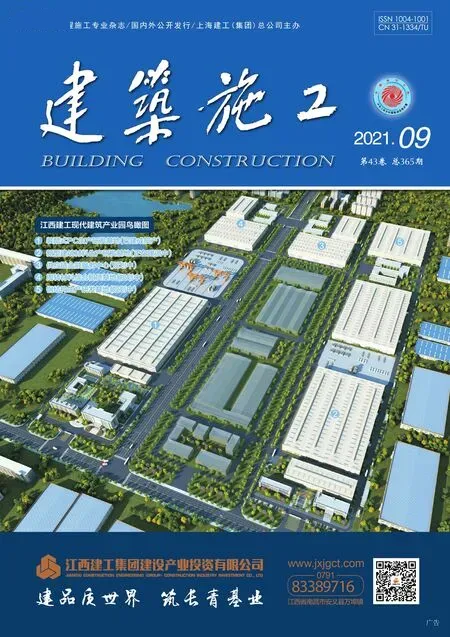大體積混凝土柱施工溫度場監測與模擬研究
左俊卿 王 碩 房霆宸 陳逸群 于曉輝 寧超列
1. 上海建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200080;2. 上海超高層建筑智能建造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上海 200080;3. 同濟大學上海防災救災研究所 上海 200092;4. 上海建工建材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200086;5. 哈爾濱工業大學土木工程學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近年來,隨著工程建設規模的不斷擴大,預拌大體積混凝土在建筑施工中的應用變得十分普遍。根據GB 50496—2018《大體積混凝土施工標準》的定義[1]:對于最小幾何尺寸不小于1 m的混凝土結構實體,由于混凝土的傳熱性能較差、熱阻率較高,在澆筑和硬化過程中,混凝土內部的水泥水化將產生大量的水化熱。這些水化熱聚集于混凝土的內部,使得混凝土內部溫度迅速升高,而混凝土的表面與空氣直接接觸,散熱較快。因此,混凝土的內部和表面之間將形成較大的溫差[2],容易導致混凝土產生不均勻的溫度變形和溫度應力[3]。同時,由于混凝土的強度在澆筑和硬化過程中尚未充分發展,因此通常會在混凝土表面和內部產生溫度裂縫。這些裂縫若是貫穿性的,將對結構的功能性、整體性和耐久性產生較大的不利影響[4]。
圍繞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施工過程中的溫度演化規律,國內外學者迄今為止開展了大量的試驗、理論和數值研究[5-9]。早在20世紀30年代,國外學者就認識到膠凝材料水化放熱引起混凝土結構內部溫度升高是產生裂縫的根源,因此率先開展了大體積混凝土水化放熱產生的溫度裂縫研究[5]。1968年,Wilson[6]首次利用有限元法對大體積混凝土的溫度場進行了數值模擬,驗證了計算結果的準確性。2005年,Schindler和Kevin[7]提出了通用的水化熱模型,表明混凝土的水化熱與其配合比有著直接的關系。在國內,早在20世紀50年代,朱伯芳[8]就對大體積混凝土的防裂技術開展了系統研究,推導了無熱源且初溫均勻分布的混凝土冷卻溫度場、有內部熱源的大體積混凝土水管冷卻降溫溫度場的理論計算公式,并成功用于混凝土大壩工程。圍繞建筑結構工程,王鐵夢[9]從實際工程出發,根據大量的現場試驗和工程項目,研究大體積混凝土裂縫產生的原因,提出了“放”和“抗”的混凝土設計準則,編寫的《工程結構裂縫控制》一書,對建筑結構溫度應力引起的裂縫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總結了冶金系統對工程結構溫度裂縫控制的實踐經驗,并提出了經典的“跳倉法”施工方案。近年來,隨著我國高層、超高層建筑結構的大量涌現,預拌大體積混凝土的溫度場研究進一步深入,其抗裂控制效果得到諸多工程項目的檢驗[10]。
遺憾的是,目前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施工過程中的溫度場研究大多以混凝土基礎底板為研究對象[11-13],較少關注其他大體積混凝土構件的溫度場,而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施工期間的溫度場與多種因素相關。結構混凝土的溫度變形和開裂不僅與內部水化放熱過程、外部環境溫濕度交換等有關,而且受構件的尺寸大小和邊界約束條件等因素影響顯著。因此,本文以上海市徐匯區的某具體工程項目為研究背景,針對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研究自然環境變溫條件下施工過程中的溫度場分布與演變規律。
1 工程背景
該工程位于上海市徐匯區徐家匯商圈的核心地帶,東至恭城路、南至虹橋路、西北至宜山北路、北鄰名仕苑住宅區,總用地面積為66 017 m2。軌道交通9號線區間隧道橫穿地塊北部,基地東側緊貼軌道交通11號線車站。具體的地理位置,如圖1所示。

圖1 工程項目地理位置
該項目由2幢辦公塔樓和商業裙房組成,如圖2所示。其中,T1塔樓高220 m;T2塔樓高370 m;酒店15層,高76 m;裙房7層,高56.5 m。鄰軌道交通9號線一側地下2—4層;主體建筑地下室6層。地上建筑面積為529 706 m2,地下總建筑面積為250 487 m2,項目的總建筑面積780 193 m2。T2塔樓標準層結構柱的尺寸為2 300 mm×2 300 mm,高5 000 mm。根據GB 50666—2011《混凝土結構工程施工規范》中8.7.4的第4條規定[14]:“對基礎厚度不大于1.6 m,裂縫控制技術措施完善的工程可不進行測溫”,而該結構柱的厚度大于1.6 m,因此應進行測溫。為保證工程的安全性,在現場施工澆筑混凝土模擬柱,柱體混凝土等級為C80,采用56 m的汽車泵澆搗,為一次性連續澆搗,且全部采用預拌混凝土。柱配筋84φ25 mm(每邊22φ25 mm),構造配筋為φ10 mm@200 mm。混凝土的施工配合比為145∶410∶770∶950∶80∶12.5∶80(水∶水泥∶沙∶石∶粉煤灰∶外加劑∶礦粉)。

圖2 建筑結構示意
2 監測數據
對于該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采用大體積混凝土多點遠程測量系統測溫設備進行測溫,傳感器采用進口高精度集成電路作為感溫元件。
為保證感溫器在安裝和測試過程中不出現進水損壞情況,對傳感器預先進行封裝處理。封裝好的傳感器具有抗干擾性強、精度高、離散性小和可靠性高等諸多特性。測溫系統如圖3所示。

圖3 測溫系統示意
測點的布置根據GB 50666—2011《混凝土結構工程施工規范》8.4.7中的相關條文進行。考慮到是模擬試驗,在現場監測時增加一定的測點數量。在大體積混凝土柱試件內部設置4個橫向截面測區,每個截面設3個測點,分別命名為Ai、Bi、Ci、Di(i=1,2,3,4),測點1和2的間距為575 mm,測點2和測點3的間距為505 mm。相應地,混凝土側面與模板間的測點各設1個(A4、B4、C4、D4),測點3和測點4的間距為70 mm。另外,設環境溫度測點1個。該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一共有17個測點,如圖4所示。

圖4 混凝土測溫點布置示意
該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澆搗時間為2018年9月20日16:30,測溫系統從同日14:52開始,測溫試驗歷時10 d,測得的最高溫度為87.7 ℃,最高溫升為50.4 K,測點溫度峰值出現在9月21日,即1 d之后,此后逐步下降。這一現象與預拌大體積混凝土在澆筑過程中水泥水化放熱,致使溫度升高,此后隨時間推移,水化放熱過程逐漸平緩,造成溫度隨之下降的規律基本一致。另外,測溫情況顯示:由于混凝土的澆搗時間較短,各測點的入模溫度較為接近,基本在35~38 ℃間。內部溫度的最高值則根據各個測點的位置不同略有不相同,如圖5所示。可見,在澆筑過程中,各測區中心位置(測點A1、B1、C1、D1)的溫度最高,越靠近柱的表面(測點A4、B4、C4、D4)溫度越低,且逐漸具有明顯的波動特征,表明混凝土柱外表面的溫度受外界環境溫度的影響顯著。此外,同一測區的不同測點溫差較大,如C測區的測點C1和測點C4溫度峰值差可達到40.6 K。另一方面,A測區的溫度峰值明顯小于B、C和D測區。其中,測點C1的溫度峰值最高,出現時間最晚,測點B1和測點C1其次,測點A1最低,表明A測區受柱底邊界約束條件的影響,其升溫幅度和升溫過程更為緩慢。

圖5 各測區溫度變化示意
圖6為外界環境溫度測點的溫度變化曲線示意。可見,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在澆筑和養護過程中,外界環境溫度的變化波動較為頻繁,且具有一定的幅度。其間,最高溫度為36.4 ℃,最低溫度為21.4 ℃,溫度差可達15.0 K。顯然,外界環境溫度的這種頻繁波動將影響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水化過程,對溫度場的變化造成顯著影響。

圖6 外界環境溫度測點的溫度變化曲線示意
3 數值模型
基于上述溫度場監測數據,開展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數值模擬。鑒于水化熱引起的溫度場變化是一種隨時間變化的非穩態傳熱過程,因此本文采用三維實體模型對柱的水化熱溫度場進行模擬。不失一般性,本文采用Ansys Workbench軟件建立有限元模型,模型的尺寸與現場混凝土柱的設計尺寸一致。混凝土柱的下部地基取有限厚度且與混凝土柱直接接觸。整體模型采用等參單元劃分,模型共包含節點88 580個,三維實體單元19 624個。建立的有限元數值模型如圖7所示。

圖7 混凝土柱有限元模型
3.1 熱傳導方程
由于混凝土在澆筑時,水泥水化將釋放大量的水化熱,使得混凝土的內部溫度上升,其內部形成隨齡期變化的溫度場,可將混凝土柱視為具有內部熱源的連續介質,進行瞬態溫度場分析。因此,采用具有內置熱源、均勻介質且正交各向異性的三維熱傳導微分方程進行描述:

式中:T——混凝土內部任一點在t時刻的溫度;
ki(i=x,y,z)——混凝土的導溫系數;
c——混凝土的水化熱;
ρ——混凝土的密度;
W——水泥用量;
Q——水泥隨時間變化放出的熱量。
3.2 水化熱模型
混凝土在水化過程中產生的熱量主要來自水泥的水化熱作用。水泥的水化熱是影響混凝土內部溫度場分布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計算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溫度場分布,首先要確定水泥的水化放熱規律,標定水泥水化熱模型中的關鍵參數,其取值對于保證有限元模擬結果的準確性意義重大。因此,對預拌構件混凝土用膠凝材料進行水化熱測試,開展6種水泥編號的7 d水化熱試驗。表1為這6種水泥的配合比。

表1 水化熱試驗配合比
圖8為對應的水化放熱速率曲線示意。可見,水泥的水化放熱速率曲線隨時間的推移呈現快速升高,然后快速下降的趨勢。其中,2#水泥具有最高的水化放熱速率,4#水泥具有最低的水化放熱速率。結合水化熱試驗的配合比可知:水泥的水化放熱速率與水泥用量呈正相關關系,粉煤灰和礦渣的配比變化對水泥的水化放熱速率影響較小。目前,描述水泥水化放熱速率的經驗表達式有3種,分別為:指數型、雙曲線型、復合指數型[15]。經過試算,本文基于指數型模型和水化熱測試結果標定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中的水化熱模型參數。其中,根據預拌大體積混凝土的配合比,可計算獲得水化熱模型的最大值為400 kJ/kg。
3.3 初始溫度條件
初始溫度條件為混凝土的入模溫度。在數值模擬中,若入模溫度過高,會導致混凝土峰值溫度過高,容易產生內外過大溫差;若入模溫度過低,則容易導致混凝土難以初凝。理論上,澆筑每一立方米的混凝土都存在時間差異,因此混凝土各點的溫度各不相同,但因事實上很難獲得這個溫度差異的精確測量數據或理論解析表述,故可認為混凝土整個結構的初始溫度相同,不隨空間位置變化。根據實時監測數據,該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入模溫度可設為35 ℃。
3.4 邊界條件
邊界條件影響混凝土的散熱過程,表征混凝土表面與周圍介質之間溫度相互作用的規律。通常有4類邊界條件[16],對于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存在3類不同的邊界。首先,混凝土柱的底部與地基直接接觸,接觸面上的溫度和熱流連續,因此符合第4類邊界條件,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λi(i=1,2)分別為混凝土柱和地基的導熱系數。其次,混凝土柱的頂部與空氣直接接觸,符合第3類邊界條件,其計算公式為:

Ta——外界環境溫度。
最后,混凝土柱的四周表面與空氣接觸,但有模板覆蓋,因此仍定義為第3類邊界條件,并采用等效表面散熱系數法進行計算。此時,混凝土表面的放熱系數β應考慮保溫措施的影響,其計算公式為:

另外,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底部地基為有限厚度,但為簡化計算,將地基底部和四周定義為第2類邊界條件,即絕熱狀態。
4 模擬結果
圖9為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在第1天和第2天的溫度分布云圖。可見,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中心截面的最高溫度范圍隨時間的推移逐漸縮小,且在前2 d內變化迅速。1 d之內,混凝土柱的內部溫度可從入模溫度35 ℃急劇上升至88.1 ℃,此后緩慢下降。同時,混凝土柱內部的各處溫度隨時間的推移不斷降低,而混凝土柱的表面溫度幾乎與環境溫度持平。因此,該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內部溫度在澆筑過程中變化劇烈,需要從水泥材料配比、施工方案、養護方案等方面,加強對大體積混凝土柱內部的溫度控制,避免溫度裂縫的產生。

圖9 混凝土柱溫度分布云圖
圖10顯示了各測點的現場溫度監測數據與數值模擬結果的對比情況。

圖10 測點溫度監測數據與數值模擬結果對比示意
由圖10可見,4個測區不同測點的數值模擬結果與溫度實測數據基本吻合,表明該數值模型能夠較好地反映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水化過程中的溫度場分布和隨時間變化的趨勢。其中,越靠近混凝土柱中心位置的測點,溫度實測數據與數值模擬結果越吻合;越靠近混凝土柱表面位置的測點,溫度實測數據與數值模擬結果的吻合程度越差,其原因與澆筑和養護過程中,外界環境溫度變化較為劇烈,造成邊界條件參數難以準確標定有關。
5 參數分析
由于影響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澆筑成形過程中的溫度場分布與變化的因素較多,因此依次變化不同參數,固定其他參數,開展不同因素的參數敏感性分析,獲得這些因素對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溫度場分布與變化的影響規律,對于如何加強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內部溫度控制,避免溫度裂縫產生具有重要意義。
5.1 水泥用量
水泥用量是影響混凝土的水化放熱過程,決定水化放熱量大小的最直接因素。水泥用量越多,混凝土的水化放熱量越大,內部溫度的升高變化越大。為探究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溫度場與水泥用量的關系,分別模擬當水泥用量為300、400、500 kg/m3時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溫度場分布與變化。提取混凝土柱不同時刻的最高溫度數值,具體如圖11所示。可見,當水泥用量為300 kg/m3時,混凝土柱的內部最高溫度為73.8 ℃,出現在澆筑后20 h;當水泥用量為400 kg/m3時,混凝土柱的內部最高溫度為86.87 ℃,出現在澆筑后24 h;當水泥用量為500 kg/m3時,混凝土柱內部的最高溫度為99.95 ℃,出現在澆筑后24 h。因此,水泥用量對混凝土柱水化放熱后的溫度峰值有較大影響:水泥用量越大,溫度峰值越高,但內部溫度達到峰值的時間與水泥用量呈弱相關。

圖11 不同水泥用量下混凝土柱最大溫度變化示意
5.2 入模溫度
混凝土的入模溫度是混凝土水化溫升的基礎。為了研究不同入模溫度對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溫度場的影響,分別模擬當入模溫度為15、25、35 ℃時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溫度場分布與變化。提取混凝土柱不同時刻的最高溫度,具體如圖12所示。可見,當入模溫度為15 ℃時,混凝土柱的內部最高溫度為69.55 ℃,出現在澆筑后36 h;當入模溫度為25 ℃時,混凝土柱的內部最高溫度為78.79 ℃,出現在澆筑后28 h;當入模溫度為35 ℃時,混凝土柱的內部最高溫度為88.18 ℃,出現在澆筑后24 h。因此,入模溫度對混凝土水化溫升峰值有較大影響。入模溫度越高,混凝土柱的內部溫度峰值越高,溫升的速率越快,混凝土內部達到溫度峰值的時間將提前。然而,與水泥用量的影響不同,在上述3種入模溫度下,模擬結束時混凝土柱的最大溫度基本相同。在實際施工過程中,宜將混凝土的入模溫度維持在較低溫度。

圖12 不同入模溫度下混凝土柱最大溫度變化示意
5.3 導熱系數
混凝土的導熱系數決定水化熱在混凝土中傳導的速率,從而影響混凝土的內外溫差和溫度場的分布。為了研究混凝土的導熱系數對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溫度場的影響,分別模擬當導熱系數為10、15、20 kJ/(h·m·K)時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溫度場分布與變化。提取混凝土柱不同時刻的最高溫度,具體如圖13所示。可見,當導熱系數為10 kJ/(h·m·K)時,混凝土柱的內部最高溫度為89.75 ℃,出現在澆筑后32 h;當導熱系數為15 kJ/(h·m·K)時,混凝土柱的內部最高溫度為87.8 ℃,出現在澆筑后20 h;當導熱系數為20 kJ/(h·m·K)時,混凝土柱的內部最高溫度為86.39 ℃,出現在澆筑后20 h。因此,混凝土的導熱系數對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溫度峰值和核心區的降溫速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導熱系數越大,溫度峰值越低,且降溫速率越快。

圖13 不同導熱系數下混凝土柱最大溫度變化示意
5.4 邊界條件
邊界條件決定混凝土與外界熱量交換的程度。由于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頂部和底部分別與空氣和地基接觸,邊界條件不易發生改變,而柱四周表面與模板接觸,通過改變模板的材料和厚度可改變混凝土柱與外界空氣的對流系數。因此,為了研究不同邊界條件對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溫度場的影響,分別模擬當混凝土柱四周的對流系數為200、1 000、2 000 kJ/(m2·d·K)時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溫度場分布與變化。提取混凝土柱不同時刻的最高溫度,具體如圖14所示。可見,當對流系數為200 kJ/(m2·d·K)時,混凝土柱最高溫度為90.57 ℃,出現在澆筑后44 h;當對流系數為1 000 kJ/(m2·d·K)時,混凝土柱最高溫度為87.45 ℃,出現在澆筑后24 h;當對流系數為2 000 kJ/(m2·d·K)時,混凝土柱最高溫度為86.45 ℃,出現在澆筑后20 h。3種工況下,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核心區的溫度上升速率基本一致,但對流系數越小,溫度峰值越高,且出現溫度峰值的時間越晚;在溫度下降部分,3種工況的差異明顯:對流系數越小,溫度下降越慢。

圖14 不同對流系數下混凝土柱最高溫度變化示意
6 結語
1)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由于澆搗時間較短,各測點的入模溫度較為接近,基本在35~38 ℃之間。此后,隨著水泥水化放熱,混凝土柱內部溫度逐漸升高,最高可達87.7 ℃,溫度峰值出現在1 d之后。其后,隨著時間的推移,混凝土柱的內部溫度逐漸平緩。
2)施工過程中,外界環境溫度具有明顯的波動變化特征。這種波動變化將影響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水化過程和溫度場分布,尤其影響混凝土柱外表面的溫度場變化。
3)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溫度場分布與變化,受邊界約束條件的影響顯著。越靠近混凝土柱底位置,升溫幅度越低,且升溫過程更加緩慢。
4)通過設置合理的初始溫度條件、標定水化熱模型參數和設定邊界約束條件,可采用三維實體模型對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水化熱溫度場進行數值模擬,計算結果與溫度實測數據基本吻合。
5)影響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澆筑成形過程中的溫度場分布與變化的因素較多。其中,入模溫度對升溫過程影響顯著,混凝土導熱系數與柱四周的對流系數對降溫過程影響顯著,水泥用量不僅對升溫過程影響顯著,而且對降溫過程影響顯著。
綜上,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溫度場在施工過程中的變化較為劇烈。因此,不僅需要從混凝土材料配合比的角度進行合理設計,而且需要考慮外界環境溫度變化和邊界約束條件,開展合適的施工方案和養護措施,以加強預拌大體積混凝土柱的內部溫度控制,避免溫度裂縫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