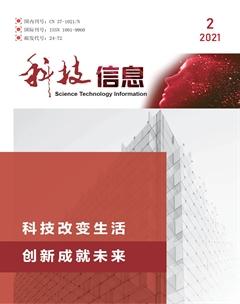如何實現破產重整企業信用修復
趙靜璞
摘要:探討已經破產企業信用修復的系列問題,首先介紹了信用修復對于破產企業而言的必要性,其次介紹信用修復需要關注的內容,從發揮立法的指導性作用、建立健全府院聯動機制兩方面提出建議,幫助企業完成信用修復。
關鍵詞:破產重整;企業;信用修復;市場經濟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經濟狀況瞬息萬變,由于擔保圈、資金鏈等問題引起的區域性金融風波時有發生,企業面臨的風險指數逐年攀升。破產重整制度因其獨特的風險處置化手段在出清僵尸企業、優化營商環境方面不斷發揮著重要作用。下文圍繞實現破產重整企業信用修復這一話題展開論述。
一、破產重整企業信用修復必要性
現如今,很多金融機構,在對企業發放融資資金前,都需要對企業的信用情況進行審查及評價,最終根據評價結果來決定是否對該企業發放貸款[1]。但大多數破產企業在破產重整前,都會在人民銀行的征信系統中留有一定的不良信用記錄,這也就導致破產企業雖然已經實現了破產重整,但卻無法在金融機構或者商業銀行中獲取更多的融資貸款,保障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在這一條件下進行企業信用修復,可以及時避免以上問題,重塑企業信用。
二、破產重整企業信用修復內容
(一)失信銀行征信系統記錄
銀行征信信息主要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和各類別商業銀行對企業信貸業務、資產抵押、金融資信等級及其他獎懲記錄等[2]。為降低財務風險,進一步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對于與其存在信貸關系的企業,中國人民銀行都建立相關的征信檔案并記錄進入征信系統。逾期還款甚至到期不予還款的現象在破產企業進入破產重整程序之前大量存在。因此,破產重整企業可能會在銀行的征信系統內留下不良記錄,這些不良信息如若延續到破產重整企業重整成功后,就會給破產重整企業進行繼續經營或者重新融資帶來困難。
(二)負面稅收部門記錄
稅務部門信用信息主要是有關公司稅收的收集和管理,審計信息以及其他薪酬和罰款記錄的信息。實際上,如果在破產重整企業的重組之后引入了新的公司投資者,則將需要向稅務機關更改注冊證書的法定代表人。當破產重整企業被列為異常納稅人的范圍,其原始法定代表人也將被列入黑名單,稅務部門將不會據此更改法定代表人。這無疑會給破產重整企業尋找投資人帶來巨大困難,也會給投資人帶來經濟損失。
(三)不良工商系統記錄
我國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設立有“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該系統對于破產重整企業原有行政處罰和股權變更信息進行了詳細記錄,但是因破產重整導致股權變更并不會進行區分,對該不良記錄,破產重整企業進行重整后并不能進行申請刪除。工商系統不良的記錄意味著就算破產重整企業重整成功后,仍然會被原來破產企業的不良記錄所拖累,導致其喪失在經營環境下處于不具競爭的地位。
三、破產重整企業信用修復的建議
(一)發揮立法的指導性作用
目前,由于無統一規定指導,各地相關規定交叉復雜,信用修復領域的探索長期處于無序狀態,因此,加快建立統一的立法體系才是解決信用修復問題的最根本途徑。在立法過程中,可將國外立法與國內探索相結合,基于我國國內現狀,從企業信用缺陷所涉及的直接問題出發,建立相對完善的信用修復體系。
立法過程中,如整體企業信用修復法律推進存在較大阻力,可以基于破產重整程序出發進行探索與突破,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對此問題予以明確。由于重整企業的特殊性,重整后的企業在內部架構、股權變更等實質方面基本與新生企業無異,因此,在立法過程中,可以將企業進入破產重整程序作為前提性條件,對修復發起主體、修復涵蓋內容、修復程序、修復限制等方面進行規定,規范破產重整企業信用修復的具體操作。
信用修復并不是無限制地修復,實質應當為在限制范圍內的修復。企業選擇進入重整程序,在獲得“殼”所帶來的便利資源同時必然需要承受“殼”所帶來的部分不利因素,因此,針對附隨的信用缺陷修復也必然需要給予限制。在對限制范圍的立法規定中可以采用列舉式的模式,列明不予修復的類型,對于類型之外的情況持開放態度,此立法模式能夠適應我國信用修復體系不完善、實務操作問題眾多的立法現狀,給予信用修復領域更多活力。其中,不予修復的類型可基于“主觀惡意+客觀行為”的原則把握,對于存在嚴重違法且造成惡劣影響的行為所導致的信用缺陷,應當給予限制修復。
(二)建立健全府院聯動機制
前文提及,破產重整企業信用缺陷往往涉及多領域,除常見的銀行、工商、稅務、司法等方面外,部分專門企業還涉及其他方面的信用缺陷。但是由于這些缺陷信息都分散于各個機構和部門,在修復過程中往往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嘉興市處理此問題時的方式是:成立企業破產重組盤活工作協調小組,小組成員主要由法院、人民銀行、財政、工商等相關部門組成,定期召開協調會,協調解決相關困難。
例如一些地區采取府院聯動機制的具象化,近年來,府院聯動機制日益成為處理破產案件最高效的方式之一,在實踐中的應用程度非常廣泛。但是,現階段的府院聯動的操作模式雖然具有一定的能動性,但是在體系性方面不占優勢,每一個案都需要進行單獨探索,而無法充分吸收前期工作的經驗。結合現有企業信用修復的經驗,現行保障機制中規定了建立組織協調機制、建立組織協調機制、建立信息共享機制等保障性措施,綜合對召集人、辦公室駐地、會議召開方式、信息共享模式等具體操作問題進行了明確。該文件將“府院聯動機制”從抽象化的概念以具體的形式落地,并且提供了可行的具體操作模式,使“府院聯動機制”不再處于空中樓閣的抽象,真正能夠解決企業破產處置中的相關具體疑難問題。重整企業也能夠依托此文件,通過此機制最大限度進行信用修復,真正意義實現企業再生。
結束語:
綜上所述,由于我國在此領域的相關法律規范尚不完善,破產重整企業信用修復面臨諸多問題。從企業破產法的立法目的來看,破產重整實現債權債務的集中清理,各類債權在破產程序內得到公平清償。因此,破產重整企業的信用修復是其重生的關鍵一環,今后實踐中需要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促使破產企業可以快速重塑信用。
參考文獻:
[1]姜鑠.論我國企業破產重整之信用修復——基于比較與功能的視角[J].上海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1,19(03):57-63.
[2]劉敏,王冬冬,王東豫,趙程.破產重整企業金融信用修復問題研究[J].金融發展研究,2020(10):8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