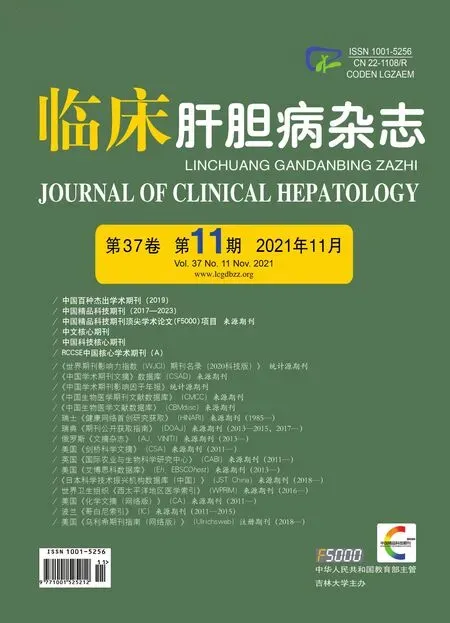藥物性肝衰竭的臨床特點及診治策略
賴榮陶,謝 青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 感染科,上海 200025
藥物性肝損傷(DILI)和藥物性肝衰竭的發生率逐年上升[1],越來越受到臨床醫師、監管部門和制藥企業的重視。由于可導致嚴重不良反應,DILI是藥物上市后再撤市的主要原因,給患者帶來巨大傷害的同時也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DILI是西方國家急性肝衰竭(ALF)的最常見原因,對乙酰氨基酚(APAP)相關的ALF疾病進展迅速,針對APAP過量所致ALF,多個國家已提議更改藥物產品標簽,有限地配制含APAP的麻醉性鎮痛劑,以降低這種可預測的、劑量依賴的肝損傷和肝衰竭風險。APAP相關的ALF與特異質性DILI(iDILI)相關的ALF相比,自發存活概率較高。由于目前缺乏對宿主易感性和發病機制的深入了解,iDILI往往不可預測,由iDILI誘發的ALF患者初期難以確診,自發恢復可能性極低,預后更為兇險,因此也成為多個國家緊急肝移植的主要適應證。鑒于處方藥和非處方藥的廣泛使用,DILI已成為全球主要的健康問題之一,DILI相關的ALF真實發生率在全球被嚴重低估。迫切需要全面認識藥物性肝衰竭的臨床特征,尋求新的可靠診斷方法和有效的治療策略。
1 藥物性肝衰竭的全球流行病學數據
根據美國急性肝衰竭研究小組(ALFSG)數據,APAP過量和iDILI是導致ALF最主要的兩個原因,占所有ALF病例的50%以上,其中iDILI相關ALF占ALF病例的11%左右[2]。在英國,APAP是導致ALF的主要原因,占57%左右[3]。我國一項大規模回顧性研究[4]顯示,在25 927例DILI患者中,280例(1.08%)進展為肝衰竭。西班牙的一項多中心回顧性研究發現17.2 %的ALF病例與非APAP的藥物特異質性有關;法國一項基于人群的大型研究數據顯示補充劑和替代藥物(CAM)所致ALF病例占21.1%[5-6]。藥物性ALF約占兒童ALF的20%,兒童藥物性ALF的最常見原因仍是APAP(占英、美兩國兒童ALF的15%),而其他藥物如抗結核藥和抗癲癇藥占ALF的5%左右。兒童DILI的發病機制同樣包括藥物的直接肝毒性和特異質性反應[7]。
2 藥物性急性肝衰竭(DIALF)的定義及臨床特征
ALF是以突然發生的凝血功能障礙和肝細胞損傷為表現的臨床綜合征,其特點是既往沒有潛在慢性肝病的個體中肝功能迅速惡化,發生肝性腦病(HE),并伴隨其他器官功能障礙。僅出現凝血功能障礙或黃疸,但沒有意識改變的患者則定義為急性肝損傷。重度急性肝損傷以肝損傷標志物(血清轉氨酶升高)和肝功能受損(黃疸和INR>1.5)為特點,常先于HE發生。HE的臨床表現對于ALF的診斷至關重要,但精神改變最初可能很微弱,臨床不易察覺,因此在出現HE的第一個跡象時必須強化篩查。對于重度急性肝損傷患者,應密切篩查HE的任何可能體征。
ALF最初由Trey和Davidson[8]在1970年定義為暴發性肝衰竭,是指一種潛在的嚴重肝損傷,在預先沒有肝臟疾病的患者中出現首發癥狀,8周內出現HE。1993年,該綜合征被重新定義,患者在出現黃疸后7 d內發生HE稱為超急性肝衰竭。患者在出現黃疸后8~28 d出現HE稱為ALF;出現黃疸5~12周內發生HE稱為亞急性肝衰竭。HE發作前的病程超過28周被歸類為慢性肝衰竭。國際肝臟學會小組將超急性肝衰竭定義為<10 d,將暴發性ALF定義為10~30 d,將亞急性肝衰竭定義為5~24周[9]。
2.1 APAP所致急性和超急性肝衰竭 服用過量APAP的患者可發生意外的DIALF,當營養狀況不佳,谷胱甘肽儲備減少或過量飲酒誘導細胞色素P450時,對APAP敏感性增加。其特征是血清轉氨酶的極端升高(>10 000 IU/L)和膽紅素水平正常。代謝性酸中毒、血清乳酸升高、低血糖和急性腎損傷可能發生在臨床演變的早期階段。服用過量APAP的患者早期表現可能與代謝性酸中毒和乳酸升高有關,但轉氨酶水平僅輕度升高,且凝血功能障礙也很輕微。這種臨床綜合征被認為是一種直接的藥物作用,與功能性線粒體損傷有關,并隨著APAP水平的下降而消退。這些患者應適當補充循環血容量和N-乙酰半胱氨酸(NAC)治療,必要時需要腎臟替代療法治療酸中毒。如患者進展為快速的多器官功能衰竭 和HE,可能會在數小時內從輕度1級昏迷發展到4級昏迷。有研究[10]發現,不符合急診肝移植標準的患者預后良好,符合肝移植標準的患者在優質的重癥監護輔助下存活率為20%~40%。
APAP所致的超急性肝衰竭多表現為嚴重的凝血功能障礙,血清轉氨酶顯著升高,伴隨早期膽紅素正常或僅中度升高。盡管有明顯的肝外器官衰竭,但超急性肝衰竭患者仍有機會自發恢復[11]。
2.2 非APAP所致ALF iDILI相關的ALF(iDIALF)臨床特征不同于APAP相關的ALF。iDIALF發展更慢,可持續數天至數周,更常見的是輕度轉氨酶升高和更明顯的黃疸。保健品(HP)、膳食補充劑(DS)、傳統中藥(TCM)、天然藥(NM)及其代謝產物及輔料(TCM-NM-HP-DS)或稱為HDS(以下均簡稱HDS)導致的iDILI相關ALF患者從出現黃疸到HE的時間間隔會更長[12]。不到10%的iDILI患者會進展為ALF,但一旦進展為ALF,超過80%的患者會死亡或需要緊急肝移植[13]。iDIALF在老年患者中更常見,尤其是>60歲的老年患者[2]。肝細胞損傷型DILI患者通常表現為ALF的臨床病程,而膽汁淤積性DILI更可能導致亞急性病程。亞急性肝衰竭通常會出現血清轉氨酶輕度升高、黃疸加深和輕中度的凝血功能障礙[14],通常有脾腫大、腹水和肝體積縮小,一旦發生HE,這些患者自發存活的機會非常低。
違禁藥物也是導致ALF的原因之一,以年輕人居多。導致ALF的違禁藥物包括可卡因、安非他明類衍生物(搖頭丸)和苯環利定。可卡因誘導的肝毒性通常表現為急性肝細胞損傷,類似于APAP誘導的肝毒性或缺血性肝炎。由于細胞色素P450同工酶對可卡因代謝產物的直接肝毒性或與多器官衰竭或過高體溫引起的肝缺血損傷,導致小葉中心壞死和脂肪變性。約50%的患者可自然恢復。搖頭丸和苯環利定引起的ALF,除ALF本身的臨床表現外,還經常表現為體溫過高、低血壓、橫紋肌溶解、腎衰竭和彌散性血管內凝血[15],臨床醫師在門急診接診該類患者時要注意甄別可能的違禁藥物服用史。
伴嗜酸性粒細胞增多和系統癥狀藥疹綜合征(DRESS)是一種非常罕見的藥物超敏表現,表現為發熱、嗜酸性粒細胞增多、明顯皮疹和淋巴結腫大。含硫化物、部分抗驚厥藥和抗微生物藥常與 DRESS 有關。在DRESS患者發生ALF前,應考慮大劑量類固醇治療。與ALF相關的藥物尚有抗結核藥(尤其是異煙肼)、抗生素(尤其是呋喃妥因和酮康唑)、抗癲癇藥(尤其是苯妥英和丙戊酸鹽)、非甾體類抗炎藥和丙基硫氧嘧啶和雙硫侖[2]。一些患者不會主訴攝入藥物史,特別是違禁藥物、中草藥或營養保健品等。中草藥或營養保健品在亞太地區運用尤為普遍[16]。臨床醫師應仔細詢問服藥史,尤其是過去6個月內服用的所有藥物(處方藥和非處方藥)、HDS的情況以全面排除導致ALF的藥物可能。
3 藥物性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的定義及臨床特征
ACLF的定義于2009年由亞太肝病學會(APASL)首次提出,并于2014年和2019年再次更新[17],APASL對ACLF的定義是在慢性肝臟疾病的基礎上,出現急性肝損傷表現,黃疸(TBil>5 mg/dL)和凝血功能異常(INR>1.5),4周內出現腹水和/或HE[18]。既往肝病基礎上的DILI定義為氨基轉移酶水平升高≥基線水平2~3倍或膽紅素水平>基線水平2倍。藥物暴露與ACLF(TBil>5 mg/dL和INR>1.5 以及腹水和/或HE)的近期發展存在很強的時間相關性則定義為藥物相關的ACLF[19]。需說明的是,如何更加全面定義ACLF,全球學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甚至提出多達13種相關理論來描述該綜合征[20]。
在已存在肝功能異常或有慢性肝病的患者中,服用藥物更易發生DILI,例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或酒精性肝病患者使用APAP(即使在治療劑量下)后肝毒性風險增加[21]。APASL對ACLF的研究[18]發現,藥物是導致ACLF發生的最常見原因。2019年,由29個國家組成的APASL ACLF 研究聯盟在3132例ACLF患者前瞻性隊列研究[19]中發現,329例ACLF(10.5%)與藥物有關,HDS(71.7%)是最常見的可疑藥物,其次是抗結核藥(27.3%)。在亞洲ACLF患者中,藥物所致的ACLF 90 d總病死率(46.5%)高于非藥物誘導的ACLF(38.8%)。TBil、INR、乳酸水平、HE及MELD 評分是慢性肝病基礎上發生藥物相關ACLF死亡的可靠預測指標。
4 藥物性肝衰竭的診斷
目前缺乏藥物誘導肝衰竭特異診斷標志物,診斷仍然基于藥物暴露與臨床表現之間的時間關聯、肝損傷模式與相關藥物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其他原因的排除。Roussel Uclaf 因果關系評估(RUCAM)量表是DILI因果關系評估中廣泛使用的工具,能夠對肝損傷的臨床、生化、血清學和放射影像學特征進行評分,并給出反映相關藥物可能性的總體評分來判斷DILI的風險大小[22]。補充和替代藥物包括中草藥和保健品在內的藥物在許多東方國家用于治療各種疾病,包括中國、韓國、新加坡和印度等。這些藥物的使用與肝損傷的因果關系評估存在困難,特別是當患者服用多種成分的產品時,診斷更具挑戰。
肝活檢不是診斷藥物誘導肝衰竭的必要檢查,如果有強烈的臨床因果關系可確定肝衰竭的患者不需要常規進行肝活檢。但是,如果懷疑自身免疫性肝炎、惡性腫瘤浸潤或其他潛在的慢性肝病,在肝衰竭情況下,經臨床醫生充分評估肝穿刺的風險和獲益后決定是否行經頸靜脈肝活檢。組織學上的肝損傷模式結合臨床信息可能有助于識別病因。在iDILI相關的ALF中,某些組織學特征有助于判斷預后。例如,廣泛的肝細胞壞死、膽管反應、纖維化、微泡性脂肪變性、膽管膽汁淤積和門靜脈病變已被證實與DILI發病6個月內的ALF、死亡或肝移植相關[23]。
5 藥物性肝衰竭的治療
NAC已被證明在成人可安全、有效地治療APAP相關ALF,即使在攝入APAP后超過48 h或更長時間給藥。NAC通過補給谷胱甘肽、增加攜氧含量和抑制炎性細胞因子的產生而發揮作用[24]。然而,NAC在非APAP相關ALF中的獲益仍存在爭議。一項前瞻性研究[25]顯示,在iDILI相關的ALF患者亞組中,使用NAC后病死率降低至28%,而對照組病死率為53%;但另一項前瞻性試驗薈萃分析[26]顯示非APAP相關ALF患者接受NAC治療并未提高總生存率。由于NAC有較為明確的作用機制和安全性,臨床上可考慮用于iDILI相關的ALF,但可能無法提高總生存率。皮質類固醇激素是否能治療DILI也一直備受爭議,目前無臨床研究證實皮質類固醇激素對iDILI相關ALF有益。ALFSG登記的一項隨機、雙盲臨床研究[27]顯示,皮質類固醇并未改善DIALF患者的總體生存率和自發生存率。因此,不建議在iDILI相關ALF患者中使用皮質類固醇激素。
肝移植可使ALF病死率明顯下降。盡管如此,有些患者在肝移植后仍有早期死亡或發生移植排斥反應的風險,尤其在移植后第1年。對器官共享聯合網絡數據庫1987年—2006年的數據分析[28]表明,接受肝移植的DIALF患者中,APAP、抗結核藥物、抗癲癇藥、抗生素和其他藥物的1年預估生存率分別為76%、82%、52%、82%和79%,成人和兒童存活率相似;抗癲癇藥引起ALF患兒移植后病死率顯著升高,可能與丙戊酸誘導高氨血癥導致更嚴重的HE有關;抗癲癇藥物所致ALF、需要高級別生命支持和血肌酐升高是移植前預測肝移植后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親體肝移植可減少ALF患者肝源等待時間,且結果相似[29]。
6 藥物性肝衰竭的預后和臨床預測模型
APAP相關ALF的臨床病程可在72 h內自發恢復,或迅速演變為多器官衰竭和死亡[12]。而iDILI相關的ALF進展相對緩慢,但預后更差。由于特異質性藥物反應導致ALF患者的自發生存率低,不進行肝移植的病死率為60%~80%。因此,iDILI相關的ALF患者比APAP相關ALF患者更可能得到肝移植機會。血清IL-17水平與HE嚴重程度相關,是非APAP相關ALF患者死亡或肝移植的獨立預測因子[1]。筆者團隊在2015年的DILI臨床隊列[30]中發現,IL-22與DILI患者轉歸明顯相關,IL-22持續低水平表達的患者可導致病程遷延,甚至重癥。
目前已開發多種預后評分系統來確定緊急肝移植的必要性。MELD評分是一種替代的預后評分系統,其在預測非APAP ALF患者的病死率方面優于英國國王學院醫院標準(KCC)評分,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76%和73%[31];美國ALFSG也開發了相關的預后評分系統,通過結合HE程度、ALF病因、血管加壓素的使用、血清膽紅素和INR多個臨床變量來預測21 d的無移植存活率。ALFSG評分系統的受試者曲線下面積為 0.843,MELD評分0.717,KCC標準為 0.560~0.655,ALFSG預測能力似優于MELD評分和KCC標準[32]。西班牙DILI注冊登記系統數據顯示,AST>17.3×ULN、TBil>6.6×ULN和AST/ALT>1.5能更精確地預測藥物相關ALF的發生(特異度為82%,敏感度為80%)[33]。
與西方國家主要由APAP導致ALF不同,來自亞太地區的數據和我國的DILI流行病學調查顯示,iDILI是亞太地區ALF的主要原因之一。iDILI不可預測,缺乏可供研究的動物模型,加之用藥成分復雜,臨床發現和診斷極為困難,使得iDILI相關的ALF發生率被嚴重低估。2021年7月我國已啟動一項DILI真實世界研究,將有助于深入了解藥物性肝衰竭的真實發病率,同時加強對藥物代謝、肝臟再生和宿主特異質性的深入研究,將有助于了解藥物相關的肝衰竭發病機制,為藥物性肝衰竭提供新的診斷思路和治療策略,提高臨床救治率。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賴榮陶負責起草全文;謝青負責修改文章關鍵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