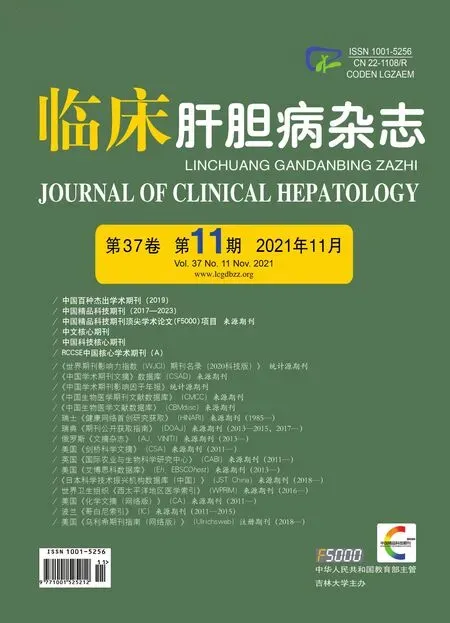繼發性血色病合并亞急性肝衰竭1例報告
楊三三,陳安海
遵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消化內科,貴州 遵義 563000
1 病例資料
患者男性,56歲,因“間斷上腹痛2個月余,加重伴乏力、納差6 d”于2019年11月28日入本院住院治療。2個月余前無明顯誘因出現上腹痛,伴發熱,最高體溫達41 ℃,腹瀉、嘔吐,嘔吐物為胃內容物,經治療后好轉。10余天前大量飲酒后再發腹痛,性質同前,治療后好轉。6 d前無明顯誘因再次出現上腹痛伴乏力、納差,困倦、惡心、欲吐、厭油、鞏膜黃染、尿黃,自行服用少許“筋骨草”粉末無好轉,遂就診于本院門診,查肝功能明顯異常,故收住院。病來未解白陶土樣大便,無消瘦。既往史及個人史:曾在廣西務工,其附近種植大片桉樹,周圍水質呈黑色,平素飲用該水泡茶;既往無肝炎病史,否認貧血及鐵劑服用史; 有飲酒史,約200 g/d,30余年,未戒;其父因不明原因“肝癌”去世。查體:肝病面容, 全身皮膚、鞏膜黃染,未見明顯皮膚色素沉著,無肝掌、蜘蛛痣等, 腹平軟, 臍周壓痛,以劍突下明顯,肝大,可于劍突下5 cm處觸及,質軟,緣鈍,表面尚光滑,無觸痛,脾肋下未觸及,移動性濁音陰性,雙下肢不腫。肝功能:ALT 1200 U/L, AST 843 U/L, GGT 280 U/L, ALP 270 U/L,TBil 288 mmol/L;凝血功能:PT 15.4 s,PTA 69.6%,APTT 39.3 s;血清鐵蛋白 614.8 mg/L;AFP:115.87 ng/ml;血常規:WBC 4.89×109/L, RBC 4.66×1012/L, Hb 136.0 g/L,PLT 109×109/L;CK-MB 36 U/L;甘油三酯1.74 mmol/L;隨機血糖7.67 mmol/L;尿常規:尿膽紅素++,銅藍蛋白21.40 mg/dl;甲、乙、丙、戊型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相關抗體,EB病毒,巨細胞病毒、風疹病毒,單純皰疹病毒,艾滋病,梅毒病毒血清標志物均陰性。心電圖: 正常;心臟彩超示:(靜息狀態下)主動脈瓣輕度反流、左室舒張功能減低;MRI上腹部平掃+增強+MRCP示:肝左葉小囊腫;全腹部CT示:肝實質密度減低,考慮脂肪肝或肝實質水腫,少量盆腔積液。診療經過:動態監測肝功能、凝血功能,PTA降至46.8%,立即予嚴格戒酒、保肝降酶、退黃、輸血漿等治療后復查各項指標,凝血功能好轉,肝功能各項酶學指標明顯下降,但TBil呈進行性升高,出現“膽酶分離”現象,提示病情進展,但黃疸原因待明確,故予完善MRI上腹部平掃+增強+MRCP了解肝臟性質及是否存在占位、結石等,結果陰性。為明確病因,遂行代謝性疾病相關檢查,查血清鐵蛋白614.8 mg/L、鐵蛋白飽和度 95.7%,初步考慮血色病可能。靜脈放血和螯合劑治療是治療血色病的常用方法,反復放血排鐵是此病最有效、最經濟的治療方法[1],經患者及家屬同意后,于2019年12月3日行第1次血漿置換+雙重血漿分子吸附系統(DPMAS),術后復查TBil明顯下降;于2019年12月6日行第2次血漿置換+DPMAS,患者自覺癥狀及抽血結果均提示病情有所好轉。針對鐵過載,本擬行尿鐵檢測及肝組織活檢尋找病因,但本院條件有限,故未能完善。治療上連續予甲磺酸去鐵胺治療5天,復查鐵代謝相關指標明顯好轉。另外,考慮到其父因不明原因“肝癌”去世,需高度警惕遺傳因素,建議患者行血色病基因檢測,除外原發性血色病可能,征其同意后外送患者及其子女全血標本檢測。2020年1月14日結果回報:未見HFE、HJV、SLC40A1、TFR2及HAMP基因突變。綜上考慮,明確診斷:繼發性血色病;囑患者徹底戒酒,嚴格限制含鐵飲食攝入,繼續保肝,門診隨診。2020年4月30日患者返院復查AFP、肝功能、鐵代謝指標均恢復正常。
2 討論
遺傳性血色病(hereditary hemochromatosis,HH)是鐵代謝異常而引起鐵負荷過多沉積于心、肝、腎等實質性器官的一種常染色體遺傳性疾病,常出現肝硬化、肝癌、糖尿病、心力衰竭、垂體及性腺功能減退、關節疾病和皮膚色素沉著等[2],可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該病起病隱匿,臨床癥狀不典型,其發病遍及全球,但在我國較少見,且多為散發病例,故易被誤診或漏診。
本例患者以不明原因上腹部痛伴乏力、納差為主訴入院,起病急且重,黃疸進行性加深,凝血功能差,病情迅速向肝衰竭進展,藥物療效欠佳。根據美國肝病學會血色病診治指南要點[3],并結合該病例特點,診斷繼發性血色病成立。但由于其病因多樣,尚未能完全明確。首先,針對肝損傷,患者有服用筋骨草病史,故不能完全除外藥物造成或加重了肝損傷,但筋骨草有保肝作用[4],服用量少,故不作為首要考慮;其次,患者病前工作地水源區域種植大量桉樹。據研究[5-6],桉葉中含有多種人體必須微量元素,其中Fe、Ca、Mn含量較高,可與大量黃酮類化合物形成絡合物,故其水提物易為人體及動物吸收利用。桉樹根據樹種、所吸收營養成分的不同,其所含微量元素的含量會出現差異。該片區水質呈黑色與桉樹是否存在一定的相關性有待研究,故不能完全除外是否存在桉樹相關因素致繼發性血色病可能。本擬篩查與患者共事人員的鐵代謝指標是否異常,但因實施難度大,未予落實。此外,該患者既往有長期大量飲酒史,此次發病前也有飲酒史,故酒精也可能是其發病原因。
根據《肝衰竭診治指南(2018年版)》[7],肝衰竭可分為急性肝衰竭(2周內)、亞急性肝衰竭(2周~26周)、慢加急性(亞急性)肝衰竭(存在慢性肝病基礎)、慢性肝衰竭(存在肝硬化基礎)4類;再根據臨床表現的嚴重程度,將亞急性和慢加急性(亞急性)肝衰竭分為早、中、晚期,未達上述分期標準前稱為肝衰竭前期。故該病例符合亞急性肝衰竭前期向早期發展的表現。
亞急性肝衰竭發展迅速,難治療,預后差,病死率高[8],是多種因素引起的嚴重肝損傷,導致其合成、解毒、排泄和生物轉化等功能發生障礙,可出現膽紅素代謝異常,大量蓄積體內而產生重度黃疸。當內科綜合治療無法清除人體內已堆積的有害物質時,可進一步行人工肝血漿置換法治療,該方法為非生物型人工肝(non-bioartificial liver,NBAL)的一種,可分離肝衰竭患者體內的毒素及肝毒性物質,并將無害成分及正常新鮮血漿重新輸入人體,改善肝功能,同時改善凝血功能[9],這是目前治療肝衰竭的有效方法之一。目前臨床上應用的NBAL類型多樣,常用的治療模式包括血漿置換、DPMAS、血液灌流等,另外,血漿置換聯合DPMAS等不同類型NBAL組合也應用于臨床,其原理特點及適應證各有不同,需結合肝衰竭患者不同的臨床表現,選用恰當的人工肝治療模式,制訂個體化的治療方案。血漿置換+DPMAS療法可有效降低血清膽紅素水平,提高早期肝衰竭治療的有效率[10],該病例也證實了這一點。
血色病在亞太地區發病率低,盡管沒有典型的血色病體征及影像學表現,但當出現不明原因肝損傷,甚至達到肝衰竭時,應發散臨床思維,考慮到不常見的代謝性疾病,甚至可將相關指標作為常規檢查項,做到早診斷、早治療,當藥物療效不佳時,應根據患者具體情況及時采取有效的人工肝血漿置換治療,可顯著改善患者癥狀,甚至完全恢復正常。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楊三三負責收集臨床數據及論文撰寫;陳安海負責指導撰寫文章,修改文章以及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