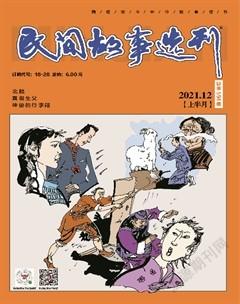一支竹笛
故事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在江南某縣有一所藝校,說是藝校,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以培訓各類樂器為主的輔導班。班上有二十來個學生,有學二胡的,有學琵琶、古箏的,也有學吹奏樂器的。其中,有兩名學生,一個叫張強生,一個叫李才能,兩個人學的都是笛子。
這兩個孩子都來自農村,學習非常刻苦,每天勤學苦練,進步很快,一首名曲,別人要學上一個星期才有點像樣,而到他們手中,一兩天下來,不但能完整地吹奏出來,且細節處理也十分到位。所以,輔導老師都很看好他們,說這兩個孩子很有天賦,只要假以時日,必將前途無量,今后也許成為像馮子存、陸春齡這樣的笛子大師也不是沒有可能。
這天,藝校來了幾位省藝術團的老師,說團里現在正缺少一位笛子吹奏員,聽說這里有兩個好苗子,就專程過來看看,要是真的不錯,那他們就會錄用其中的一位。
當天下午,一場專門的測試就在學校的教室里舉行。幾位老師先讓張強生和李才能分別作了簡短的自我介紹,然后又反反復復地對兩人的手掌、手指進行了仔細的查看,才拿出兩個曲譜,要他們當場讀譜。不大一會兒,這幾個環節兩個人都順利地完成了下來。省城的幾位老師相互交流了一下,都露出了贊許的神態。接下來,就進入了最重要的測試——現場吹奏。
根據要求,兩個人都要分別吹奏一首自選曲目和一首指定曲目。首先上場的是李才能,他順利地完成了指定曲目,然后開始吹奏他的拿手曲目《姑蘇行》。只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稍稍屏氣凝神,輕輕地吹奏了起來,他的幾個手指在竹笛上輕盈地跳動,一首優美的旋律隨之在空中飛蕩起來,那曲調時而高亢、時而低回,時而悠揚、時而激昂,讓人聽得如癡如醉。一曲終了,那些前來測試的老師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
輪到張強生上場,本來兩個人的水平一直不相上下難分伯仲,但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張強生一吹那首指定曲目,就感覺很不對勁,一到小拇指按著的那個尾孔的音飄出來,總感覺明顯地走了調。等到他吹奏自選曲目《揚鞭催馬運糧忙》時,這一現象更加嚴重。這首曲目,張強生可是拿過全省比賽的大獎的,可不知怎么回事,在今天這節骨眼兒上卻如此地不給力。雖然輔導老師也感到不可思議,但現實就是這樣。最后,張強生自然而然地落選了,李才能最終成了省藝術團的一員。
后來,不斷聽到李才能在笛子界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后成了讓人敬仰的笛子演奏家。
而張強生呢,隨著藝校輔導班結業,他就回到了家鄉。在這期間,他幾次想把那不爭氣的笛子給劈了,但最后還是決定要永遠地留著它,他要用這失敗的一幕,成為激勵自己的動力,所以他用一條紅綢系在那笛子上,將其掛在自家最醒目的地方,以此來時時鞭策自己。
也許張強生命中與笛子有緣,最后他沒能成為一個專業的笛子演奏家,卻陰差陽錯成了一個著名的生產笛子的企業家。
他的家在一個叫銅嶺橋的小山村里,當地盛產一種竹子名為苦竹,據說當地的地下蘊藏著豐富的銅礦石,那竹子在生長過程中充分吸收了豐富的金屬元素,所以硬度高密度大,加上這竹子大小適中節疏枝直,是制作笛子的優質材料。很久以前,這里就有人開始制作竹笛,據傳,用銅嶺橋的苦竹制作的竹笛,早在明清時期,就曾作為貢品被送進了宮里。但是,由于處于窮鄉僻壤交通不便之地,制作笛子的產業一直不成氣候。當張強生回到家鄉后,交通早已大為改善,不久又逢改革開放,國家鼓勵多種經營,于是,他就萌生了制作笛子的想法。為此,他到處尋訪制笛藝人,苦心拜師學藝,終于學到了一手制作竹笛的好手藝,然后,他就招來三五鄉親,辦起了加工竹笛的工坊。
四十多年過去了,張強生從一個毛頭小伙,成了一位年逾花甲的老漢,他的小工坊也早已成為擁有200來名工人的規模企業。幾十年來,他在制笛技藝上精益求精,在選料上嚴格把關,只要有一點點瑕疵,他就嚴禁流向市場。因此,張氏竹笛在業界擁有非常高的聲譽,產品供不應求。
一天,一輛黑色奔馳一路疾駛來到張強生的企業,車子一停,下來一位手拿公文包、嘴上叼著雪茄的中年人。中年人找到張強生后,自我介紹說:“張總好,我是亞細亞國際培訓集團的營銷總監,為了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我們集團在全球50多個國家設有中國民族樂器培訓機構,主要培訓對象是各國愛好中國民族樂器的少年兒童,其中笛子培訓是一個重要的內容。久聞張總公司生產的張氏竹笛質量上乘音質優美,經過董事會研究,決定向你公司定購一批竹笛,今天我特受總裁之命前來與你對接洽談。”說完雙手遞上了一張名片。
張強生接過名片,一邊讓座,一邊看了看名片,“哦,是趙總監,歡迎歡迎!謝謝你們大集團看得上我們鄉下小企業,我們一定全力以赴,按照你們的要求精心加工制作。”
“好,好,謝謝張總,相信我們的合作一定會很愉快。”趙總監連連點頭說道,“我們已經了解了國內張氏竹笛大致的銷售價格,因為我們這次需要的量比較大,時間上也要求比較緊,我們知道貴公司要完成這批生產任務,壓力也一定較重,所以我們出的價可以比你們現在的價格高一些。”
“價格好商量,只是不知趙總監你們要多少?要何時交貨?”
“10萬支,交貨時間最遲三個月。”
“什么?10萬支?三個月交貨?”張強生一聽差點兒跳起來。
“怎么樣,想不到一筆生意就會這么大吧?”趙總監略帶得意地說,“我們是跨國集團,在全球50多個國家開了五六百家培訓機構,10萬支分到每個點,也就只有2000來支,并不算多啊。”
“啊,這么多啊,我們小公司還真接不了這個單。再說……”
“張總是不是感覺價格上可再商量一下?這樣吧,我也是爽快人,一口價,比你們的銷售價高50%,這樣你可以滿意了吧?”
“不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這么大的量,我們實在難以承接。”
“張總啊,我是慕名而來的,你看,我合同也帶來了,按照行規,20%的定金的現金支票我也帶來了,你就……”
“趙總監,不是我不想接你的單,這么大的單對我們企業來說,確實是一個賺錢的好機會,哪個企業不想賺大錢?但是,為了保證竹笛的質量,可不能亂來,你說對嗎?”張強生真誠地說道,“我們生產的竹笛,之所以在市場上口碑不錯,除了工藝上嚴格把關,我們在用料上也一直堅守著老祖宗傳下來的標準。”
“那我倒要聽聽,你們老祖宗傳下來的是什么標準。”
“第一,砍伐的竹子,一定要長滿三年的;第二,選擇的竹子都是長在山陰背陽的地方的;第三,砍下來截成段后,一定要放在陰涼、通風處晾上整整兩年,讓竹子的水分自然晾干;第四,砍竹子只能在冬天,這個季節砍下來的竹子才不會受蟲蛀。”張強生頓了頓接著說道,“現在我們可以制笛的庫存竹子,根本沒有那么多,我也不會昧著良心來糊弄你,我今天給你一支不合格的竹笛,裂了,彎了,就吹不出準確的音來了,小孩子拿到這種笛子,弄不好啊,會毀了一個笛子天才,這樣的事我是絕對不會做的。”說完,他抬頭望了望掛在墻上那系著紅綢的竹笛。
趙總監聽完張強生的話,禁不住拍起手來:“張總,你偉大,了不起!我走南闖北到現在,還從未碰到過像你這樣講信譽的企業家,與你做生意,我們心里踏實。你現在的庫存能做多少支笛子,我全包了,今后,我們會成為長期合作伙伴的。”
“好,這話中。現在的庫存啊,大約能做兩萬支。”
“好,那我們就先簽個兩萬支的合同吧。”
為了趕緊完成這兩萬支竹笛的制作,除了工人們加班加點,必須要增加一個調音師,因為竹笛做出來以后,都要經過樂感很強的調音師進行適當修飾,這樣才能確保每支竹笛的音準。但具備條件的調音師卻很少,張強生就在微信上發出了招聘調音師的信息。
那天,一位老者風塵仆仆地來到了張強生的辦公室,張強生抬頭一看,竟然是當年與他同場競技現在已經是大名鼎鼎的笛子演奏家李才能。
“才能,怎么是你?你怎么來了?”
“強生,我是來應聘的,更是來贖罪的。”李才能上前一步,一把抱住了張強生,不禁淚如雨下。
原來,當初省藝術團來招聘,李才能為了勝過張強生,一念之間,竟偷偷在張強生的竹笛上動了手腳,他用一張粘貼紙,悄悄地粘在張強生竹笛尾孔的前面,這樣,等張強生吹笛時,管內的氣流受那粘貼紙的阻擋,就影響了尾孔的正常發音。
其實,張強生后來就發現了這一情況,他估計是李才能所為,但是,又沒有什么證據,他就只好默默地埋在心里。后來,他一直留著那支竹笛,也沒有把那粘貼紙撕掉,他想,或許有一天,事情會弄個水落石出的。
而李才能做了這樣的手腳,心里一直非常后悔,用這樣不正當的手段戰勝了張強生,他始終愧疚難當,多次想來向張強生請罪,可總下不了決心。這次,他聽到張強生為了堅守信譽,回絕了賺大錢的機會,他更感到自己當年是那么的卑劣,如果不卸下這個包袱,他將永遠生活在自責之中。因此,看到張強生急招調音師,他就來了,并要用自己專業的技藝,助張強生一臂之力。
這時,只聽張強生爽朗地說:“才能,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要是沒有這樣的過節,這世界上啊,可能就少了一位笛子演奏家,我啊,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帶著鄉親們賺錢。”
當李才能看到墻上掛著的那支竹笛,一看就知道是張強生當年用的那支,就取了下來,真誠地說:“強生,請把這支留著我丑陋一面的笛子給我吧,讓它像鏡子一樣,時時刻刻照著我,余生再也不要犯渾了。”
選自《一字集——郁林興故事新作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