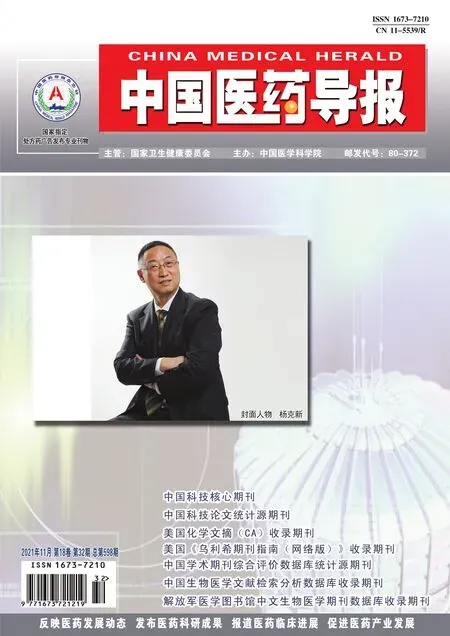“殘疾人服務”APP 居家康復管理模式在腦卒中偏癱患者中的應用效果
趙玉茜 孫 帥 謝偉迪 曹 斌 吳 琛
1.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康復醫院康復中心,北京 100144;2.解放軍總醫院京南醫療區門診部,北京 100071;3.北京市殘疾人聯合會,北京 100069
腦卒中是中老年人常見的急性腦血管疾病之一,常導致偏癱等后遺癥[1-2]。腦卒中偏癱患者主要表現為單側上下肢、面肌、舌肌等部位運動障礙,輕者肌力下降,重者活動受限、生活不能自理[3]。有研究表明,有效的康復治療可促使受損的腦部神經發生可塑性改變或功能重組[4-6],但不規范的康復治療卻阻礙甚至加重了腦卒中偏癱患者的康復進程。鑒于此,本研究探討了“殘疾人服務”APP 居家康復管理模式在腦卒中偏癱患者中的應用效果,旨在為腦卒中偏癱患者居家康復提供新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 年1 月至2020 年1 月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康復醫院(以下簡稱“我院”)接收的192 例腦卒中偏癱患者,按隨機數字表法將其分為對照組(96 例)和研究組(96 例),患者及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納入標準:①符合腦卒中偏癱的診斷標準[7];②出院后預期可存活半年以上;③腦卒中首次發病。排除標準:①有精神疾病既往史或家族史;②有其他中樞神經疾病;③治療依從性差;④合并其他嚴重系統疾病或癌癥晚期。其中,對照組男49 例,女47 例;年齡43~83 歲,平均(63.5±8.4)歲;病程2~20 個月,平均(8.2±2.6)個月;文化程度:文盲46 例,小學及初中34 例,高中及以上16 例;家庭月人均收入:≤1000 元42 例,>1000~2000 元35 例,>2000 元19 例。研究組男51 例,女45 例;年齡45~87 歲,平均(65.3±9.2)歲;病程2~21 個月,平均(15.4±4.2)個月;文化程度:文盲45 例,小學及初中33 例,高中及以上18 例;家庭月人均收入:≤1000 元45 例,>1000~2000 元34 例,>2000 元17 例。兩組年齡、性別、病程、文化程度及家庭月人均收入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我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與批準。
1.2 研究方法
1.2.1 對照組接受常規腦卒中偏癱患者出院后居家康復治療,主要為常規藥物治療、并發癥防治、門診隨訪及常規居家康復訓練建議,干預時間為3 個月。
1.2.2 研究組接受“殘疾人服務”APP 居家康復管理模式治療,干預時間為3 個月。該模式的主要流程為:(1)成立由康復醫師、內科醫師、心理咨詢師、康復治療師及社區殘疾人聯合會干事組成的“殘疾人服務”APP 居家康復管理團隊,團隊成員均接受相關知識培訓且考核達標。(2)入戶及康復治療,先由殘疾人聯合會干事與患者及家屬進行前期溝通,然后由康復醫師、內科醫師及康復治療師入戶采集患者檔案信息,進行康復評估和制訂康復方案,開展初次康復治療并確定下次康復治療內容。此后,根據患者康復情況給予入戶康復治療,≥2 次/周。建檔信息及治療過程均記錄于康復治療師的手機“殘疾人服務”APP。(3)康復治療內容:①心理干預,及時評估患者心理情況,用溫和的語氣與患者溝通,了解其生活及心理需求,多聊患者感興趣話題以激發其康復信心和生活積極性。②飲食指導,飲食以清淡、富含營養的流質食物為主,忌辛辣刺激、高熱值難消化食物的攝入,并保證一定新鮮瓜果蔬菜的攝入,對于嚴重偏食者則依營養學相關理論[8]和患者病情制訂個體化差異的營養方案并切實執行。③運動功能訓練,康復治療師根據患者功能評定結果確定患者康復目標和內容,內容包括翻身、坐位、站位、步行、關節活動、肌力增強、平衡協調、姿勢矯正等,所有訓練均在確保患者安全的前提下進行。④康復指導及按摩,為患者開展肢體擺放、飲食洗漱及排泄護理等指導,根據患者需求運用拿、揉、搓、掐、點、叩、滾、捏、擦等按摩方式緩解其疼痛。⑤家屬(照料者)指導,對患者家屬(照料者)進行居家飲食起居護理、康復訓練、康復護理及家庭環境改造等方面指導,囑家屬(照料者)多帶患者進行戶外運動、人際交往等,使患者盡可能多地感受到家庭關懷。(4)質控措施:①對不同患者設置階段康復目標,并嚴格按照操作流程開展;②明確分工,抽樣督察,由專人隨機線上或線下抽查入戶康復管理工作,并進行績效考核;③設立雙向反饋機制,若入戶康復治療人員技術手法與自身需求有較大差異時可撥打監督電話,康復治療人員應在下次上門前予以改進,在康復治療過程中若發現患者存在家庭支持差、嚴重心理問題等應及時上報以調整治療方案。
1.3 觀察指標
利用改良Barthel 指數(modified Barthel index,MBI)[9]、Fugl-Meyer 運動功能評分(Fugl-Meyer assessment scale,FMA)[10]、Berg 平衡量表(Berg balance scale,BBS)[11]依次對兩組干預前后的日常生活能力、肢體運動功能、平衡力進行評估,評分越高則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及各項功能越好。其中,MBI≥60 為生活基本自理,40<MBI<60 為生活需要部分協助,20<MBI≤40 為生活明顯依賴,MBI≤20 為生活完全依賴[9]。利用抑郁癥篩查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12]、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13]對患者干預前后的抑郁心理、自我效能水平進行評估。其中,PHQ-9評分越高則抑郁心理愈重,GSES 評分越高則自我效能水平越強。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3.0 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研究過程中研究組退出2 例,本研究最終納入190 例患者,對照組96 例,研究組94 例。
2.1 兩組干預前后MBI 比較
干預前,兩組MBI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干預后,兩組MBI 均高于干預前,且研究組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1。
表1 兩組干預前后兩組干預前后MBI 比較比較()

表1 兩組干預前后兩組干預前后MBI 比較比較()
注:MBI:改良Barthel 指數
2.2 兩組干預前后平衡能力、肢體運動功能比較
干預前,兩組BBS、FMA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干預后,兩組BBS、FMA 評分均高于干預前,且研究組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2。
表2 兩組干預前后平衡能力、肢體運動功能比較(分,)

表2 兩組干預前后平衡能力、肢體運動功能比較(分,)
注:BBS:Berg 平衡量表;FMA:Fugl-Meyer 運動功能評分
2.3 兩組干預前后抑郁心理、自我效能水平比較
干預前,兩組PHQ-9、GSES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干預后,對照組PHQ-9 評分與干預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研究組PHQ-9 評分低于干預前,且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干預后,兩組GSES 評分均高于干預前,且研究組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3。
表3 兩組干預前后抑郁心理、自我效能水平比較(分,)

表3 兩組干預前后抑郁心理、自我效能水平比較(分,)
注:PHQ-9:抑郁癥篩查量表;GSES:自我效能感量表
3 討論
腦卒中偏癱對患者及其家庭生活質量都帶來了極大影響[14-17]。由于康復周期較長,患者除常規臨床用藥外,還需要有效的居家康復治療,但很多患者由于家庭支持不足或照料者相關康復知識匱乏導致其出院后居家康復效果不良[18]。相關調查表明有90%以上的腦卒中患者有上門康復治療的需求[19]。因此,開展有效的居家康復治療對提高腦卒中偏癱患者生活質量和降低家庭負擔意義重大。
本研究中對腦卒中偏癱患者開展“殘疾人服務”APP 居家康復管理后,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力、運動功能、平衡能力均優于常規干預模式,與陳赟等[20]對腦卒中偏癱患者開展家庭專人康復管理有類似效果。這是因為在“殘疾人服務”APP 居家康復治療過程中,康復管理團隊可利用手機APP 對患者及時開展多學科評估和制訂階段性康復方案,也可以更便捷地調取治療記錄和調整方案,使患者康復進程得到有效跟蹤和連續管理。另外,≥2 次/周的上門康復治療可及時糾正家屬錯誤的康復認知,并通過引導患者進行漸進式肢體功能訓練與飲食管理以幫助患者逐步恢復體能和肢體功能,從而使其日常生活活動能力及各項功能得到有效改善。
腦卒中偏癱患者多伴有負面心理,有報道表明腦卒中后抑郁總發生率高達55%[21],極大地增加了患者的死亡和卒中復發風險[22],本研究也提示腦卒中偏癱患者有一定抑郁心理和低自我效能水平。自我效能作為一種完成某行為目標或應付某種困難情境能力的成功信念[23-24],通常與患者抑郁心理負相關[25-27]。相對于常規居家康復治療,實施“殘疾人服務”APP 居家康復治療后,腦卒中偏癱的患者抑郁心理有明顯降低、自我效能水平有明顯提高,與李學軍等[15]對腦卒中偏癱伴心理障礙患者實施授權教育的干預結果一致,這可能是因為APP 居家康復治療團隊在藥物治療、物理治療的基礎上更重視患者心理干預和家庭關懷。在康復治療中,疏導患者負面心理、鼓勵患者重新面對生活可激發患者自主康復意識和提高戰勝疾病信心[28-29]。開展家庭關懷教育可以讓患者感受家庭溫暖和充分發揮家庭康復有效性。此外,該模式為公益醫療項目,嚴格控制服務質量,不僅降低了患者家庭經濟壓力,也進一步促進了患者各項康復指標的提高。
綜上所述,“殘疾人服務”APP 居家康復管理模式可促進腦卒中偏癱患者生活質量、運動功能和自我效能水平的提高,降低負面心理,值得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