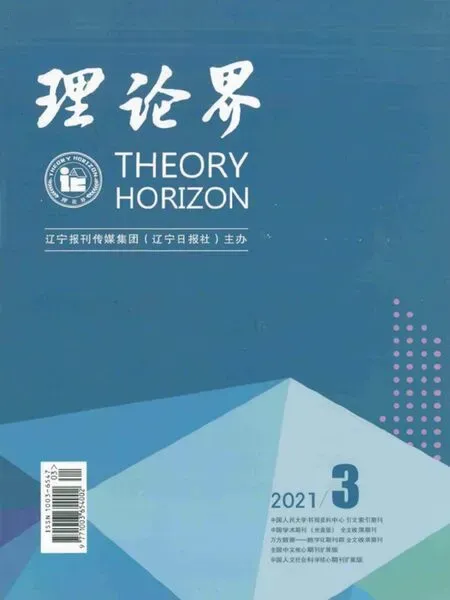論唐代律絕的敘事藝術
梁思詩
相比于沒有體制限制的古絕,律絕在抒情、敘事上自由度相對較低,主要受限于聲律與押韻,至于對仗似乎并不是必須嚴守的硬性要求。詩人們常常打破對仗的限制,使用連貫的結構,在四句結構的連接與跳脫上開拓敘事的自由度。在近體詩體系中,律法對于絕句的束縛是最低的,絕句能以極少的語言表達無窮的余味,事件并不完全局限在詩作字面上。誠如王靖獻所言:“絕句的簡短并未束縛住敘事的充分展開,而是將它轉為極度的精確與完整,運用絕句所特有的省略多余細節的方法,并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懸念導向最終的高潮。”〔1〕
關于唐代絕句的發展,王世貞曾云:“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2〕誠然,綜觀整個唐代,每個時期的律絕都不乏出色之作,其敘事性從初唐至晚唐一直都是存在的。學者們大多認為杜甫拓展了絕句的書寫范疇,將敘事議論納入絕句之體。但在杜甫之前的詩人們也是不乏用律絕來敘事的。那些敘事性鮮明之作,通常指絕句組詩,杜甫率先以組詩的形式敘述時事;元稹用絕句組詩寫悼亡題材,記敘亡者生前經歷;王建作《宮詞》百首寫宮廷生活的點滴;晚唐周曇、胡曾等人運用大型絕句組詩寫歷代史事。然而除了組詩外,單首絕句詩亦獨具敘事藝術。
一、鏡頭與蒙太奇:事件的畫面呈現
用畫面代替敘述的語言是絕句體敘事的首要特征。沈祖棻曾指出:“七絕這種以短小的篇幅來表達豐富深刻內容的特征規定了:……它所寫的就往往是生活中精彩的場景,強烈的感受,靈魂底層的悸動,事物矛盾的高潮,或者一個風景優美的角落,一個人物突出的鏡頭。”〔3〕絕句中的一個畫面就如同電影中的一個鏡頭,而那些敘述的語言就如同電影的畫外音。在絕句中,往往一詩一事,且事件由詩題交代,詩中敘述語和景語雙重話語并存,且二者所表現的都是同一件事。詩人常用敘述語將事件簡單敘述一遍,又用景語重復展現一遍,畫面就是事件的物化和情景化,是對事件的藝術性提升,使事件有了色彩和可觀性。古代批評家早已注意到這點,沈德潛《說詩晬語》云:“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為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4〕有些詩甚至沒有敘述的語言,只將畫面呈現在讀者眼前,如同電影片段,如張籍《宮詞》:“新鷹初放兔猶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5〕
以鏡頭敘事的絕句通常以七言為主,因為七言字數略多,可以較細致地描繪情景,而五言詩則往往只能以意象代替畫面,以物體代替空間,這要求詩人創作時須調動更多的巧思。許多詩作的敘事抒情都由一個鏡頭完成,這個鏡頭是靜止的,畫面中的事物都承載著詩人的情意。如:
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銷磨。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其二)
莫嘆迢遞分,何殊咫尺別。江樓到夜登,還見南臺月。(賈島《上谷送客游江湖》)
悠悠洛陽夢,郁郁灞陵樹。落日正西歸,逢君又東去。(元稹《西還》)
前兩首詩都是前兩句敘述,后兩句寫景。第一首將鏡頭對準了詩人老家門前的湖水,常在的自然景象對照著常變的人事,表達了詩人經久未歸、恍如隔世的對周遭世界的疏離感。第二首詩的鏡頭是江樓望月。月是離別詩中的常見意象,只因月有圓缺,象征離合,而且月是牽系著兩顆離別之心之物。第三首中詩人單點出了樹和落日兩物,畫面簡凈,突出了友人在夕陽西下之際離去的身影,落日對照離別,成為詩中最凸顯的鏡頭。
在更多的詩里,鏡頭往往不止一個,而是不同的鏡頭交互切換,一如電影的蒙太奇。蒙太奇是一個電影術語,指鏡頭的剪輯與組接,使得組合在一起的畫面具備了單個鏡頭沒有的意義。在文學作品中也常使用蒙太奇手法,作者使用跳躍的筆法,將不同時間地點的畫面組接在一起。由于絕句的四句體制,每一句或每兩句詩就能表現一個鏡頭,詩中沒有議論或敘述的語言,全靠這些畫面的接合來展現事件、傳遞情感。
鏡頭的剪切通常可以實現時空的跳躍,書寫回憶中的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的變遷。鏡頭剪切組接的方式有很多,有些通過嵌合不同的地點來連接不同的時空,如杜甫《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岐王宅”“崔九堂”接合了詩人關于李龜年的不同回憶。有些詩是以時間副詞將不同的時空連接在一起,如崔護《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此詩的核心意象是人面和桃花。前一個鏡頭是紅彤彤桃花映襯著人面,暗指當初詩人對—女子一見傾心;后一個鏡頭是桃花仍舊盛放,卻已不見人面,意謂此女子離去之后詩人的失落感。
更多詩作采用的結構是以前后兩聯作為切分,將鏡頭分別對準不同時空。鏡頭的切換通常在第二句或第三句進行,兩組鏡頭所記之事往往性質不同、情意不同,兩相對照,組成詩人悲切的心緒。如:
二年音信阻湘潭,花下相思酒半酣。記得竹齋風雨夜,對床孤枕話江南。(韋莊《寄江南逐客》)
野花如雪繞江城,坐見年芳憶帝京。閶闔曉開凝碧樹,曾陪鴛鷺聽流鶯。(韋應物《春思》)
洛陽一別梨花新,黃鳥飛飛逢故人。攜手當年共為樂,無驚蕙草惜殘春。(李頎《遇劉五》)
君王游樂萬機輕,一曲霓裳四海兵。玉輦升天人已盡,故宮猶有樹長生。(李約《過華清宮》)
四詩全用前后兩聯兩組鏡頭相對的結構,但這些鏡頭相互間并不一定有對比意義,且多數重點在于回憶中的畫面。如韋莊詩前一個鏡頭是詩人花下飲酒,而后一個鏡頭更具畫面感,且連用兩句描寫當年對床夜話的場景。韋應物詩是野花如雪對碧樹流鶯,重點同樣在后兩句。李頎詩的前一個鏡頭是“梨花新”,具有比興意義,即時令更替,詩人與故人舊別,如今重見已是別樣的境況;具體描寫仍在后一個鏡頭。李約詩寫安史之亂前后對比,是常見的題材和寫法。作品前兩句為回憶,概括書寫,從第二句“四海兵”開始轉折,最后將鏡頭落在宮中的樹木,表現繁華逝去后的寂寥與冷落。
鏡頭組接的寫法不僅可以實現時空的跨越,還能呈現出虛實相間的藝術境界,如想象與現實的對照。如白居易《邯鄲冬至夜思家》:“邯鄲驛里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此詩前兩句寫詩人當前的處境,畫面中,遠行的詩人獨自在異鄉的驛館里顧影自憐。后兩句寫詩人想象中的畫面,此刻遠方的家人應該正坐在一起談論著遠行的人。
二、行為與事件片段化:敘事的基本要素
通常在一部敘事文學作品中,人物的行為是基本要素,一個故事或事件是由行為組成的。在體制極短小的絕句中,詩人往往將人的一些簡單行為寫入詩中,以此來表現事件。由于缺乏上下文的渲染和映襯,行為在絕句體中便格外凸顯。單個或數個行為只是整個事件中的一部分,構成事件的片段。詩人挑選入詩的片段,往往是最能表現詩人情感的,他略去那些繁瑣的過程不寫,單寫那些典型的、感人至深的片段,使詩歌在敘事的同時又表達了詩人濃濃的情意。離別通常是律絕中常見的典型片段,如:
紅顏愴為別,白發始相逢。唯馀昔時淚,無復舊時容。(高適《逢謝偃》)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李白《贈汪倫》)
依遲動車馬,惆悵出松蘿。忍別青山去,其如綠水何?(王維《別輞川別業》)
第一首詩不僅一聯之中兩句對仗,且兩聯之間相互對應,即今昔兩個時空。其中分別與相逢是兩個相對的行為,也是本詩的題旨。詩人僅以“紅顏”對“白發”,“昔時淚”對“舊時容”來表現分別與相逢這兩個情感色彩濃厚的片段。至于分別與重逢的具體情形,分別的緣由,期間經歷了多少曲折,概不敘述。第二首詩前兩句敘事,后兩句抒情。前兩句截取了李白乘舟即將離開時的片段,“忽聞”一詞不僅寫出了李白的驚喜,還寫出了汪倫及時趕來、為李白獻上一曲離歌的情態。短短十四字就將情景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第三首詩截取的亦是離別的片段。“動車馬”和“出松蘿”是詩人離開輞川別業時的行為,“依遲”和“惆悵”寫的是伴隨著行為的詩人的心情和神態,表現出詩人依依不舍之態。
與離別相對,歸來也是一典型片段,如《回鄉偶書二首》其一: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此詩選取的是年老的詩人時隔多年之后回鄉的片段。在此詩中,詩人的自我形象十分立體鮮活,詩的第一句先交代詩人的生平經歷,第二句寫其外貌,并著重交代自己的衰老變化,以此引出后兩句孩童見到詩人時的調笑,側面表現了詩人無可奈何的心理。此詩所寫的不是詩人自己的行為,而是他人的行為,以他人來見證自己,這是此詩的獨特之處。
除了典型場景之外,有些詩表現的是生活中的片段和剪影,并不是一個完整的事件,詩人的“行為”只是一些日常舉止,隱藏在這些行為背后的不是一個具體事件,而是日常生活時光。如:
三年患眼今年校,免與風光便隔生。昨日韓家后園里,看花猶似未分明。(張籍《患眼》)
憐渠已解詠詩章,搖膝支頤學二郎。莫學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鬢如霜。(白居易《聞龜兒詠詩》)
主人不相識,偶坐為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賀知章《題袁氏別業》)
紅燭臺前出翠娥,海沙鋪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盡,數數看誰得最多。(張籍《美人宮棋》)
這幾首詩分別寫的是患眼疾后的感受、孩童初諳世事、沽酒、下棋等,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小小的經歷,其中一些尋常得不足為道。這些詩具有記事性,洋溢著詩人的閑情逸趣。
有時,同樣是生活片段,在一些詩作中,詩人在人的行為中寄寓了某些情思,賦予了行為以特殊性。試比較下面兩首同寫醉與醒的詩:
醒來山月高,孤枕群書里。酒渴漫思茶,山童呼不起。(皮日休《閑夜酒醒》)
積善坊中前度飲,謝家諸婢笑扶行。今宵還似當時醉,半夜覺來聞哭聲。(元稹《醉醒》)
第一首詩四句分別寫一個動作,連貫相接,組合成詩人酒醒后的一個生活片段。在時間上也許只有短短幾秒鐘,呈現的是詩人慵懶的姿態,字里行間流露出一種閑適之意,體現了絕句體獨特的表現力。第二首詩較之前一首單純的日常呈現而言,融入了詩人對時間流逝的體悟,對人世變化的感懷。詩的前兩句是回憶中的片段,寫的是詩人在街坊中尋歡作樂的情形;第三句將今日之醉對比過去之醉,詩中并未寫明“哭聲”是誰的哭聲,但這一事象外化了詩人內在的感傷情緒。此詩中所有表示行為的動詞都沾染著詩人的感傷情緒,每一個動作都象征著以往之歡樂逝去不復返的悲劇性。
一個行為能代表一個小小的事件,一個動作往往能成為整首絕句的敘事核心。除了醉與醒這種私人性的動作外,多數動作都涉及了實施者和承受者雙方,其中就包含了人物關系與矛盾、人物之間的互動,從而形成一個事件。如王勃《別人四首》其一:“久客逢馀閏,他鄉別故人。自然堪下淚,誰忍望征塵?”這首詩中的核心行為是“下淚”和“望”,二者都具有對象性。詩人因友人的離別而落淚,他所凝望的是友人離去時掀起的征塵。這兩個動作共同體現了詩人送別友人后孤身一人的悲哀。又如賈島《寄令狐相公》:“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哪可到,行客替生愁。”這首詩中的核心行為是“問”,有逢人便問,問了又問,反復問同一個問題的意思。這表現的是詩人行路漫漫的難捱和孤獨,以及急于抵達的迫切心情。動作的承受者是行客,動作產生的結果是被詢問的行客也替詩人發愁。詩人這是通過寫他人之愁來加深自己的愁。又如金昌緒《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這首詩中的核心行為是“打”和“啼”,因黃鶯啼叫驚醒了女子,女子才怒打黃鶯。這是詩歌主要講的一件小事。第三句中的“夢”又從打黃鶯引申出另一件事,即第四句中的“到遼西”。此處表面寫夢,實則寫男女分離之事,構成了以一件事映襯另一件事的“事中事”結構。
三、想象與留白:詩人與讀者的共謀
絕句的敘事任務往往是詩人與讀者共同完成的。絕句向來無法做到將一個完整的事件和盤托出,詩人將一個場景或一個片段寫出來,讀者由此進行聯想,補全詩人所未能道盡的繁復與瑣碎,即通過側面寫事的方式來召喚讀者的想象。德國接受美學家沃爾夫岡·伊瑟爾提出了文本的“召喚結構”,其具體含義是指:“文學作品中存在著意義空白和不確定性,各語義單位之間存在著連接的‘空缺’,以及對讀者習慣視界的否定會引起心理上的‘空白’,所有這些組成文學作品的否定性結構,成為激發、誘導讀者進行創造性填補和想象性連接的基本驅動力。”〔6〕在接受美學家們看來,一部文學作品只有有了讀者的補充才算是完結。作品是由一個個語符構成的,作者并不是這些語符意義的賦予者,讀者可以參與到文本中詮釋語符的意義。
在中國古典批評家那里,含蓄是絕句的一大特色,楊載曰:“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7〕冒春榮《葚原詩說》:“務從小中見大,納須彌于芥子,現國土于毫端。”〔8〕胡應麟《詩藪》云:“杜以律為絕,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言律壯語,而以為絕句,則斷錦裂繪類也。李以絕為律,如‘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絕妙境,而以為律詩,則駢胟枝指類也。”〔9〕胡應麟舉出李白這兩句詩,認為其如若作為絕句中的兩句,則有言簡而境深的藝術美感,無需多言,寫到此處恰到好處。而杜詩的兩句卻好比律詩中間某聯,不僅對仗精壯,而且仿佛話未說完,需要補充。
首先,由于絕句體制短小,詩人只能將事件的一部分或一些線索寫在文本中,剩余的部分需要讀者的想象來補全,形成了“事在詩外”的范式。這種書寫在五言詩中尤為突出。敘事所包含的因素有人物、時間、地點、事件、事物、細節等,而詩人只能在二十字內進行敘述,他該如何將這些因素都囊括進詩中,同時還要符合律體的平仄規則與押韻,這十分考驗詩人的技巧與才情。詩人通常要將一些敘事因素剔除,比如文本中喪失了時間或地點等信息,這些信息或是被補充在了詩題中,或是需要讀者自行補全。而挑選哪些部分寫入詩中,又成了需要詩人們深思熟慮之處。如劉長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字面上,此詩記述了一個雪夜晚歸的片段,然而在詩中,詩人自身的存在是朦朧的,抒情意味也極微弱。詩中的“夜歸人”可以指詩人自己,也可以指他人。若是詩人自己,那么前兩句便是詩人跋涉雪地時所見的景象;若是他人,那么詩人可能已在室內,望見窗外雪景,聽見犬吠聲,想象趕路人的到來。夜歸人是誰,他因何這么晚才來到此處,他經歷了一些什么,來到這間貧寒茅舍,他是否感到孤獨與無奈,這一切詩文均不作交代,只由讀者自由興發想象。這首詩的闡釋向來是多歧的,可能與劉長卿大歷年間受誣陷被貶有關,因此詩境才如此凄楚。此詩的內容還算是較為豐富的,具備了時間、地點、人物、細節,但在另一些作品中,詩人寫入文本的內容更少,如白居易《問劉十九》: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從詩題可知,詩中的人物為詩人與劉十九,時間是冬天,事件是二人煮酒。詩人寫入詩中的只有兩個物件:酒和爐。這就如同一幅寫意畫,畫中只有兩個人,以及一個煮著酒的爐子,場景中的其他事物都由讀者自行想象,比如他們是在家中還是在驛館?二人因何相聚?他們會聊些什么?除了飲酒還做了些什么?除了二人外還有無其他人?他們正處在一個怎樣的人生境況之下?詩人沒有在作品中給出任何提示,除了酒和爐以外的一切都可由讀者隨意幻想。
有時,詩中所隱藏的事也并非由讀者自由想象,那些具體的真實的事件,詩人在詩中只稍做提點,余下的部分需由讀者到詩人的生平經歷中去找尋。如韓愈《贈張十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攜手城南歷舊游。忽見孟生題竹處,相看淚落不能收。
這首詩所敘的第一件事是張籍眼疾康復,韓愈與其攜手舊游。而第二件事則是第三句中提及的“孟生題竹”,詩中沒有交代此事的具體情由,只說韓愈因此落淚不能自已。孟郊在元和九年過世,他生前曾和韓愈游玩于此,作有《城南聯句》,而今韓愈故地重游,回憶往昔,感嘆斯人已逝,才不由得落淚感傷。
其次,由于律絕較少散文的直白的敘述,較少使用包括介詞、連詞、助詞等在內的虛詞,更加少用口語,如前文所述,絕句多使用鏡頭表現,用意象化的語言,注重情景的描繪,很多時候,事件都是通過景語來呈現的。這時,便需要讀者自行將這些意象和景語翻譯為敘事的語言。這也需要讀者的參與和聯想力,是詩人與讀者合作的結果。如戎昱《收襄陽城二首》其一:
悲風慘慘雨修修,峴北山低草木愁。暗發前軍連夜戰,平明旌旆入襄州。
詩題已經指明事件,如若用散文記述此事,則會詳述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以及涉及的人物與細節。而此詩卻無以上因素,甚至沒有人物。詩人首先通過兩句景物描寫呈現戰場衰颯蕭條的景象,之后再說此地發生過連夜戰,而戰斗的結果,詩人也不直敘,而是用旗幟飄揚入襄州的畫面來做象征。
四、對仗、章法與敘事:句式結構的變化
盡管對仗并不是律絕的硬性要求,但對仗在律絕中是普遍存在的。律絕中的對仗通常只是字面上詞性及語法的對仗,在句義上,每一句詩的相互關系更多是順承與引申的關系。有的作品盡管句式上對仗,但敘事卻不被對仗所囿,而是能將事件的發展、敘述的推進、情感的流動寓于對仗之中。如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此詩兩聯都對仗,且四句均為“二、二、三”的句式,盡管句式齊整但全詩的敘事與情感卻是遞進的。前兩句“異鄉”對“佳節”,在句意上呈因果關系,因為獨在異鄉,所以佳節時才倍感思親。第一句已然完整地描述了詩人孤獨的狀態,第二句又通過佳節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狀態之可悲。第三、四句寫的是“思親”的具體內容,是詩人想象中的情境,兩聯詩組成了不同的時空層次,分別寫發生在兩個時空的兩件事,每件事拆成兩句來寫,兩件事之間遞進相承,主人公都是詩人自己,第一句中的“異客”即是第四句中的“一人”,第三句將筆觸延展開去,第四句重新照應開頭,形成一個閉合結構。
其次是前兩句對仗,后兩句不對仗,這是律絕體制中較為常見的一種。如皮日休《傷小女》:
一歲猶未滿,九泉何太深。唯馀卷書草,相對共傷心。
此詩前兩句寫詩人已離世的女兒,“一歲”對“九泉”,是生與死的對比,直言女兒逝世過早,實在可悲;“未滿”對“太深”,加強了這種悲情。后兩句從死者轉向生者,寫斯人已逝后空虛的情境。此詩運用散文化的語言,將事件直接講述出來,質樸的語言與對仗的形式相互結合又相互掙脫(用虛詞作對仗),使得敘述不僅沒有被對仗所禁錮,對仗反而起到增強情感的作用。對于上述這類結構的詩而言,后兩句不對仗更實現了敘事與抒情的自由度,尤其是可以在末句留下悠長的情感余韻。散句相對于對句更具備這樣的功能。
前兩句不對仗,后兩句對仗的詩如杜審言《贈蘇綰書記》:
知君書記本翩翩,為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前兩句寫實事,后兩句寫虛事,即詩人假想中的情景。這兩句詩通過事象的對比,“紅粉樓”對“燕支山”,拓寬了時空界限,其中還隱含了兩個人,即相思的男女;“日”與“年”相對,不同的地點,卻流淌著一樣難熬的時間。胡應麟《詩藪》曰:“自少陵絕句對結,詩家率以半律譏之。然絕句自有此體,特杜非當行耳。”他舉出了杜審言此詩中的后兩句,言其“詞竭意盡,雖對猶不對也”。〔9〕胡應麟是從絕句末句應“言盡而意不盡”的角度進行評判,然而以對句作結通常難以實現此種藝術效果,因為對句本身是一組完整的結構,很難使句意延伸開去。尤其當這組對句以敘事為主時,它既表明敘事任務的完成,也使全詩的情與意戛然而止。
四句皆兩兩對仗的敘事詩作數量極少,如李賀《蝴蝶飛》:
楊花撲帳春云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家胡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
前兩句寫女子在閨中等待男子的情境,對偶描寫場景是常見之法。后兩句中胡蝶對少年,胡蝶代表喜訊征兆,少年代表喜事。前兩句寫室內,實寫人物當下處境;后兩句寫室外,虛寫即將發生之事,盡管后兩句亦為對仗,但因其虛寫,給人打開了無限的遐想空間,句絕而意不絕。在詞句上,前兩句與后兩句各自對仗;在整體結構和詩意上,前兩句與后兩句相互對仗。盡管四句對仗的詩更適于鋪排寫景,但只要在具體寫法上將句子寫活,這四四方方的體裁同樣可以進行敘事。詩人能將板滯的句式改善得靈活巧妙,比如在對偶中融入豐富的詞性,除名詞外,還有副詞對偶,動詞對偶甚至虛詞對偶等,如此,詩句呈現的便是動態的場景而非靜態的圖畫。若單獨看每件事,則它們均是社會生活中的禍患,而將這四件事疊加起來,相互對應,便體現了當下社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百姓連遭禍害的悲劇。正如謝榛在《四溟詩話》中曾引左舜齊語云:“‘一句一意,意絕而氣貫’,此絕句之法。”〔10〕
許多律體絕句四句皆不對仗,四句相連,順承下來,流暢貫通,每一句都不能單獨切割。如李商隱《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
此詩四句緊密聯系。第一句寫從軍,因離家太遠,家人無法給詩人寄來衣裳。由于沒有足夠的衣裳防寒,天降大雪,詩人愈加寒冷狼狽。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無助的詩人格外想家,格外奢求溫暖,以至他夢到了家中的織錦機。全詩由一句引出另一句,后一句也回應著前一句,這是最適用于敘事的一種章法,詩人僅需依據邏輯和情感將事件流暢地敘述下來即可。
關于絕句的結構,古代批評家重點論述第三句。批評家們多認為第三句是轉折,楊載曰:“多以第三句為主,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至如宛轉變化功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7〕施輔華《峴傭說詩》曰:“若一二句用意,三四句全作推宕作指點,又易空滑,故第三句是轉柁處。”〔11〕《文體明辨序說》曰:“大抵絕句詩以第三句為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旨趣深長。”〔12〕具體到詩作中,確實是以第三句轉折為多。絕句詩多數僅敘一事,而詩人們常常將一事拆為兩層或多層來寫,在第三句插入一個小小的轉折,以呈現出情感的豐富性。例如宋之問《渡漢江》:
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前兩句寫詩人離開故鄉多年,沒有音訊。第三句寫詩人終于回到故鄉,如果按照前兩句的內容順承下來,返鄉應是令人期待的,但此句卻寫出了相反的情緒,“怯”。這是由于詩人離鄉多年,早已不知故鄉的人事變化,故鄉的人也認不得他,因此,故鄉于他而言又是陌生的,這便使他產生了懼怕的心理。
另外需要補充的是關于絕句的起與結。絕句的起結方式多種多樣。在起頭方面,主要為以景起,或以事起。以景起主要為比興,引入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意象,或描繪一個場景,引讀者走入事件的情境。前者如李頎《奉送五叔入京兼寄綦毋三》的起句“云陰帶殘日”;后者如王昌齡《青樓怨》的起句“香幃風動花入樓”。至于結尾的方式同樣多樣不一。在敘事性作品中,詩人寫的通常是一件小事或一個行動,末句通常意味著敘事任務的終結,而隱藏在這件小事背后的背景并不是由末句來引導的,即絕句對讀者的召喚并非全由末句來承擔,前三句同樣可以引起讀者的想象。或者說,主要引起讀者想象的并非某句詩,而是詩人選取寫入詩中的小事、小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