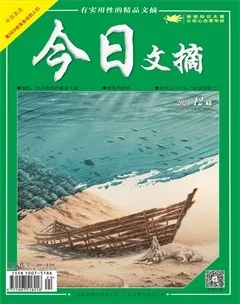近代的歐洲人為什么喜歡戴假發?

我們經常在歐美影視劇中看到近代的歐洲人,尤其是貴族,都喜歡戴著白色的滿頭卷卷的假發。這在我們看來,就像他們看清朝人的大辮子一樣奇怪。他們為什么喜歡戴這樣的假發,這個風氣又是怎樣興起的呢?
這還要從法國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三說起。波旁王朝時期的法國,尤其是路易十四統治時期,是歐洲第一流的強國,對當時的政治、文化、社會生活方面影響非常深刻。
路易十三算得上是有為之主,在紅衣主教黎塞留的輔佐下,讓法國逐漸成為歐洲最舉足輕重的強國。但有為之君也有自己的苦惱,他是個禿頂。為了掩蓋這一缺陷,他便戴上了假發。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路易十三這一無心的舉動,讓貴族們紛紛效仿。他的兒子“太陽王”路易十四也因為頭發稀疏,也喜歡佩戴假發,他的貴族們因此將其變成法國上流社會一種時髦的裝扮。因為法國當時強大的文化影響力,戴假發遂風靡歐洲。據說當時的假發款式有數十種,連頭發濃密的人都喜歡戴。按說女人們留著長發,無需再戴假發,但她們是天生的時尚追逐者,所以上層社會的女人們都戴著各式的假發出席社交場合。
英國國王查理二世因為國內資產階級革命,父親查理一世被處死,他在法國流亡過一段時間。受此風氣的影響,他也開始戴起假發。1660年,他回國復辟,又把這種風氣帶回到英國。英國17世紀著名的作家和政治家塞繆爾·佩皮斯在他著名的日記中曾多次出現與假發相關的記載。1663年11月2日,當佩皮斯聽到了國王和大貴族們都要戴假發的傳聞,他在第二天就把自己的頭發剃個精光,定做了假發。他在日記中寫道:“告別自己的頭發還是有些許傷感。但一切都結束了,我就要戴假發了。”在1665年9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起床后穿上我的絲質西裝,很好,還有買了好一陣子但不敢戴的新假發,因為我是在暴發著瘟疫的西敏買的它,我在想瘟疫之后,人們怕假發是從死于疫癥的人頭上取來的頭發制造的,怕被傳染就沒人敢買假發,假發的時尚會怎樣呢?”在1667年3月27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我要去斯旺找我認識很久的假發師傅杰瓦斯,他給了我一頂假發,卻滿布虱卵,要送回去讓他弄干凈!”
因為戴假發是從社會上層逐漸流行起來的,所以,戴假發逐漸成為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由此可見,假發的流行,上層社會的帶動是一個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假發的流行,也與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息息相關。因為17世紀時,歐洲普遍缺乏供暖系統,人們洗澡洗頭都極不方便。像威名赫赫的“太陽王”路易十四,一生才洗了7次澡。長期不洗澡洗頭,就容易滋生寄生蟲,尤其是頭發,毛發濃密,經常流汗,就容易長虱子。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頭發剪短或剃光,然而頭發剪短或剃光,又不能體現貴族的身份,不如戴假發,兩全其美。
假發之所以能夠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除了貴族把它作為一種時尚外,還有一個現實的問題,那就是假發價格昂貴,一般人戴不起。17世紀時,假發的制造非常精細。當時還沒有機器生產,全靠人工,一位熟練工匠制造一個假發需要幾天的勞動。一個法官的假發就要1800英鎊,而一個普通的假發也得300英鎊。這些錢在今天都是一筆不菲的開支,更不要說工業革命前的西歐了。因此,戴假發不是普通人能夠負擔得起的。而且當時的假發相當笨重,戴起來也不舒服,經常勞動的人自然是不會戴的。
除了價格昂貴、佩戴不方便之外,假發的修飾和維護也是相當煩瑣的。18世紀的假發經常會加上一些花粉,還會加上一些顏料。加粉的假發容易掉粉,而且難以打理。所以,它自然就不受普通人的青睞了。到了18世紀晚期,年輕的男性索性把粉加在自己的頭發上。當時婦女佩戴的假發大而精巧,引人注目,但這種假發很重,還包含發蠟、發粉以及其他裝飾品,成為奢華的標志。
然而,隨著18世紀中期工業革命的開始,人們的思想逐漸開化。沒有假發束縛的自然頭發慢慢地被更多人接受。在歌德的代表作《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中,維特的天然頭發在當時引發一股自然的時尚潮流。法國大革命爆發后,革命黨人力圖建立平等的社會,掃除階級的差異,代表身份地位的假發自然也在移風易俗的對象之列了。加之1795年,英國政府開始對發粉征稅,這讓假發和發粉的時尚遭受打擊,并于19世紀開始逐漸衰落。到了19世紀,假發變得較小和莊重。在法國,假發已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但是在英國,假發作為身份的象征仍然維持了一段時間。法國在大革命后,假發雖然不再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卻與職業威望相聯系。一些行業和領域把假發作為他們專業服飾的一部分,如法官和律師。這種習慣一直維持到今天。英聯邦的法官和律師出庭或者參加重大典禮活動都佩戴假發,這在以往的英國殖民地,至今仍然有這樣的傳統,這反讓假發成為曾經殖民統治的一種印記。
一代風尚的流行,必有它產生的歷史背景,曾經在西歐中上層社會流行的假發,在現在看來雖有些奇怪,卻折射出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還能看到現在某些社會現象的傳承,這不能不說是回望歷史時的一種收獲。
(劉莎莎薦自《領導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