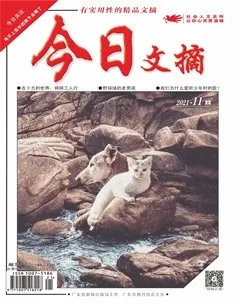我的深夜食堂張小嫻

曾經有個女孩問我一個很可愛的問題,她問我:“人為什么在夜晚變得格外脆弱?”
那是因為夜晚太黑暗,太漫長了吧?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夜晚不用上班。人并不是白天不脆弱,而是下班了,只剩下自己一個了,終于可以盡情脆弱和哭泣。
三更半夜,無論是因為饑餓,還是因為寂寞或者高興而在外面吃,各有各的難忘故事。夜晚的故事,離開了熾烈的陽光,也就變得格外溫柔。
三口子的深夜食堂是我童年一段美好而溫柔的回憶。那時爸爸要值夜班,爸爸很愛吃,也很會吃,我常常熬夜不睡,就是為了等他下班回來帶我去吃好吃的。過了12點鐘,終于聽到熟悉的腳步聲,爸爸回來了,我也餓了,他大概早已想好這天晚上要吃什么,高高興興地領著我和媽媽去吃各種夜宵。
我們住在灣仔,香港的灣仔從前有個別名叫“不夜天”。這里是個五光十色、夜夜笙歌的地方,到了夜晚依然燈火通明。灣仔有那么多過著夜生活的男男女女,是銷金窟,也是一片江湖,自然也就有很多通宵營業的排檔和小飯館。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們差不多每晚都會去一家叫“三六九”的小菜館。“三六九”做的是上海菜,我最愛吃那里的排骨面和芝麻湯圓。他們的芝麻湯圓每一顆都像橘子那么大,我的童年卻是怎么吃都不胖的童年,瘦骨伶仃的,大人都以為我肚子里住了一窩蟲子。
那時的“三六九”有兩層高,燈光很白,空調很冷,常常有各式人物登場,應該也有許多癡男怨女。可惜我那時太小了,還不懂得旁觀別人的故事。
灣仔現在還有一家“三六九”,已經不是舊時那一家,也不在原址,依然是半夜才打烊,聽說味道比不上從前了。
這些年來,我一直尋找好吃的排骨面,可是,很多上海菜館的菜單上都沒有這道主食。一碗排骨面賣不了多少錢,老板寧愿多賣些賺錢的小菜。
即便我能找到兒時常吃的排骨面、港式西餐的黑椒牛排和排檔的海鮮小炒,無論如何也不會是童年的味道了。那家燈光很白、空調很冷的館子已經不在,排檔和西餐廳也消失了,三口子而今只剩下一個人,我也早過了怎么吃都不胖的年紀,再也不敢吃夜宵了,會長肉啊。
童年之后,我再次偶然吃夜宵,是在電視臺混的那段日子。那時年輕又好奇,跟最要好的幾個同事和朋友常常徹夜到處找吃的,聊天聊到半夜才舍得回家。20世紀80年代是香港電影和樂壇興旺的年代,名氣最大的深夜食堂是九龍尖沙咀的“水車屋”,它比漫畫里的深夜食堂華麗得多,檔次也高很多。
“水車屋”做的是日本菜,刺生、壽司、熱食,一應俱全,他們家的鐵板燒跟日本只用男廚師不一樣,全都由年輕漂亮的女廚師來做,做法和味道也變得很港式。“水車屋”是不打烊的,那是個還沒有狗仔隊的年代,娛樂圈無論臺前幕后的人,都喜歡在這兒吃夜宵,這里每晚星光熠熠,梅艷芳和張學友是熟客,不醉不歸。在娛樂圈工作而從來沒去過“水車屋”的,肯定不是什么有頭面的人。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娛樂圈風光不再,“水車屋”也漸漸沒落,所有的店都關門了。香港現在可以吃夜宵的地方來來去去就那幾個,跟我童年相比,太乏味,也太沒趣了,我都提不起勁去吃。
出家人過午不食,清心寡欲,這使我更覺得喜歡吃夜宵的人煙火味特別重一些,欲望多一些,也放縱些。人在夜晚不一定格外脆弱,卻也許是格外寂寞和孤獨,也容易感傷,需要慰藉和懷抱。要是沒有慰藉和懷抱,那就只好把自己投向面前的食物,這時候,味道已經不那么重要了,只為了跟自己或者某個人消磨一個夜晚。
夜晚真的是太漫長嗎?而其實,它和白天差不多一樣長,只是太黑暗;這黑暗卻又偏偏讓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內心,照見了苦和樂。有時候,醒著是比夢著更虛幻。
(白瓊薦自《現代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