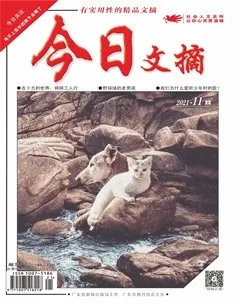我們為什么愛聽少年時的歌?

去年年底,我做了一次不算小的手術。按照一貫的行事風格,我很冷靜地請了假、辦理入院手續,安頓好孩子,冷靜地被推進手術室,又冷靜地被從手術室里推出來。整個過程里,我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獨立、成熟、有擔當的成年人。
術后要臥床6個小時。閑著無聊,我拿出耳機聽了會兒音樂。幾首歌平平淡淡地過去,突然傳來一段吉他低低的旋律,無比熟悉,卻無論如何也想不起是什么歌。在理智尚未來得及做出任何回應之前,一陣酸酸楚楚的感覺從心底泛起,眼淚完全不由自主地落下來。
然后,我聽到自己的抽泣聲一點點變大。靈魂仿佛離開身體,從遠處默默旁觀自己像個孩子一樣,情緒徹底失控。我聽到護士嚇壞了,一直問我怎么了。我聽到自己一直在說,“我的孩子還小,我的孩子還小……”我聽到隔壁床剛做完乳腺切除術的老奶奶一直在安慰我,“姑娘,沒事,沒事……”
平靜下來很久以后,我才意識到,那首歌是張國榮的《全賴有你》,是我18歲第一次離開家鄉、在旅途中一直循環播放的一首歌。“曾在遠處,白雪封天,孤身旅客,縮起肩……”當年,大概是蒼茫大雪、天涯孤旅的意象,暗合了少年離家的愁緒。如今,又與生命漂泊無依、如夢幻泡影的中年感慨碰撞在一起,如排山倒海般,在瞬間摧毀了一個成年人用漫長的時間武裝起來的盔甲。
手術結束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被一種愁緒籠罩。我聽30年前的老歌,看30年前的老劇,就好像身體和心智被一個13歲的自己乘虛而入,遲遲不肯離去。
我聽Beyond的《海闊天空》,總想起童年時南方小鎮灰灰的天,低垂的浮云,想到我的世界曾經那么小,那么封閉,仿佛一切都是已知的。只有當八月臺風季節到來,巨大的風,伴隨著滂沱的雨,那種摧枯拉朽式的自然偉力讓我意識到外面有一個更大的世界,一個仿佛來自時間深處的神秘宇宙。但是,如今這個神秘宇宙似乎仍在通過這首歌告訴我些什么,“走遍千里,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
我聽張國榮的《風繼續吹》,會想起十七八歲的心事,初到陌生的城市,破舊的公交車,坐一路,想一路。冬天的風從窗口灌進來,就像歌里反復吟唱的那陣風,“風繼續吹,不忍遠離,心里極渴望,希望留下伴著你……”可能就是因為那段時間聽得太多了,所以這首歌在我的印象里總是莫名帶了一點北方冬天的肅殺和清冷。但隔了多年之后再聽到這首歌,才明白它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張國榮是用一種淡泊的惆悵,來唱一段郁結的深情。那種復雜的情感,年少的時候如何能懂?
我曾經認識一個年輕的英國人,名校畢業,明明可以做一個金融界精英,卻抱著一把吉他來了中國。他說,他喜歡中文情歌,尤其是90年代的粵語情歌,因為其中有一種特別的深情是英文歌中沒有的。還有哪首歌比《風繼續吹》更深情呢?
我聽溫兆倫的《隨緣》,會忍不住看看天空,看是否真的有人躲在背后。“回頭看這一生,人如飛蟲墮網內,恨的苦的都必須承受”……有些事情發生了,我們只能當作人生的事實接受下來,但有時候潛意識里一轉念,仍然會大吃一驚,比如,原來我已經失去了母親,原來我已經這么老了……
心理學家說,當一個人處在人生的轉折點時,特別容易懷舊。懷舊是大腦的一種防御措施,將我們從充滿焦慮的高壓情境中拯救出來,帶我們去那些潛意識里被認為是“安全”的地方。
我1990年上初中,到2000年大學畢業,整整10年,當時覺得那么漫長的時光,再回頭看時,原來也不過是轉瞬即逝。但感謝互聯網,那10年時間里聽過的歌,看過的劇,如今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再次聽到看到。如果說記憶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無論你失去什么,都能從中找到撫慰的話,如今我就躲在那一方記憶構筑的小天堂里,企圖對抗外面那個未知的世界,其中當然有幻覺,有媚俗,有懦弱,有自我欺騙,但也有英雄主義在。
英國心理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理論。他說,對一個孩子來說,尤其在生命的早期,對外面的世界會有很多的恐懼。所以,他們會挑選一個玩具,作為自己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間的過渡性工具,以應對自己的恐懼、焦慮和失望。就像《花生》漫畫里那個聰明絕頂的萊納斯,無論走到哪里,總是隨身帶著一張毯子。那張毯子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但因為他對它有著絕對的控制權和所有權,所以它又好像是他自己的一部分,這讓他感到安全。
一個人終其一生,要努力維系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的清晰界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們成年人同樣需要一張毯子,允許偶爾的自我放縱、嬉戲和瘋狂。
所以,那些老歌,對于我來說,大概就是萊納斯的毯子。它們曾經提醒少年時代的我,原來人可以過一種更生動、更有趣、更開闊的生活;世界可以有另一種樣貌、另一種秩序,另一種可能。但現在,借著它們,我卻渴望回到過去的時光,一個更安全、更穩固、更自足的世界,更多的愛,更多的善意,更多的自由,更少的責任。那時候,我相信無論多么悲傷的童話也會有一個美好的結局。
(蕭繡薦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