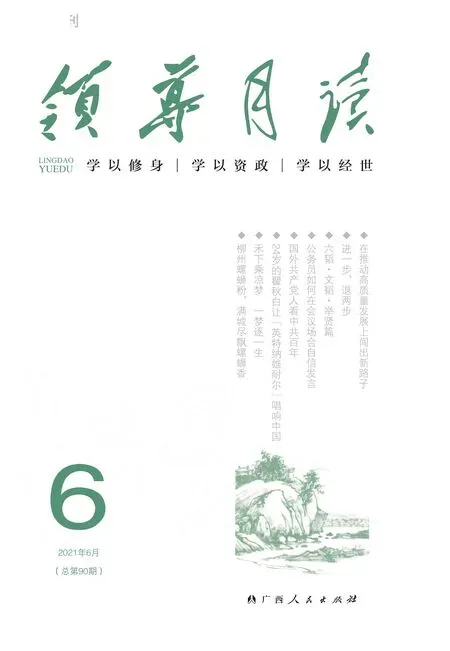輕裝上陣好為官
田 晶
明代名臣于謙,從23歲中進士入仕到59歲逝世,為官36年,不論是監察吏治、判冤決獄,還是勸課農桑、治河救災,抑或保衛社稷、匡君舉賢,都為人稱道,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600余年來,于謙的大名在煌煌青史中彪炳,在文人詩篇里吟詠,也一直被普通百姓特別是故鄉杭州人民傳頌。回顧其一生,于謙之所以能造福天下蒼生、實現自我價值,“輕裝上陣”是關鍵因素。
不慕榮華 尚儉戒奢
于謙步入仕途后,一直堅持簡樸生活,未被物欲污染。據他自述,“吾家素貧,日用節儉”,同朝為官的刑部郎中夏時正也說,于謙“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從正統十二年(1447年)末出任兵部右侍郎起,于謙權任越發重要,成為朝廷棟梁,卻仍然堅持簡樸的生活,住所十分簡陋,僅能遮風避雨。皇帝得知此事,專門給他賞賜了一座西華門附近的府第,于謙提出“國家多難,非臣子安居之日”,還表示如今邊事尚未平息,霍去病都知道“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自己怎能不知?因皇帝堅持己見,于謙便把朝廷賞賜的衣物、兵器等封存于新居,仍然回舊房居住。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朝遭遇土木堡之變,國家社稷危在旦夕。于謙臨危受命,出任兵部尚書,主持北京保衛戰,取得輝煌勝利。因立下不世功勛,朝廷加封于謙為少保,總督軍務,按照慣例可以享受雙俸。僅僅13天后,于謙就提出辭去少保一職,后屢屢請辭未獲允準,便又要求辭去雙俸,并稱自己家里僅有幾口人,一份俸祿已經夠了。
常年身居高位,于謙不免要遭到一些人的猜忌。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就連同僚都主動替他說話:“日夜與國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一子一女且不顧,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尋一個來換于某。”面對無可置疑的事實,非議者也只能羞慚自退。
不結私黨 秉公用權
古代官員往往基于同鄉、同門等關系結為朋黨,在這種畸形的圈子文化里,黨同伐異、公權私用成為常態。但于謙不論是巡撫各地,還是朝堂為官,不論是揚名立萬,還是遭遇挫折,從未阿附權貴、勾結朋黨,始終持公心、秉公權、行公事。
宣德二年(1427年),29歲的于謙奉命巡按江西。寧王朱權的封地在南昌。王府官屬依仗皇親身份,驕橫跋扈,經常對商民強買強賣,商民稍有不從即被抓進府內,乃至毆打致死,因地方官員畏懼權勢,多年來無人敢管。于謙到任后查明事實,秉公辦案,嚴厲懲治了罪行嚴重的十余人,并公開立碑為戒,從此寧王府官屬再不敢胡作非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百姓蒙冤則為其昭雪,在江西任上,于謙輕車簡從,遍訪民間,清理歷年積案,雪冤數百人之眾,深得江西百姓愛戴。
不結黨、不營私,襟懷坦蕩的于謙得以真正做到上匡社稷、下安黎庶。遍覽史冊,于謙給皇帝的奏章中,筆墨最多的就是對民生的呼吁和對強國的建議。如正統元年(1436年),于謙向剛剛即位不久的英宗提出“存恤孤貧、減省吏役、優養軍士”等十條建議,全部被采納。在巡撫河南、山西期間,于謙多次深入災區調查研究,每每上奏要求賑災免糧并屢獲允準,惠及無數黎民。
不謀私利 家風謹嚴
封妻蔭子是很多古代官員的人生目標,更有一些官宦人家蓄養家奴、裙帶蔓延、盤根錯節,導致為官者疲于應付乃至禍起蕭墻。但于謙家風謹嚴,從未替家人謀私利,因而得以實現報效國家之志,不致被親屬牽累。
于謙之妻董氏僅為一小官吏之女,卻孝友敦睦、知書達理,有“賢內助”之稱。據于謙自述,董氏“女紅之暇,誦讀詩書,每有所得,輒為文辭”。特別是因于謙清廉,家庭開支每每捉襟見肘,妻子卻一直安之若素,并未流露出不滿的情緒。于謙長期在外為官,而家中又沒有雇用仆婦,只有妻子一力維持。在于謙49歲時,多年艱辛操勞的董氏病逝,未過五旬的于謙便立志終身不再娶妻納妾,以表夫妻篤篤深情。
于謙有一子名叫于冕、一女名喚璚英。初為人父時,于謙已經高中進士,在官場上嶄露頭角,然而他卻從來無意讓后輩錦衣玉食,而是嚴格要求子女勤讀詩書、孝敬高堂、安于清貧。
于謙為女擇婿之事常被后人稱道。當時錦衣衛底層軍官朱驥品行清白,無錢娶妻。擔任高官的于謙了解朱驥為人,便主動提出將女兒嫁給他。這不但讓周圍人無法理解,就連朱驥本人都不敢接受,于謙卻堅持自己的看法,仍然讓二人成親。后來朱驥勤奮任事,獲得認可,雖因于謙冤案受到牽連而戍邊,但在平反后官復原職,逐漸升任錦衣衛都指揮使,口碑不俗。
不為愛女擇貴婿,反替孝子辭封蔭。景泰二年(1451年),因于謙在北京保衛戰中立有大功,有人建議朝廷授予于冕官職,于謙力辭,表示為人父者都希望讓子女富貴,自己也并非沒有此心,只是國事當前必須重公義而輕私恩。皇帝仍堅持加封,于謙只好告誡于冕道:“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
袖中不裝金銀才裝得下清風,心底沒有私欲才能有國家和人民。于謙輕裝上陣,清白為人,卻創造了沉甸甸的功績,留下了濃墨重彩的歷史記憶。
(摘自2021年4月16日《紀檢監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