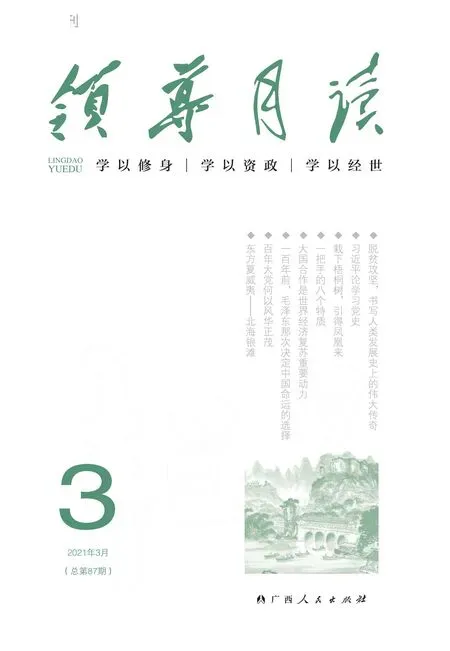“自愛”:先秦儒家的成人之道
楊永濤
儒家的學問究其根本是做人的學問。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怎樣去達成這樣的目標?是孔子以降的儒家學者所共同探索的目標。
關于《荀子》中“自愛”一詞的仁學解讀,將為我們理解原始儒家成人之道提供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
“自愛”只是愛自己嗎?
上文我們對孔子關于“成人”二字的解釋進行了疏解,而先秦儒家的成人之道(成仁之道)還沒有完全展現在我們面前。如何全面地理解儒家的仁道,答案就在下段文獻中的“自愛”二字。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從字面上看,文中“自愛”是愛自己的意思,而且今天比較流行的《荀子》英譯本都將“自愛”譯為“love himself”。如果這樣理解,那“自愛”與“使人愛己”還有區別嗎?為什么孔子對于子路和顏回的評價差別巨大?評子路為士,評顏回為明君子?在這一章的具體語境中,“自愛”反映的不僅僅是愛自己,更多的是要不斷地完善自己,自尊自愛,并且能夠推己及人,成為儒家德性中最高的成人,也就是圣人。
先秦諸子很早就已注意“愛”在人類的情感與人生價值的重要性。尤其是墨家強調“兼愛”,意思是沒有區別地愛任何人。而儒家的“仁愛”卻強調有條件地愛,人只有先敬愛自己的父母,才能一步步擴展,去愛別人。就像是石落水中的水波紋一樣,層層向外。越向外接觸到的范圍越大,人群越多,伴隨著的是感情越淡,水紋波動得也就越淺。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稱這種現象為差序格局。這無疑是符合人情人性的,也是儒家之愛的本有特質。就文意而言,顏回所提出的“愛”具有更高的道德境界,“自愛”并不僅僅是愛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指通過讓自己得到不斷的完善的同時,也能夠讓別人耳濡目染到自己的“仁愛”的品德,從而督促每個人在自覺的“自愛”過程中都能得到互相提升。進而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理解:第一個層面是“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德自覺,第二個層面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道德教化。因此,這個“自愛”在儒家那里是一個自我完善并且能夠證成他人自足圓滿的過程。
“自愛”一以貫之于孔子仁學。
由上可理解,“自愛”并不是“愛自己”那么簡單,更多的是圍繞著“自己”進行道德操練,并且自覺地、平等地感化、教化他人。這是一個一體兩面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不停滯的,是一直前進的,正與《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荀子》中的“學不可以已”等不斷學習的精神一致。人對于精神生命的追尋是無盡的,對于強調修身的中國哲學而言,道德的修持體現在每時每刻、不同地域之中,入圣之機或許就在“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等剎那間對仁道的真切體悟。
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認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把“忠”描述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把“恕”描述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強調了自我與他人之間如何相處,這里并不是強調“我”與“他人”是完全二分的,而是把“他人”的事情當作“我”的事情,看成是“我”自身的發展。孔子和荀子都指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是說,古代的圣賢都是通過“自愛”之道來修身學習。而今天的人去學習是為了自己的私利。這也正合上文所指忠恕之道。
對“自愛”一詞的仁學解讀,是打通從孔子到荀子仁學發展理路的重要一環,這段文獻是先秦儒家發展到戰國中后期孟荀合流的重要表現。將其放在先秦儒家成人之道的視角進行考察,不僅使得先秦時期“成人”這一理想圖景更加明確和豐富,也讓我們對“自愛”這一實踐路徑更加清晰和自覺。因此,從思想史演進的角度看,“自愛”或許是先秦儒家成人之道的最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