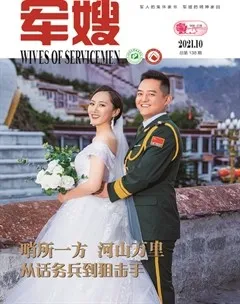空降河源
河源哨所

河源哨所是新疆伊犁軍分區(qū)阿拉馬力邊防連的一個季節(jié)性執(zhí)勤哨所,海拔3000米以上。
2004年7月,依據(jù)中國和哈薩克斯共和國《邊界協(xié)定》,河源地區(qū)主權歸中方所有。當月,新疆伊犁軍分區(qū)數(shù)十名官兵及物資首次被空運到河源執(zhí)勤點。2013年5月,哨所陸路通車。
哨所榮立集體三等功1次。
穿梭于大峽谷中的直升機漸漸在目光中遠去,數(shù)十名官兵還在使勁地揮手,一群白鵝扇動著翅膀擠到隊伍前……2011年5月23日至30日,新疆軍區(qū)某陸航部隊將伊犁軍分區(qū)數(shù)十名官兵及物資空運到河源地區(qū),在河源哨所履行神圣的戍邊使命。
我離開邊防已經(jīng)多年,但那次作為軍事記者采訪邊防哨所的細節(jié)依舊歷歷在目。
河源地區(qū)山高路遠,條件艱苦。每年進駐河源的官兵,是伊犁軍分區(qū)從數(shù)千人中千挑萬選出來的精英,要經(jīng)過個人申請、軍事考核、組織考察等程序。
“河源,我們來了!”那天,一下飛機,帶隊干部黃潤庭就和官兵一起大吼了三聲,響徹云霄的吼叫聲令人振奮,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卡贊古里哨所官兵也在河對岸列隊,揮手歡迎我方官兵到來。
直升機停留10分鐘后返回阿拉馬力邊防連繼續(xù)拉運物資,聽說,這輪任務有多架次空中巡邏、拉運物資、轉(zhuǎn)移人員。我決定等最后一個架次再飛離河源。
送走直升機后,黃潤庭帶領大家整理軍容。
3分鐘后,官兵排成兩隊,一面嶄新的國旗被固定在旗桿上,迎風招展。官兵凝望鮮艷的國旗,高聲合唱國歌。
白天工作,晚上站哨。哨所人雖少,卻管理嚴格。經(jīng)過3天時間的營院整飭后,哨所官兵開始沿線巡邏。班長王龍告訴我:“雖然山高路險,卻擋不住少數(shù)非法抵邊人員來挖藥材、撿鹿角等,官兵需要時刻保持警惕。”巡邏地段多沼澤山谷,不時有官兵陷入泥潭、身體被荊棘劃破流血,大家卻沒有停止腳步,依舊到點到位、無怨無悔行走在邊境線上。
5月26日,是我原定要離開河源的日子。但因為天氣原因直升機無法飛抵哨所,我只得留隊,繼續(xù)聽官兵講哨所故事。
哨所流傳著“姚一勺”的故事。“姚一勺”大名姚飛剛,是這里的第二任哨長。2005年8月,他帶隊到河源執(zhí)勤,一個多月后,陰雨連綿,運送給養(yǎng)的直升機無法到達。生活物資告罄,官兵只能靠儲備的馕餅維持生活。后來馕餅也所剩無幾,姚飛剛便將馕餅切成碎丁放進鍋里煮湯,官兵每頓分一勺。為最大限度保持能量,姚飛剛命令除必須執(zhí)勤人員外,其他人全部臥床休息。有人提議在當?shù)夭东C野生動物充饑,姚飛剛卻給大家上了一堂對馬鹿、野豬等野生動物保護的課。馕餅吃完了,哨所附近的野菜也被吃光了,在大家萬分焦急之時,天空撕開了一條縫,陽光傾瀉而下,接著,直升機將生活物資運抵哨所。從此,姚飛剛便被大家稱為“姚一勺”。
饑餓可怕,寂寞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每天與毒蛇打交道。河源原來是一片無人區(qū),雜草叢生,蛇患嚴重。為了驅(qū)趕毒蛇,官兵動手制作了帶有聲光的驅(qū)蛇器。有牧民給官兵支招,毒蛇聞到鵝糞味,就主動躲得遠遠的。于是,每年進哨所時,官兵都帶上數(shù)十只白鵝圈養(yǎng)在營區(qū)。白鵝有領地意識,經(jīng)常叨死山鼠,且能驅(qū)趕毒蛇,是名副其實的“編外哨兵”。

河源氣候多變,時常山洪暴發(fā)。一次,士官馬朋儉和戰(zhàn)友一起外出巡邏,返回時,河水上漲,無法過河,他們只好逆流而上。山越爬越險,天黑前仍找不到過河之處。黑夜來臨,氣溫降到-20℃,電臺也發(fā)不出信號。情急中,馬朋儉爬上最高山頭,脫下衣服點燃,為哨所官兵指示信號。寒風中,他在帽子上寫下遺書,做好了長眠深山的準備。危急時刻,一起執(zhí)勤的軍犬“阿黑”不停狂吠,救援官兵及時趕到。
…………
5月30日上午,天高云淡,山澗中響起了隆隆的直升機聲,我即將離開哨所,心中戀戀不舍。
“毛主席的戰(zhàn)士最聽黨的話,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艱苦哪安家……”這首《毛主席的戰(zhàn)士最聽黨的話》,誕生于阿拉馬力邊防連,一茬茬官兵在這首歌曲的激勵下,真心獻黨、用心戍邊,他們挺著比山還高的脊梁,成為邊境線上最美的風景。
“山靜景無語,曲徑行人稀。莫嘆哨影單,花開香四季。”我至今還記得黃潤庭向我推薦的這首河源執(zhí)勤人員石文斌寫的《河源頌》。這首小詩溫潤了我的眼,撞擊著我的心:哨所方寸地,月共九州圓。
編輯/牛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