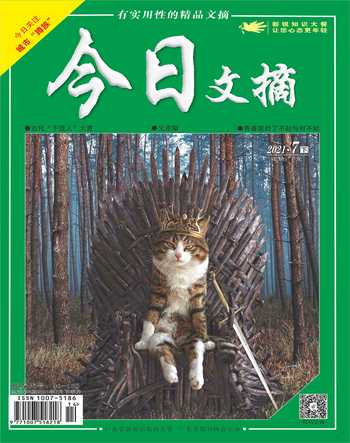在全球最貴城市,我吃到最劃算的美食

新加坡人不怎么做飯,因為一日三餐幾乎都可以在流動攤販的集中地——小販中心(HawkerCentre)解決。早晨一份咖啡多士,中午一碟海南雞飯,夜晚再來碗魚頭米粉,“國民食堂”的名聲由此而來。去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將新加坡小販文化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用餐時間一到,上班族便魚貫而出,涌向周邊的小販中心。他們動作很快,心中早有目標,自覺排成長隊——桐記的老字號牛肉粿條,牛肉湯需經一天一夜熬制;聯合本記的煲仔飯,全程用炭火爐燒熟;現做現賣的香脆咖喱角,售完即止;竹腳中心的黃姜飯很有內味;椰漿飯配冰可樂,飽肚解渴;售價5新幣的云吞面,還配有菜心和叉燒。
小販中心售賣的食物中,飯、面、小吃是基本大類。人口組成多元的新加坡,口味自然也混雜。在小販中心,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歐亞人(歐洲白人和亞裔混血)的代表美食皆可覓得,不同種族的人們并肩做生意,也一起埋頭大快朵頤。
品味獅城美食,小販中心無疑是最具性價比的選擇。這個常年被票選為全球最貴城市的地方,以生活成本高昂而知名。但在小販中心,你可以找到最平價的米其林美食。2016年,首次登陸新加坡的米其林指南,為“了凡香港油雞飯面”送上了星星。創始人陳翰銘,年輕時跟香港師傅學做燒臘,后來在牛車水(新加坡華人居住區)謀得一間兩平方米的小檔口,開攤做小販。一道簡單美味的油雞飯,只需要3.8新元。到2019年,58家上榜米其林推介的餐館里,有過半數出自小販中心。
電影《摘金奇緣》中,哪怕是亞洲富豪,剛落地新加坡,第一頓飯也要先去著名的小販中心紐頓熟食中心。這部現象級電影因為其中對亞裔的刻板印象而飽受爭議,但對于小販中心的描繪倒是非常準確:在桌子上放一包紙巾,是當地人的常規占位操作,先找位置后點餐,用餐體驗更順滑;對衣著細節的呈現同樣貼切,想要享用平價美味,必先要做好與熱浪共處的準備,哪怕富人光臨,也不例外。在沒有空調的小販中心,背心短褲無疑是更明智的選擇。
新加坡小販中心大多建在市鎮組屋(公共住房)區,上百個攤位緊挨密布,填滿第一層鋪面。吊扇小風扇,固定的彩色桌凳,便是一個小販中心基本的配置。檔主在小格間里烹煮,食客在一旁用餐。整個新加坡共有超過百家小販中心分布于各地。它們和商業步行街、社區廣場、地鐵公交站點一起,組成功能完整的公共空間,服務著居民。
草根階層的店主都是小本經營,在幾平方米的小空間里謀求生活:賣魷魚蕹菜的潮汕大叔,70年代也曾經是一名“走鬼”(流動小販),擺攤技能沿襲自上一輩,至今店名還是用父親的名字。他61歲了,依然凌晨四五點就要開始準備,一站就是一整天。做煎餅生意的印度媽媽,一個人要帶四個小孩。剛開始做小販的時候,只想當場放棄。但是生活并沒有給她太多選擇。一眨眼,兒子都比她高了。吃了好多年的苦,如今只覺得感恩。她說,真是太好了,終于都熬過來了。在芳林開店的老太太,廣式米粉一賣就是一輩子。在她爸爸做小販的年代,買一雙5角新幣的拖鞋都是一種奢侈。那時候,別人譏笑他為何節省至此,爸爸回復一句話,“因為我有一個家”。
迷途的中年人在這里從頭來過,患難夫妻在煙火氣里互相依靠。庶民美食,出自庶民之手。上萬個攤位背后,是最平凡的百姓。一碗云吞面,從3角賣到5角,又從5角賣到7角,一點一點撐起整個家。
小販文化申遺成功后,新加坡首先致謝的,是行業里的從業者。“滿足國人口腹之樂,豐潤國家精神滋養”,舌尖上的新加坡,由辛勞與汗水共同打造。小販中心依組屋區而建,而組屋又承載了新加坡逾八成人口。黃皮膚黑皮膚,有錢的沒錢的,在同一個屋檐下用餐。
新加坡人在這里填飽肚子,在這里閑談社交,在這里度過日辰。人們珍視這些并不高級的地方。在新加坡的網站,你甚至可以找到動畫化的小販中心地圖指引。信息之詳細,分類之清晰,具體至每一個檔位的號碼、名稱和營業時間。對于當地小販文化的保育,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但和其他很多傳統一樣,新加坡的小販文化目前面臨著傳承的難題。起早摸黑的辛苦活,顯然不是理想的事業志向。掌勺的當家人,大多已至知命耳順之年。年輕一代如何選,只能隨年輕人去,“他們愿意就接,不愿意的話,也就到我這里結束啦。”老一輩人都這樣說。
(楊佳薦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