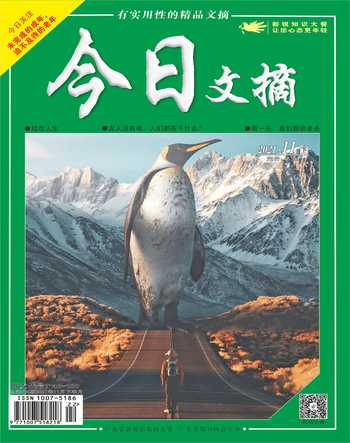你在的光陰

接近一周沒有下樓,也沒有任何下樓的欲望,只從窗戶看著對面樓房的防盜門里,零零星星地有人走出來,又消失在有風穿街而過的巷子里。
我笑起來,老鼠的孩子會打洞,她果然是我親生的。
又陪阿爾姍娜看一則捉蟋蟀的視頻,里面賣蟋蟀的人,明顯是我們山東泰安一帶的口音,于是我也跟著說起山東話,逗阿爾姍娜玩兒。她聽不懂,急得掉出眼淚,邊哭邊問我:“媽媽,你為什么要這樣說話?”
我笑起來:“因為每個人都有故鄉啊!你小時候說蒙語和普通話,媽媽小時候就說山東話,是因為外出讀書才改說普通話!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地方的方言,這有什么奇怪的呢?就像你以后要學習蒙語、漢語和英語,也是為了能夠更自由地行走世界啊!”
她半懂不懂地擦掉眼淚,跟著我的腔調,也說了一句蹩腳的山東話,直把我差一點兒逗出眼淚。
午休,我和阿爾姍娜躺在一起,肌膚相觸,親密無間。昏暗的光線中,她突然溫柔地親我,而后重復那句幾乎每天都要對我說的話:“媽媽,我愛你。”
“我也愛你。”我回吻她。
我們同時閉上雙眼。慵懶又幸福的睡意,溪水一樣漫過我的身體。
晚間下樓去便利店,懶得換衣換鞋,直接趿拉著拖鞋就出了門。
阿爾姍娜便問:“媽媽,你不怕別人笑話你嗎?”
我在溫柔的夜色中大笑起來:怕什么,這么黑的天,誰認識我呢?
的確,我愛這居于鬧市中的老舊小區,時光在這里猶如隨地可見的老人,緩慢而又沉靜。云朵每日都閑散地掛在我的窗前,從不結實的桃樹,在黃昏中散發出圣潔的光。小孩子們風一樣來去,安紗窗的,收廢舊電器的,賣西瓜的,在午后空曠的大道上,發出單調寂寞的叫賣聲。處處都充溢著自由的氣息,就連一個臨街的廢棄商鋪,銹跡斑斑的木門上,也閃爍著慵懶的閑情。
“媽媽,我們出去走走吧,外面風景那么好。”幾乎每天,阿爾姍娜都會這樣懇求埋頭寫作的我。在她的心里,只要踏出了單元門,就處處是美好風光。小到一只飛蛾,大到一架飛機,在她的眼里都熠熠閃光。
只是夜色中從家到便利店這一程路,她就喋喋不休地跟我說了許多的話。那些細碎的言語,剛剛說出口,便被風吹走,卻在我的心里,留下一絲可以回味的甘甜。猶如一只蜜蜂,飛赴很遠,從千萬朵花蕊中采集而成的一滴晶瑩的蜜。
(龍詠思薦自《品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