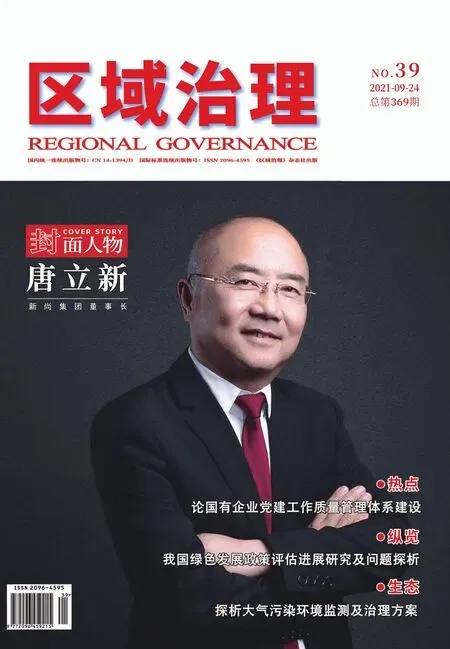高空拋物罪的適用研究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陳思遠
一、適用中的問題
刑法系我國基本法律之一,在我國法治體系中基于起保障性、基礎性作用。高空拋物行為是近年來我們社會生活中頻現的一種違法現象,為保障公民對合法權益的需求、國家對于社會治理的需要,我國刑法“立改廢釋”的節奏明顯加快。這次修正案公布,增加了新的罪名,變更了犯罪具備的因素,擴大了根治犯罪的范圍,從根本上擴大了我國的犯罪打擊力度。《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設立了高空拋物罪的刑事罪名,并于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正式施行,此舉值得贊揚。全國首例高空拋物案件的宣判,對高空拋物行為的理解適用,具有樣本作用,及對公眾的警示作用。
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及該罪的前后相應規定為基礎,并以修正案規定變化為邏輯進路,探討高空拋物罪的適用研究。《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應調整,已然窺見到未危機公共安全的高空拋物行為,被評價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兩者在罪責性質與程度存在固有差異,于是將危及公共安全的高空拋物行為,從作為整體的高空拋物行為中明確剝離出來。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高空拋物行為不當地拔高評價為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修正案出臺以前,未能明確辨析兩者之間的本質差異,造成了一些罪刑不相適應的案例。
為此本文重點關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高空拋物罪法益嬗變背后的價值取向;二是高空拋物罪的現實適用;三是附帶考察高空拋物罪司法實踐的進展。
二、高空拋物罪法益嬗變的價值取向
(一)理論保護作用
如果說高空拋物“入刑”,契合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是從宏觀維度探尋《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危及公共安全之高空拋物行為納入刑法規制范圍的現實背景,以及不同部門法之間的銜接互補,毋寧高空拋物“入刑”的刑事法理正當根據則更多從刑事法學內部,挖掘將危及公共安全之高空拋物行為犯罪化的微觀正當性與合理性,由此為《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條尋獲堅實的法理基礎。[1]
特定行為是否需要納入刑法規制范圍,需由多種因素共同決定的,其中嚴重社會危害性是根本性的決定因素,缺乏社會危害性或者社會危害性程度輕微的行為,不論是刑事立法還是刑事司法都不應該作為犯罪處理。然而嚴重社會危害性僅為特定行為“入刑”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如果特定行為已經能夠在現行刑法罪名體系中通過教義學的合理詮釋或者刑事司法解釋的細化釋明予以妥當評價和認定,便可準確且充分地實現相關罪刑規范及犯罪構成的規范目的,“入刑”即非必要。“規范目的是立法者設立某一法律規范的真實動機”。[2]刑法分則為每一條文都具有特定的規范目的,如果已有刑法條文足以實現規范目的,就無需另外規定新的條文。[3]就高空拋物行為而言,若現有刑法規范已經能夠實現對其不法與罪責全面評價,尚未岀現需要刑事立法填補的處罰漏洞,那么通過刑法修正,增設新罪名專門規制高空拋物行為將顯得毫無價值。筆者認為,《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懲罰危及公共安全的高空拋物罪刑條款,以抽象危險犯的形式增設高空拋物罪,在填補處罰漏洞、完善罪名體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實際保護作用
作為刑事立法的“璀璨明珠”,刑法基本原則是作用于刑事法治全部環節,對刑事法治具有綱領性、全局性及貫穿性功能的基本思想、理念。不僅刑事司法要嚴格遵守刑法基本原則,刑事立法也必須受到刑法基本原則的強力約束。《刑法修正案(十一)》通過立法犯罪化的方式將危及公共安全的高空拋物行為納入刑法規制范圍,精準地貫徹了罪刑法定與罪責刑相適應兩項刑法基本原則。
一方面,高空拋物“入刑”有助于準確評定高空拋物行為的不法屬性,有效規范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適用,最大限度規避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口袋化”特征。特定行為納入犯罪圈可以通過立法和司法兩條路徑,即立法犯罪化和司法犯罪化。借助司法解釋或司法習慣將特定行為作為犯罪進而規制,固然能彌補立法犯罪化在效率上的缺失以及立法上的滯后和保守,但因其大多借助對刑法分則模糊性概念、兜底性條款或者補充性罪名的擴張甚至類推適用予以實現,始終在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貫徹上招致詬病。[4]由于刑法分則缺乏對高空拋物行為的直接規制,刑事司法實踐為回應社會關切,不得不通過司法解釋或者個案處理的方式將高空拋物行為如前述那般不當地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當避免擴張該罪的內涵淪為“口袋罪”,本次高空拋物行為直接“入刑”,為將來準確處理此類案件供給明確的罪刑規范,使對高空拋物行為的刑法規制再度回到法治軌道,系對罪刑法定原則應有的回歸和堅守。
另一方面,重罪重罰、輕罪輕罰乃罪刑相適應原則最基本的內涵和要義,高空拋物“入刑”并非有學者所言之“司法解釋條文轉化為刑法條文的立法舉措。”[5]之所以高空拋物罪的法益由“公共安全”徹底扭轉為“公共秩序”,主要是因為高空拋物行為多為擾亂公共秩序。高空拋物行為法益歸屬調整,實則邏輯更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體現謹慎的刑事立法觀。高空拋物罪的分則體系調整,實質上是對該罪法益本質認識的變化,背后涉及一定的價值取向。
三、高空拋物罪的具體適用
(一)高空與物體的界定
明確“高空”和“物品”二者的含義是司法實踐中認定高空拋物罪的關鍵。2021年1月,刊登于《檢察日報》的《準確認定高空拋擲物品犯罪》一文表達出如下觀點:“高空”是指“距地面較高的空間”。由于“高”與“低”是相對而言的,因此沒有也不可能存在一個明確的“高空”標準,但可以肯定的是,形成“高空”的區域,不應僅限于高層建筑,還應囊括因地形等原因形成空間差的陡坡、懸崖、人行天橋等地。所謂的物品并非沒有限制,包括重器、銳物等。本罪法益尤為特殊,一頁白紙無論怎樣拋擲均不會產生危險,但不能認為一本書就不具備危險,本罪涉及的物應當更為具體地結合拋物場景進行判斷。總之,本罪“物”的范疇,具體而言應結合拋物場景、性質及拋擲時間等現實因素考察,實質性判定是否對公共秩序造成擾亂。
(二)故意與過失犯罪的含混性
《刑法》第291條之二僅對于拋擲物品做出了規定,似乎并沒有包含過失情形,在某種程度上是否能將過失致使物品墜落的情形予以規制不無疑問。《法發〔2019〕25號》文件嚴格區分了“拋物”與“墜物”的概念。首先,從高處墜落的物品一般是加害者的過錯造成的。然而高空拋物行為并不一定成立故意犯罪。盡管高空拋物行為系所謂主觀故意,而行為人可能對危害的結果發生并不具有故意。《關于高空拋物行為的意見》規定,“在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情況下故意拋物”一般屬于若干故意犯罪。我認為,這樣的決定實際上很容易引起偏向誤導,只要故意拋物,就構成故意犯罪。[6]
在客觀情形幾乎無差的高空拋物情形中,一旦認定為故意心態,即便是間接故意通常被認定為高空拋物罪;一旦認定為過失,則直接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或過失致人重傷罪。實務中的做法,令人無從得知審判邏輯的自洽性。例如“杜明利高空拋物案”,①杜某醉酒后陸續將多只酒瓶從19樓拋下,造成車輛物損失8768元。法院認為,被告杜某徑直構成高空拋物罪;管見以為,裁判理由有待商榷,杜某行為也可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然法院卻并沒有進行論證。《刑法修正案(十一)》盡管要求“情節嚴重”,但這一要件在司法實務中名存實亡,該修正案出臺后實務人員往往對高空拋物行為作簡單機械地處理。由《法發〔2019〕25號》至《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法益嬗變目的是告誡實務人員應當重新認識高空拋物行為的性質,不能機械地套用《法發〔2019〕25號》文件規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當謹慎細致地加以區分。
行文至此,筆者不妨提出高空拋物罪存在的“混合罪過”或稱“復合罪過”情形。在實踐中,有些犯罪行為存在形態并不能夠與故意犯罪或者過失犯罪所持有的主觀心態完全相一致。[7]多數學者通常將罪過視作故意、過失的統稱,即犯罪行為人對自己行為及其后果所持的主觀心態。“混合罪過”概念最早為了說明濫用職權罪的主觀方面而提出,包括故意、過失兩種主觀心態,系“同一罪名的犯罪心態既包括故意也涵蓋過失的罪過形式”。管見以為,基于認識的模糊性特征,理論與實踐中難以準確區分過于自信的過失與間接故意的罪過形態,從而二者剝離結合為復合罪過。總之,應當透過體系化的視角考察高空拋物行為,不因其獨立成罪而濫用。高空拋物罪可以適當涵蓋過失類行為,打破“一個罪名、一種罪過”的桎梏。從某種意義上說,高空拋物罪的設置具有一定兜底性質。
(三)入罪要素價值位階
考察本罪構成要件的適用。不難發現,高空拋物罪的行為場所應當是高空。建筑物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特別強調,所以從高處扔物品不一定可構成本罪。這種犯罪并不需要實施者站在高處,即使實施者用機械的手段將物品送到高處,然后松開控制,物品自然掉落,也仍應視為犯罪,成立高空拋物罪。或者行為人利用自身能力將一塊鐵錠扔至高空后下墜,理應成立本罪。然而,如果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高空拋物行為,但對風險進行了控制,例如大聲呼喊警示、目力觀察等注意行為的,可以認為缺乏主觀故意,不構成本罪,若造成實害后果的,成立相應的過失類犯罪。較之《法發〔2019〕25號》文件使用“拋棄”一詞,《刑法修正案(十一)》采“拋擲”一詞更為貼切妥當。拋擲行為與墜落存在本質區別,倘若過失墜落或者意外墜落,便不屬于本罪的規制范圍。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認為拋擲行為對于危害結果的發生是確認行為人存在故意的絕對依據。實踐中存在對危害結果發生缺乏主觀故意,但確實實施了高空拋擲行為的情形,此時便不宜以本罪定罪處罰。值得探討的是,本罪能否以不作為方式構成?答案是肯定的,如臺風來臨之際,行為人將物品置于易墜落之處,意圖或者放任物品墜落;或者經過管理人提醒,仍然放任危險發生而未采取避免措施,若有確切證據得以證明,成立本罪沒有疑義。
四、高空拋物罪司法實踐的進展
(一)“情節嚴重”的實務認定
《刑法》為高空拋物行為配置了“情節嚴重”的構成要件,那么如何理解“情節嚴重”便成了該罪的重點。高空拋物罪設置的目的在于預防和打擊犯罪,但是法益變化帶來的處罰范圍的擴張,將會成為司法上的隱憂。實務部門不能單以為“保護頭頂上的安全”為藉口,濫用高空拋物罪。[6]據此,有必要防止違法行為犯罪化,及輕罪的重化。有人或許會認為,高空拋物罪法定刑,最低為單處罰金,因此可以放松嚴格的構成要件,擴張該罪的打擊范圍。但是公民被定罪污名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必須加以警惕,尤其本罪作為故意犯罪,定罪后的附隨后果帶來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刑法本身,那么刑法的正當性就會遭到質疑。
“情節嚴重”這一規范要素可以作為高空拋物罪的調節器,在司法實踐中適當地平衡、調節本罪的打擊范圍。“情節嚴重”大體上應當包含:多次實施、經勸阻后仍然實施;所拋擲物品本身具有傷害性,例如刀具、斧子等金屬器具;從較高的樓層或者建筑拋擲物品,可能產生人身傷亡、財產毀壞的危險;人員密集的場所,例如學校、車站等實施的;造成公共場所秩序混亂的;其他嚴重情形。有待司法解釋予以進一步厘清厘定。
(二)高空拋物罪司法實踐中的競合
對《刑法》第291條之二第2款有關競合的規定,應當予以重視,該注意條款表明下級法院應當避免機械地適用高空拋物罪,而將原本能夠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等行為錯誤地按照高空拋物罪論處,從而不當降低了被告人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例如,“盧永年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②法院認為,被告人盧某的行為危害了公共安全,如認定構成高空拋物罪,則會遺漏評價犯罪行為對公共安全的侵害。法院說理充分,充分辨析高空拋物罪“情節嚴重”的基礎上,盧某拋物行為已然危害了公共區域的安全。兩者競合,取其重者,已見灼然。
首先,“目前來看,高空拋物罪極易與尋釁滋事罪發生競合。”[8]高空拋物罪入刑,主要是為了規制沒有危害公共安全,但仍有必要給予刑事處罰的行為,這些行為大致分三種:其一高空拋物造成人身損害,尚未達到輕傷以上后果,情節嚴重;其二高空拋物造成財產損害,同時不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等其他犯罪,情節嚴重;三是高空拋物行為既沒有造成人身損害又沒有造成財產損害,但是擾亂了公共秩序,情節嚴重。然而,此三種情形在《刑法》293條尋釁滋事罪中,均能涵蓋,既往實踐,對上述情形也普遍按照尋釁滋事罪論處。
其次,高空拋物犯罪與故意毀壞物品犯罪很容易競合。故意毀壞財物三次以上,或者三人以上聚在一起毀壞財物,都成立故意毀壞財物的犯罪。承上文所述,高空拋物行為,極易造成財物毀壞。相應地,高空拋物罪就極易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競合。然而,在不符合故意損壞財物罪的成立要件時,若其情節嚴重,當然會以高空拋物犯罪論處。例如從高處扔出的物品,其價值不足以以故意毀壞財物罪論處,情況若非常嚴重,也可視為高空拋物罪。
總之,高空拋物罪極易與尋釁滋事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競合。立法者增設高空拋物罪,似乎可以認為目的在于對競合行為的法定刑做到罪刑均衡。競合理論一直以來都是刑法問題中,棘手且復雜的問題。[9]因此,司法實務部門,在面臨競合問題時,容易顧此失彼從而邏輯上不能自洽和周延。
五、結論
考諸其他國家對于高空拋物和高空墜物行為的規制,多是以民事手段為主,極少數國家會選擇使用入刑的方式。社會治理的原則應遵循序漸進的方法和手段,規范的嚴苛程度必須平衡社會生活的需要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從治理社會上看,刑法絕不是最好的手段,其威懾、教育之功能,是通過其嚴厲的懲罰,嚴厲的前科制度而有效的發生作用。從某種意義上,是具有一定“破壞性”的手段,刑法的治理原理是以對正常生活、生產秩序的“干預”為代價的治理手段。
高空拋物罪可以適當涵蓋過失類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高空拋物罪的設置具有一定兜底性質。特殊情景下,行為人若意圖或者放任物品墜落;或者經管理人提醒仍然不采取避免措施,倘若有證據證明,高空拋物罪也可以不作為的方式構成。尋釁滋事罪足以應對沒有危及公共安全的拋物行為,高空拋物獨立成罪也可避免罪刑倒掛產生司法不公。但對于司法機關而言,則需要頻繁面對和處理新增犯罪所產生的犯罪競合問題。高空拋物罪處罰情節輕于尋釁滋事罪,應當警惕高空拋物罪淪為“口袋罪”。
保護公民“頭頂上的安全”非常重要,只是需警惕在維護“頭頂上的安全”的同時,給公民頭懸“達摩克里斯之劍”,是否會給社會生活帶來更大的困擾。如果萬般皆刑,這個社會是沒有發展動力的。在治理犯罪和社會生活、社會發展的平衡中,刑法有時會需要讓渡,甚至“無為”。
注釋
①江蘇省蘇州市姑蘇區人民法院(2021)蘇0508刑初129號刑事判決書。
②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2021)滬0106刑初49號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