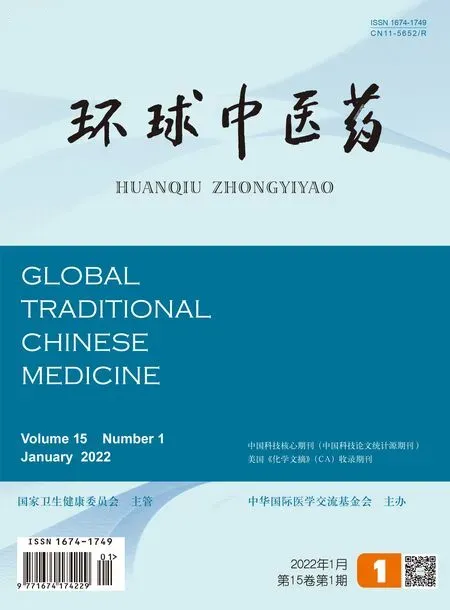通督調神針刺結合中藥治療克羅深瀨綜合征一例
計海生 王穎 李慧惠 劉秀秀 韓為
1 病歷摘要
患者,男,37歲,2018年9月18日因“四肢麻木乏力2年余”就診于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腦病一科。患者于2016年8月出現雙足底麻木、雙下肢乏力,就診于多家醫院,診斷為吉蘭巴雷綜合征,給與營養神經、激素沖擊、增強免疫等藥物治療,癥狀未改善。2017年5月份,患者雙下肢乏力加重,漸至不能行走。2017年9月至上海華山醫院確診為克羅深瀨(POEMS)綜合征。患者多處就診治療,癥狀改善欠佳,前來本院尋求中醫治療。就診時見患者皮膚色暗,面部有痤瘡,肝脾腫大。查雙上肢肌力3級,雙下肢肌力3級,四肢腱反射消失,肢端感覺麻木,四肢末端手套、襪套樣感覺異常,雙足底刺痛覺減退,雙下肢水腫。納、眠差,二便調。舌紅,苔黃膩,脈滑數。西醫診斷:POEMS綜合征;中醫診斷:痿證,證屬濕熱浸淫。治則:通調元神,健脾益氣,培補肝腎,清熱利濕,舒筋通絡。治療方案:(1)針刺取穴:胸1~腰5夾脊穴、百會、大椎、筋縮、命門、陽陵泉、足三里、懸鐘。留針30分鐘,每15分鐘行針1次。針刺每日1次,每周6次,2周為1個療程,連續治療2個療程。(2)內服中藥:蒼術10 g、黃柏10 g、懷牛膝10 g、薏苡仁20 g、炒白芍30 g、萆薢10 g、木瓜10 g、當歸10 g、益母草20 g、炙甘草6 g。28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
2018年10月16日二診。患者痤瘡較前改善,查雙上肢肌力4級,雙下肢肌力3級,雙下肢水腫減輕,腱反射稍有恢復,肢端麻木感減輕。納食好轉,眠尚可,舌紅,苔黃微膩,脈滑。予前方加茯苓10 g,繼服28劑;針刺方案如前,選穴加陰陵泉、內庭。
2018年11月13日三診。患者痤瘡明顯減少,四肢活動度改善。查雙下肢肌力4級,雙下肢無水腫,腱反射稍弱,可下地行走,四肢手套、襪套樣感覺異常減輕,雙足底刺痛覺逐漸恢復。納可,眠安,舌淡,苔薄黃,脈濡。予前方去萆薢,加炒白術10 g,繼服28劑;針刺方案如前,選穴去陰陵泉、內庭,加跗陽、三陰交。
2018年12月11日四診。患者痤瘡基本消失,查四肢肌力4級,腱反射正常,肢端麻木感減輕。舌淡,苔薄白,脈細。辨為脾胃虧虛證,前方去益母草,調整蒼術和黃柏為6 g,加黃芪15 g、懷山藥10 g,繼服28劑;針刺方案如前。
隨訪至2020年12月29日,患者病情未有加重,期間患者定期接受針刺及內服中藥治療。
2 討論
2.1 現代醫學對POEMS綜合征的認識
POEMS綜合征是一組主要表現為多發性感覺運動性周圍神經病,常伴有漿細胞異常及多系統損害的臨床癥候群。其主要表現包括多發性周圍神經病變、臟器腫大、內分泌病變、單克隆漿細胞紊亂或者M蛋白血癥和皮膚損害。該病起病隱匿,常見癥狀為四肢針刺樣或手套、襪套樣感覺異常,伴肌無力,隨著疾病進展,臨床表現逐漸增多,可累及多個系統。目前本病的發病機制尚未明確,有學者認為主要發病機制是血清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水平升高[1]。由于該病罕見,尚無大規模臨床數據資料支持,暫無標準治療方案。推薦的治療方案包括自體造血干細胞移植、免疫調節劑、自身細胞因子誘導的殺傷細胞、烷化劑、單克隆抗體、蛋白酶體抑制劑及放射治療等[2],這些治療方法對POEMS綜合征都有著良好的前景,其中以干細胞移植與免疫調節劑較為有效[3]。該病臨床表現多樣,有著較高的誤診率,發病至診斷中位時間約為12個月[4-5]。本例患者的臨床表現為周圍神經病變、低蛋白血癥、血VEGF增高、皮膚病變、內分泌失調、肝脾大、血肌酐升高、血小板及紅細胞增多,符合2017年梅奧診所診斷標準[6]。
2.2 從肝腎不足、濕熱致痿論治POEMS綜合征
中醫學關于POEMS綜合征報道較少,依據患者四肢痿軟無力癥狀可將本病歸為“痿證”范疇。《證治準繩》言“痿者,手足痿軟無力,百節緩縱而不收也”。《素問·痿論篇》指出“肺熱葉焦”為痿證的主要病機,將痿證分為筋、脈、肉、皮、骨五痿,與五臟相應。筋骨肌肉雖為痿證的病變部位,但痿證根源在五臟虛損,五臟失調皆可導致痿證的產生[7],尤與肝脾腎關系密切。本病常以虛實夾雜或本虛標實為基本病機,常治以扶正祛邪,將補益陰陽氣血、調養臟腑和清利濕熱相結合。
《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指出“因于濕……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為拘,弛長為痿”,《證治匯補·痿躄》有言“濕痰痿者……此膏粱酒濕之故……令人四肢不舉是也”,提示濕熱、飲食不節是痿證的病因之一。該患者長期飲酒,加之勞累過度,飲食不節,嗜食辛辣厚味,損傷脾胃,運化失司故內生濕熱致痿,以實證為主。后久病致虛,損傷中氣,脾胃受納、運化、輸布水谷精微功能失和,津液氣血生化之源不足,無以濡養臟腑,以致肌肉筋骨失養,且伴有肝腎虧損,耗傷氣血陰精,以虛證為主,夾濕夾熱,表現為虛實夾雜之候。
2.3 以扶正固本、補虛瀉實為法,針藥并用治療本病
本患者濕熱浸淫為標,臟腑虛損為本。初診時濕熱搏結,熏蒸華蓋,是以肺熱葉焦、皮毛虛弱,發為皮膚暗沉、面部痤瘡;中焦無力運化水濕,濕熱內生,阻礙脾胃氣機升降,故見納差;濕熱下注肝腎,久病耗傷元氣,水濕運化失司故見肝脾大、下肢水腫。濕熱浸淫經脈,閉阻氣機,氣血不足、肌膚失養致肢端麻木感覺異常。臟腑虧虛可致濕熱內生,而濕熱傷津耗氣亦加重臟腑之虧損。故治療當以扶正固本、補虛瀉實,而標實之濕熱壅盛當急除。以針刺配合中藥,補脾調肺恢復氣機升降,滋腎養肝以助濡養筋脈,使濕熱祛,臟腑調,氣血充,經脈通。
通督調神針法是國家級名老中醫張道宗教授提出的臨床治療方法[8],通督調神即疏通督脈,調整元神。針刺取督脈穴位及夾脊穴為主穴,配以少陽經、陽明經等穴位[9],以通督調神為綱,以氣血同調為法,共奏通調元神、培元固本、清熱利濕、舒筋通絡之功。百會為百脈之會,貫達全身,與腦聯系密切,五臟六腑之氣血皆會于此,能通達陰陽脈絡,調節機體陰陽平衡;大椎為六陽經之會,可啟太陽之開,清陽明之里,和解少陽以祛邪外出,為解熱要穴;筋縮主手足不收,與肝相應,肝藏血主筋,可活血疏筋;命門可振奮督脈陽氣,與腎相應,為元氣之根本,與五臟六腑關系密切。筋縮與命門相合,亦取滋腎養肝,肝腎同調之意。張教授認為督脈貫脊而行,夾脊穴位于督脈之旁,充督脈之經氣,應為督脈之經外奇穴,屬于督脈。夾脊穴又與膀胱經經氣相通,可調臟腑陰陽,通行氣血[10]。《素問·痿論篇》:“陽明虛則宗筋縱……故足痿不用”。陽明經多氣多血,可潤宗筋,故取足三里,其為足陽明經合穴,可疏經通絡、健脾益胃、調理氣血、化濕扶正。脾胃為后天之本,五臟六腑皆稟氣于胃,顧護脾胃可增督脈調五臟之效。陽陵泉、懸鐘為少陽經穴,能輔助督脈通行氣血,二穴又為筋會、髓會,有強筋壯骨之功,與筋縮相配加強舒筋通絡之效。內服湯藥以清熱燥濕、健脾益氣、培補肝腎、舒筋活絡為法,以四妙散為基礎方,加入活血利濕、舒筋通絡、平補肝腎藥味以標本兼顧。
二診患者上肢活動度稍有改善,苔膩減輕,此為濕邪稍退、脾氣漸復,邪氣有頹勢,當加強瀉實之力。治療先清濕熱,瀉中寓補,散中有收,使祛邪而不傷正氣,故針刺加陰陵泉、內庭強清熱祛濕之效,湯藥加茯苓增利濕健脾之功。三診患者癥狀改善較明顯,可下地行走,苔薄黃,脈濡,可見濕熱之邪減弱,而機體病久脾胃虛弱、肝腎虧損,此時當加強補虛之力,減瀉實之功,故針刺配穴去陰陵泉、內庭,加跗陽、三陰交;中藥去萆薢,減祛濕化濁之力,加炒白術益氣補虛,健脾助運。四診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恢復較佳,舌淡,苔薄白,脈細,可見邪氣已微,但正氣未復,證屬脾胃虛弱,故減蒼術、黃柏劑量,去益母草,加黃芪、懷山藥補益臟腑筋脈。后堅持治療,針刺與中藥在原方基礎上隨癥加減,堅持通督調神、固本培元法則。
2.4 通督調神針法可應用于多系統疾病的臨床治療
通督調神治療痿證是建立在腦-督脈-經絡-五臟這一軸上,《黃帝內經》有言:“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凡刺之法,必先調神”“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石學敏院士[11]指出:“百病之始,皆本于神。”督脈是唯一一條既屬于腦又絡于腦的經脈,“腦為元神之府”,主宰人的生命活動,督脈通則神得調,神調則神明得制,神明得制則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肌肉筋骨各司其職,外在五體、五華各盡其用,機體“陰平陽秘”[12]。若腦神失職則臟腑功能失調,或致精氣血津液虧虛,五臟六腑及外在五體、五華“不榮”而痿,或致水濕、痰飲、瘀血等邪實阻滯經脈“不通”而痿[13]。張教授認為在十四經中,督脈占有絕對重要的地位。《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清陽發腠理、實四支”“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可見陽氣溫煦作用之重要。陽氣不足無力推動與運化,精神不能互化,神失所精、筋失所柔,而“形神分離”致痿。因此要重視調督脈,發揮陽氣氣化功能,使精神互化,形與神俱。督脈不僅本身與臟腑有聯系,也可通過背俞穴調節臟腑之氣[14],直接影響臟腑的功能活動。督脈既與多條經脈相交會,又與多個臟腑有聯系,自然擴大了其治療范圍,構成了它對多系統疾病的治療作用,而POEMS綜合征為多系統病變,與通督調神針法的理論相符合。研究表明針刺可以減少炎性因子的表達,增加神經生長因子的表達,發揮神經保護作用[15],因此通督調神針刺對周圍神經受損有較好的療效。
針藥結合的治療方式目前在臨床中廣泛應用,其不僅僅是針刺與中藥二者相加,而是二者的相輔相成。慢性疾患及疑難雜癥遷延日久、氣血過度消耗、臟腑功能衰弱,此為陰陽形氣俱不足,單用針刺或內服中藥可能無法達到預期的治療目的,從而影響療效。另一方面,該病例提示中醫藥的療效與治療持續的時間有關,中醫治療慢性疑難雜癥也需要在一定時間內持續治療以維持療效。希望本案能為治療POEMS綜合征提供中醫學思路與線索,為臨床治療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