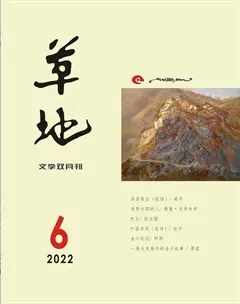金玉滿堂地,鄉村振興時
金川縣勒烏鎮新開宗村,一道山路穿梭在綠林高山,斜而不險,視野開闊。火熱的太陽照在盤蜒向上的柏油路面和沿路房屋的青瓦、樹葉上,明亮的綠意喜人,人與自然調性和諧。我從山路向下看,有一瞬心悸,再往飄渺的遠山望,心情又翩翩然起來。
嗡嗡響動的車廂里,十幾個人漫談文學、時事。省作家協會的曉鴻老師講講藏戲、說說往事,十分有趣。老師是第一眼就讓人感到親切的人,有英挺的鼻子,焦點集中的小眼睛,有時候是深刻嚴肅的,更多時候則松弛隨性中保持著機敏。大方的幽默感和積極果敢的文人態度,讓很多話題都帶上更有趣的意味。我向來不愛坐車,容易發悶,一路上竟然覺到車廂里的空氣都清新快活了。
曉鴻老師很贊同一句話,“文學是人學”。這句話作為現當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命題之一,最先由文藝理論家錢谷融先生凝練先賢論述提出,道明了文學基本的藝術邏輯。我其實想斗膽進而說“文學大概是心學”。在我眼里,文學是以一顆顆活生生的心臟為原點,層層波動著的欲望的浪,一朵朵浪花相似,卻各有不同。
當晚的座談會上,我和自由撰稿人蘇拉老師交談。他直言,你們是從政府的角度談鄉村振興,我從農民的角度看,鄉村振興全看人的意識發展水平,心到則眼到手到。我內心知道意識之根深蒂固,土壤深厚,沒辦法做到短時間廣泛改變。但我還是說,鄉村振興項目的推進也是一個帶動大家提高意識水平的載體,需要邊干邊提高。我是這樣的人,不管事情多困難,只要是正確的,那一定要強化所有積極因素的影響。但這是經不起反思的,容易落于偏聽偏信,做不到客觀辯證。
蘇拉老師說,嗯嗯,這么說那也是。然而這不是辯論,我顯然是以一種小現象模糊了大規律的邏輯。那么到如今,鄉村振興是否有土壤,什么是鄉村振興的原生動力。
從這個角度,我去看此行金川縣的幾個鎮村。從新開宗村到金江村、安寧村、八角塘村、結木村,有的盛產玉米、萵筍、羊肚菌、雪梨、甜櫻桃,有的坐落著中國碉王,有的高山草甸風光令人流連。在五處村寨,我看到不同的自然資源,發現具有相同特質的人。安寧村甘牛社7名黨員帶領57名農戶在全縣率先砍掉傳統經濟林木和農作物,大面積栽上甜櫻桃,頗有華西村吳仁寶的果敢性格。金江村的劉維建從最初的自家五畝地發展到如今的二十畝地,引進新品梨,發展加工業,可謂步步為營,穩扎穩打。
因為居家年輕人不多,我更多是和劉維建等中年一代交談,他們身上恰恰積淀了原汁原味的本土性格。他們熱愛溝通,語言生動,將歷史、事業和自家生活融為一爐講,是真正有主人翁意識的新農民。
此刻再回味他們的神采和話語,越來越品到一種樸素務實的民間智慧和鄉風文明。如果有一片象征他們性格底色的產業園,里面最濃艷的色彩應當是觸目一熱的紅色。那紅色,必定是異域的火龍果,結的是包容和開放的果實,圍繞果實,跳動著好學和進取的火星,源源不竭。
在海拔已達2919米的結木村,我見識到有些許不同的風土人情。在大家口中,結木村是更為傳統淳樸的村落,不太融入商品交易市場。有時候剛剛采了菌子下山遇到人來買,村人喜笑顏開直要送給人家,成為當地市場里的一個例外。結木村嘎尖山,坡上草坪風光秀美,四下遠望景致壯麗,溫度又適宜,假日游玩最好不過。山上的農家樂老板娘臉上掛著高原紅,笑容溫厚,忙里忙外,腳步輕靈,利落得很。問到生意,她說,已經挺滿意,很感恩,這比出去打工好多了,人少時她也無償讓來客乘涼。她們的不爭之心,內里有智慧的,是潤滑劑一般的,給客人留下入心的好印象。
五村普遍對集體經濟認同度高,對政策方針領會力強。此外,他們對黨政干部有信賴感。比如數千人雨中送行的羅從兵同志,村民言談中可聽可感的一批優秀干部。在村民眼里,他們是真正執掌公義之旗的“公家人”。我親身接觸的是縣鄉村振興局副局長,一名瘦瘦小小的年輕女生,言談果斷深刻,工作勤奮實在,同時又十分細膩善良,私下里為殘疾畫師宣傳作品,幾次個人購買。這樣的領導干部,可以開一方之風氣。縣委縣政府能重用這樣能力全面又愛心爆棚的年青人,無怪乎可以形成如此好的群眾基礎和發展土壤。
那么,什么是鄉村振興的土壤和原生動力。綜上所述,是文化振興。大概就囊括這些了:一股向上攀沿的進取文化,一道攜手并進的協作文化,一方廉潔務實的行政文化。有了一片生機涌動的發展土壤,基礎建設、產銷對接、技術升級等系列措施便可以真正見行見效,產業之花便能真正怒放,宜居之果才能真正結生。
在新開宗村,支部書記馬發勇被問到集體經濟分紅情況,馬書記略有些不好意思,覺得分紅數據不夠亮眼。后來,他才說到,他們當家的需要系統規劃,他們目前主要把錢花在基礎設施上了,這是最需要也是最難的。我腦袋里仿佛叮的一聲,剎那間想到我家鄉多處垮塌摧殘的鄉道,再看那條來時的柏油村道,竟有些晃眼。
金玉滿堂地,鄉村振興時。新開宗村們善抓時機,善用資源,善聚民心,可說天時地利人和,振興土壤豐沃。我們很多地方的人應當走出家門,深入地看看這些發展領先的村落,精準自查自己是協作機制需要強化,還是市場定位有偏差,還是技術和銷售需要如何再加以專業化等等;而后再瞧瞧他們,還有他們的孩子,那一張張笑臉,那是縱然在聚斂百年發展紅利的城市說到農村家鄉,也是保持平視的一種笑。我們廣大農村接下來要知道,到了鄉村振興的時代,應是農民為主體的時代,要主動,要進取。
責任編校:周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