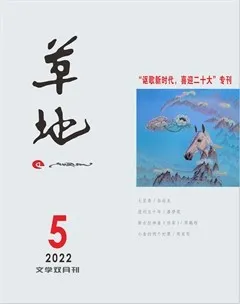電視相伴的歲月
妹妹打來電話,說她打算在老家新房中安裝一臺投影儀,再淘汰掉家里那臺電視。電話這頭的我,在雙重情感糾結中陷入了沉思,為羌寨山區進入了高速發展的新時代而驕傲和欣慰,同時又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感傷,是念舊?是不舍?我說不清。當記憶的時光機帶著我折返一段段往事,我才慢慢了悟這樣的情愫緣何而起。
那是1982年的春天,我的家鄉——岷江河畔的綿虒老街,迎來了全公社第一臺電視。占這個“首”字的不是別人,正是我的爺爺高老頭,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倒不是因為他家多富有,而是他培養了一個愛鉆研電器的兒子——我的父親。
父親是羌區第一批農業機械專業的大學生,那時候還沒有恢復高考,都是由公社集體推薦優秀青年外出就讀,能在公社眾多青年中被遴選并推薦讀大學,那必定是大眾都認可的“四好青年”,除了家庭成分好以外,還得思想政治好、文化學習好、道德品質好。父親以前在公社集體經濟中吃苦耐勞、甘于奉獻,還特別有鉆研精神,那時候集體磨坊的電動磨面機壞了,他琢磨個三五天,總能把它修好。憑著這些不大不小的貢獻,父親在少數的少數中得以脫穎而出,得到大家伙的一致認可。父親也不辜負期望,在學校總是專業知識學得最扎實的那一個,四年學成后,父親響應國家分配,在一所工業中專當老師,這所學校離家鄉也就十來公里,所以只要家鄉公社有需要,父親定然是有求必應的。
參加工作后,父親憑著一腔熱血和不斷探究的勁頭,又從農業機械觸類旁通,學起了機電一體化,后來學校的電子機械課程,父親也能輕松駕馭。到了1980年,在當時的岷江中上游地區購買電視仍然不是件易事,一是一般家庭無法承受較為昂貴的價格,二是電視采購源頭仍然緊缺,許多單位還沿用七十年代憑票購買的政策。沒有一些特殊渠道很難在當地買到電視。彼時的父親已經與母親組建了小家庭,一直想買一臺電視孝敬爺爺奶奶,可資歷尚淺的父親,總是排不到配票資格。
有一天,父親從報紙上得知電視可以自己組裝,并且成本極低的消息后,便一發不可收拾地扎進了車間,他勤學好問反復操作,從一張張錯綜復雜的電路圖,摸索出了電源、電路和信號通道的電視組裝技術。光有技術還不行,在當時設備供應有限的汶川縣城是根本無法買到電視零部件的,為了買齊所需,他周末就坐最早的班車趕往成都電子市場,要知道那時的成阿公路還是不足三米寬的213國道,班車也不是每天發車,到了成都,若是錯過了公交車,還得步行再步行。買好東西后當天已經無法折返了,只有等下次發車,有時一等就是兩天,回到學校已經深夜了。為此,父親老跟別人調課,又抽空再把缺的課時補回來,就這樣連著跑了好幾個周末,幾乎跑遍了當時成都為數不多的幾個電子市場。據他后來回憶,那一個多月,他不僅磨破了三雙布鞋,還磨破了嘴皮,最后不得已,賠盡笑臉外加四包紅芙蓉香煙,才在電子市場一個庫管員手里淘到了顯像管和二手的電視外殼。雖說過程曲折了些,可父親總算買齊了材料,這讓他更加勁頭十足,信心倍增,廢寢忘食地搗鼓了兩個月,裝好拆,拆了又裝,終于將一堆電阻、電容、顯像管、線路板組裝成了一臺12英寸的黑白電視。
父親用自行車把電視馱回老家的那一天,跟爺爺奶奶一同合不攏嘴的,還有左鄰右舍的街坊們。爺爺家率先進入了從聲到形、從光到影的老街新媒體時代。原本靠半導體聽廣播的爺爺樂開了花,寬大的手掌一揮,“一家看不香,大家看才香”。從此以后,每到晚飯時間,周邊的叔伯姑嬸便早早來到我家堂屋外等候了。長凳、門檻、面柜、木桶、小木墩,甚至通往閣樓的木梯都從上至下坐著兩三人,好不熱鬧。
那時沒有機頂盒,更沒有寬帶網絡,有了電視,電視信號怎么解決呢?這可難不倒我的萬能父親。他帶著幾個小伙爬坡上坎,在公社對面的山梁上尋了一個空地,制作安裝了一個小型差轉臺發射塔。再在我家的房背上用竹竿鐵絲等材料制成接收天線。這樣,差轉臺接收到電視信號的載頻,強化放大后再通過房頂的天線接收轉發到電視,電視就有了聲音和圖像。因為需要從中央臺到地方傳輸信號,加之山區地形阻擋,電視信號異常微弱。邊看邊調試就成了常態,時而伴著雜音雪花,時而伴著干擾上躥下跳。按照今天超清電視的標準來說,那樣的音像效果是絕對沒法看的。
當然,這些都發生在我來到這個世界之前。待我長大后,經常聽見父親和幾個老哥們聚在一起掰扯許多年前的那些事,他們大聲講著,時不時傳出爽朗的笑聲。看到大家對父親投去由衷敬佩的目光。我便老愛去打岔,那時候有我嗎?他們總笑著打趣,你?你娃娃那時還不曉得在哪里神游呢……
到后來有了我,我便成了爺爺的小跟班。從我記事起,每晚大伙來圍觀前,爺爺總說,快,趕緊去把那兩根“毛根”轉好,別耽擱大家看“正片子”(電視劇)。爺爺口里的“電視毛根”其實就是電視上方的兩根可收縮的鋁桿,把鋁桿拉出來旋轉方向,以此尋找最清晰的角度。我便乖巧地踩著小木凳去夠那兩根總也不聽話的“毛根”,我之所以樂于干這事兒,是因為每次調好了總會聽到一陣猛烈地夸贊,小小的我對大家的贊美之詞是毫無抵抗力的。
現在再回想,不得不佩服當年大家那股執著勁兒,在微弱的電視信號前,不僅沒人中途離場,還默契地營造著最為舒適的觀影氛圍。夏天,街坊們手握篾扇,兜里揣著自家晾曬的南瓜籽、紅薯干,還有剛摘下的花紅小果相互分享;冬天,在懷里的烘籠焐上兩個烤土豆、烤紅薯,好不愜意。我家餐桌上也時常添些叔嬸們捎來的蕎面饃饃、富條饃饃。爺爺自然是滿心歡喜,他從沒想過老高家有一天會成為全公社最受關注的對象,他甚至有些享受每晚家里人聲鼎沸的鬧熱氛圍。父親呢,看著家里的熱鬧勁兒,再看看爺爺那自豪滿滿的臉,總要一個人傻樂好久。
“高老頭,你家公子可是引領了綿虒公社的新潮流啊。”在聽了供銷社李伯伯的一番恭維后,本來還有一絲顧忌電費的爺爺便來者不拒了,只要哪個犄角旮旯還能擠下一個人,他便熱情地招呼進門。他自己呢,蹲在院子外,瞅著滿屋的觀影人,驕傲地吧嗒著蘭花煙袋。時不時地吼上一句,坐在梯子上的娃娃別亂跳啊,小心摔下來;璐娃子,快去把你奶奶炒的黃豆子拿出來給叔叔嬸嬸些散一散,邊吃邊看才香勒……然后又自顧自地吐一口濃烈的蘭花煙。我呢,屁顛屁顛地端著竹簸箕挨個散豆子,時常是散完了豆子又換回一簸箕的七零八碎,爺爺總要笑著刮我的鼻子。
聽母親說,電視劇《霍元甲》播放的那段時間,寨子上好幾個青年在看了霍元甲力克俄國大力士,一洗東亞病夫之辱后,深受感染,每天扎馬步打沙袋,自創迷蹤拳法,力爭成為綿虒公社的精武高手。那時候,田間地頭、曬壩磨坊,大家的熱點話題必然是霍元甲。至于那幾位苦練功夫的影迷是否練成了武林高手我不知道,但這臺不大的電視當年的確在小鎮掀起了一股狂熱的追劇浪潮。
若是碰上哪一天公社大停電,街坊們就守著爺爺家那盞微弱的煤油燈嘮嗑,一直聊到很晚,估摸著不會來電了,才悻悻地各自回家。第二天再看連續劇時因為接不上頭一天的劇情,大家對供電所又是一通抱怨。
即使不停電,遇到雨雪天氣,差轉臺也會出故障。遠在十里外工作的父親一收到爺爺捎來的口信,二話不說背著工具箱就往老家趕,他爬上山頭修理調試,山下的人用紅布揮舞作為信號反饋。那個物資匱乏的年月,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總是那么純粹、樸實和樂觀,當電視里恢復了那首熟悉的片頭曲,坐在堂屋等待的人們,像久旱逢甘雨般歡呼雀躍。我至今仍然記得25瓦燈泡下大家手舞足蹈的開心樣。
對于這些不太順暢的觀影體驗,大家卻沒有太多埋怨。滿足而幸福地看完上一集,然后推測著下一集的劇情。這些趣事在若干年后的綿虒小鎮,仍能從街坊四鄰的閑談中聽到。到我上幼兒園的時候,已經是收看86版《西游記》和《烏龍山剿匪記》的年月了。父親繼續攻克技術難題,又為老家組裝更新了一臺14英寸的黑白電視,大了兩英寸在今天看來不算什么,在當年可算是質的飛躍了,至少坐在離電視稍遠的位置也能看清人像了。我們一幫小孩兒邊看邊模仿孫猴子、豬八戒、白骨精,在堂屋里上躥下跳,直至挨了大人們的巴掌才消停,可往往沒安靜幾分鐘又開始蹦跶起來。
一如往常,天一擦黑,爺爺家就進入了喧喧嚷嚷的集體觀影時間。大家在歡笑、緊張、怒罵中邊看邊議論,時常用劇情中的人物相互打趣,遇到稍驚悚的情節,還有人大聲尖叫,這樣的不淡定者定會招來一陣數落,人嚇人,嚇死人勒!爺爺就笑,這兩年大家看電視都文明多了,還記得前兩年看《霍元甲》,有幾個小伙子差點沒把我的寶貝電視給砸了。說完,爺爺總要豁著牙開懷大笑。每到周末,公社廣播站會放映免費的壩壩電影,不過電影上座率遠比不過我家的電視收視率。大家都說忙完一天的農活,圍坐在我家一起看電視是最悠閑的時刻。
再后來,前來看電視的街坊越來越少了。因為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家戶戶都有了電視。所以集體觀影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復返了。同樣到了晚七點,爺爺獨自打開電視旋鈕,調到中央一臺看新聞聯播,不,應該是聽新聞,五分鐘內準能聽到他的呼嚕聲,我們見他睡著便去扭換頻道,他立馬清醒,含糊著語氣嗔怪,讓你們關心國家大事,又在那兒瞎換臺。其實,那時的電視頻道就那么幾個,換來換去也換不出個名堂。我們猜想,爺爺不過是還沒從忽然冷清下來的觀影氛圍中適應過來而已。
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家經歷了從黑白電視到彩色電視的飛躍,這次飛躍的原動力來自電視劇《渴望》的開播,母親天天念叨著想看看有色彩的北京,有色彩的四合院,真是應了此劇萬人空巷的“渴望效應”。這一次,對家人有求必應的父親斥巨資買了一臺18英寸的長虹牌彩電,幾乎花光了他四個月的工資。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彩電可比黑白電視強百倍,能看清煙花和連衣裙的色彩,能看清城市和藍天的色彩,能看清天安門和四合院的色彩,還能看見劉慧芳和王滬生的色彩。雖然對于年少的我來說,這色彩僅限于視覺上的色彩,劇中更深層次的感情色彩還無法看清。但這些色彩足以給我的記憶烙上深深的印記。
沒過兩年,遙控彩電的上市,讓我和妹妹對表哥家好一通羨慕。我和妹妹繪聲繪色地向父親描述著哥哥家的遙控彩電多么方便,隨時隨地切換自如,不用頻繁起身換臺,也不用在廣告時間干等。這一次,父親從《電子與科技》雜志上了解到,可以把普通的手動彩電加裝遙控裝置。又是一番苦心鉆研。毫無懸念,一個月后,父親只花了幾十塊錢便從成都買回一套加裝設備,我家的18寸彩電從此有了遙控功能。我和妹妹到處炫耀,一炫耀不打緊,又給父親增加了“練手藝”的好機會,父親單位家屬小院的、老家鄰居們的普通彩電全都集體升了級。大家由衷地感謝父親讓他們又省了一筆換新電視的錢,父親呢,總是淡淡地一笑。一直以來,周圍親友習慣性的對父親刮目相看,父親也就習慣性的助人為樂了。
至于電視信號,差轉臺顯然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收視需求了。九十年代末,風靡一時的大鍋蓋衛星天線登上了歷史舞臺,扭電視“毛根”的舉動至此成了大家茶余飯后的笑談。全鎮廣播站統一安裝模擬衛星電視接收機(俗稱“大鍋蓋”),閉路電視能接收十多個頻道,到2000年左右,汶川市場上逐漸出現數字衛星接收機,接收到的電視頻道也增加到了三十多個,豐富的電視節目讓觀眾有了更多的選擇,所以街坊鄰居對這個大鍋蓋很是青睞,我家也不例外。之后,市面上開始出售一些小型的電視鍋蓋,商家包教安裝,百分之九十的農戶在自家房頂安裝小鍋蓋,接收到的頻道就更多了,信號也比公家統一安裝得好,關鍵還省了一筆收視費。不過,因為衛星鍋蓋有很多弊端,私自安裝到后來都被列為違規行為,隨著法律法規的完善,衛星鍋蓋的時代也基本成為了歷史。
與此同時,錄像機、VCD和DVD光碟機作為電視伴侶又進入千家萬戶。那時候網絡不發達,娛樂活動少,租看電視劇光碟占據了小鎮年輕人大半的閑暇時光。因為是獨家經營,所以小鎮上的那家光碟出租店的生意特別火爆。光碟出租金2元到5元不等,時間一長,我跟小鎮上光碟出租店的老板熟悉了,便可以享受VIP待遇——租兩部送一部。香港TVB拍攝的電視劇是我追看的主要目標,什么《縱橫四海》《大時代》《尋秦記》《天龍八部》等等,可以說是如數家珍。而看瓊瑤小說改編的電視劇《一簾幽夢》《海鷗飛處彩云飛》《蒼天有淚》等軟綿綿的劇情,軟綿綿的主題曲,竟也勾起了一個“假小子”對愛情的懵懂幻想。從早到晚哼唱“問一聲那海鷗,你飛來飛去有何求,問一聲那彩云,你飄來飄去多煩憂。”期待著有一天能偶遇自己的真命天子。用父親的話說,我那時被港臺劇嚴重洗腦了,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當我開始用港臺腔給妹妹輔導作業時,終于被忍無可忍的父親臭罵了一頓。挨罵歸挨罵,追劇的腳步不能停啊,九十年代末的經典電影、恐怖片、諜戰片、愛情片、懸疑片我一部接一部的無縫銜接。老板都打趣,他的光碟出租店快要滿足不了我這個追劇狂人的需求了。
轉眼進入二十一世紀,電視更新換代的速度不斷加快,我家的彩電也從18英寸逐漸變為21英寸、32英寸、42英寸、55英寸、75英寸。從背投電視到藍光電視、等離子電視,再到液晶電視。即使到了今天,電視的時代也并未終結,現在市場上的8k量子點超高清平板電視,100英寸、120英寸,什么防爆、聲控、智能功能,應有盡有。正如廣告詞宣傳語所說:帶給你更為壯闊深邃的視界,仿佛置身其中。黨的十八大以后,隨著信息網絡建設的日益完善,即使是在羌區農村,互聯網和數字電視信號也基本達到全覆蓋。現在家鄉綿虒的電視信號都是靠光纖傳輸,速度快、清晰度高,還可以隨意選擇安裝電信、移動兩家國企寬帶,逐步實現了山里人足不出戶知天下的夢想。
時過境遷,電視已經陪伴我和家人四十個年頭了,那個托著煙袋笑守在電視外圍的老人走了,那個心靈手巧無所不能的機電超人也走了。一些老物件躺在老家的閣樓上落了厚厚的灰塵,而那些關于電視的所有期待、驚喜、和諧、共享,都化身時代的章節,一一封存于我人生的旅程中。懷古而觀今,科技在不斷進步,許多新生事物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改變著我們的生活,但老物件留存在我們骨子里的情感價值是無法取代的。至于電視,我相信,它定會在一個新生領域以不同的形態繼續年輕。
責任編校:石曉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