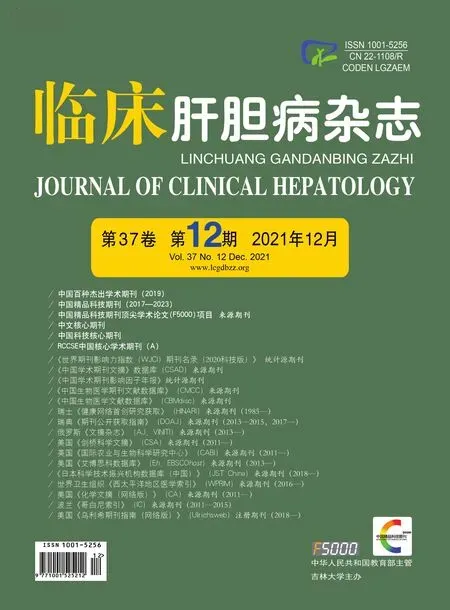炎癥標志物對肝癌合并不同類型門靜脈栓子的預測價值
周鵬鴿, 盧高峰, 任笑盈, 張 濤
鄭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消化內科, 鄭州 450014
門靜脈血栓(portal vein blood thrombus, PVBT)是指發生在門靜脈主干和/或門靜脈分支的血栓、伴或不伴腸系膜靜脈及脾靜脈血栓形成[1],有研究[2]表明PVBT的形成可能與全身炎癥狀態或局部炎癥反應有關,且在肝癌患者中的發病率為 28%~34.8%。此外,肝癌患者的癌細胞易侵犯肝門靜脈進而形成門靜脈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PVTT發病無特異性,多伴發于中晚期肝癌患者中,且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感染和炎癥可能在PVTT的發生中起重要作用,肝癌一旦合并有PVTT,不僅增加了門靜脈阻力,減少門靜脈血流,還會使肝功能進一步惡化,預后極差,生存期降低[3-8]。對于肝癌合并PVBT或PVTT形成后患者通常沒有臨床癥狀,常在體檢或篩查肝癌時偶然發現,本研究旨在分析肝癌合并PVBT/PVTT患者的生化及常規血液指標變化特點,并探討炎癥指標在不同類型患者中的表達水平及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6年1月—2020年12月于本院診治的肝癌合并PVBT患者為PVBT組,肝癌合并PVTT患者為PVTT組,隨機選取同期住院的肝癌未合并門靜脈栓子患者作為對照組。所有肝癌患者診斷參照歐洲肝病學會發布的肝癌診療指南[9],門靜脈栓子的診斷及分類參照中華醫學會《肝硬化門靜脈血栓專家管理共識》[10],并根據2020年美國肝病學會肝臟血管病、門靜脈血栓和肝病患者手術相關出血實踐指導[11]對所有患者行多普勒超聲檢查,對于有門靜脈阻塞患者進一步行MRI或CT明確PVBT或PVTT的診斷;無門靜脈栓子患者是指本次及既往入院影像學檢查未發現門靜脈阻塞的患者。根據Child-Pugh分級評估肝病的嚴重程度。納入標準:(1) 臨床確診為原發性肝細胞癌;(2)均經彩色多普勒超聲、CT血管造影或MRI明確PVBT及PVTT情況;(3)有相關檢查資料、住院治療并有完整臨床資料者。排除標準:(1)曾經或正在接受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療;(2)脾腸系膜或外周靜脈血栓形成;(3)合并其他系統惡性腫瘤;(4)脾切除術后。
1.2 研究方法 回顧性查閱所有納入研究對象的病史、入院時實驗室指標及輔助檢查結果,包括年齡、性別、肝硬化病因,Child-Pugh分級,記錄并分析ALT、AST、Alb、TBil、RBC、PLT、WBC、中性粒細胞百分比(NE%)、淋巴細胞百分比(LY%)、單核細胞百分比(MO%)、CRP、血沉(ESR)、IL-6等實驗室檢查結果。
1.3 倫理學審查 本研究方案經由鄭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號:2021207,納入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納入PVBT組51例,PVTT組37例,對照組50例。3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病因、Child-Pugh分級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1)。
2.2 生化及常規指標比較 ALT、AST、TBil、RBC、PLT、WBC、NE%、LY%、MO%在3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而Alb、CRP、ESR、IL-6組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2)。兩組間比較,PVTT組Alb顯著低于PVBT組和對照組(P值均<0.05);PVTT組ESR、CRP、IL-6顯著高于PVBT組和對照組(P值均<0.05);PVBT組CRP、IL-6顯著高于對照組(P值均<0.05)。
2.3 Alb、CRP、ESR、IL-6對不同類型門靜脈栓子預測價值分析 Alb在PVTT組與PVBT組的AUC分別為0.659(95%CI:0.544~0.773)和0.508(95%CI:0.392~0.624)。CRP在PVTT組與PVBT組的AUC分別為0.826(95%CI:0.737~0.915)和0.635(95%CI:0.526~0.745)。ESR在PVTT組與PVBT組的AUC分別為0.679(95%CI:0.561~0.797)和0.503(95%CI:0.388~0.617。IL-6在PVTT組與PVBT組的AUC分別為0.873(95%CI:0.799~0.947)和0.701(95%CI: 0.600~0.803)(圖1)。

注:由于Alb為負相關指標,故對其取倒數處理。
3 討論
本研究分析了肝癌合并PVBT或PVTT患者的生化及常規血液指標,并探討了炎癥指標Alb、CRP、ESR、IL-6的表達情況。相較于PVBT組和對照組,PVTT組Alb處于較低水平。Alb是格拉斯哥預后評分(GPS)的兩種指標之一,GPS也被證實是包括肝細胞癌在內的許多癌癥的重要獨立預測指標[12],并被認為是代表炎癥性疾病和晚期癌癥中營養缺乏的象征,可直接影響肝癌細胞的生長以及侵襲性[13],而PVTT作為一種肝細胞癌的肝內轉移形式,其侵襲性明顯高于無轉移者,本研究也表明較低的Alb水平與更具侵襲性的腫瘤參數相關(即PVTT的形成),這與先前報道[7-8]結果一致。此外,在肝細胞癌患者中Alb水平降低是PVTT患者較為重要的危險因素,其對肝細胞癌合并PVTT患者的預測價值(AUC=0.659)較對PVBT的預測價值高(AUC=0.508)。
IL-6是一種促炎細胞因子,可通過不同的信號途徑促進細胞增殖、逃避凋亡以及增加癌癥的侵襲力[14]。本研究發現,IL-6是預測肝癌栓子類型最重要的細胞因子,對PVTT的預測價值(AUC=0.873)明顯高于PVBT患者(AUC=0.701)。有研究[15]表明,較高的血清IL-6水平反映了腫瘤的負荷,與腫瘤的大小、分期和侵襲性(如門靜脈侵犯和門靜脈癌栓形成)顯著相關。此外,肝癌細胞本身可能是IL-6的來源,IL-6通過自分泌機制刺激腫瘤生長,其中,IL-6通過激活核因子-κB和信號轉導與轉錄激活因子3(STAT3)發揮作用,這兩個轉錄因子對肝癌的發生和轉移非常重要,這可能促進腫瘤生長和轉移[16-19],這與本研究結果一致,這種關聯意味著高水平的IL-6可能是侵襲性增加以及對門靜脈侵犯的高危因素。然而PVBT組IL-6雖低于PVTT組但仍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因此推測炎癥可能是導致肝硬化肝癌患者門靜脈血栓形成的另一原因,晚期肝病患者門靜脈壓力升高,腸道黏膜屏障被破壞,細菌易位導致炎癥的發生,當暴露于局部或全身炎癥時,內皮細胞被激活并促進門靜脈血栓形成[20]。
CRP是GPS的另一指標,也是一種由肝細胞產生對抗炎癥反應的急性期反應物,其水平受促炎細胞因子,特別是IL-6的調節[21]。本研究表明,CRP水平是另一個重要的預測因素,對PVTT的預測價值雖較高(AUC=0.826),但低于IL-6的預測價值(AUC=0.873)。循環CRP的產生主要依賴于IL-6[22],這也就意味著CRP的水平可能與IL-6水平呈正相關,且同樣作用于肝癌患者門靜脈癌栓形成機制,及影響門靜脈血栓形成。然而,其預測價值低于IL-6預測價值,可能是由于循環CRP水平除了跟全身炎癥狀態相關之外還受高脂、高蛋白飲食、飲酒等因素影響[23-24],具體機制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雖然ESR也常常被認為是炎癥指標,但研究結果顯示,與其他炎癥指標如CRP、IL-6對血栓與癌栓的預測價值不同,PVTT組ESR水平明顯高于PVBT組與對照組,但預測價值普遍不高(PVTT組AUC為0.679,PVBT組為0.503)。CRP在肝臟和肝癌細胞中合成,并與IL-1和IL-6以及STAT3相互作用,可影響單核細胞殺瘤活性[25]。相比之下,使用抗凝全血的血沉試驗不能反映炎癥反應的主動過程,而是炎癥過程的被動反映,即是影響血液黏度的纖維蛋白原、血漿蛋白水平,因此,CRP和ESR可能反映了炎癥過程的不同方面[8,26]。
研究[25,27-28]表明,炎癥指數與肝細胞癌侵襲性顯著相關,包括PVTT的形成。本研究表明,從炎癥水平出發,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對肝癌患者合并不同的栓子類型做出判斷,炎癥指標IL-6、CRP、ESR在肝癌伴門靜脈癌栓患者中高表達,Alb低表達,且預測價值高, 而在肝癌伴門靜脈血栓患者中表達相反,值得進一步行前瞻性研究證實。本研究PVBT及PVTT的診斷均依賴于影像學檢查,栓子主要位于門靜脈主干,不排除不同分組患者有門靜脈分支內微小栓子形成,可能對研究結果造成一定的影響,且本研究樣本量偏小,還有待進一步擴大樣本量從而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利益沖突聲明:本研究不存在研究者、倫理委員會成員、受試者監護人以及與公開研究成果有關的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周鵬鴿負責課題設計、收集數據、資料分析、撰寫論文;盧高峰負責擬定寫作思路,參與資料分析、修改論文、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任笑盈、張濤參與收集數據、資料分析、修改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