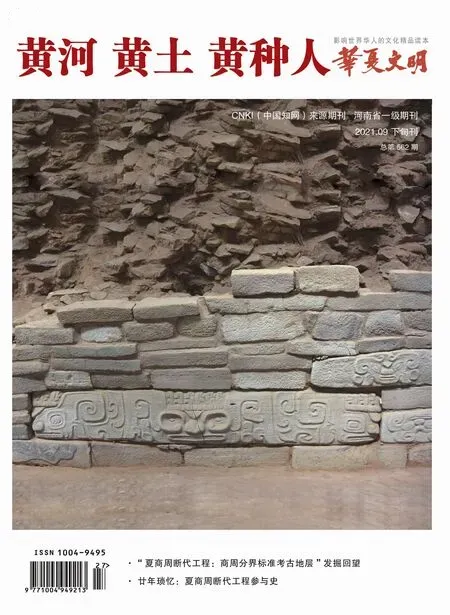中心與兩翼:五代北宋核心區越窯瓷業面貌研究
□郭璐莎
考古調查及發掘材料證明,上林湖窯區是五代北宋時期越窯的生產中心,東錢湖窯區及上虞窯寺前窯址群構成其重要的兩翼。由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對上虞窯寺前窯區的認識僅限于調查的材料,因此無法全面把握這一時期越窯的生產面貌。本文對比上虞窯寺前窯區各窯址、上林湖窯區寺龍口窯址、東錢湖窯區郭童岙窯址的出土材料,同時結合經過調查發掘的其他窯址材料,對它們出土的器物進行橫向及縱向比較,并據此討論三個窯區之間的關系。
一、出土器物特征
主要從器物種類、造型變化、紋飾與裝飾方法、稀有原料使用以及裝燒工藝等五個方面入手,對五代北宋時期三個窯區越窯生產的四個不同時段,即第一期(五代,907—960 年)、第二期(北宋早期,960—1022年)、第三期(北宋中期,1022—1077年)以及第四期(北宋晚期,1077—1127年)的器物進行分析。
(一)五代時期器物特征
由于東錢湖窯區相對缺少這一時期的器物,因此,分析主要圍繞上林湖窯區及窯寺前窯區出土的器物進行。
1.種類方面。寺龍口窯址出土碗、盤、盞、盅、執壺、缽、盒、套盒等器物共12種。相比之下,窯寺前窯區的器物種類就少得多,如付家嶺TG2出土的器物種類僅包括碗、執壺、罐等三種。
2.造型變化方面。表現最為突出的即是對金銀器造型的仿造。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并提升瓷器自身的價值及競爭力,越窯從唐代開始便出現許多模仿金銀器造型及紋飾的器物,這種對金銀器的工藝模仿在五代及北宋早期都有體現。這一時期上林湖窯區及窯寺前窯區出土的一些器物,如將碗、盤等器物的口沿加工成花口或葵口,將執壺的腹部制作成瓜棱狀,制成上下相套的方形委角套盒,以及托杯式及托臺式盞托等,在造型上與金銀器十分相似[1]。
3.紋飾與裝飾方法方面。現存的大量唐代越窯青瓷雖多以素面示人,但仍可見較多印花、刻畫花及堆塑貼花等裝飾工藝的運用。發展至吳越國早中期,這三種裝飾方法都變得極為少見,應當與此時制瓷工藝更加追求“類玉”效果有關。然而,杭州玉皇山錢元瓘墓則出土了一件極為罕見的釉下褐彩云紋盤龍罌(圖1),在窯址中很難找到具有與此裝飾手法相似的標本,應是為錢氏貴族特殊定制的不同于一般實用器的奢侈品。

圖1 釉下褐彩云紋盤龍罌
4.稀有原料使用方面。唐代的金銀器代表了當時金屬工藝的最高水平,同時金、銀這兩種材質作為貨幣也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因此,從唐代開始,越窯青瓷不僅在造型上對金銀器進行模仿,而且有些器物甚至直接使用金、銀進行裝飾,蘇州七子山五代錢氏貴族墓出土的金扣邊青瓷碗(圖2)和杭州玉皇山錢元瓘墓出土的涂金青瓷罌即是明證。上林湖窯址Y65出土了一件盤,口沿有刮釉現象,應是用來包鑲金銀邊的[2]115,它的出土為鑲嵌金銀邊找到了實物證據。

圖2 金扣邊青瓷碗
5.裝燒工藝方面。這一時期除了使用匣缽,還使用大量支具和墊具。匣缽以缽形及筒形為主,少見M形,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使用了一種原料與瓷器基本相同的瓷質匣缽(圖3),接口處涂釉封口,待器物燒成之后打破匣缽取出,因此與一般瓷質匣缽相比,這樣的匣缽無法重復使用。這種涂釉封口的瓷質匣缽出現于唐代晚期并一直沿用至五代。研究者表示,涂釉封口的瓷質匣缽隔絕了匣缽內部氣體與窯內氣體的交換,形成獨立的匣內還原氣氛,從而影響器物釉色[3-4]。且匣缽與坯件同質,所以它們的熱脹冷縮率相同,避免坯件在匣缽內出現移位現象,使器物足端比較光潔,從而減少次品,提高精品率[2]114。

圖3 執壺及匣缽
(二)北宋早期器物特征
這一時期的出土遺物數量較五代時期大幅度增加。
1.種類方面。寺龍口窯址新增的器物種類有水盂、熏爐、爐、洗、唾盂,目前已確認的種類至少有16種;東錢湖郭童岙窯址的器物種類有碗、盤、盞、盅、執壺、缽、盒、盞托、罐、水盂、杯等11種;窯寺前窯區的器物種類比第一期豐富得多,有碗、盤、盞、盅、執壺、缽、盒、套盒、盞托、罐、水盂、小碟、唾盂等共13種。三個窯區的器物種類相差并不明顯。
2.造型變化方面。仍然對金銀器的造型進行模仿,除了繼續將碗、盤等器物的口沿加工成花口或葵口外,與第一期相比,它們的足端變尖,并向外撇,這需要復雜的成型及裝燒技術。金屬器中有些器物的圈足足端十分輕薄且明顯外撇,是與器物主體分別捶揲成型再焊接起來的[5]。為了達到同樣的效果,越窯青瓷也通過接足的方式使尖圓外侈的圈足成為可能。因此,這一時期的器物總體上都呈現這樣的變化,但上林湖窯區的器物造型更為豐富,且式樣更為精致。
3.紋飾與裝飾方法方面。器物內部及表面纖細流暢、繁密嚴謹的細線劃紋樣與金銀器的許多裝飾紋樣如出一轍,例如,以纏枝紋、寶相花紋、龜心荷葉紋為主題的植物紋,以蝴蝶紋、仙鶴紋、鸚鵡紋為主題的動物紋,還有少量的龍紋、鳳紋及人物紋,同時器物的口沿等處還飾有卷云紋、半花紋等附屬紋樣[6]。(圖4)若仔細觀察,則能發現與金銀器的利鏨刻剔工藝極為相似,細線劃花除了用于組織輪廓造型外,還應用于花紋的細部處理,最典型的是花瓣和闊葉內筋脈的處理[5]。同時,半浮雕效果的蓮瓣紋也常常裝飾在碗、盤和唾盂的外腹,有些器物內底戳印蓮子。對比三個窯區器物的紋飾,發現上林湖窯區寺龍口窯址出土的器物涵蓋了上述各種紋飾,最為豐富,同時也最為精致;上虞窯寺前窯區各窯址的紋飾不論在豐富程度上還是在精致程度上幾乎可以與上林湖窯區媲美(圖5);東錢湖郭童岙窯址的紋飾則相對單調得多,除了少量的蝴蝶紋、鸚鵡紋及蓮瓣紋外,大部分器物的內壁或內底都為簡單的細線劃云草紋。

圖4 花鳥紋碟

圖5 鳳紋碗
4.稀有原料使用方面。至目前為止,窯址中并沒有發現以金、銀作為裝飾的器物,這可能與越窯青瓷開始使用大量的精細劃花有關,由于在尋求自身裝飾途徑上有較大突破,因而減少了以金、銀等作為裝飾的情況。
5.裝燒工藝方面。這一期的裝燒窯具、支具等與上一期相比有了許多變化。第一,大量使用墊圈,由于出現了大量足墻較窄且向外撇的圈足器物,若仍如以前那樣使用泥點或泥條墊在器物的足緣上,那么在墊燒過程中,器物的重量會全部落在足端,這樣必定會使其承受過大壓力而塌陷。使用墊圈支在器物的外底圈足內,使得器物的重量承在器物的底部,受力面積增大,有利于器物的燒成。第二,M形匣缽的大量使用,由于器物內底常飾有精美花紋,若疊燒,則會在器物內底留下痕跡而影響器物美觀,因此這類器物必須使用匣缽單件裝燒。若仍用第一期盛行的缽形及筒形匣缽,則會因為匣缽太高而占用窯內空間從而造成浪費。因此,這一期出現了大量較為低矮的M形匣缽,許多M形匣缽的外底還刷一層稀薄的淡青色釉,從而避免焙燒過程中砂灰對器物的影響。
(三)北宋中期器物特征
出土遺物仍然非常豐富,但與第二期相比有明顯變化。
1.種類方面。寺龍口窯址新增器類有夾層碗、五管燈及韓瓶,但套盒、爐、洗、唾盂都不再出現,共有種類約11種;東錢湖郭童岙窯址的器物種類與第二期相比幾乎沒有區別;窯寺前窯區也是如此,但與上林湖窯區相似的是,套盒、唾盂等在這一期的地層中也不再出現。
2.造型變化方面。胎體普遍變厚,器物的底部增厚,同時碗、盤、盞等器物的圈足變高、變厚。器物的造型變化較少。
3.紋飾與裝飾方法方面。不僅繼續使用劃法,還使用大量的刻法,一般采用斜刀。刻、劃或單獨使用,或結合使用。碗、盤、盞等器物的內底腹常刻多重蓮瓣、摩羯紋、牡丹紋,也有少量刻鳳紋,細線劃的云草紋、簡菊紋有時作為主題紋樣裝飾在碗、盤等器物的內底,有時作為附屬紋飾裝飾在執壺、罐、缽等器物的表面。同時,屏風式的布局方法也是這一期的特點,執壺的腹部一般用雙線凸棱分隔成4個或6個部分(圖6),碗、盤等器物內腹則用雙線分成5個部分,在其間用刻畫花技法裝飾一些圖案。上林湖窯區與窯寺前窯區出土器物的紋飾內容較為豐富,刻畫運用自如;東錢湖郭童岙窯址的器物仍然沿用大量細線劃云草紋,只是更為草率,寥寥幾筆即成,刻花內容大多以多重蓮瓣為主,其他少見。東錢湖另一處窯址上水岙的出土器物則要精美得多,細線劃花與粗刻花并用,既有蓮瓣紋(圖7)、牡丹紋等植物紋樣,也有摩羯紋、鴛鴦紋等大量動物紋樣[7]。

圖6 執壺

圖7 雀繞牡丹蓮瓣紋缽
4.稀有原料使用方面。不再使用金、銀等貴金屬來裝飾瓷器。
5.裝燒工藝方面。仍以M形匣缽為主,還有少量筒形、缽形匣缽。墊具有墊圈、復合形墊具等,由于器物的圈足變高,墊圈也變高,同時變得較細長。在裝燒工藝上,這一期除了使用匣缽單件裝燒外,還開始出現碗、盤等器物的明火疊燒。
(四)北宋晚期器物特征
瓷器的器類及風格大體承襲第三期。
1.種類方面。與第三期相差不大,但韓瓶數量陡增。
2.造型變化方面。器物內底厚度再次增大,有些圈足變得更高,有些圈足則變得矮小內束。
3.紋飾與裝飾方法方面。大多數器物為素面,少數器物如碗、盒、高足盂外腹及器蓋蓋面上采用開光布局的裝飾手法,紋飾主要為刻畫太陽紋、菊花紋及摩羯紋。
4.稀有原料使用方面。不再使用金、銀等貴金屬來裝飾瓷器。
5.裝燒工藝方面。由于這一期器物大多為明火疊燒,只有極少數器物為匣缽裝燒,因此支具和墊具的數量及種類很多,相應地,匣缽數量很少,且主要為缽形。墊具大部分為墊圈,且高度更高,出現了喇叭形墊具、束腰形高墊圈,另外還有覆盂形、缽形墊具,筒形和僧帽形支具等。從裝燒工藝來看,大部分器物為明火疊燒,甚至于內底刻畫花紋的器物也由明火疊燒而成。
二、三個窯區的共時性分析
上林湖窯區器物種類最為豐富,造型變化最為多樣,紋飾與裝飾方法最為精美,在窯址中能找到使用稀有原料作為裝飾的標本,在整個五代北宋時期都是越窯青瓷生產的中心;上虞窯寺前窯區的器物種類、造型變化以及紋飾與裝飾方法稍遜于上林湖窯區,第一期器物產量較少、質量也比較低,應當用于試燒,第二期器物技術特征與上林湖窯區十分接近,已明確成為越窯青瓷生產的重要一翼;東錢湖窯區目前相對缺少第一期產品,與上虞窯寺前窯區相比,其成為另外一翼的時間較晚,從器物質量來看,第二期所生產的器物與另外兩個窯區相比有較大差異,從第三期開始質量才不相上下。
具體來看,上林湖窯區從唐代開始就成為越窯生產的中心,發展至五代北宋,仍然在越窯發展歷程上占據中心地位,不論從其生產規模上還是從產品質量上都可以看到這一點。研究者以往依據調查材料認為東錢湖窯區的生產期在五代北宋,產品質量比上林湖稍差,但是與上虞窯寺前窯區相比更為精美,其出路很可能以外銷和進貢為主[8-9]。然而,隨著考古調查的深入及發掘資料的更新,發現東錢湖窯區的生產期可能并沒有早至五代;其產品也說不上比上虞窯寺前窯區好;最后其出路很可能以外銷為主,因為東錢湖窯區的發展與它靠近明州港有很大關系,有研究者提出明州在晚唐五代時期貿易地位并不突出,其城市規模無法與周邊的杭州及揚州等地媲美的觀點[10],這可能也是東錢湖窯區的窯址缺乏第一期產品的原因所在。
另外,上虞地區瓷業遺存延續時間更長,唐代以前上虞地區是早期越窯的生產中心,盡管到了唐代,上林湖地區的瓷業發展更為迅速且占據了生產中心的位置,然而上虞當地悠久的制瓷傳統并未消失,唐代仍在繼續保持生產,一直延續至五代北宋,因此上虞地區存在第一期至第四期的瓷業遺存。而對東錢湖的調查發掘顯示,75%的瓷業遺存都屬于第三期至第四期。這兩個窯區的發展軌跡并不相同,上虞地區的生產從未間斷,且與上林湖窯區的生產軌跡相一致,其產品除了供應社會需求外,主要用于上貢,同時可能用于外銷。而東錢湖窯區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民眾需要外,則主要用于外銷,同時可能承擔一定的上貢任務。
三、三個窯區的歷時性分析
第一期器物在造型上對金銀器的模仿既需革新技術還需精工制作;有些器物使用金、銀等貴金屬來進行裝飾,也體現了器物在追求精致化程度上的技術改進;使用封口釉的瓷質匣缽也體現了生產過程中對精致器物的燒成技術要求,瓷質匣缽與制成器物的原料相同,這就使得匣缽制成成本增加,最終導致產品成本提高,因此,這些精致器物的供應對象應為上層社會。此時的生產不僅有面向民眾的一般化生產,還有面向貴族的精細化生產。五代吳越國時期,越窯青瓷尤其是“秘色瓷”的生產尤為重要,是維系其政治、經濟關系的主要渠道之一,越窯窯址以及當時貴族墓葬中所出土的大量“秘色瓷”就是明證。
第二期器物除了繼續對金銀器進行造型上的模仿外,還使用大量與金銀器相似的紋飾,瓷質匣缽數量減少,但為了增加產量及提高質量,窯工大量使用涂了釉的M形匣缽及墊圈,表明這一階段產量增加,且依然延續了第一期的一般化生產和精細化生產。從北宋建立政權(公元960年)到吳越歸宋(公元978年),上貢越窯青瓷的數量激增,上林湖窯區的生產已經供不應求,窯寺前窯區及東錢湖窯區的及時補給保證了當時的生產。由于上貢需求,此時的器物仍然需要在質量上“把關”,同時還需提高產量。
第三期器物種類趨于單調,在造型上更注重實用性,紋飾與裝飾方法操作起來更為簡便,應是為了減少生產時間從而降低成本,在裝燒工藝上也能明顯顯示出這一點,顯然,北宋中期以后三個窯區的產品質量開始走下坡路。
第四期器物種類迅速減少,出現大量韓瓶,同時器物粗厚且表面多沒有裝飾,即使少量器物內底有刻畫花也極為潦草,幾乎都為明火疊燒而成,顯然這一時期窯工為了盡可能節省成本,
在制成產品的各個階段都顯得十分粗放,但從調查及發掘情況來看,第四期生產產量仍然不容小覷。當地普通居民對越窯產品仍有極大需求,這說明當地越窯制瓷業仍然能夠獲得利潤并得以生存。
四、結語
上虞窯寺前窯區出土的窯址材料表明,其生產面貌與上林湖窯區的生產面貌更為相似。同時,改變了以往學者所認為的上虞窯寺前窯區的產品不如東錢湖窯區產品的既定印象。不同時段的器物在種類、造型變化、紋飾與裝飾方法、稀有原料的使用及裝燒工藝的差異,顯示瓷業生產在技術革新、社會需求條件下做出的不同反應。技術革新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期對其他材質如金銀器的造型進行模仿,以及為了生產出還原焰下的青綠釉面而發明了瓷質封釉匣缽。第二期對金銀器紋飾進行模仿,為了增加器物產量同時又保證器物燒成質量而發明了涂釉匣缽及墊圈等。從第三期開始,器物在造型上更為實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器物底部明顯增厚,不再模仿金銀器式樣的尖細撇足;而刻畫花的大量使用,一方面放棄了越窯以釉取勝的優勢,另一方面也沒有將其第二期的細線劃花繼續發揚光大,反映的是瓷業生產在技術革新上不再投入更大的精力。第三期及第四期的器物在各個方面如造型、紋飾、裝燒工藝等方面都顯示出減少生產時間以獲取利潤最大化的特點,這與北宋政府在這一時期將越窯青瓷作為獲取經濟利益的重要渠道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