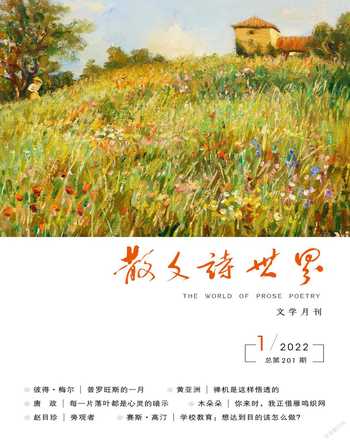空 闊 組章
郭 輝(湖南)
雪雁飛
晴空一碧如洗。
雪雁飛——多像是天使抖開的一匹玉色絲絹。
湛藍湛藍的天壁,抹上了一連串一連串透亮的啼叫。然后,又一滴一滴拂拭下來,撒落在坦蕩如砥的大野之上。
清遠,明澈,充滿了節奏感和幸福感。
我仰起頭來,看到那些高八度的音節,一閃一閃,發著光,并且有形有狀——
如一只只高腳琥珀杯,盛滿了對愛的想象和沖擊力,以及追夢者的情愫。又如一片片潔白的雪花,飄飄而下,儲滿了勃勃生機。
我忽發奇想——
今天,氣象從容,萬事萬物都感覺到了神的存在。
這華色含光的日子呀,或許,正是雪雁的生日。
多么美好,多么祥瑞——動態的鮮活的如天空一樣闊大的生日。
黑翼角鼓動著的魂靈,把萬里藍天,當作了永遠飛翔,生生不息的
——巢穴!
尋芳記
時令已是秋寒了,卻聽得說,山深處,有一個叫七里村的茶園,還開著氣數未盡的花。
——就去。
山路瘦長瘦長,依稀可辨,就像是誰在故鄉的皮膚上,撓出來的一道淺痕。
走在上頭,能感受到它對我們的陌生感,和幾許明顯的不屑。
路邊的茅草脫盡了水色,焦黃焦黃,有的冷若冰霜,有的陰陽怪氣,使眼底下的山野,愈顯蒼涼。
而掠過鼻尖眉梢的寒風,似手也愈加傷感。
多虧有一個穿著紅色羽絨服的女孩,一邊走,一邊哼著莫名的曲子。
曲子顛顛簸簸,卻給我們的尋找,增添了一點意趣與暖色。
翻了一道坡又一道坡。
過了一座坳又一座坳。
遇到過幾戶山里人家,有點頭的,有搖頭的,有的說是在上七里,有的說是在下七里。
有一位年過花甲的大爺,自愿做向導,領著我們在山里頭,左一轉,右一轉,好不容易尋到一個小水庫,壩上有一棟木房子,房子旁有一個苗圃,但早已人去房空,草木凋敝……
最終,我們什么也沒有找到。
茶園呢?花呢?芬芳呢?
都像是隱匿在時間之外,人間的秩序之外……
龍拱灘
水要遠去,船要遠去。
而一條龍,把傳說與風骨,留在了那里。
那年五月,我帶著年幼的小妹,去到龍拱灘邊。
水色正清涼,草色正迷茫,綠芝麻開出了眾多的小白花,就像是準備淹滅春光的一場無情雪。
忽然起風了,起云了,灘頭的白楊樹,綠葉子一片沙沙響。
要下雨了嗎?我對人間氣象暫且一無所知。
荷鋤的祖父告訴說——
晚上灘響,白天晴朗;晚上無聲,白天雨淋。
小妹問:為什么呀?
祖父答:龍作怪呢。
我嚷嚷著要看龍,看龍口中的大寶珠。
祖父指一指江上——
雨天看龍,龍在霧中,忙著施法;晴天看龍,龍在水中,忙著拱灘……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
故地重游,祖父早就不在了,我也老了。而且,傳說也舊了,江水也淺了,灘涂也瘦了。只有一座新修的攔江大壩,巍巍然站在龍拱灘上首,挺著腹,昂著頭。不可一世的樣子,
仿佛是它鎮住了龍,又仿佛是在告白塵凡——
拱得翻的,那叫龍椅;拱不動的,那叫江山!
化粑
過了大半輩子了,一直是待在資水河邊的三堂街上。
甚至沒有上過一次縣城。
從沒有過故鄉的概念。就像谷米子磨成粉后做成的化粑粑,從來不把那一格格黃篾蒸籠,當作自己的故鄉。
父親早早就死了,只有娘親帶著他,苦捱苦捱地過日子。
渡船碼頭上首的飯鋪里,剛出籠的白生生熱騰騰的化粑,天天香氣撲鼻。
他常常叫化子一般望著,望著,饞得流口水。
好心的大師傅躍爹,只要瞅著沒人了,就會偷偷塞給他一個。有時還叫他,給娘也帶上一個。
化粑粑軟,化粑粑甜,怎么吃也吃不厭。
讀了三個四年級后,他寧愿被打死,也再不去上學了。
憑著蠻蠻的一副身板,幾斤蠻勁,他天天跟著街上的搬運工,下碼頭擔石灰,擔河沙,擔鵝卵石,掙上幾個小錢。
多多少少,為娘減輕一點負擔。
可是后來,娘一撒手,也撇下他走了。
他只得一個人討生活。
在白鐵鋪里,打過克鐵匠的下手;去白合庵旁的茅棚子底下,守過堯絲村的山;還在河里駕過吃唱拉撒睡都在一起的渡船。
手里有幾個錢,就去買化粑粑,常常是一日吃上三餐。
街坊們都說,他就是吃化粑的命……
我再次見到他時,是三十多年之后了。
在一場喜宴上,席面快要散了,他端坐于一張杯盤狼藉的桌子邊,顧自吃著殘羹剩飯。
頭發僵亂,臉面油黑,皺紋如鏤。特別打眼的,是一臉的蔸腮胡子,像一蓬入冬的野草,里頭還裹著兩三粒白米飯。
目光遲滯,旁若無人,像是一尊泥塑。
我心里頭不由一緊,一時百味雜陳,百感交集。
如果走上前去,他會認得出我這個兒時的玩伴嗎?
我早就忘了他的真名實姓了,但一下子就記起了他的小名——化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