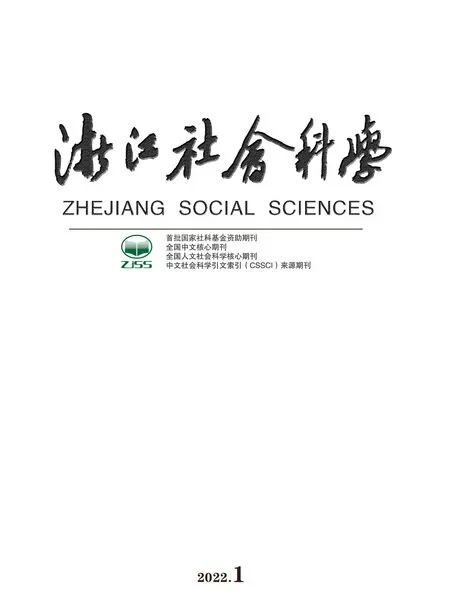碳排放權交易是否促進企業投資效率?*
——基于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的準實驗
□ 張 濤 吳夢萱 周立宏
內容提要 碳排放權交易政策是我國實現“雙碳”戰略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利用企業分批、分期進入碳市場這一準實驗,評估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與作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碳排放權交易能夠有效提升企業投資效率,這一作用主要體現在緩解企業投資不足,而對企業過度投資的影響有限。考慮平行趨勢問題、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仍然成立。進一步分析發現碳排放權交易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減輕政策性負擔以及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等途徑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積極影響。并且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投資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低碳排放行業以及非國有企業中更為明顯。本文結論可為加快全國統一碳市場建設提供參考,對于實現“雙碳”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一、引言
碳排放權交易(以下簡稱“碳交易”)是指通過配額制度確定碳排放權初次分配,將過度排放的外部性內部化,同時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對排放權進行再次分配,減少控排帶來的效率損失。2021年2月1日起《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管理辦法》”)開始施行,厘定了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以下簡稱“全國碳市場”)的基本框架,2021年7月16日全國碳市場正式啟動交易。在碳排放權交易之外,我國也展開了其他與碳排放相關的金融產品創新。2021年7月,浙江省麗水市通過《關于全面推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示范區建設的決定》,提出“開展碳排放權質押、碳匯質押、碳賬戶、碳期貨、碳期權等碳金融創新”,拓展了碳交易的產品和方式,是對在更大范圍內發揮市場減碳能力的積極探索。對已有的碳市場交易經驗進行總結,能夠為全國碳市場建設和先行示范區的碳金融創新提供重要的經驗參考。
碳排放導致的氣候問題是經濟增長的附屬產物(趙昕東和沈承放,2021)。基于產權理論和生態現代化理論衍生而來的碳市場能夠解決碳排放的負外部性問題(曾文革和黨庶楓,2017),是我國實現高效減碳的重要制度安排。但碳市場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從2013年開始,我國先后在深圳、北京、上海等省市開展碳交易試點工作,不僅積累了配額確定、交易規則制定等政府規制經驗,參與碳交易的企業也在碳盤查、 碳交易和碳資產管理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為建立全國統一的碳市場奠定了基礎。碳交易制度是實現“雙碳”戰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積累的減碳“中國經驗”。碳市場不僅能夠調節碳排放的負外部性,同時也可能對企業創新和產業升級等產生溢出或抑制作用,影響企業價值、生產效率和財務績效等(沈洪濤和黃楠,2019;周暢等,2020)。但當前關于碳交易政策對微觀市場主體影響的研究尚未涉及到企業投資效率層面,碳交易政策如何影響企業投資效率,亟待學術界給出經驗證據。
本文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隨著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應用范圍的不斷擴大和對企業行為影響的不斷深化,本文研究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進一步豐富了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影響企業投資行為的經驗證據;第二,本文考察了多批次碳交易試點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樣本范圍更大、研究結論更為科學;第三,已有文獻大多將碳交易試點地區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對政策微觀影響衡量的精確度較為有限,而本文通過手工收集2013~2016年各個試點納入碳排放交易的企業名單,將試點企業名單數據與上市公司數據相匹配,以此精確篩選出參與碳交易的企業。
二、制度背景與理論分析
(一)我國碳排放權交易的制度背景:從CDM到全國碳市場
市場無法自發解決環境污染導致的外部性問題,從而產生了對于政府環境規制政策的訴求。根據環境規制對經濟主體的不同約束方式,通常可分為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和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碳交易政策就是典型的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排放權交易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經濟學家庇古提出的“庇古稅”,主張通過征稅或補貼來彌補市場失靈所引起的環境過度污染問題,但“庇古稅”的弊端在于很難量化污染的外部性。而后“科斯定理”給出了優于“庇古稅”的解決辦法:通過明確的產權界定將排污的外部性內部化,借助市場機制可以將排污控制在最優水平。
相比于歐美等發達國家,我國碳交易市場建設起步較晚,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2~2012年,這個階段的市場機制主要是項目層、收益性的、單向的國際交易。中國可以通過國際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將“核證的溫室氣體減排量”出售給發達國家。第二階段為2013~2020年,是碳市場的培育發展階段。2011年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發改辦氣候 〔2011〕2601 號),批準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及深圳7 個省市開展碳交易試點工作。2013年7 個省市先后發布各自的碳交易管理辦法,并正式啟動碳市場,2016年福建省成為全國第8 個碳交易試點地區。表1 簡單梳理了我國各個碳交易試點的基本情況。第三階段為2021年全國碳市場啟動交易,標志著我國碳交易進入全國統一市場階段。《管理辦法》規定了全國統一的重點排放單位標準,并確定碳排放配額總量和分配方案由生態環境部根據國家要求制定。全國碳市場啟動結束了各試點碳市場“各自為政”的情況,將碳市場的調節功能放大到全國范圍。
碳交易政策作為一種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以“誰污染,誰付費”為原則,通過價格機制將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內部化,約束企業的碳排放總量。該制度具體實施過程為:首先,政府根據環境容量確定整體減排目標,即實現總量控制;其次,按照一定的納入標準確定試點企業;再次,各試點地區選擇基準法或歷史法將初始碳排放權分配給納入碳交易體系的企業;最后,企業基于自身成本約束,選擇在二級市場買進或賣出碳排放權。由于存在經濟激勵,減排成本相對較低的企業會率先進行減排,并通過出售多余的碳排放權獲取額外收益,減排成本較高的企業則通過購買碳排放權來降低減排成本,以此實現全社會減排成本最小化。
(二)碳交易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理論分析
關于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理論界存在兩種對立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碳交易政策會產生履約成本和控排成本,影響企業內部資源配置效率,導致投資偏離最優水平;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碳交易政策能夠激勵企業創新、優化企業資源配置、緩解委托代理問題,同時還能減少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提高企業投資效率。

表1 中國各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情況
直觀地看,不論是政府制定減排要求、征收污染稅還是排污權交易都會產生新的成本,使企業生產偏離原定的最優狀態(林伯強等,2021)。原因在于環境規制加大企業污染治理成本和制度遵循成本(Gray & Shadbegian,2003),部分企業可能會采取減產、停工等措施(Petroni et al.,2019),擠出企業正常投資,降低投資效率。史敦友(2021)研究發現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工具可能會產生技術創新“擠出效應”。隨著各試點市場對于配額的分配越來越嚴格,企業面臨的減排壓力越來越大,企業被迫將大量資金投入到減排設備購置和減排技術改造上,導致投資不足現象更加嚴重。此外,很多企業重履約而不重交易,將參與碳交易視作改善與政府關系的途徑,而不是一種低成本降碳的方案(Yang et al.,2016),這種隱形的政府干預同樣可能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負面影響。由此可見,碳交易政策作為一種環境規制會使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卻可能沒有產生節約減排成本的作用,從而損害企業投資效率。
關于碳交易對企業投資效率正面影響的研究,主要有“波特假說”和信息顯示理論。基于“波特假說”的理論分析認為環境規制,尤其是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Jaffe & Palmer,1997),能夠提高企業的研發投入力度,通過倒逼企業進行設備升級或投資相關技術來提高盈利能力,以削減環境規制帶來的高額成本支出 (Rassier & Earnhart,2015;陳屹立和鄧雨薇,2021;萬攀兵等,2021)。這將使企業的生產效率隨之提高,并進一步促進企業投資效率的提升。此外,環境規制可能表現為一種外部壓力,這一外部壓力有利于企業克服投資惰性,并與內部治理機制形成互補關系,轉化為促進企業投資效率的激勵因素(Ambec & Barla,2002)。基于信息顯示理論的分析則認為,不同于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碳交易政策通過再造一個交易市場,減少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和委托代理問題,可能會在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減輕企業政策性負擔等方面發揮其積極影響,從外部提高企業投資效率(許東彥等,2020)。此外,配額過剩也可能是碳交易政策提升企業投資效率的途徑,從歐盟的碳交易市場數據來看,歐盟制定的配額總量目標遠高于實際排放,導致配額規制無效,甚至企業可通過配額獲利。配額過剩使獲得碳排放權交易資格的企業不受配額約束,同時還能享受到加入碳交易市場帶來的政策優惠和信息顯示優勢,以較低成本獲得資金,從而提升企業投資效率。
綜上所述,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需要規范的實證研究進行檢驗。尤其是在建設全國碳市場和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開局之期,理清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能夠為我國進一步完善碳市場建設提供必要參考。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說明
1. 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企業投資效率,根據Richardson(2006)的研究,以企業實際投資水平與期望投資水平的殘差作為企業投資效率的代理變量。若殘差大于0,表示過度投資,記作overinv;若殘差小于0,表示投資不足,本文對殘差小于0 的值取絕對值,記作underinv。另外,本文還對整體殘差值取絕對值(noninv)用以表示企業的非效率投資,noninv 值越小,企業的投資效率越高。
2. 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以企業是否被納入碳交易(did)作為核心解釋變量,若是則取值為1,否則為0。基于手工收集整理各碳交易試點地區公布的納入碳交易企業名單①,通過各企業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與上市公司數據庫相匹配,將被納入碳市場交易的企業賦值為1,否則為0。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各地區發布的碳交易企業名單會有所調整,既有一些因倒閉破產而退出的企業,也有新增參與碳交易的企業,但由于各地歷年新增上市企業不多,且本文已剔除破產企業,因此本文以2013~2016年各試點地區第一批被納入交易的企業作為處理組。
3. 控制變量
本文的控制變量分為兩類:一是企業層面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lnsale)、企業年齡(age)、企業現金持有量(cash)、企業負債率(tl)、總資產收益率(roa)、企業是否為國有控股(soe)以及是否兩職合一(dual)。企業規模(lnsale)以當年該企業營業收入的對數來測算;企業年齡(age)以樣本所在年份與企業成立年份之差進行量化; 現金持有量(cash)主要通過貨幣資金及交易性金融資產與企業總資產之比來度量;企業資產負債率(tl)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來衡量;總資產收益率(roa)為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重;企業是否為國有控股企業(soe)主要根據企業的國有股占比是否超過50%進行賦值,若是則定義為1(即絕對控股),否則為0;兩職合一(dual)即以企業總經理與董事長是否為同一人來取值,若是同一人則為1,否則為0。二是城市層面控制變量,具體包括地區GDP 的自然對數(lnGDP)、第二產業比值占GDP 的比重(industry)。
(二)模型設定
考慮到碳交易政策在不同地區并不是在同一時間發生的,而是各試點地區分批分期逐步展開。因此,本文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法對碳交易政策與企業投資效率間的關聯進行定量評估。基準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i 表示城市,j 表示企業,t 表示年份。變量noninvijt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表示i 城市t年份j 企業的非效率投資程度,該值越小,則企業的投資效率越高。變量didjt為核心解釋變量,表示第t年j 企業是否可參與碳交易,被納入碳交易的企業則取值為1,否則為0;λt為年份固定效應;μj為企業固定效應。Xjt和Zit分別指代模型中企業層面及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εijt是隨機擾動項。系數β1反映的是碳交易政策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具體影響,若β1>0 則說明碳交易政策將促進企業的非效率投資;反之則對企業非效率投資有抑制作用。
(三)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為有效分析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本文選取2007~2019年中國滬深A 股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對象,并根據以下原則對樣本進行篩選:第一,剔除ST、ST*以及PT 等非正常交易企業;第二,剔除金融行業企業樣本,主要是考慮到金融行業的特殊性,其會計準則與其他行業會計準則有較大差異;第三,剔除財務數據嚴重缺失以及數據極端異常的樣本。本文所涉及的企業層面數據主要來源于CSMAR 以及Wind 數據庫。城市層面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碳排放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碳排放數據庫(CEADs);還有部分指標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工業統計年鑒》;納入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企業名單通過各個試點所披露的數據手工收集。此外,為避免離群值對回歸結果造成影響,本文對連續變量進行了1%和99%分位處的縮尾處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見表2。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為研究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本文將是否參與碳交易(did)作為解釋變量,企業非效率投資程度(noninv)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下表3 列(1),在控制相關變量、年份效應及個體效應的情況下,參與碳交易能夠顯著抑制企業的非效率投資程度,即碳交易政策能夠促進企業投資效率。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參與碳交易倒逼企業優化內部投資決策;第二,在碳交易制度下,高碳排放企業通過購買碳排放權來降低其減排成本,低碳排放企業通過出售碳排放權獲得資金收益,從而提升企業的投資效率。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3 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基準回歸
進一步地,文章分析了碳交易對過度投資(overinv)以及投資不足(underinv)的影響。從表3列(2)可以看出,參與碳交易對企業過度投資無顯著影響,可能的原因在于企業以減碳投資對其他投資用途進行替代,使企業投資組合符合低碳發展要求,雖未緩解過度投資,但可能提升企業的節能降碳能力。從表3 列(3)可以看出,碳交易政策顯著緩解了企業投資不足的情況。可能的原因在于納入試點的企業在向社會公布碳排放量的同時也傳遞給社會自身產能較大、實力較強的信息,從而更容易獲得外部融資支持,緩解企業投資不足的問題。綜合而言,碳交易市場的信號顯示功能和優化投資組合功能同時發揮作用,過度投資企業本身可能受融資約束較弱,參與碳交易主要起到優化投資組合作用,但對過度投資抑制作用有限,這一點從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為負可以簡單判斷;對投資不足企業,參與碳交易則同時起到緩解融資約束和優化投資組合作用,顯著提升企業投資效率。
(二)平行趨勢檢驗
雙重差分法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在政策事件發生前,處理組和對照組的變化趨勢應該是一致的。就本文而言,企業的非效率投資程度是否在碳交易政策實施之前就存在下降趨勢這一問題尤為重要。為此,本文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平行趨勢檢驗。首先文章構建了衡量企業是否納入碳交易的時間差變量,pre_ 代表樣本被納入碳交易前與被納入碳交易當期的時間差;post_ 代表樣本被納入碳交易后與被納入碳交易當期的時間差;current 代表樣本企業被納入碳交易的年份。若雙重差分法檢驗結果是穩健的,那么在current 之前的時間差不應該顯著抑制了非效率投資。本文參考Alder et al.(2013)的做法,將模型(1)擴展為模型(2):

其中t 表示年份,currentj表示j 企業被納入碳交易的年份。式中的取值方式為當tcurrentj=n 時,取值為1,否則為0。在這一檢驗中,文章重點關注系數τn。如圖1 的結果所示,在企業被納入碳交易之前(pre_5 至pre_1),回歸結果顯示碳交易政策對企業的非效率投資程度無顯著影響; 而在企業被納入碳交易之后(post_1 至post_3)的第三年,碳交易政策對企業非效率投資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已有文獻證實碳交易的政策效應存在較長的周期性(李治國和王杰,2021),因此這一滯后性結果可能與政策效果表現滯后以及政策實施初期碳交易的具體制度不健全有關。

圖1 平行趨勢檢驗圖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按以下方法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 首先,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樣本選擇性偏誤,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緩解這一問題,再利用雙重差分法來估計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其次,為減少模型的系統性偏差,將企業的非效率投資按照大小劃分為三分位組,并剔除中間組樣本,重新對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最后,為保證投資效率指標不受新增投資衡量方式的影響,參考劉慧龍等(2012)的方法,改變企業投資的衡量方式并重新對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經過上述一系列穩健性檢驗,本文發現碳交易政策能夠顯著提升企業投資效率②。
五、進一步檢驗
(一)機制分析
為進一步明確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機制,本文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分別對企業融資約束、 政策性負擔以及企業技術創新等作用變量進行檢驗。具體地,首先,融資約束是衡量企業外部融資難易程度的指標。現有文獻中關于融資約束的衡量指標主要有KZ 指標、WW 指標以及SA 指標等。為了避免內生性的影響,本文主要參考Hadlock & Pierce(2010)的研究,選取企業規模(size)以及企業年齡(age)這兩個外生指標來構建融資約束指標(sa),計算公式如式(3)所示:

其次,政策性負擔分為社會性政策負擔和戰略性政策負擔,本文主要參考林毅夫等(2004)的研究,以企業實際資本密集程度與企業按要素稟賦決定的最優資本密集程度之差進行衡量,計算公式如式(4)所示:

其中,cit即為估計出的企業最優資本密集程度(資 本/勞 動 力);sizet-1、levt-1、roat-1、growtht-1以 及tangt-1分別表示t-1年的企業規模、 資產負債率、資產收益率、成長性以及資產結構,其中資產結構以固定資產凈值占總資產的比重來衡量。同時還控制了地區效應、行業效應及年份效應。殘差δ 即為模型關注的指標,表示企業實際資本密集程度與最優資本密集程度的偏離。文章以δ 的絕對值作為政策性負擔(ovci)的取值。若δ>0,說明企業實際資本密集程度超過了最優資本密集程度,代表企業的戰略性政策負擔(overci);若δ<0,說明企業實際資本密集程度低于最優資本密集程度,表現為企業冗員過多或員工福利承受壓力大,代表社會性政策負擔(undci)。
最后,本文以企業申請的發明專利衡量技術創新指標(invent)。用這一指標原因在于:其一,盡管已有文獻大多將企業研發投入作為企業創新研發的代理變量,但考慮到技術創新活動所具備的高風險特征,研發投入轉化為企業創新產出的難度較大,因此用這類指標測算將存在高估企業創新能力的可能;其二,根據中國專利法,現有的企業專利分為發明專利、 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三種類型。其中,發明專利代表的是企業產品與方法上的創新,相比于其他兩類專利技術含量更高,因此發明專利更能體現企業的創新能力以及核心競爭力。基于此,本文用企業申請發明專利數量來度量企業創新,具體度量公式為invent=ln(發明專利數+1)。
1. 緩解融資約束
根據MM 理論,在完美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投資決策以及投資行為與其資金結構無關。但在現實情況下,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問題會加大企業的融資成本,導致融資約束。基于此,本文試圖探究融資約束是否為碳交易政策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機制。具體以融資約束(sa)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4 列(1)所示,結果表明在控制相關變量、年份效應以及個體效應后,碳交易政策顯著緩解了企業的融資約束。由此可知,通過參與碳交易可能能夠減少信息不對稱和委托代理風險,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從而提升企業投資效率。
2. 抑制政策性負擔
政策性負擔(ovci)作為企業效率低下和預算軟約束的根源所在,將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負向影響。政策性負擔又分為社會性政策負擔與戰略性政策負擔。其中,社會性政策負擔主要是由于企業雇用過多人員,致使其資本密集程度低于以要素稟賦決定的最優資本密集度; 戰略性政策負擔指的是企業投資于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所產生的負擔。為了檢驗碳交易政策是否通過影響政策性負擔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文章對碳交易政策與政策性負擔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表4 列(2)結果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實施對企業的政策性負擔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進一步地,文章檢驗了碳交易政策對社會性政策負擔(undci)與戰略性政策負擔(overci)的影響。從表4 列(3)可知,碳交易政策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抑制企業的社會性政策負擔,列(4)則顯示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戰略性政策負擔無顯著影響。由此可知,碳交易政策可能通過緩解企業的社會性政策負擔來提升企業投資效率。
3. 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波特假說”指出適當的環境規制對于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使企業的生產能力得到提高,同時抵消環境規制所帶來的制度成本。考慮到企業創新行為是由一系列投資決策及行為產生的,因此本文試圖探究碳交易政策是否通過技術創新這一機制來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由表4 列(5)的檢驗結果可知,碳交易政策顯著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從而“波特假說”得到驗證,說明碳交易政策的實施能夠激勵和推動企業進行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形成的先行優勢以及其帶來的潛在收益進一步反饋于企業的投資效率,由此帶來企業投資效率的提升。
(二)異質性分析
1. 行業碳排放強度差異
為了進一步探討碳交易政策對投資效率在行業層面的異質性影響,本文依據碳排放強度將行業劃分為高碳排放行業和低碳排放行業。參考余壯雄等(2020)的方法,首先計算各行業的碳排放強度,即利用各行業能源消費品的碳排放量分別除以各自的工業銷售產值;其次,基于全國各行業碳排放強度的年度中位數將所有行業分為高碳排放行業與低碳排放行業③。若某行業在某年的碳排放強度高于所有行業的中位數,則定義該行業在該年為高碳排放行業,若低于所有行業的中位數,則為低碳排放行業。在此基礎上,本文通過分樣本回歸考察碳交易政策影響企業非效率投資的行業異質性。回歸結果見表5。
由回歸結果可知,碳交易政策顯著抑制低碳排放行業企業的非效率投資程度,而對高碳排放行業企業投資效率無顯著影響。一方面,該結論說明低碳排放企業通過碳排放權交易能夠獲得一定的額外收益,并且交易信息的公開使其融資約束有所緩解,以此促進投資效率;另一方面,對于高碳排放行業的企業而言,由于固定資產投資回報的周期性較長,其投資決策短期內可能無法體現到生產效率或是收益上,即碳交易制度對高碳排放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短期內可能無法觀測。

表4 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機制檢驗

表5 碳排放權交易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異質性檢驗
2. 企業性質差異
為理清不同企業所有權類型下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本文按照企業是否為國有企業進行分組回歸。表5 列(3)、(4)的回歸結果顯示,碳交易政策顯著抑制非國有企業的非效率投資,但對于國有企業卻無顯著影響。我國國有企業由于政治關聯優勢等原因,較少受到融資約束的限制,主要產生過度投資的非效率投資行為,民營企業是受融資約束限制的主要對象,主要產生投資不足的非效率投資行為。故而,碳交易政策不能顯著地提升國有企業投資效率,但是能夠減少投資不足,顯著提升民營企業的投資效率,這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碳市場是我國實現“雙碳”戰略的重要抓手。本文利用企業分批分期被納入碳交易市場這一準實驗,從微觀角度探究碳交易政策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作用渠道與內在機制,主要的研究結論如下:第一,碳交易政策顯著抑制企業非效率投資,且這一結果通過了穩健性檢驗;第二,碳交易政策可緩解企業投資不足問題,而對企業過度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第三,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積極影響主要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 抑制政策性負擔以及促進企業技術創新三個作用機制實現;第四,碳交易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積極影響主要作用于低碳排放行業以及非國有企業。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應加速推進全國碳市場的建設,將更多行業和企業納入到全國碳市場,擴大碳市場邊界,充分發揮碳市場對企業投資效率的積極作用。結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中辦發〔2021〕24 號)等中央文件和麗水市等示范區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方面的探索實踐,堅持“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原則建設碳交易市場,積極推動碳交易產品和交易方式創新,有利于更好地解決碳排放的外部性問題。第二,要嚴格審查微觀主體的減排效果(陳林和萬攀兵,2019),完善碳市場的信息披露機制,提高市場主體間的信息透明度,充分發揮碳交易市場的信號顯示作用,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提高企業投資效率。第三,堅持分類管理原則,充分考慮高碳排放企業與低碳排放企業、 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差異性,設置排放配額應該兼顧公平與適度從緊原則,發揮碳交易制度在優化投資組合、 倒逼企業提升內部管理效率等方面的作用,提升企業投資效率。
注釋:
①由于北京市2013年納入碳排放交易的企業名單未公開,故采用2014年替代。
②限于篇幅,關于穩健性檢驗的詳細回歸結果及解釋說明留待備索。
③本文主要是在采礦業(B)、制造業(C)、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D)等行業進行高碳排放與低碳排放的劃分,并將其他行業界定為低碳排放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