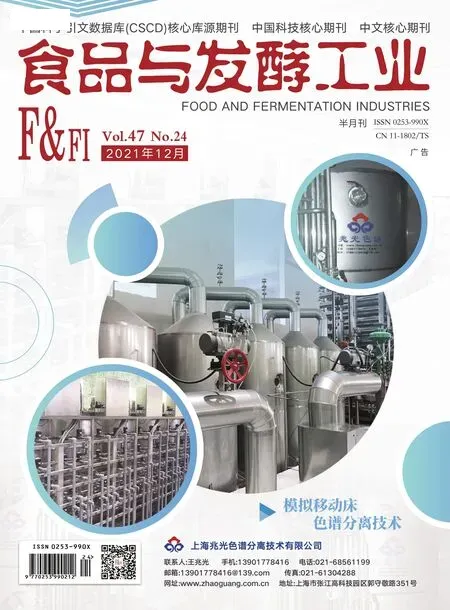食源性沙門氏菌在人體胃腸道中耐受及致病機制研究進展
董曉璐,秦曉杰,劉陽泰,孫天妹,劉弘,王翔,李卓思,董慶利*
1(上海理工大學 健康科學與工程學院,上海,200093)2(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上海,200336)
沙門氏菌是一種革蘭氏陰性腸道菌,在自然界中分布廣泛、種類繁多,目前已檢測出2 600多種血清型,其中部分血清型可導致人患病[1]。沙門氏菌主要通過受污染的食物、水和糞便進行傳播,其引發沙門氏菌病(salmonellosis)的特征性臨床癥狀主要有急性胃腸炎、敗血癥、傷寒和副傷寒等[2]。據我國食源性疾病監測系統顯示,2003—2017年全國共報告899起與沙門氏菌有關的食品安全事件,最終導致21 881人患病,11 351 人住院,4人死亡[3]。因此,沙門氏菌是一種重要的食源性致病菌,會對人體健康構成嚴重威脅。
食源性沙門氏菌一般由受污染食物進入人體,通過侵染小腸上皮細胞,再利用自身攜帶的多種毒力因子作用導致人罹患沙門氏菌病[4]。沙門氏菌在胃腸道內會面臨一系列對其生長和生存不利的逆境條件,如胃酸、高滲透壓、高濃度膽鹽、金屬離子、營養限制和腸道菌群的競爭作用[4-5]。然而,沙門氏菌能夠通過調節自身基因的表達來應對這些逆境,進一步黏附、定殖和入侵宿主細胞,最終導致人患病[6]。明確沙門氏菌對人體內壓力因子的耐受性及其致病機制對于有效控制沙門氏菌感染有重要參考價值。
近年來,關于食源性沙門氏菌在逆境條件下的生長、失活和毒力表達研究已廣泛開展,但主要集中關注食品加工、貯藏、流通等體外環節。本文則著眼于食源性沙門氏菌的體內存活及侵襲過程,對其在人體胃腸道環境中的應激耐受機制和致病機制進行概述,以期為食源性沙門氏菌的體內研究提供參考。
1 人體胃腸道中沙門氏菌的應激耐受機制
沙門氏菌在人體胃腸道內會經受多種應激條件(圖1)[6-7]。其中,胃酸、膽鹽和高滲透壓是最主要的脅迫因子[4, 6]。沙門氏菌通常能夠抵御和適應這些逆境,進而在人體胃腸道內存活。以下將對沙門氏菌在這3種應激條件下的耐受機制進行概述。

圖1 沙門氏菌在人體胃腸道內受到的應激條件Fig.1 Stress conditions encountered by Salmonella in the huma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1.1 胃酸應激下沙門氏菌的耐受機制
沙門氏菌通過食物被人體攝入后首先要承受pH值為1~5的胃酸應激[7]。人體每天產生約1~2 L胃液,鹽酸含量為5 475~5 840 mg/L[8]。研究表明胃酸過少會導致沙門氏菌感染風險增加,例如,對于急性沙門氏菌病患者,接受過胃切除術患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較高[8]。GAWANDE等[9]研究發現將沙門氏菌接種于農產品表面進行酸處理可提高沙門氏菌在酸中的存活時間,該結果說明人食用食物后胃環境pH值的暫時升高可能有助于沙門氏菌在胃中生存。此外,有研究指出,一些富含脂肪或高蛋白的固體食物來源可以保護沙門氏菌免受胃酸的影響[10]。這些因素都會增加沙門氏菌在人體胃環境內存活的可能性。
除了上述胃酸不足和食物基質的保護外,沙門氏菌已進化出多種應答機制來增強自身在酸環境下的生存能力。其中,沙門氏菌主要抗酸機制是酸耐受應答(acid tolerance response,ATR)反應,也就是沙門氏菌經弱酸適應后,在致死酸性條件下存活能力增強的反應[2]。如圖2所示,沙門氏菌的酸耐受應答機制主要包括3個方面,分別是酸休克蛋白(acid shock proteins,ASPs)、pH穩態系統和細胞膜脂肪酸組成[11]。

圖2 沙門氏菌主要的耐酸機制Fig.2 The main acid tolerance mechanism of Salmonella
ASPs可預防或修復沙門氏菌由酸應激引起的大分子損傷,目前已發現的ASPs包括RpoS、鐵調節系統Fur、雙組分系統PhoP/PhoQ和OmpR反應調節子[12]。ASPs的表達有助于沙門氏菌在低pH值的酸性條件下生存[13],有研究通過蛋白質組學分析表明鼠傷寒沙門氏菌酸適應誘導了其60個ASPs的表達,該菌經低酸適應后與未經酸適應相比在隨后的酸應激中存活能力顯著增強[14]。沙門氏菌胞內pH穩態主要通過賴氨酸脫羧酶系統和精氨酸脫羧酶系統維持,其中賴氨酸脫羧酶系統由轉錄調節因子、賴氨酸脫羧酶和賴氨酸-尸胺反向轉運蛋白組成,賴氨酸脫羧酶消耗細胞內H+將賴氨酸轉化為尸胺,再由賴氨酸-尸胺反向轉運蛋白排出尸胺以換取胞外的賴氨酸;精氨酸脫羧酶系統通過消耗H+,將精氨酸轉化為胍丁胺排出細胞以換取外部精氨酸,使整個過程得以持續進行[15]。除此之外,細胞膜組成中不飽和脂肪酸與飽和脂肪酸比率的降低以及環丙烷脂肪酸含量的增加也會導致沙門氏菌存活能力和耐酸性增強[11]。盡管沙門氏菌酸耐受機制的相關研究已很全面,但是仍有部分具體機制如RpoS在酸脅迫過程中的表達程度以及OmpR調節哪些基因參與耐酸反應等需要進一步闡明。
1.2 膽汁應激下沙門氏菌的耐受機制
食物中的沙門氏菌在經過胃酸的抑殺作用后,會受到另一逆境條件——膽汁的應激。膽汁由膽固醇在肝臟中合成并在膽囊中貯存和濃縮,在人體攝入食物后釋放到十二指腸,可參與膳食脂肪和脂溶性維生素的消化和吸收[16]。膽汁由多種化合物組成,以鈉(145 mmol/L)、氯(90 mmol/L)和各種膽鹽(40 mmol/L)為主要成分[17]。膽鹽可作用于沙門氏菌細胞膜并破壞其完整性和通透性、誘導RNA二級結構的形成、DNA損傷、改變蛋白質構象致其錯誤折疊或變形以及通過產生氧自由基引起氧化應激等[18]。因此膽汁也是抑制沙門氏菌存活的重要因素之一。
現有研究證實,沙門氏菌通過脂多糖轉運、雙組分系統和外排泵來抵抗膽汁應激[5, 9]。沙門氏菌細胞膜中含有脂多糖,脂多糖中O抗原的缺失會導致沙門氏菌對膽汁的耐受性降低[19]。HERNANDEZ等[20]通過對沙門氏菌耐膽汁突變株進行全基因組測序發現這些菌株中脂多糖轉運基因的突變率很高,證實了脂多糖結構在沙門氏菌膽汁耐受機制中的作用。PhoP/PhoQ是一種重要的雙組分系統,VELKINBURGH等[21]的研究表明,在較低的膽汁濃度下,缺乏PhoP/PhoQ系統的沙門氏菌突變株與野生沙門氏菌相比更容易受到膽汁的抑殺作用,而具有PhoP/PhoQ系統活性的菌株在60%的膽汁濃度下也能夠存活較長時間。PROUTY等[22]對鼠傷寒沙門氏菌中AcrAB外排泵進行分析,發現膽汁存在時AcrAB的轉錄活性是無膽汁時的8倍。除了以上所述幾種調節機制外,沙門氏菌還可能在膽結石表面形成生物膜或入侵膽囊上皮細胞來避開高濃度膽汁[23]。由此可知,沙門氏菌作為腸道細菌已經進化出較為完善的膽汁耐受機制,可確保其在腸道中的存活和定殖。
1.3 腸滲透壓應激下沙門氏菌的耐受機制
沙門氏菌在腸道內面臨的主要逆境條件除了膽汁外還有小腸內的高滲透壓。小腸對各種營養的吸收受多種因素的制約,而腸道內容物的滲透壓是制約腸吸收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一定濃度范圍內,腸內容物濃度越大,腸吸收越慢;濃度過高時,腸壁會出現反滲透現象,使內容物的滲透壓降至一定程度后再被吸收[24]。一般情況下,沙門氏菌需要維持高于生長介質的胞內滲透壓,才能產生細胞膨壓,而細胞膨壓可以促進沙門氏菌生長和分裂[25]。腸道中的高滲環境會引起沙門氏菌細胞內水分流失,導致細胞內代謝不平衡,從而影響沙門氏菌營養吸收、DNA復制、細胞分裂等各種生理過程[26]。因此,沙門氏菌適應腸道高滲透壓應激的能力對于其生存和生長至關重要,需要通過自身的滲透壓耐受機制來適應腸滲透壓的變化。
沙門氏菌主要通過K+轉運系統和滲透保護劑系統的調控適應腸道中的高滲透壓應激[11]。Trk和Kdp兩個轉運系統可對細胞內K+濃度的升高進行調節,其中Trk系統由TrkA、TrkE和TrkG三類蛋白質組成,Kdp系統由KdpA、KdpB和KdpC三類蛋白質組成[7]。如圖3所示,沙門氏菌的操縱子otsAB會促進海藻糖合成,并且使甜菜堿、脯氨酸和膽堿等滲透保護劑通過特定的轉運體(丙氨酸、ProP、ProU和OsmU等)進入細胞,使細胞內外溶質發生被動擴散[27]。除此之外,ompC編碼OmpR/EnvZ雙組分系統的孔蛋白OmpC,能為可溶性物質進出細胞提供通道[11]。高滲透壓應激可能導致沙門氏菌孔蛋白OmpF的表達水平降低、OmpC的表達水平增加,而孔蛋白OmpC尺寸較小,只允許小分子通過,故可作為通道促進親水性小分子的擴散[26]。以上所述調控系統在沙門氏菌耐受腸道高滲透壓的過程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圖3 沙門氏菌對高滲透壓的應激反應Fig.3 The stress responses of Salmonella to high osmotic pressure
綜上可知,雖然人體胃腸道內存在很多不利于沙門氏菌存活及生長的逆境條件,但是沙門氏菌已經進化出多種耐受機制來適應這些逆境,從而為后續在腸道中的定殖創造機會。然而,人體胃腸道是一個復雜的抑菌體系,沙門氏菌并非面臨單一應激條件,而是會受到各類應激條件連續作用的影響,因此還需對沙門氏菌在體內應激條件連續或協同作用下的存活及耐受行為進行深入研究。
2 人體胃腸道中沙門氏菌的致病機制
沙門氏菌侵襲宿主細胞的過程如圖4所示。沙門氏菌在穿過腸黏膜層之前首先要黏附腸上皮細胞,腸黏膜表面派爾集合淋巴結(Peyer′s patches,PPs)上的濾泡上皮細胞是沙門氏菌入侵的最佳起始部位。濾泡上皮中稀疏分布著捕獲抗原的微皺褶細胞(microfold cell,M細胞),當沙門氏菌黏附到M細胞后,利用Ⅲ型分泌系統(type three secretion system,T3SS)將效應蛋白分泌到胞外并遷移到宿主細胞,從而引起宿主細胞肌動蛋白骨架的重排,誘導膜褶皺的形成。該膜皺褶可以將黏附的沙門氏菌吞噬到一個大囊泡里,即 SCVs(salmonella containing vacuoles)。SCVs是沙門氏菌可以在宿主細胞內生存和繁殖的唯一場所。此時,腸上皮層啟動促分泌應答,促使吞噬細胞從黏膜下層移至腸腔,沙門氏菌隨吞噬細胞遷移從腸系膜淋巴結進入并擴散至其他部位,入侵肝臟、脾臟等不同器官或組織,從而引起人體各種臨床癥狀[13, 28]。

圖4 沙門氏菌致病的基本步驟Fig.4 Basic steps in Salmonella pathogenesis
沙門氏菌在黏附和入侵腸上皮細胞直至最終擴散到其他器官的過程中,有很多毒力因子在發揮作用,如毒力島、毒力質粒、菌毛和脂多糖等[4]。以下將對這幾種毒力因子進行概述。
2.1 毒力島
沙門氏菌的毒力島(Salmonellapathogenicity island,SPIs)是其進化過程中通過水平基因轉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HGT)獲得的,位于細菌的染色體或質粒上,在沙門氏菌感染、黏附、入侵、傳播以及細胞內生存中起著重要作用[29]。其中SPI-1和SPI-2是沙門氏菌較為重要的毒力決定因子。
SPI-1幾乎存在于沙門氏菌所有血清型中,在沙門氏菌侵襲非吞噬細胞過程中起關鍵作用,并參與宿主細胞誘變和誘導巨噬細胞凋亡的過程[30]。SPI-1編碼與沙門氏菌侵襲力相關的Ⅲ型分泌系統,該系統能夠對若干個環境和生理信號做出應答反應,同時這些應答反應又控制著 SPI-1 編碼區內外效應蛋白的分泌[31]。VALDEZ等[32]研究結果顯示SPI-1不僅促進了沙門氏菌對上皮細胞的入侵,還促進了沙門氏菌在吞噬細胞內的生存和復制。該發現表明,SPI-1在沙門氏菌侵襲腸上皮非吞噬細胞和侵襲后于上皮細胞內快速增殖兩個環節都起了關鍵作用。
SPI-2是由沙門氏菌致病性相關毒力基因組成的一個基因簇,是沙門氏菌在胞內存活和發揮毒力的重要毒力島[33]。SPI-2與沙門氏菌在宿主吞噬細胞內的生存和傳播相關,并使沙門氏菌逃避巨噬細胞的殺傷作用[34]。雙組分系統BarA/SirA可與SPI-2相關基因的啟動子結合,調控沙門氏菌的運動性和生物膜形成[35]。有研究顯示,SPI-2基因突變會導致SPI-1中sipC、prgK和hilA基因(編碼SPI-1基因的轉錄激活因子)的表達降低,說明SPI-2和SPI-1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36]。
除了SPI-1和SPI-2,沙門氏菌中常見的毒力島還有以下幾種:SPI-3可編碼巨噬細胞生存蛋白MgtC和轉運蛋白MgtB;SPI-4可誘導沙門氏菌對腸上皮細胞的黏附作用;SPI-5可編碼SopB(由SPI-1的T3SS分泌)、PipB(由SPI-2的T3SS遷移到SCV);并可誘導牛促炎免疫反應[37]。綜上,SPI-1主要在沙門氏菌入侵腸上皮細胞過程中起主要作用,而SPI-2、3、4則主要負責沙門氏菌在宿主細胞內的生存和增殖。
2.2 毒力質粒
沙門氏菌黏附及入侵腸上皮細胞還與其攜帶的毒力質粒有關。大多數沙門氏菌都具有血清型特異性毒力質粒,大小約50~90 kb,與沙門氏菌的致病能力密切相關[38]。毒力質粒包括5個開放閱讀框(open reading frame,ORF),即spv(Salmonellaplasmid virulence)操縱子[39],spv操縱子由5個基因組成,其中spvR是第一個被轉錄的基因,它編碼的效應蛋白SpvR可調節其他4個基因(spvA、spvB、spvC和spvD)的表達[40]。SpvB是一種細胞毒蛋白,具有避免肌動蛋白聚合的功能[41];SpvC是一種抗炎效應因子,可抑制免疫信號傳導,在宿主的促炎反應中發揮著重要作用[39]。ROLHION等[42]證明了SpvD在抑制免疫應答中的重要性。但是,SpvA的調控機制及其在毒力中的作用尚未完全闡明,故需要對spv操縱子進行更全面的研究。
2.3 菌毛
沙門氏菌表面的菌毛在細菌生物膜形成、腸道定殖和入侵中起重要作用[29]。FBREGA等[39]通過對鼠傷寒沙門氏菌基因組進行測序,發現了13個操縱子(agf、fim、lpf、pef、bcf、stb、stc、std、stf、sth、sti、saf和stj)與菌毛合成基因具有同源性。BUMLER等[43]通過遺傳方法研究了3種菌毛操縱子(fim、lpf和pef)在鼠傷寒沙門氏菌黏附于不同上皮細胞系(HEp-2和HeLa)中的作用,這些操縱子分別編碼I型菌毛,長極性菌毛和質粒編碼性菌毛,結果顯示只有鼠傷寒沙門氏菌lpf突變體對HEp-2細胞的黏附性顯著降低,而末端基因缺失顯著降低了鼠傷寒沙門氏菌對HeLa的黏附性。上述研究表明,菌毛合成相關基因的組成決定了細菌腸道感染過程中黏附的上皮細胞類型。
2.4 脂多糖
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LPS)也是沙門氏菌的一種毒力因子,它由類脂A、核心寡糖(C-OS)和O-抗原多糖(O-PS)組成,其中,類脂A和C-OS可激活T淋巴細胞,而O抗原則可以激活B細胞分泌抗體[44]。脂多糖在沙門氏菌感染宿主的過程中會釋放出內毒素,導致宿主白細胞先減少后增加、血小板減少、肝糖消耗、黏膜出血,最終休克死亡[45]。CRAVEN[46]通過對雞進行灌胃的方法測定了鼠傷寒沙門氏菌野生型和LPS缺失株對雞腸道細胞的侵襲能力,結果發現LPS缺失型鼠傷寒沙門氏菌定殖于雞腸道和脾臟中的細胞數量顯著低于野生型,表明LPS在沙門氏菌侵襲宿主細胞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沙門氏菌毒力因子多且作用機制復雜,目前認為SPI-1和SPI-2在沙門氏菌入侵人體細胞和在細胞內存活發揮了較為主要的作用,質粒和菌毛等毒力因子中某些操縱子的作用機制仍需進行深入研究。未來或可關注這些毒力因子之間的協同或交叉關系,尋找更多在沙門氏菌致病過程中起作用的毒力因子,有助于明確沙門氏菌感染人體并導致人患病的根本原因,為預防和治療沙門氏菌病提供思路。
3 沙門氏菌耐受與致病能力的相關性
受沙門氏菌污染的食品在加工、貯藏及運輸過程中會受到很多逆境條件的抑殺作用。然而,由于食品基質的保護或沙門氏菌自身的抗性,這些逆境條件可能無法將沙門氏菌完全殺滅,甚至會誘導沙門氏菌抗性、毒性和耐藥特性增強。
首先,食品加工及貯藏環節的逆境條件可能使沙門氏菌對后續家庭烹飪環節的熱處理產生耐受性。例如,YE等[47]通過分析腸炎沙門氏菌表型和基因表達,發現酸適應后細菌熱脅迫(rpoH、uspB和htrA)、鹽脅迫(proP、proV和osmW)和冷脅迫(cspA、cspC和csdA)的相關基因表達顯著上調。其次,食品加工及烹飪過程中的冷、酸、熱、滲透壓脅迫等體外應激條件也可能誘導沙門氏菌對體內應激條件產生耐受性。例如,DE MELO等[48]通過人工胃腸道模型測定了經酸和滲透脅迫后的腸炎沙門氏菌和鼠傷寒沙門氏菌對人體胃腸道的耐受性,結果表明經脅迫后的兩種血清型的沙門氏菌對膽鹽的耐受性及胃腸道存活能力都顯著高于未經脅迫的對照組細菌。沙門氏菌感染人體的能力也可能會因前期的一系列逆境條件的應激作用而增強。例如,SIRSAT等[49]測定了亞致死熱應激下鼠傷寒沙門氏菌毒力基因的表達以及對Caco-2 細胞的黏附和侵襲能力,結果顯示熱應激誘導了SPI-2和SPI-5基因的表達,相對于未經熱應激的細菌,熱應激后的細菌對Caco-2細胞的黏附能力更強。最后,體外和體內各應激條件的脅迫也可能導致沙門氏菌的耐藥性增強。例如,DE SALES等[50]利用人工模擬胃腸道模型測定了15株腸道沙門氏菌的耐藥性,結果發現其中有12株在體外模擬處理后對環丙沙星出現耐藥性,這些結果說明食品加工過程中的殺菌條件和胃腸道逆境環境可能導致沙門氏菌產生耐藥性。
因此,沙門氏菌對人體內各應激條件的耐受反應可能使其對其他逆境條件產生交叉保護,或導致其毒力因子的作用增強,從而提高對人體的致病能力,增加感染風險。目前關于沙門氏菌抗性及毒性機制的研究多集中于食品加工或貯存環節的應激條件對沙門氏菌后續生理行為產生的影響,而較少關注沙門氏菌通過食物被人體攝入后面臨的應激條件對其耐受及致病機制的影響,故需對沙門氏菌在人體內應激條件下毒力因子作用機制進行深入研究,或許能為更有效地控制沙門氏菌感染提供指導。
4 結論與展望
當前國內外關于沙門氏菌體內耐受及致病能力研究主要集中在表型的測定,對于沙門氏菌在人體胃腸道應激條件連續或協同作用下的調控機制研究仍有不足。未來應重點關注體內應激條件下沙門氏菌調控因子的具體作用方式,通過體內耐受性與致病性之間的交互影響進一步探究沙門氏菌對人體的感染能力。
基于此,本文從以下4個方面作出展望:(1)沙門氏菌在逆境下發生的適應行為使其能更好地在人體胃腸道中生存,繼續深入探討沙門氏菌的抗逆分子機制,可為開發沙門氏菌防控技術提供新的靶標。(2)對沙門氏菌毒力質粒和菌毛中某些作用機制尚不明確的操縱子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探索沙門氏菌更多的毒力靶點和更具體的作用方式,明確沙門氏菌導致人患病的根本原因。(3)將胃腸道連續應激的人工模型應用于沙門氏菌毒力基因等分子水平調控的研究,有助于構建更符合真實情況的沙門氏菌劑量反應關系。(4)可將食品加工及貯存環節的殺菌方式與體內應激條件對沙門氏菌抗性及毒性影響的研究相聯系,為預防和控制沙門氏菌感染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