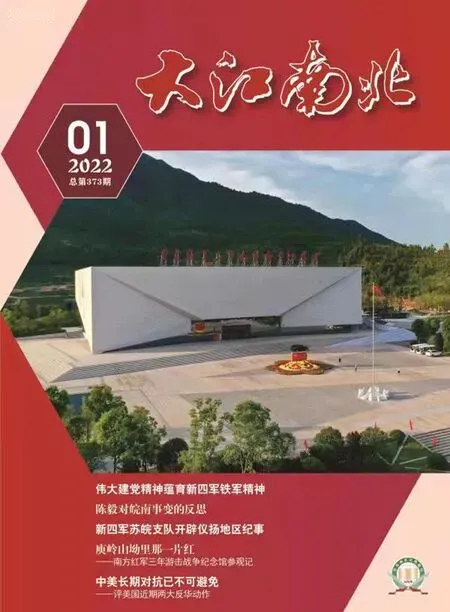我的俄語老師
馬鎮興
1963年秋,我考入縣城最好的中學,分在學俄語的班里。俄語老師叫張定遠,30多歲,中等身材,斯斯文文的樣子,衣著樸素,平易近人。聽說,張老師是為解決兩地分居,從北京一個部屬研究所調過來的。
初學外語,我感到新鮮和好奇,但很快發覺俄語學起來不容易,比如字母P是個卷舌音,需舌尖卷起來再發出顫音。這種顫音是漢語里沒有的,所以學起來頗費力。張老師和藹可親,但教學上認真嚴格、一絲不茍,對這個學習難點不厭其煩地耐心教、反復練,一對一地教每個人過關。
當時的教學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張老師從講臺上走下來,讓我們依次站起來發這個音。為了聽得清楚,他盡量靠近我們的座位,側著耳朵凝神傾聽,發對的點頭示意通過,發錯的則示范糾正,一遍又一遍直到發對音為止。難關終于攻克,大家興奮異常,“哈拉索”(好)、“達瓦里希”(同志)說個不停(這兩個單詞均含有字母P)。
興趣是學習的最好動力,尤其是學習外語。我慢慢地喜歡上了俄語,除了興趣,更是因為張老師的課上得好。每天我最盼望的是俄語課,課堂上也常常搶著朗讀和答問,大概回答得比較好吧,總能得到張老師的表揚。多年后談起往事,才知那時有好幾位同學不服氣,說張老師偏心,怎么不給他們發言的機會呢?一笑之余,不也證明當年喜歡張老師課的學生還真不少嘛。
張老師還與我們一起收聽俄語廣播,并隨時翻譯講解。幾個學期下來,我感到頗有收獲,俄語聽力有了扎實的提高。
初中畢業上山下鄉,同學間音信杳然,也從此與張老師失去了聯系。但我對俄語的興趣沒有因人生境遇的巨大變化而泯滅,在插隊落戶的漫長歲月里,仍時不時背背學過的俄語單詞和一些名言警句,模仿張老師的口吻說說那些課堂用語。返城工作后,我特地到書店買了一本俄語語法書,時不時拿出來翻翻,以期盡可能留住對這門語言日漸遠去的記憶。
正是這種對外語始終如一的喜愛,促使我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走上了自學英語之路,經過幾年的刻苦學習,1980年恰遇省人事部門公開招錄外語人員,我報名應考并有幸被錄取,由此改變了人生的軌跡。回望來路,這一切的起點,應歸結于初中學俄語所打下的基礎。這些不都是張老師當年悉心培育的嗎?所以,我總情不自禁地想起并由衷感激張老師。
張老師在教俄語時為激發我們的興趣,也常順帶介紹一些與語言相關的人文歷史、民族習俗。潛移默化中,我曾夢想有朝一日去看看這個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半個世紀后我終于夢想成真,2017年7月與妻子一起踏上了俄羅斯的土地,一睹其旖旎風光、名勝古跡,感受其熟悉又陌生的語言氛圍。在圣彼得堡一家商店購買軍用望遠鏡時,我還與一位俄羅斯服務員進行了俄語對話,雖說僅是最簡單的“你好”、“中國”、“謝謝”、“再見”等,但于我來說畢竟是第一次,一種激動和興奮之情涌上心頭。
50多年后,我們老同學相聚,我打聽老師們的音訊,才獲知張老師已不幸因病去世。我們無不悲痛惋惜。后來聽母校熟悉他的老師說,張老師曾因孩子多、負擔重,經濟拮據,生活不易,可他一直以樂觀和堅韌默默承受著生活的艱難,勤勉敬業,以教書育人為樂,贏得師生的尊重,也讓我對他多了一份認識、增添了一層敬意。我永遠懷念他。
(本欄編輯 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