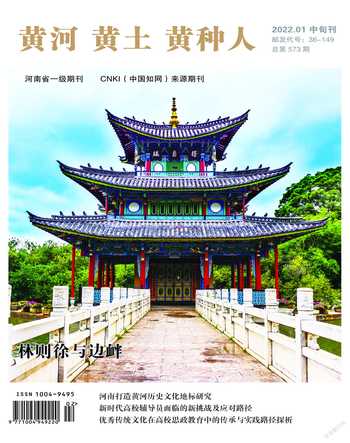1840—1860年清政府財政分散對近代化影響問題研究
田牛
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為應對軍費開支,減輕財政壓力,清政府被迫改革既有財政制度,部分放棄高度集中財政機制。在近代化大門開啟的19世紀中葉,清政府財政權力下移與外移成為不爭的事實,對后發國家近代化產生消極影響,洋務運動受到較大沖擊,清政府難以聚集全國之力推動近代化。現階段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財政權力下移、外移的過程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就財政權力下移對近代化影響的研究,涉及較少。文章擬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財政下移過程分析財權分散對近代化的消極影響。
一、鴉片戰爭前的清代財政制度
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自然經濟占絕對優勢。為適應這種經濟基礎,清政府實行以高度集中、中央統收統支為特點的財政管理制度,具體特點如下。
(一)戶部掌握主要財政權力
中央戶部掌握較大權力,總理全國財政收支,掌“軍國支計”。除在中央設戶部管理全國財政外,地方財政由總督、巡撫代表皇帝統理一省或數省。各省由布政使掌管當地田賦、稅收,每年將所在省的戶口、田畝數量報予戶部。布政使司和督撫在財政職責上沒有隸屬關系,其受戶部垂直領導,是戶部的派出機構。清政府規定:各直省道庫儲錢糧,該督撫每年于春秋二季將實在庫存銀兩造具春秋撥冊報部。戶部復明數目,除存留本省支用及協餉之外,余悉解部充餉。每歲冬季,各直省督撫將次年一歲應需俸餉預造冊報部,戶部按數撥給。由此可見,布政使司所掌管的一省錢糧,大部分為戶部直接支配的國家錢糧,而真正屬于本省的留支款項,戶部早有定制,數額很少。另外,清政府相當重視鹽政,以山東清吏司作為管轄鹽政的主要部門,負責鹽務日常事務,并考核各地鹽政官員。關稅方面設稅官監督管理商稅。清代前期,全國各地設有25處常關。其中,20處直屬于戶部管轄,負責征管貨物流通稅;5處隸屬工部,負責征收竹木等實物稅。但無論督撫還是布政使,都必須無條件服從戶部指揮,執行戶部決定。
清代皇室財政獨立于國家財政之外,管理機構為內務府,下設廣儲、都虞、會計、掌儀、慎刑、營造、慶豐7司。雖然皇室財政收支與國家財政分離,但發生虧空可以由國家財政彌補。如清乾隆中期,戶部增加內務府用銀60余萬兩;清道光時期,再次發生戶部和內務府儲存銀兩、物資互調現象。
(二)戶部制定稅收政策
為規范行政開支,清政府制定了相對完善的奏銷制度,它本質上屬于一種決算制度。清政府以農歷年為會計年度。規定每年年末,先由各州縣制造草冊,以四柱法(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上報所在省份布政使司。布政使司核對后,發回照造;如有錯誤,則予以指明,發回編繕補送。布政使司匯總各州縣總冊后報予戶部,并依路程遠近,分四月、五月、六月不等。戶部收到各地奏銷冊后,立即進行嚴格審核,如有不實,即刻發回,令該省復查登答,限于十月前回報。各省督撫也負有考核之責,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以前督撫要自行編報奏銷總冊,以后變為在總冊上加蓋印章,簽署“并無遺漏濫支”,最后,由戶部匯總報表上奏皇帝。奏銷制度使中央政府實現了對地方政府在財政上的有力控制,是清前期高度集中的財政管理制度的具體體現之一。清政府在總結歷代經驗的基礎上,雖進行了適合實際情況的改革,但仍未改變封建財政管理體制的根本性弊端:注重集權,忽視權力之間的互相制約,最終導致腐敗的發生。
二、鴉片戰爭后到太平天國運動前后的清政府財政制度
(一)關稅自主權的喪失
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明確要求中國開設福州、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為通商口岸。在上述五口岸建立新海關,把原來統一管理的海關分成海關和常關,即設在開放口岸的洋關和仍然由中國政府管理,重點課征國內貨物通過稅、船稅的舊關(即常關)。1843年,清政府同英國簽訂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即《虎門條約》,又批準五口通商章程中的《海關稅則》。它規定制定新關稅原則——值百抽五,造成中國進口商品稅率下降一半以上,如此低的稅率使關稅失去保護本國工業的功能。在1854年的《天津條約》和其后的《中英通商章程》中,英國把值百抽五的稅率以條約形式固定下來,即“前在江寧立約第十款內定進、出口稅,彼時欲綜處稅餉多寡,均以價值為率。每值百兩,征稅五兩”。
(二)關稅管理權的喪失
西方列強很早就覬覦中國海關控制權。1853年,上海爆發小刀會起義,攻占上海縣城。清政府駐上海道臺吳健彰逃入租界,英、美、法乘虛派兵占領海關,并擅自把上海港變成“自由港”。吳健彰迫于無奈在兩條舊船上設立水上海關。侵略軍居然派軍艦趕走中國臨時海關,同時在蘇州河北岸的稅務所也遭到列強騷擾。次年,吳健彰與英、法、美領事簽訂《上海海關協定》,明確規定三國各派一人參與海關事務管理,承認其對海關事務具有投票權。對此,劉錦藻痛心地說:“各國所施于我之稅則,我不能施之于各國,約載利益均沾,各國能沾,而中國卻不在沾之列,此豈得謂之互市焉?……國朝始令納船鈔而已,別無所謂洋稅也。有,亦上下于官吏之手,朝廷不甚以為輕重也。海警疊告,乃訂稅則,先不講求,臨時無措。各國為土貨計,民用計,出入口稅輕重均有比較,茫無所聞,而值百抽五,漫焉一許,大錯已成,迄與今日。”
三、太平天國運動對清政府財政制度的影響
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為渡過統治危機,更好地調動統治力量對抗太平軍,清政府被迫調整滿漢矛盾,整合中央和地方關系,實施權力資源的再分配。這些措施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就財政體制來說,莫過于財權下移。
清前期直到清咸豐元年(1851年)基本沿襲明朝財政管理體制,實行中央集權財政制度。這種局面在太平天國運動中被打破。巨額的軍費使本已困難的財政雪上加霜,清中央政府無力支撐新興的湘、淮軍隊,只好令其“就地籌餉”,承認了地方的征稅權、制定稅收政策權。各督撫乘機擴大自身權力,借口軍務,截留丁漕各款供本省軍需,用后也不上報戶部,使奏銷制度名存實亡。京餉撥解制度也發生了變化。為保證中央財政收入,清咸豐帝下旨各省以“所有該部歲撥京餉,著準其本年為始,歸入冬撥案內,與各直省協撥兵餉一律酌撥”,即督撫每年向中央繳納規定數量的白銀。這次政策調整等于默認了地方官員自行籌款的權力,也無力要求他們繼續服從戶部指揮。不久,清政府命令各地以省為單位,籌款上解,最終形成以督撫為領導的地方財政體系,中央集權制度被極大地削弱。
上述情況表明,鴉片戰爭后清政府中央集權財政體系逐漸瓦解,列強與地方共同侵蝕中央本不富裕的財政收入。清廷財政權力的分散,造成清中央政府掌控社會能力的減弱,成為近代化進程推進的制約因素之一。日本明治維新之后,廢藩置縣,聚集較多的社會財富,成為近代農工商業起步的原始積累來源之一。據統計,1887年,中國經濟總量是日本的9.77倍,財政收入卻不到日本的3倍。雖然清廷財政收入所占國民經濟比重低于日本有較復雜的歷史原因,但是財政權力分散、各省擁有相對獨立財權是不容忽視的原因。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財政主權遭到沖擊和破壞,財政權力出現外移傾向,西方勢力開始對海關等財政機構進行滲透和干涉。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清政府陷入嚴重財政危機。為挽救統治危機,清政府被迫放棄部分財政權力,承認地方財權事實,中央集權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近代化客觀要求中央政府具有較強的財政權力和融資能力,清政府財權下移與外移客觀造成近代化進程中資金短缺,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阻礙因素之一。
【基金項目】2021年度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創新課題“明清以來西南地區地方治理的理論與實踐及其當代啟示”(編號:CXLL2105)。
參考文獻:
[1]趙爾巽.清史稿[M].上海:中華書局,1976.
[2]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清]王慶云.石渠余紀[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4]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編輯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M].上海:中華書局,1978.
[5]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M].上海:三聯書店,1982.
[6]卿汝楫.美國侵華史[M].上海:三聯書店,1953.
[7]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12.
[8]華文書局出版社.清文宗實錄[M].北京:華文書局,987.
[9]周志初.晚清財政經濟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2002.
(作者單位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對外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