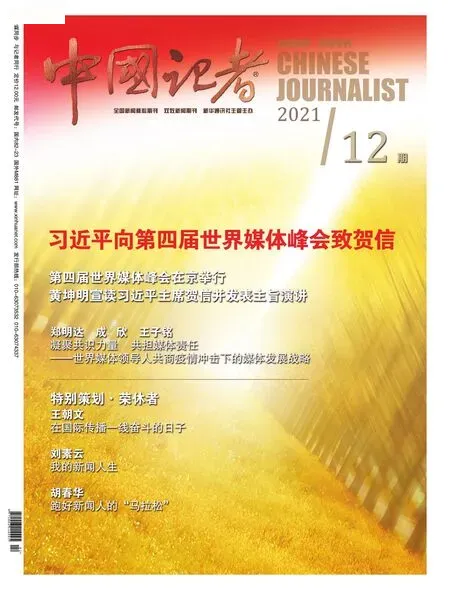那些時刻我記得
□ 杜娟

2001 年7 月,作者在進行新聞人物采訪。
37年的新聞工作中,有3年(2001年至2003年)左右,我是《遼寧日報》“新聞人物”專版的記者之一。期間,采寫了一些包括新聞老前輩、文化名家、科學家、專家學者等在內的新聞人物稿件。在進入我的新聞工作尾聲之際,回顧那段經歷,深感收獲良多。在這里分享幾次難忘的采訪經歷。
科學問題不能馬虎,新聞工作亦然
2001年5月刊發的《我想拯救每一滴水》是我在專版最初采寫的稿件之一,訪的是在污染土壤治理以及農業環境污染防治等方面卓有建樹的孫鐵絎先生。
完成此稿,幾經周折。至今記得當年的采訪情景。2001年5月初的一天,我與特約攝影人到孫先生的辦公室進行采訪。采訪中,他講述自己如何成為一名環境保護研究者的經歷和心路歷程,給我留下很深印象。采訪結束后,這位老知識分子與工作人員沿著辦公樓前的小徑送別我們。那天風輕云淡,柳枝婆娑。我自覺采訪得不錯。待到寫作稿件需要敘述相關科研理念和項目時,卻難以為繼,我這才發現許多關鍵問題沒有采訪清楚,甚至采訪前沒有考慮到。當時我很窘迫,以至于在沒有捋清思路的情況下,又電話采訪了幾次。每一次,孫鐵絎先生都詳細道來,不厭其煩,還說,科學問題不能馬虎大意。因為涉及一些專業問題,成稿后,我請其把關,他一一指出需要修改之處。彼時,自己雖已有十多年的新聞從業經歷,但面對陌生領域的采訪對象,還是很懵懂。經過多次采訪,反復修改,才完成稿件寫作,版面負責人提煉了一個精彩的標題,來體現這位“老科研”的情懷——“我想拯救每一滴水”。后來,我多次反思這次采訪,覺得自己當時無法進入受訪者的語境是關鍵問題,之所以如此,除了新聞敏感不夠,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相關知識。再進一步說,是采訪前準備工作做得不好。作為一名新聞人物版記者,面對的每一位采訪對象都有其獨特性,因此,做足訪前準備尤為重要,其中包括不斷提高自己的學習能力。如果采訪前捋清相關科研工作的脈絡及其學術和社會價值,再提煉出具體問題,那次采訪可能就不至于成為一次不充分的采訪。我一直記得那位“老科研”的話,科學問題不能馬虎大意,新聞工作亦然。
兩位志愿者想要的生活
2002年,我先后采寫了兩名志愿者。他們選擇的生活方式都始于各自的愛好:一個熱愛野生鳥類攝影,由此走上環境保護志愿者之路;另一個自幼酷愛電影,后來,以放映電影的方式,送文化和科技到鄉村,成為一名文化志愿者。
《每年寒假我都去山東見天鵝一面》寫的是愛鳥志愿者,他是大學教師。采訪時,聽他講述守望天鵝和黑臉琵鷺的故事,特別感動:“我在車祝溝拍了這么多年的天鵝,到了什么程度呢,天氣不好時,我會坐在避風處看天鵝,那種享受沒法形容……”1995年冬天,他在去山東榮成車祝溝的鄉道上第一次見到來越冬的天鵝,抓拍瞬間,那些小生靈就飛進他的心海。此后五六年,每年寒假,他都去那個小村子與天鵝見一面。聽他講起自己與其他志愿者救助車祝溝天鵝湖里一只生命垂危天鵝的過程,回憶那只盤桓在空中的天鵝如何落到湖面,又如何一點點地靠近湖邊,與患病天鵝相依在一起的情景,真是如歌如泣。
這位志愿者對多種鳥類都有仔細的觀察和獨特的藝術呈現,同時開始環境保護行動:在小村里辦攝影展,進入多所大中專院校進行公益講座,以自己拍攝的野生鳥類照片為切入點,宣傳環保理念。
這次采訪,我獲得了一個新視角,即從個體角度對人與自然的關系有了一些新認知,還有那些細節中閃現的愛、悲憫、擔當的光澤,至今沒有泯滅。
《這就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采寫的則是我們省內一支老兵義務放映隊的隊長。在我采訪的2003年,這支成立于1996年10月的義務電影放映隊已經義務放映行程5萬多公里,走了100多個鄉鎮,200多個村莊,為城鄉近70萬觀眾放映電影321場。這位在松江流域平原長大的老兵義務放映隊隊長自小喜歡看電影,少時曾經追隨鄉村電影放映隊在本村和鄰村看電影。在部隊里,他如愿以償地成為電影放映員。轉業創業兩年后,他買了臺電影放映機,在有關部門支持下,組織起義務電影放映隊,后來,又更新添置設備,專門買了臺面包車,每周末與放映隊的退伍老兵一起下鄉村放映電影,延續著自己少時的電影夢。1996年10月,他們第一次到鄉村放映電影回城沒幾天,就收到村里小學生寄來的感謝信。回顧在鄉村放映電影的感受時,他說:“當放映機的第一束光穿越黑暗,投到銀幕上時,我就像是回到童年,回到在部隊給戰友們放映電影的時光中,我突然發現,一生中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內心是高興和滿足的。”他當時還說,每次放電影回來,心里總是有新感受,總是有一種動力觸動他要把電影放映下去。“鄉親們需要,我們就永不停機。”
這些質樸的話語令我琢磨了很久。在他想要的生活里有夢想、傳承,有友愛、奉獻、堅守,有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我覺得選擇這種生活方式最終離不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些,對我的新聞工作大有裨益。
關注我們自己的文化
2002年3月,采寫知名學者湯一介、樂黛云伉儷,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
我記得按照約定,3月28日8時許,還沒等我們敲響其寓所的門,湯教授就開門了,這是一位謙和的學者。采訪中,湯一介饒有興致地講起自己少年時讀斯諾撰寫的《西行漫記》后,與小伙伴策劃去延安的往事。這次采訪,印象深刻的一是他回憶的幾位文化大家對自己成長的影響,包括其父湯用彤。湯用彤曾任職、任教于北京大學,學貫中西。湯一介說,他的父親研究學問認真求實,“人家說他越是有學問越是慎重”。湯一介說:“我覺得,做學問如果不真誠,就沒有意義。學術腐敗就是沒有對學問忠誠和忠實的信念”。二是對傳統文化中一些理念有了一些認識。湯一介治學歷程與新中國的發展密切相關。當時,他以全球化為背景,解釋了為什么每一次文明的飛躍都要回到自己文化之根的原因。聽他講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自我身心內外和諧之間的辯證關系,受到啟發。
樂黛云是新中國培養出的第一代知識分子,50歲開始研究比較文學,在國內開風氣之先,帶出一代人。采訪中,聽她講述自己17歲時如何從偏遠的山村只身北上,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以及此后的治學經歷,深為其豁達的心境和堅持向前走的意志所感染。樂黛云的學術研究始終關注人類文化的發展。采訪中,我們請教經濟全球化會不會導致全球文化趨同這個當時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她說,任何國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都要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沒有文化的多樣性就不會有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
采訪兩位學者,不僅開闊視野,而且讓我認識到,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學識、見識和情懷該有多重要。
聽穆青說“寫”與“不寫”
2001年,“新聞人物”版策劃推出曾在遼寧日報前身東北日報工作過的名家系列報道,我負責采訪穆青。那年8月,在新華社穆青辦公室,這位已經卸任的老前輩接受了我們的采訪。20年過去了,當時的采訪情景至今還能記得。
1966年,穆青與馮健、周原合作采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刊發,反響熱烈。我們的采訪由此開始。我記得他說,這篇新聞報道他們前后采訪了近兩個月,“當時焦裕祿已經病逝,我們就采訪焦裕祿接觸過的干部和群眾,一次次召集他們開座談會。一提起焦裕祿,大家就噼里啪啦掉眼淚,我們都哭,筆記本好多頁上都有淚痕……”
我記得他還說:“我就尋思,這么一個具備了優秀品質的真正共產黨員,如果不把他寫出來,那我們算什么記者呀,我們對得起蘭考人民嗎?”我問采訪焦裕祿事跡時最令他心動的是什么,穆青說:“我永生不忘焦裕祿無私奉獻、克服困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我覺得我們寫不好,都對不起他。”
采訪中,提到其卸任后完成的《十個共產黨員》一書,穆青說:“過去我的工作實在是忙,沒有時間下去。那本書中有好幾個人物是我退下來后寫的。我覺得不把他們寫出來我有愧,等于欠了這些黨員一筆債,這筆債壓得我寢食難安,要把他們寫出來。”他還說:“脫離群眾的干部,我一個也不寫。”
他話音不大,但是,每句都有分量。
這位新中國新聞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以親身經歷,加深了我對新聞工作者使命與擔當的認識。
如今,之所以分享這些時隔近20年的采訪經歷,是因為受訪者的故事一直影響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