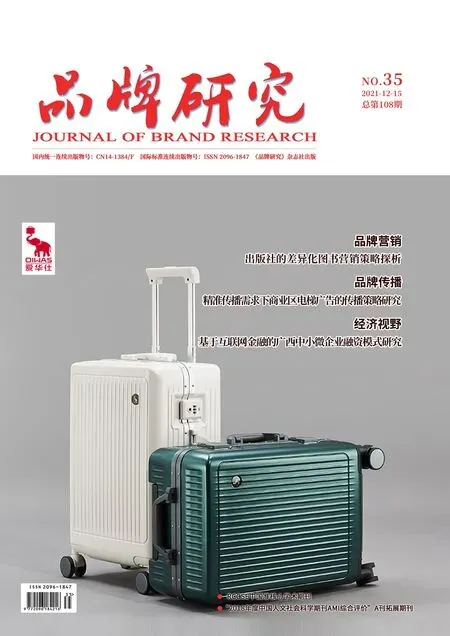其他綜合收益波動、違約風險和債務融資成本
文/蔡芯瑤 郝莉莉(東華大學旭日工商管理學院)
一、引言
在財務報告中列示綜合收益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反對派認為其他綜合收益具有波動性和不可預測性,有違傳統對收益的認知,其列示將會迷惑和誤導投資者。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其財務會計準則公告 (SFAS No.130)中指出“一些受訪者認為,綜合收益將在不同時期出現波動,這種波動將與管理層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有關[1]。”與將其他綜合收益項目從報告中排除的論點相反,支持者認為盡管管理層不太可能直接控制其他綜合收益的變動,但管理層所從事的經濟交易會影響其他綜合收益的確認,因此,包含其他綜合收益的綜合收益項目能夠更為全面、完整地反映公司整體的業績。
盡管學術界和準則研究者們對其他綜合收益列示及其作用看法不一,但從實踐來看,隨著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和金融市場環境日益復雜,在公允價值計量理論基礎上發展的“綜合收益觀”已得到全面推行和廣泛使用。從國內準則發展來看,我國財政部在2009年提出在利潤表中增列其他綜合收益和綜合收益總額的科目,到2014年進一步說明并規范其定義和列報內容與方式[2]。財政部對準則的不斷完善反映了相關部門對綜合收益信息越來越重視,其列表也越來越重要。
二、文獻回顧
現有其他綜合收益的研究集中站在資本市場股權投資者角度(Dhaliwal et al 1999[3];Hooder et al 2006[4];Black and Cahan 2016[5];王鑫2013[6];王艷、謝獲寶2018[7]),較少從企業債權融資角度分析其信息價值。自引入綜合收益觀后,其他綜合收益作為不能在當期確認的利得和損失,其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使得投資者獲得了關于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的信息[8]。同時,它與金融風險緊密相關[9],存在波動性和暫時性等特征[10],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傳達企業未來經營管理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的信息風險。現有大部分文獻研究認為相較于傳統凈利潤而言,包含其他綜合收益的綜合收益總額具有更大的波動性(Hodder et al 2006[11];Khan and Bradbury 2015[12];曾雪云等人2016[13])。部分學者證實了其他綜合收益波動與違約風險、債務融資成本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與信用評級則具有顯著負相關關系,證明了其他綜合收益的債務契約有效性[14][15]。但對于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影響債務融資成本的作用路徑還未有文獻進行研究。本文在已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納入違約風險這一中介變量,從企業風險的角度探討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對企業債務成本的影響機制。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對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
基于會計準則得到的財務數字是債權人用來評估公司財務健康和經營能力的一種傳統標準,這種標準已經在債務契約和貸款協議中使用了數百年[16][17]。企業會計信息直接影響債權人對于企業經營活動現狀的評估。
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對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共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其他綜合收益作為會計盈余的補充信息,能使企業資產的賬面價值更接近未來現金流的折現價值,其過高波動會導致企業盈余和經營現金流的不確定增大。第二,該項目的變動還與管理層無法控制的市場因素相掛鉤,反映了市場價格、匯率及利率的變化[18],其過高波動表明企業面臨的市場風險會增加。第三,由于在確認、計量上具有主觀性和不可預測性,管理層為了自身利益,可能會背離會計真實中立的原則,通過對財務數據的操縱來進行盈余管理,如調整其他綜合收益結轉時點[19][20]。綜上所述,其他綜合收益過高波動會引發債權人對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平滑凈利潤的擔憂,也增大了企業未來經營的不確定性。為了保障還本付息的權利,債權人會要求更高的風險補償,提高企業債務成本。為此,本文提出假設:
H1: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其他綜合收益波動越大,債務融資成本越大
(二)其他綜合收益波動與違約風險
根據Merton(1974)[21]的信用風險定價理論,公司債是一份由無風險債券與賣出看跌期權構成的投資組合。看跌期權代表了債權人出售期權的權利,該權利基于公司資產的市場價值,當公司資產的市場價值低于債務面值時,股東就可以選擇違約,即行權。在杠桿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公司資產的市場價值波動越大,違約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他綜合收益對股票的市場價值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具有價值相關性。其波動會引發公司資產的市場價值變化,從而導致公司違約風險增加。為此,本文提出假設:
H2: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其他綜合收益波動越大,違約風險越大
(三)其他綜合收益波動、違約風險與債務融資成本

表1 變量定義表
代理理論認為,債權人要求到期償還本金與利息的權利與股東分享公司剩余價值的權利存在本質區別,這會導致雙方之間存在利益沖突,特別是超額支付股利會減少可用于償還債權人借款的資產,導致財富從債權人轉移給股東,從而增加債券持有人的違約風險[22]。根據信號傳遞理論,銀行等債權人依賴企業的會計信息披露評估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降低信息不對稱風險[23],而違約風險是銀行授信的主要原則,銀行在向企業發放貸款前需要評估企業違約風險進行債務定價。姚立杰等 (2010)[24]指出,企業未來用以償付債權人債務的現金流會由于企業過高的盈余波動導致較高的不穩定性,這增大了債券持有人的決策風險,使得企業債務成本增加。本文預期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會通過提升企業違約風險作用于債務融資成本。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可能會導致企業未來資產價值變化,導致債務違約的可能性上升。企業需要以更高的利率吸引債權人的資金,而這導致了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H3: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會提高企業的違約風險,進而提升債務融資成本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9年至2019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其中,公司財務數據選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與股票收益率相關的數據選自萬得(Wind)數據庫,并通過公式計算得到研究變量。主要使用Excel和Stata16.0進行數據分析和回歸檢驗。
為了避免異常值對結果的影響,本文參考歐陽愛平、鄭超 (2014)[25],石巖、盧相君 (2014)[26],宋雨婷等人 (2021)[27]的研究,按照如下標準處理初始樣本數據:(1)剔除ST、*ST公司;(2)剔除金融企業樣本;(3)剔除其他綜合收益缺失的樣本;(4)剔除所有者權益非正的樣本;(5)剔除財務數據缺失樣本。為了消除極端值對回歸的影響,對所有的連續變量進行5%分位數上下的縮尾處理。最終得到16735個觀測數值。
(二)變量設計
1.被解釋變量:債務融資成本(Cost1)。借鑒鄭軍(2013)[28]、魏志華等(2012)[29]、李子廣等(2009)[30]的做法,采用企業財務費用占期末總負債的比重來考察。
2.解釋變量:其他綜合收益波動(Varoci)。借鑒Bao et al(2020)[15];曾雪云、秦中艮等(2016)[9]學者的研究,以公司第t-2年到第t+2年每股綜合收益的五年標準差作為自變量。
3.中介變量:違約風險(DD)
本文借鑒Bharath & Shumway(2008)[31]提出的信用風險定價模型,測量違約距離。違約距離越小,企業違約風險越大。違約距離的計算方式如下:

其 中,DDit是 違 約 距 離,Equityit為公司總市值,Debitit是股票發行總數與年末市場價值的乘積;為公司債務的面值,是公司年末短期負債與年末長期負債的二分之一的總和;rit-1是滯后一年的年度收益率;Tit設置為1年;σVit是公司資產波動率,通過股票收益率σEit計算而得,其公式如下:

4.控制變量
參考謝獲寶(2019)[7];趙艷和張云(2018)[19]、楊潔(2020[32]等人的研究,選取如下8個控制變量:
(三)研究模型
根據溫忠麟等(2005)[33]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構建以下模型檢驗假設:
為檢驗假設H1,構建模型(1):

為檢驗假設2,構建模型(2):


為檢驗假設3,構建模型(3)

(四)描述性統計
表2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由表2可知,債務融資成本最大值與最小值差值為4.8%,說明企業間債務融資成本有明顯差異。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均值是0.008,標準差是0.014,說明從整體來看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存在一定差距。中介變量違約風險最大值為0.375,與最小值0.021之間差距較大,說明不同企業面臨的違約風險差距較大。

表2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五)相關性分析
表3列示了變量相關性分析結果。債務融資成本與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正相關,在1%水平下顯著,其他綜合收益波動與違約風險顯著正相關,違約風險與債務融資成本之間在1%水平下顯著負相關,初步驗證了假設成立。

表3 主要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
(六)多元回歸分析
進一步對主要變量進行OLS回歸分析得到表4結果。列(1)(2)顯示,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均顯著影響債務融資成本與違約風險。當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增大時,相應地,企業違約風險和債務融資成本均會提高。列(3)加入違約風險中介變量后,其他綜合收益波動(Varoci)與債務融資成本(Cost1)的系數從列(1)的0.0648降至0.0639,兩者仍在1%水平下顯著。表明違約風險在其他綜合收益波動對企業債務融資成本的影響關系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假設H3得到驗證,即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會導致企業整體資產價值的波動,違約距離會隨之降低,企業債務融資成本隨著違約可能性增大而相應提高。

表4 假設回歸結果
(七)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以下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通過替換被解釋變量,采用企業利息支出加上手續費支出和其他財務費用的總額占期末總負債的比重[34][35]作為債務融資成本代入模型進行回歸檢驗,回歸結果符合研究假設;借鑒Altman[36]、徐玉德和陳俊[37]等人的做法,運用Z值模型(Z-Score模型)測量企業債務違約風險,替換中介變量后回歸結果符合研究假設;通過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進行回歸檢驗,檢驗結果依舊符合預期假設。綜上所述,研究模型通過穩健性檢驗。
五、結論與建議
通過本文結論得到如下結論:過高的其他綜合收益波動暗示了企業宏觀市場環境不穩定性以及管理層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的傾向,它會造成企業未來資產價值和經營現金流的不確定性增加,增大企業無法到期償還債務的可能性,向債權人傳遞了一定的風險信號。債權人會通過提高利率或其他限制條款等方式彌補自身的風險溢價,最終使得企業的債務成本增加。該結論支持了相關準則委員會認為企業財務報表應向投資者提供其他綜合收益信息的觀點,也能夠幫助資本市場投資者和債權人更好地理解其他綜合收益本身的信息價值。
根據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了如下建議:首先,凈資產收益率或者總資產收益率是衡量企業業績的傳統指標,其他綜合收益可以為信貸市場債權人提供凈利潤之外的風險信息,未來對企業風險的評估可以納入其他綜合收益項目,把其作為輔助指標進行決策。其次,由于其他綜合收益相關準則本身比較復雜,各組成項目在未來現金流入的時間和金額上也存在差異,且資本市場投資者或債權人對該科目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因此,其過高的波動會增大報表使用者對企業經營狀況的擔憂。企業應規范列報和披露其他綜合收益,并對其異常、過高的波動做出合理、必要的說明,以提升會計信息質量,增強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的投資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