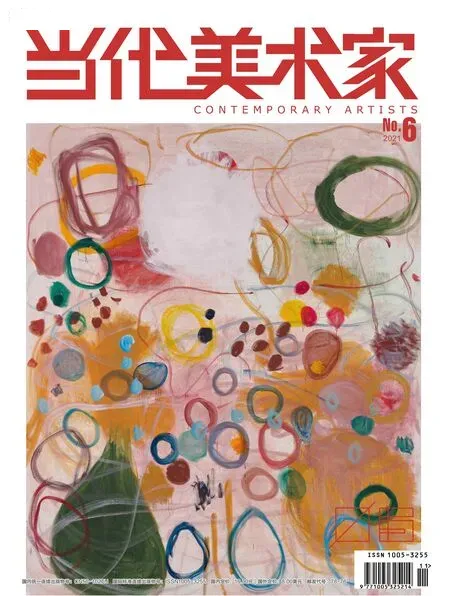錄像:告別烏托邦時刻(1986)
[美]瑪爾莎·羅斯勒 Martha Rosler
譯者 常馨 Translated by: Chang Xin
【文獻說明】《視頻:告別烏托邦時刻》(Video: Shedding The Utopian Moment)是瑪爾莎·羅斯勒(Martha Rosler)參加1984年在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舉辦的主題為“視頻藝術”的學術會議上的發言稿,稿件原標題為《擺脫烏托邦時刻:錄像的藝術館化》(Shedding the Utopian Moment: The Museumization of Video),隨后被編入這次會議的刊物《視頻》(Video),由勒內(Rene)主編,1986年1月由Artextes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文作者瑪爾莎·羅斯勒是美國當代藝術家,其作品形式包括攝影、影像/文字、視頻藝術、裝置藝術和行為表演等。其作品通過女性經驗來關注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間,作品主題也涉及到現代媒介,戰爭等公共議題。
我們已經知道,受20世紀60年代一些“事件”的推動,錄像藝術在其發展早期曾經歷了一個烏托邦式的時刻。彼時,對“生活準則”的思考(包括對生活最終目標的質疑),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知識和藝術的追求。傳播學和系統論取代了戰后早期在西方占統治地位的表現主義藝術范式,新的理論基于麥克盧漢和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遠見,也受到了列維·施特勞斯結構主義的影響,(在這我只是列出幾個代表人物)。藝術家們渴望憑借一種有影響力的、介入者的形象(如果不是像薩滿法師那樣的),去往另一條通往藝術權力的道路,那就是將大眾媒介作為塑造西方文化的能量,無論是與大眾媒介和諧相處,亦或是和他唱唱反調。
無論是怎樣五花八門的想法促使藝術家們奔向電視,更準確地說是奔向20世紀60年代后期引入美國的那些便攜設備,都必然與廣播電視作為當時的主流技術有關。很多早期使用這些技術的人認為自己在進行深刻的社會批評,這種批評專門指向那些作為廣播電視文化或者說一切西方主流技術文化縮影的組織和個人。通過技術媒介,這些批評才得以實現,諷刺的是,這種媒介的互動潛能和多向傳播能力似乎是無限的。藝術家不僅回應著普通大眾的處境,同時也回應著作為當下文化生產者的藝術家面對龐大的大眾媒體產業的沉默和失語:這是文化產業與意識產業之間的對抗。
上述第二種情形的回應或許成為了更直接的動力。早期藝術家們對便攜影像技術的使用意味著對西方文化藝術機構的批判,因為這些藝術機構被認為是另一種控制結構。因此,錄像藝術以“挑戰者”的姿態登場,開始聲討藝術的生產流程、發行“渠道”,以及被動的藝術接受。早期錄像隱含著一種系統性的和烏托邦式的批判——因為錄像藝術并不打算進入藝術體制,而是試圖徹底地改造它。這可以看作是先鋒藝術的革命性遺產——藝術與社會生活的結合,觀眾和制作人的相互交流,有助于跳出現有結構來重新定義藝術。
對主流的、通俗的流行媒介的嘗試逐漸發展出了不同的脈絡。受超現實主義影響的一派希望從電視的日常語言中發展出一種新的詩學,將審美愉悅注入大眾媒體,通過“被解放”的感官創造烏托邦式的一瞥。這并非只是一種試圖短暫逃離工具化現實的享樂主義審美,而是一場解放運動。另外一派比起詩學則對信息更感興趣,這一派沒那么在意先驗的精神而對社會改造更感興趣。從政治層面來說它更傾向于集體主義而非視覺主義,它試圖開辟一個空間,在那里,被沉默的聲音可以有機會言說。
上述第一條脈絡建立在個人的感知和視角上,當然,這就意味著錄像可能成為一種不斷自我展示的私人劇場,和沉溺于自我投射中的納西索斯般的自戀媒介。確實,將個人境況和私人世界置于大眾的公共空間之上,甚至對大眾抱有敵意,這是長期被討論的現代社會的問題。然而,這種對個人經驗和感知的強調,將“表達”視為個人自由的象征(“表達”本身就是目的)成為了錄像作為“錄像藝術”被納入現存藝術結構中的開端。
藝術發行體制的核心目的是通過無視或者祛除作品中隱含的批判來馴化錄像。和之前的現代運動一樣,錄像也必須在與電子傳播技術裝置的關系中尋找自己的位置。然而,將錄像藝術館化意味著長久以來藝術界對錄像和廣播之間關系的忽略,仿佛是在支持錄像藝術對自己的“媒介的本質”進行獨特的現代主義思考。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將嘗試以攝影作為主要例子來梳理19世紀的藝術家關于蓬勃興起的科技社會和市場價值的看法具備怎樣的基本特征。我的討論一方面調用了科學與技術的辯證關系,另一方面,則調用了神話和魔法。思考20世紀早期先鋒藝術面對根深蒂固的技術消費主義所采取的策略,就需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先鋒藝術到底是走向了解放還是選擇了妥協折中?文章的第二部分探討了藝術史的歷史敘事以及利益相關的資助機構在這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文章的第三部分分析了戰后美國先鋒藝術所產生的影響,討論了麥克盧漢關于錄像藝術的形成與接受的觀點所具有的塑造力量,以此來形成對神話與技術之間的關系的思考。
第一部分:前歷史
錄像是一種全新的,有賴于新興的復制技術的藝術實踐。盡管如此,錄像藝術還是已經,或者說正在被框定在上個世紀(19世紀)所打造的盒子內。科學和機器,即技術,從19世紀開始成為新興階級的教育工具,也同樣成為了工農業理性生產的工具,推動了工農業的發展。雖然那個時代的工程奇跡驕傲地在大型展覽和博覽會上展示并供人欣賞,但關于這些科技力量及其伴隨的價值觀如何塑造社會卻不曾形成明確的共識。左右兩派的評論家都將機器的中心地位看作西方文化價值觀衰落的表現。在許多人看來,仿佛是工業化(正是它催生了技術發展)撕裂了社會結構,摧毀了鄉村生活和倡導社會凝聚以及努力工作的傳統價值觀,而正是這些價值觀賦予了生活意義。
傳播媒介以及媒介附帶的知覺效應——當然那些實體的手段,如鐵路(它用鋼筋把結合在一起)也不應當被忽略——扮演了新興中產階級(唯物主義價值觀的傳承者和社會混亂的受益者)日益壯大的霸權中的核心角色。新興的大眾媒介盡管推動了階級和派系之間關于社會權力的競爭和流動,卻也唯我獨尊地在成長中的中產階級,或者說在整個社會當中持續地宣傳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正是這種意識形態賦予了科學一個核心位置。如社會學家阿爾文·古爾德納(Alvin Gouldner)1所言,“(科學)成為了新話語結構中享有盛譽和被高度關注的范式。”更不必多說這種對科學和技術的關注包含著征服、控制和工具主義的隱含目標,而這些則導致了社會的墮落并摧毀了共同體。
從19世紀早期開始,新的復制技術并沒有因為統治精英的使用或消費而成為精英階層的專屬,而是很快融入了文化生活。或許最好的公共案例就是之前已經提到的大眾新聞業的發展,以及同樣在世紀中期被發明的攝影術。誕生于上個世紀(19世紀)的新聞業推動了公共領域的巨大擴張——一個充滿了文化人士的空間誕生了,當中包括了具有文化修養的資產階級商人,也包括了精英貴族。大眾新聞的發展與民主參與的新訴求同步出現。新的訴求希望將未受教育和無產階級大眾也包含在更廣泛的民主參與當中。然而,這種將社會從貴族精英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想法侵蝕了傳統權威,讓此前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陷入危機。
因此,文化價值觀和機器之間的沖突四處蔓延。貴族階級、新興的無產階級群眾、傳統的手工藝者、商人和藝術家都牽涉其中。藝術家一方面反抗文化的技術化和商品化,另一方面又沉溺于具有中產階級特色的“自由市場體系”當中,同時把藝術獨立劃分成為中產階級的自留地。因此,不同的社會成員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對技術樂觀主義持反對態度。無論是文化保守主義者,例如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2,還是政治激進主義者,比如羅斯金的學生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3,都在尋找一種將現代社會與既有社會價值觀相結合的方法。居于智性(和精神)生活中心地位的工具理性促使人們去尋找一種補償性的價值觀,這種想法也許并非牽強附會。浪漫主義運動,無論是向后看還是向前看,都證明了這點。
我們太沉湎于世俗,朝朝暮暮
在擁有和失去間,消耗著人生:
自然與我們形如陌路;
——華茲華斯(Wordsworth)
對于一些人來說,19世紀最糟糕的莫過于社會的政治斗爭,城市住房的瘋狂蔓延,工人階級的不斷壯大,和鄉村生活的荒蕪,而對另一些人(比如莫里斯)來說,最糟糕的則是新興階級的處境——他們匱乏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以及這種匱乏對全社會造成的不利影響。莫里斯認為這事關政治權力,然而這樣的想法卻被打上了技術悲觀主義和反技術的新人文主義的標簽。
美國歷史上對技術的態度十分迥異,起初美國思想家并不信任技術,到了19世紀中期,卻也指望著技術發明能夠改善勞動過程,在發展工業的同時保證婦女兒童的道德發展不受損害。而美國超驗主義詩人和牧師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4最初曾是一名極端樂觀主義者,但卻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變得悲觀。
盡管有懷疑、壓力和焦慮,但是很顯然,開弓沒有回頭箭。在文化圈里,即使是那些對技術樂觀主義和機械時代價值觀最為懷疑的人,也在工作中展現了對科學和大規模復制技術(幾乎是)接受的態度。舉例來說,印象派畫家們將從科學技術那里學習到的光學理論(例如掛毯的編織法)作為他們藝術作品的核心,通過對色彩的強調來與攝影保持距離。印象派拒絕在景觀中展現可見的工業主義痕跡,而是選擇了懷舊的田園牧歌般的再現方式。攝影迫使其他視覺藝術(甚至包括詩學)重新自我反思,但自己卻成為了傳統藝術的模仿者。
如理查德·魯迪西爾(Richard Rudisill)所言,美國人對視覺圖像癔癥般的狂熱早在魔燈發明以前就存在了,所以當復制視覺圖像成為可能,它毫無疑問地立刻直擊美國文化的內心。魯迪西爾還談到愛默生曾在他最有洞察力的時候聲稱自己是最好的觀察外部世界的眼睛。約翰·卡松(John Kasson)觀察到,愛默生“極為關注想象力在民主政治中的可能性”。因此,比起直接投身政治,愛默生更致力于研究“視覺的政治”。對于愛默生來說,政治民主是不完備的,除非它能夠導向完全的自由,在這種自由中,意識和感知被完全點亮……我們對于外部客觀世界地體認伴隨著對其內在性的認知,涉及道德與理智兩個方面。這種認知渴望著民主的參與,并為美國文化的形而上學思考提供了母題。
就在攝影出現之前,受藝術沙龍的影響,美國藝術在美國民眾中的受歡迎度到了一個巔峰,普通人可以通過在俱樂部中訂購或者中獎的方式占有藝術作品,這些在新聞上都有過詳細的報道。沙龍的衰落與攝影技術的興起也是同步的,而攝影技術比繪畫更貼近私人生活的核心,(很顯然)藝術家們注意到了這一點。
值得注意的是將攝影術介紹到美國的人不僅是一個畫家還是電報的發明者——薩繆爾·摩斯(Samuel F. B. Morse)——他從達蓋爾(Daguerre)那里接觸到了攝影術。當他們在摩斯位于巴黎的寓所里聊天時,達爾蓋通過背景板、紗幕和變幻的燈光所提供的原-電影式的幻覺立體透視劇院在大火中毀于一旦。因此,這個故事幾乎具備了神話色彩。盡管在摩斯那里聲音和畫面可以結合,但找到真正可以同步復制聲音和畫面的技術還是花了將近100年。
新技術的適應、融入和對抗的過程于是成為西方藝術史(美國藝術也終于在其中有了一席之地)的一部分。然而,盡管自啟蒙運動開始就有藝術家和科學合作的歷史(雖然他們的市場定位是面向中產階級的),但甚至像印象派和攝影這樣與科學技術深度融合的藝術,也都在強調魔法、詩歌、不可通約性5,并以此來挑戰科學的權威。
建立在內在性與感覺和知覺之上的想象力對藝術家確立自身權威來說至關重要,但他們卻不曾想,這種想象的力量也許是以自己的對手——科學——的新方法和新發現為基礎的。19世紀后期的藝術實踐,無論是被壓抑的超自然主義者、原始主義者、性別主義者還是作為非理性知識來源的精神頓悟,通常都不建立在視覺本身上,而是基于一種闡釋和聯覺,以及對“陰性”(feminine)自然的拒絕之上。如尼采所言,各種動力之間的辯證關系在現代文化中司空見慣。
約翰·費克特(John Feket)在《批評的微光》(The Critical Twilight)中稱象征主義“美學”陷入危機,正歇斯底里地與商品壓力抗爭。費克特稱象征主義“徹底令人絕望和感到無力”地將所有歷史和社會現實拒之門外。華茲華斯關于“得與失”的哀悼變成了審美的倒置以及神秘主義。費克特還特別提到,從蘭波所堅持的“感官的無序”的形式主義轉向更現代的(“迷戀語言并擁抱語言秩序原則”)形式主義美學,促進了當代(包含社會秩序在內的)各種秩序相關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統一。
對現代性的屈服與立體主義密切相關,因其將理性視點等同于非人的文化。我們應當注意,對現實主義的拒絕,例如立體主義將視覺引入其他的感覺,同時拒絕攝影的即時再現,給了繪畫繼續與攝影競爭的機會。感覺與形式的關系一直是藝術家關心的重點,未來主義以一種摧毀時空,摧毀歷史,摧毀傳統的斷裂的方式為現代性和城市主義帶來的“有益的震驚”而辯護。未來主義中的感覺被壓縮到形式當中,于是人物和背景變得無法區分,意識形態也(不得不)被壓抑。盡管未來主義通過抽象和壓縮的方法來處理現代性的概念,但是畢加索的立體主義則將非洲和其他“原始主義”想象作為一個偏離、打斷、表意、不可通約和表達神秘性的技巧,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理性主義的中斷。我們應當意識到,無論是立體主義還是未來主義都拒絕攝影式的空間。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把攝影塑造成了一個理性的資產階級技術控制的仆人,然而事情還有另外一面。世紀之交,攝影已經是發展成熟的一種理性再現技術,不僅能夠展示私人生活或者公共領域的各種奇觀,還成為社會控制的正式或非正式技術手段,例如:警方攝影、城市紀實、工業操作效率研究。照片成為了可供無數人消費的商品。然而,正如之前提到的,攝影美學實踐對模仿其他藝術形式的風格更感興趣。19世紀中期以后的歐洲藝術攝影與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的自畫像關系密切(從茱莉亞·瑪格麗特·卡梅隆6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也與此前對于現實主義繪畫的欣賞有關(盡管是以一種冷靜有距離感的方式,例如彼得·亨利·埃默森7)。
斯蒂格利茨8的攝影分離派9是美國第一次重要的藝術攝影實踐,沿襲了歐洲19世紀末歐洲分離運動的傳統,在這方面斯蒂格利茨有些一手經驗。斯蒂格利茨將象征主義和他的導師埃默森的繪畫現實主義美學融合在一起。象征主義聯覺,意味著感覺的同時發生,這吸引了這位曾經的工程系學生,同時他對于通過無線設備和自動鋼琴來對聲音進行機械復制同樣很有熱情。攝影的例子說明了唯美主義對技術的選擇和展現出的沉默。除了對攝影機的使用(攝影機仍然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機械干擾),大眾復制技術對藝術攝影影響頗大。斯蒂格利茨的雜志《攝影作品》創造了全國范圍,或者說世界范圍內的藝術攝影正典,一直以來照片都堅持版畫和半調圖像的形式風格。然而,這套生產流程最近才開始用于大眾傳媒。可以看出,攝影和大眾文化之間顯然存在距離。所謂的“藝術攝影”卻保留著工藝價值觀,反對“意識勞動”,依賴于自身技術——這是值得被記住的藝術攝影的悖論。攝影和印刷技術被認為是中立的,這種工具性的機器應當被置于審美精英的不凡見解之下。審美的敏感性仿佛是煉金坩堝,煉就了藝術的神秘主義轉向。
1916年,斯蒂格利茨已經完全接受了保羅·斯特蘭德10的攝影現代主義,以致于將垂死的《攝影作品》的最后兩期都獻給了他的作品,也可以說最后這兩期雜志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才繼續發行。在斯特蘭德之后,攝影機裝置和它的“性質”被廣泛認可,取代了手工負片沖洗在藝術攝影操作中的核心地位。對于斯特蘭德和一些人來說,攝像機是一種有意識的觀察工具,允許自己政治化地“切入”進城市微觀世界、鄉村和自然之中。攝影對于他們來說是通向而非遠離社會的媒介。當然了,對另外一些人而言攝影現代主義意味著新的抽象形式主義,或者說,伴隨攝影制作的急速發展,攝影的現代主義接受了科學與理性,但也允許商品世界中的物質象征主義,接受廣告成為自己的信條。然而,攝影的圖像主義已經預示了唯美主義與精英主義的聯合,它們將作為一個高大的堡壘來對抗市場的貨幣手段和無產階級勞動力,對抗將高雅藝術與現代大眾娛樂文化相結合的形式現代主義,對抗商品文化。現代主義,用康德式的表達,則是偏愛物質藝術作品本身但是對藝術作品本應表達的意義卻態度曖昧。形式主義意識形態被一些包豪斯代表人物例如拉茲洛·莫霍利- 納吉進一步深化,他們推行那些關于研究、發展、治療教育法以及實驗的科學詞匯。在藝術和建筑領域,形式現代主義則向所有階級許諾了一種更健康,更高效以及更合適的(解放性的)生活方式。而藝術潛在的革命意圖和為民主參與鋪平道路的愿景,可能很快就會轉變成對于新技術精英的順從。
可以觀察到,盡管戰后美國的現代主義被嚴格地與其他藝術形式和社會生活隔絕開,卻仍然憑借其對媒介物質的迷戀將先鋒藝術納入藝術體制的范疇。為了理解這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有必要去了解肇始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等先鋒藝術運動的目的。彼時現代科技社會已經形成并根基深厚,對傳播和復制技術的使用或者說挑釁態度是先鋒藝術制定的行動計劃。因為他們認為,盡管藝術機構已然成為了社會壓迫的組織形式之一,但仍然有助于實現革命性的社會變革。這重拾了象征主義擾亂感知秩序的努力,但這一次,先鋒派則帶著全新的政治意圖。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目的在于將藝術和日常生活融合并以此來摧毀藝術體制;通過對藝術進行改造,撼動深入人心的流行于大眾社會的工具理性主義,動搖藝術潛在的為奴役制造共識,為大屠殺尋找“正當理由”的能力。

1瑪爾莎·羅斯勒廚房符號學影像6分鐘1975
皮特·伯格將先鋒藝術的此種舉動描述為藝術體制的一種自我批評,是對“藝術作品仰賴的發行機制,和對資產階級社會中藝術地位的雙重反抗。因此,杜尚的“現成品”系列,讓藝術機構為那些被輕視的物品背書,從而暴露了真實的藝術發行機制。伯格寫道:
先鋒藝術家的意圖可以被認為是源自唯美主義的審美實踐,通過對日常生活習慣的反抗,與方法-目的鏈所代表的的理性形成了極大的沖突,隨后成為新的生活準則。
表現主義、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斷裂性力量不僅是藝術世界的越軌之舉,也同樣是對傳統社會現實的挑釁,因此被看作一種解放的工具。正如伯格提到的,先鋒藝術一方面想要用更加集體化和匿名化的實踐取代個人化的創作,另一方面也想擺脫個性化的藝術技巧和狹隘的藝術接受。然而,正如伯格做出的結論,先鋒藝術運動失敗了。因為現實是,并非先鋒藝術摧毀了藝術世界,而是擴張的藝術界吸納了先鋒藝術。先鋒藝術令人震驚的、挑釁的技藝反而成為藝術界令人眼前一亮的招牌。用艾倫?卡普羅(Allan Kaprow)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提出的對立術語來說,反抗藝術成為了藝術。
卡普羅本人作為戰后美國代表性的先鋒藝術家以及約翰·凱奇的學生,大約十幾年前或者更早曾經幫助設計了一種暫時無法被體制同化的藝術形式——“偶發藝術”。卡普羅在《非藝術家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Un- Artist)第一部分中寫道:
此時我們意識到,文化社會學以內部“啞劇”的形式出現。它唯一的觀眾是一本寫著善于創造和表演的專家姓名的花名冊。它看著自己,仿佛望向鏡中,斗爭發生在自封的牧師與同樣自封的突擊隊員,小丑,底層流浪者和三重特工的干部之間,后者似乎正在試圖摧毀牧師的教堂。但是每個人都知道結局是什么:當然了,肯定是在教堂里……
卡普羅明顯意識到,在市場的任何一個地方,獨立藝術的毀滅已成為現實,先鋒藝術家的希望被挫敗了。但是沒有比失敗更成功的了,先鋒藝術的失敗意味著在戰后它成為了學院的一部分。戰后的美國瘋狂地在西方藝術界展現霸權。穩定和秩序似乎已經成功地建立在一個疏離和孤立的藝術上。通過激烈地驅逐,或者說吸收、改造現在已經廣為人知的激進美學,高雅藝術看起來已經克服了在政治和大眾文化領域的負面影響。藝術話語通過唯美主義和原始主義,創造性引入了科學實驗關于技術和魔法的辯證關系,駛向了先鋒藝術的技術時代。
這種霸權在整個“美利堅世紀”一直持續著,直至20世紀60年代,在戰爭和美國軍事化行動的極大推動下,電視和控制論技術急速發展,危機加速了。以廣播的結構和形式為前提,電視僅僅需要給自己添加上畫面便完成了升級。上個世紀(19世紀),廣播已經建立了類似于報紙和攝影的大眾媒體地位,在散播消費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意識形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攝影一樣,廣播讓遠距離之外正在發生的此刻成為了一個和空氣一樣免費的禮物。
廣播盒子成為唯一的“直銷店”,它“售賣”精美的家具,高聳入云的建筑,大教堂、壁爐、鋼琴、盒子里應有盡有,甚至可以聽到汽船的回音。人們仿佛擁有了免費獲得的時間,看不見的東西也仿佛就在眼前,這讓廣播同時具有了科學(以及自然)和魔法的魅力。
盡管效果打了折扣,電視還是具備將攝影和電影的形式融合于一的本事。有了廣告,所有重要的文本和物質世界的圖像混在一起,包括國家的奇觀、街道的混亂,以及無論是對上層還是底層,名人還是無名小卒的私生活的窺視和干擾。電視好像是一個動起來的雜志,甚至說不只是如此。如同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馬歇爾·麥克盧漢,居伊·德波和鮑德里亞等一眾所觀察到的,電視中不斷旋轉的微縮景觀排擠掉了真實世界里更加曖昧含混不清的體驗。
阿爾文·沃德·古爾德納(Alvin Ward Gouldner)評論文化機制(米爾斯)和意識工業(恩岑斯貝爾格)之間的爭論時引用了赫伯特·甘斯1972年的文章:“美國社會最有意思的現象是……品味文化之間的政治斗爭,超越了哪種文化將在大眾傳媒中占主導地位以及何種文化將為社會提供其符號、價值觀和世界觀。”
這種爭論,讀者可以很快察覺到,延續了此前亞里士多德式的古典文化和新興中產階級倡導的科學價值之間的爭論。抽象表現主義追隨了貧窮的波西米亞式先鋒藝術的步伐,充滿了強烈的美學元素, 既沒有像斯蒂格利茨那樣輕視無產階級的同情心,也沒有舒適地身處其中。漸漸地,抽象表現主義發現自己被成功之神青睞——或者說,被詛咒。突然間,這些曾經邊緣化的脫離論者,開始制作在市場上大受歡迎的昂貴商品,藝術家的個人生活也開始被瘋狂迷戀和書寫。波洛克以和詹姆斯·迪恩相似的造型出現在《生活》雜志的封面上,成為另一個曾經反叛如今卻回頭的浪子。被當做大眾名流膜拜的藝術家成為了自身意義的對立面,然而事實一再證明,藝術家只有通過銷售自己的作品才能在發行機構中占有重要地位。人們也漸漸意識到這始終是一種精英藝術,盡管它曾經展示了懷疑和抽象,自由和貧窮,盡管它曾經讓左翼、右翼、民粹者都失望,但是如今它成為了美利堅帝國主義的代言人。
波普藝術緊隨其后,通過強調對父權制的消極和抵制,鼓吹高雅文化的光環和自治精神,大眾文化的力量被公開的程式化地接受。畢竟正是大眾文化和國家促成了抽象表現主義的“成功”,讓藝術作品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樣貼上美國制造的標簽。
通過被模仿、被貶損、被物戀和被扭曲的生產模式,憑借“明星朋友”和身體姿勢,沃霍爾在時尚奴隸和復制機器的簇擁下完成了他錯綜復雜的關于“無力”的懺悔。藝術和技術的關系令人感到諷刺,傳統的油畫和絲網印刷這樣的手工工藝流程被保留,但卻是為了用傳統技藝去復制和重新排版大眾媒體上的攝影符號。先鋒藝術的巔峰是將自己塑造成為大眾媒介的奴仆,“靈暈”終于垂憐了復制品。
正如卡普羅所寫的關于社會語境和藝術觀念的文字:
……實際上,很難不承認登月計劃的太空艙顯然比當代所有的雕塑作品都更高級;往來于休斯航天中心和阿波羅11號的宇航員們之間的對話比任何當代的詩歌都更動人;聲音失真、信號嗶嗶作響、靜電的干擾,以及通訊中斷,這超越了音樂廳里的電子音樂;人類學家被許可拍攝的貧民窟家庭生活的錄像帶,比那些著名的講述生活不為人知一面的地下電影更加迷人;拉斯維加斯那些燈火通明的由塑料和不銹鋼建造的煤氣站可能是迄今為止最無與倫比的建筑;超市購物者們那些隨機的,恍惚的運動比任何現代舞都要豐富;床底的線頭和工業殘骸的廢料比起頻繁出現的廢品展覽更加有魅力;火箭試驗留下的水蒸氣痕跡,靜止,彩虹一般,宛如繪制在天空中的涂鴉,這當然不同于藝術家將氣體作為媒材使用;“南亞劇院”中上演的越南戰爭,或者對于芝加哥八君子的審判,盡管可能站不住腳,比任何戲劇作品都要優秀……等等,等等。非藝術比起典型的藝術更加藝術。
代表著審美觀念的卡普羅,看到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的崩塌,也只能臣服于科學、技術,國家以及迅速更迭的現代城/郊主義的力量,尤其當他們開始在電視中演奏起交響樂時。20世紀60年代的“反霸權”帶來了權力——自由之間的新關系,是更平民大眾的而非前衛先鋒的,是更政治導向的而非美學導向的。學生群體反抗馬爾庫塞所謂的單向度的文化建構及其大眾主體建構。政治上被排斥的人則在反抗迫使他們變得無力的情況和組織。科學和技術的鐵手制造的軍國主義和大規模的戰爭威脅令人騷動不安。對科技和政治掌控的批評催生了共產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民粹主義者、非理性分子、反城市人士、反工業者、反精英者、反智分子、反軍國主義者,青年為中心的共產主義反文化;享樂主義、進步主義、理性主義、反性別歧視、反種族主義、反帝國主義以及生態鏈等概念也應運而生。因此,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之一的高雅藝術也陷入了懷疑,尤其是在年輕的藝術從業者當中。
除了向藝術商人,評論家和美學理論求助,藝術家還從科學、社會科學和文化理論等一切地方尋需求指引。新形式給了藝術的商品化迎頭一擊。“物性”成為一個問題,不僅僅因為藝術品成為了商品,而是因為他們在電子和大眾媒介的產物旁邊顯得遲鈍和無足輕重。
第二部:歷史
終于談到了錄像,這是一個發展得很好的領域。事實上,說起錄像的過去,神話要比歷史更多。我們可以像背誦禱文一樣細數錄像藝術發展的基礎“事實”。一些人會留意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于電視機的改造和破壞式的使用。另外一些人則更傾向于60年代中期橫空出世的索尼便攜錄影機。洛克菲勒資本的推策略鼓勵了藝術家使用這種新的小型科技。然而大家都意識到錄像藝術的歷史亟待書寫。我希望能夠思考其歷史的本質,以及對我們可能存在的價值。
歷史描述旨在為一種公共歷史的主張建立一種合法性。這樣的歷史將遵循一種準解釋性的模型來發展,一段歷史是由重大事件引起的廣泛趨勢,也就是說一方面歷史是由大人物決定的,另一方面歷史則決定和影響隨后發生的事情。錄像藝術的歷史不是社會史而是藝術史,是與其他藝術形式相關聯而非區隔開的。與此同時,錄像希望成為主流而非邊緣化的藝術形式。
為什么現在需要歷史?只是恰好到了合適的時機?還是錄像藝術的捍衛者讀到了美術館墻上宣稱攝影術已死或者衰退的涂鴉?(和那些彩色照片一樣,錄像的保存質量看起來非常糟糕,而且似乎兩者都會輕易地一起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錄像丟失了可信度,那它在展覽界就會一蹶不振。或者說,家庭影像和音樂節目的發展令形成關于錄像藝術誕生和發展的鏈條變得有趣并且必要。
有人擔心如果歷史是由一些不相關的人來寫,重要的時刻將會被遺漏。也有人意識到歷史書寫對保持資金流入至關重要。在大眾媒介中給錄像藝術一個身份催生了書寫錄像藝術歷史的壓力。或者說錄像藝術也是藝術圈的一部分,同樣是由風格鮮明和具有創作意圖的作者所完成的。人們需要在錄像藝術史中察覺到這些特征,這也是其他現代藝術建構自身歷史的一項基本原則。
有時候,試圖去模仿一種既有圖式顯得愚蠢。一個地位顯赫的美國策展人曾對遙遠的1974年作出了如下評論:
將屏幕當做窗戶的這種想法和現實中那些最優秀的人使用錄像的真實經驗是大相徑庭的。布魯斯·瑙曼或者理查·塞拉手中的視頻與其說是透明的,倒不如說模糊不清的更為合適。它是(傳統)藝術觀念的延伸。它在潛意識或者直覺的層面上令觀眾重新回到繪畫,用一種新的方式再一次觀看繪畫。
在將來,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只要曾經觀看過視頻,就都能夠意識到拿著攝影機的藝術家的手。通過特殊的筆觸能夠判斷出一幅梵高的作品不是被偽造的;很快,通過攝影機的使用手法,我們也能夠分辨出戴安·格雷厄姆(Diane Graham),布魯斯·瑙曼以及維托·阿肯錫之間的區別。成為個人標志的錄像風格將會成為一個話題,信息論將會被歸入古老的美學概念當中。
哦!我想這不會是簡·利文斯通(Jane Livingston)的錯,在1974年視頻剪輯還沒成長為能夠和“筆觸”相提并論的一個風格的標志呢!盡管她的評論聽起來滑稽可笑,但她關于“過時的美學觀點”所扮演的角色那話倒是沒錯,事實上唯美主義一直忙于從“信息”那里奪回錄像,而將錄像束縛在藝術的邊界內則是藝術圈的一廂情愿。按照藝術圈競爭的老習慣,他們抹去了電影、攝影以及廣播電視對錄像藝術的影響,無視了關于接受,實踐,原創性意義和“接觸”等相關問題。
歷史書寫并不單單是挑選和排列順序的過程,還是提純的過程。沃爾特·海恩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這位《世界作品》(The World’s Work)雜志的主編喜歡對作者們說“創世故事只用一個段落就講完了”。錄像藝術的歷史不是由學者也不是為了他們而書寫,而是為了潛在的奠基者們,為了去藝術館參觀的大眾,為了其他行業同仁,為了建立收藏和展覽的基礎。錄像藝術的歷史是流行文化的歷史,是一座萬神殿,是一段純粹的敘述。更重要的是,這段歷史是包容的而非挑釁的。出現在這段歷史早期的名字可能是并未因錄像藝術而被知曉的藝術家,也可能并非一直活躍在這個圈子內,還可能不是多年來或者現在仍有作品在藝術館中展覽的藝術家。當然,他們會是紐約客,而非底特律人,也不會是盎格魯人和圣弗朗西斯哥人,更不用提圣地亞哥人了。一些歷史記載無疑會承認歐洲人的貢獻(但那些可能更多只是是在歐洲發生過的歷史),但歷史不會忘記加拿大人,甚至日本人所做出的貢獻,想象他們已經進入西方藝術的世界!最后,作品的類型也有電影和雕塑的一席之地。錄像歷史的編纂是開放性和實驗性的,旨在創造一種具體的尚未出現的或者試圖建構的形式。我們甚至希望讓歷史留存一些開放式的記錄,而不是一切都那么確鑿無疑……
因此,一些人也許會告訴我們讓錄像進入藝術館的體系是目前最好的保留錄像藝術自治權一定程度免于市場吞噬的方法,但它仍然會限制和擠壓一些不為人知的“留白”區域,而這些區域恰恰是早期錄像藝術發展的社會環境。
第三部:神話/迷思
在每一段錄像藝術史的發端都寫著白南準的名字。瑪莎·基弗爾(Martha Gever)一篇頗有影響力的文章就談論了白南準在紐約惠特尼美術館的一場展覽中無與倫比的場景,文章稱白南準是被加冕的藝術家。換做我,我會使用“神圣化”這個詞,因為看起來他生來就是要免除錄像藝術的原罪。白南準的神話意味著他為把錄像藝術從電視的掌控中解放出來,打好了全面而堅實的地基,因此現在錄像藝術可以自由地繼續其他嘗試了。白南準還將錄像藝術歷史從無聊的復雜性當中解放出來,使一個不是那么秩序井然的現狀成為可能。我們將這位先知放在最前面,但我們現在并不需要爭論什么是金科玉律,也不需要再神化出另外一個高大形象,因為現在的錄像藝術產業仍需要嘗試許多新鮮迥異的玩意兒。
白南準的神話開始于1958年的德國(多么具有技術優勢的環境),在約翰·凱奇這位典型的現代主義的先鋒藝術家的幫助下,他頓悟了。瑪莎·基弗爾寫道后來白南準在1972年寫給約翰·凱奇的信中說:“我認為我過去14年的時光不過是1958年達姆施塔特(Darmstadet)那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夜晚的余波罷了。”大約1960年,白南準來到美國,或多或少地和激浪派運動建立了關系。激浪派是一個典型的先鋒藝術,它渴望打擊藝術體制,它將媒介、城市碎屑和語言混合使用,自命不凡地通過貶損一切獲得樂趣,激浪派也不看重藝術的作者性、珍貴性和控制性。據稱,白南準參與其中,并在一個激浪派的活動上放映了他第一盤錄像帶。再一次!就如何獲得藝術資助這個問題,白南準再一次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據說,白南準用于拍攝這支錄像帶的設備是從洛克菲勒基金處獲得的,是最早一批到達美國海岸的便攜式設備。在錄像藝術的神話里,這盤錄像帶就是教皇!
因此神話的一部分包含了一位來自東方的旅人,他來自一個被戰爭(我們的戰爭)破壞了的國家,由一位先驅式的先鋒藝術大師在德國這個科技天堂啟蒙,后來有一段時期在美國持續地挑釁電視這座“圣殿”。隨后,他捕捉神在世間的使者的畫面并將其帶回到先鋒藝術中。緊接著,他從先鋒藝術中離開,開始象征性地將意識工業整合進文化機制的方法觀念中,以此來實現美國文化光譜兩端的聯合。當然,他所做的一切始終有著來自政府、藝術館、廣播機構和其他體制的支持。
噢!當然了!他是一個典型的男人。一個站在男性權力一邊,向父權社會鞠躬的英雄,也許僅僅是看起來吧!他的作品包含著對女性身體的迷戀,將她們的身體變作一個可以被自己彈奏的樂器,此外則是對其他男性藝術家/魔術師或者先知(典型的即約翰·凱奇)的致敬和效忠。
可以說,神圣的白南準做了藝術圈一直渴望的事情,那就是褻瀆電視。他破壞、玷污、迷戀、復制電視機;用泥土填滿電視機并以此充當象征性的排泄行為;讓無知且轉瞬即逝的電視機與永恒的智慧,也就是佛陀相對而坐;在電視機里種滿植物以此將電視機和自然時節并置;將電視機變成家具的一部分以形成與建筑和室內設計的對照,最終,將電視機的信號變成了一段彩色的音樂噪音。
白南準侵犯電視的神圣性,干擾他非物質的信號,用滑稽的“創造力”搶了電視機鮮明工具性的風頭。由此,白南準將電視機變成了藝術文化的一部分,把電視看作是日常生活中受到象征主義影響的部分,也就是阿倫·卡普羅口中的“反藝術”的藝術。
基弗爾討論了白南準那些裝置帶來的催眠效果——形式化的電視信號,模擬觀眾的被動性,用審美性的娛樂替換國家和市場傳遞的信息。在一些裝置作品中,觀看者被要求平躺下來。他既不分析電視提供的信息和產生的影響,也不提供基于理性的能夠與電視信息對抗的話語,更不試圖讓這個技術為他人所用。他所提供的只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文化硬件所演奏的大規模的交響曲。白南準將電視象征性地抽離出常見的環境,至于從觀念上或者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電視造成的問題,他對此則毫無野心。人們因此困在了白南準戲謔的詩學當中。
白南準在這些神話般的歷史中的形象融合了魔法和科學這對為人熟知的矛盾。他強化而非有效挑戰主流的社會話語。這為什么重要呢?歷史上先鋒藝術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力量顯得曖昧不清。超現實主義和達達主義試圖在機器社會去反抗和摧毀藝術的體制化。他們將藝術和日常生活融合,通過解放感官,釋放異見者和反叛者的力量去改造藝術。但很明顯,他們的嘗試失敗了,然而后繼者們,包括那些電視技術的使用者,還是(應當)堅持著同樣的目標。
馬爾庫塞在1937年的文章《文化的肯定性特質》(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中強調,精英階層是如何通過文化,利用“天上掉餡餅”的誘惑以及個人成長的話術將大眾的意識從群體性生存困境轉移到個人應如何努力打造自己的心靈花園上來。馬爾庫塞簡明扼要地揭示出西方社會的文化如何打擊社會行動以及如何強化被動接受。而在西方傳統中,形式一直被當做是對觀眾產生了實際影響的方式。
讓我們簡單看看美國先鋒藝術是如何遏制大眾媒介對文化機制所造成的傷害吧。約翰·凱奇和黑山學院派幾乎全方位地影響了這些藝術的風格。凱奇和他的伙伴們教會了寂靜主義者關注日常生活,關注感知和情感,這種關注是包容的而不是排外的。然而,一旦涉及到是什么決定何為感知對象這個話題,一切便戛然而止。這種情況并不陌生,世紀之交美國的反現代主義運動也有此特征,例如工藝美術也只強調審美體驗的治療作用和精神體驗的重要性。
凱奇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作品,就像邁納·懷特(Minor White)的攝影作品一樣,受到了東方神秘主義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反理性,反因果邏輯的禪宗氣質,依賴頓悟來提供瞬時的超驗,實現從沉重日常到崇高體驗的轉變。這樣的體驗以感覺創造為基礎,在冥想中抵達此境界,但不能被翻譯成象征性的話語。約翰·凱奇式的方法有賴于先鋒藝術帶來的震驚效果,他的做法總是反常規接受過程的,或者是反常地結束。像是彈奏鋼琴的弦而非琴鍵,或者是在音樂會前專注地調音,以及將電視機變成一件樂器。像卡普羅抱怨的,這觀念實在太過強大以致于很快非藝術比起藝術更藝術了,這意味著這種本應具有挑戰性的反藝術實踐,這種反美學,這種不能被體制化的“感性意識”形式,很快就被體制化了,被貪婪的官方藝術機構吞噬了。
很多早期玩錄像藝術的人都曾有過類似的策略和想法。一部分(白南準就是其中的一員)人希望借由錄像來反對電視。這是一種反抗式的實踐,展現出一種對老大哥的敵對姿態。他們公開否認所謂的“制造藝術”的概念,道格拉斯·戴維斯(Douglas Davis)稱錄像藝術是“令人厭惡的術語”。帶有科學現代主義的詞匯“實驗”被認為是針對20世紀60年代語境的一種憤怒的政治回應。對于另一些人,信息論在藝術界和文化批評中的流行,使得重新將錄像作為有效的、社會賦權的多重信息傳輸手段,而不是個人化被動地接受意識形態或亞意識形態的灌輸。
讓我們來談談麥克盧漢。麥克盧漢最初堅定地選擇文字傳統,即閱讀,但是后來轉而支持電視。麥克盧漢以一種不容置辯的警句的方式,斬釘截鐵地將歷史簡化為一連串“技術首要導向”的序列。很多藝術家喜歡這個觀點,既因為它很簡潔明確,也因為它形式嚴謹。他們喜歡“媒介即信息”的說法,也喜歡麥克盧漢將藝術家看做“競賽的觸角”。麥克盧漢提供給反文化一種通過理解來克服一切的想象。共產主義者,無論是反文化派還是左翼人士,則都被“地球村”的概念吸引,并試圖強調一種前文字文化。同時性概念和回歸感官直覺的伊甸園的想法給了身處在異化的、壓抑性的單向度工業社會中的嬉皮士和批評者們一個玫瑰色的迷幻春夢。
約翰·費克特寫到麥克盧漢反對意識的神話般的和類推式結構(這種結構在列維施特勞斯的寫作中倒是顯得很有魅力)而是轉向邏輯的和辯證的論述,用費克特的話說“為意識移置打開了大門,由內在聯系(無論是社會、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的)轉為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先驗性整體。”費克特于是立刻引用了羅蘭·巴特關于神話的論述(此處有省略):
……神話是一種去政治的言說。人必須天然地理解“政治的”一詞更本質的含義,理解它在描述真實的人類關系全貌和社會結構時的作用,還要理解它塑造世界的力量。神話并不否認任何,相反的,神話的作用就是去談論;但用一種被簡化了的方式——神話提純了事實,讓它變得無辜,賦予了它天然和永恒的合法性,神話用陳述性而非解釋性的方式讓事情變得明晰。神話有效地從歷史邏輯轉換到了自然框架:它拋棄了人類行為的復雜性,轉而賦予了他們一個簡單的本質,于是辯證法走到了盡頭。通過那些肉眼不可見的東西,神話構筑了一個沒有矛盾的世界,一個沒有深度的,開放的(脆弱的),浸潤在顯而易見的事實之中的世界;神話還構建了令人歡欣雀躍的透明性,即事情本身即意義所在。
這是現代藝術家們做的夢!而麥克盧漢讓藝術家確信自己是一個具有洞見和神話創造能力的巫師。
麥克盧漢寫到藝術的功效應當是“令不可名狀的發生在精神維度的嶄新體驗得以被感知和被檢視。”他還提到,和科學一樣,藝術是“一種實驗室的研究方法”。他稱藝術為“一種預警系統”和“雷達反應”,也就是說,藝術并不能促使我們改變而是幫助我們維持平穩的航線(一種軍事術語)。藝術幫助我們適應技術帶來的改變,技術現在看起來似乎賦予了自身凌駕于人類這個技術的造物者之上的力量。
麥克盧漢給了藝術家一種與神話有關的神秘力量,去滿足他們征服或者削弱大眾媒介威力這樣一個無力的幻想。
藝術家們選擇去接受而非分析自身的力量,他們相信藝術的力量源自心理學和生物學領域而非社會。于是,他們拿出那些已經陳舊的配方,認為可以通過一種新的方式來使用它,這個配方記載著形式主義先鋒藝術與日常生活現象以及文化之間的關系。
我無意去追溯麥克盧漢主義對錄像藝術產生的實際影響。畢竟,藝術家和其他人一樣只是從他們周圍的話語中汲取他們所需要的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這些內容。許多進步主義者和反建制主義的創作者在麥克盧漢主義(當中當然也夾雜著一些道聽途說)的刺激下,與新媒介在藝術館體系之外展開了合作。
顯然,和其他理論一樣,麥克盧漢主義給藝術家們創造了通過反射強勢的媒體的光芒來發光發熱的機會,并且利用形式化的模仿美學給予了媒介凌駕于萬物之上的權力。
結論
一些新的錄像藝術史已經采用了這種形式化路徑來描述藝術家們將藝術元素對象化的嘗試,仿佛這樣的修修補補可以幫助逃離已經內化于整個藝術體制當中的權力結構。對形式主義方法的強調已經令藝術家無意識地,像麥克盧漢一樣,臣服于凌駕于日常生活之上的媒介力量。在將所謂的錄像藝術與其他使用錄像技術的行為區分開時,藝術家們仍心照不宣地認同了藝術的轉型是關于形式、認知和感覺的過程。至少,這促進了一種神秘的關系,即關于生產資料是如何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上被結構化、組織化、合法化和被控制的問題。
錄像藝術比一般的藝術品交易更難賺到錢。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藝術館和委托中介讓錄像藝術遠離市場交易, 但他們開出高額的費用。市場上行情冷清的藝術會不斷萎縮并最終消失在藝術評論體制內,錄像藝術自然也不例外。錄像藝術評論在主流出版物中始終是少見和不引人注目的。這樣一來,那些既得利益者又獲得了將藝術理論化的權力。在缺乏評論界支持的情況下,錄像藝術的藝術館之路必須將藝術實踐和話語中的一部分自我閹割,以變成令人感到熟悉的和被認可的模樣,好去滿足那些臭名昭著的保守的藝術館委員會成員和基金會成員——當然也已經有一些超越了這些狹隘視野的作品在藝術館中被展覽。
再次重申,這樣的歷史書寫似乎建立在完全的對電視和對藝術館體制的(偽)挑釁上,建立在將形式主義不加批判地肯定為某種神賜的能力之上,建立在對于技術官僚的科學主義的依賴上,用高度抽象的時間、空間、控制論循環和生理學取代了關于人類和社會的討論,也就是說歷史書寫建立在一種直接從過時的,不可信的形式現代主義中提取出的詞匯上。
通過將錄像藝術與雕塑、繪畫以及靜物結合,藝術館提升了裝置藝術的地位。裝置藝術無法離開藝術館的土壤存活,而藝術館通過接納無數被馴服的和充滿魅力的硬件裝置成為一個展現高科技的擴張性空間。策展的框架傾向于不同的類型,這樣一來錄像就被不得不按照陳舊的形式分類: 紀錄片、個人影片、旅行片、觀念影片、預處理圖像,現在則是恐怖片、舞蹈片和風景影片(以及音樂片)。與此同時,只有勇敢的策展人才會常規化地放映紀錄片。甚至像交互式系統這樣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帶有挑釁色彩的藝術形式,現在也很少出現了。
也許藝術館化最嚴峻的結果是領域的“專業化”,伴隨著不可避免地對所謂的“制作價值”的膜拜。事實上,這些只不過是一系列既定的商業廣播電視的風格變化,充其量也就是電子宇宙中的客觀協同作用罷了。沒有比讓藝術家為廣告制定新策略和裝點門面更適合意識產業的了。問題是,“生產價值”意味著花費巨額的資金在制作上。電腦剪輯迅速成為錄像藝術的生產標準,所花費的成本是人工剪輯影片的十倍。一些極為真摯的錄像藝術家認為這種技術形式的密集出現會暴露電視的操縱意圖。然而,先鋒藝術入侵藝術體制和高科技的失敗歷史暗示了相同的失敗的命運。
阿爾文·古爾德納這樣形容藝術和媒體之間的關系:
無論是文化機構還是意識產業,都對應著現代社會意識的分裂性特征:極端不穩定的文化悲觀主義和技術樂觀主義的混合體。文化機構更有可能成為“壞消息”的載體,例如:生態危機,政治腐敗,階級歧視;然而意識產業則扮演著希望的提供者,和專業的光明面觀察者。文化機構在政治中顯著的無能和在結構上的被孤立為他們種下了悲觀主義的種子,然而意識產業中的技術人員卻被最強大,最先進和最昂貴的通信硬件包圍著,并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他們的樂觀主義恰恰根植于這樣的日常經驗中。
我們姑且推斷美國錄像藝術家當前對于超級高科技的狂熱是出于嫉妒。否則,如果藝術家們在體制化的刺激下轉而希望借用技術的樂觀主義力量來克服自己的悲觀主義情緒,那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
另一方面,正如對“白南準神話”研究所揭示的,認為最好的挑釁方式是毀壞電視的物質存在,干擾其信號或者其他的愚蠢行為同樣是有問題的。電視的力量在于能夠利用信息,無論是有趣的,還是無聊的信息,通過不停地重復圖像來占據市場的每一個角落。我們當然可以提供一系列更具社會導向和更具社會生產力的反抗性實踐,這些實踐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本——而不是來自或圍繞著行業和機構。當然,這些藝術,必須更大程度地生存在藝術館之外,而非其內部,不過放棄藝術館的領地是愚蠢的,因為那兒仍是最容易接觸到其他制作者的地方,也是挑戰無能的藝術機構的地方。顯然,眼下或者說長久以來的問題仍然是誰在現代世界掌控了傳播方式,以及在未來即將被創造和接受的話語形式又會是怎樣的。
注釋:
1. 阿爾文·古爾德納(Alvin Gouldner,1920-1980),美國社會學家,文化批判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
2. 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主要的藝術評論家之一,也是英國藝術與工藝美術運動的發起人之一。
3.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國藝術與工藝美術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4.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生于波士頓,美國思想家、文學家。
5. 托馬斯·薩繆爾·庫恩的提出的概念。庫恩看來,是通過科學革命。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理論經過科學革命推翻另一個,這兩個理論在邏輯上是不相容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甚至是不能比較的,即是說由于它們在概念結構上的根本差異造成彼此不可比較。這種不可比較的特征,庫恩稱之為“不可通約性”。
6. 朱麗亞·瑪格麗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1815-1879),英國攝影師,以抓住模特個性的柔焦人物像著稱。她拍攝過的著名人物有托馬斯·卡萊爾、約翰·赫舍爾爵士、艾倫·特里、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她還拍攝帶有寓言或宗教意義的舞臺照片,類似拉斐爾前派的畫作。
7. 埃默森(Peter Henry Emerson,1856-1936)是英國作家和攝影師。他的攝影作品是推廣攝影藝術形式的早期例子。他以拍攝具有自然背景的照片而聞名,并且與攝影界對攝影的目的和意義存在爭議。
8. 阿爾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是一位身兼各派的全才攝影家。他早期曾是畫意派攝影高手,后又成為直接攝影的倡導者和先驅者。作為攝影分離派的創辦人,他積極向美國藝術界引進包括馬蒂斯、畢加索在內的歐洲前衛藝術家,對美觀現代藝術觀念轉變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被譽為美國“現代攝影之父”。
9. 推動攝影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與高度依賴繪畫的藝術攝影和畫意攝影相分離,帶領攝影藝術走向現代。
10. 保羅·斯特蘭德 (Paul Strand)習業于斯都格里茨,后來成為電影攝影師。20世紀美國攝影藝術界一位承先啟后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