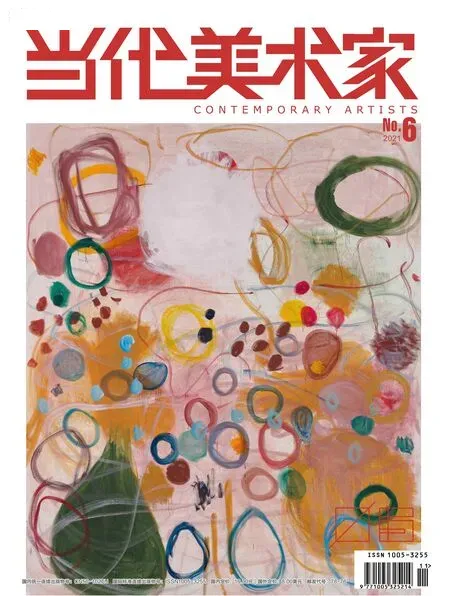民族共情語(yǔ)境下的川蜀地區(qū)藝術(shù)視角
吳洪亮 薛江 Wu Hongliang Xue Jiang

1“超融體——2021成都雙年展”民族共情單元展覽現(xiàn)場(chǎng)
“2021超融體·成都雙年展”于2021年11月7日正式對(duì)公眾開(kāi)放參觀,此次雙年展在注重當(dāng)代藝術(shù)新形式和新動(dòng)向的同時(shí),聚焦川蜀與雪域的聯(lián)動(dòng),觀照民族主題創(chuàng)作,展示以漢藏藝術(shù)交流為代表的多民族藝術(shù)共情共生,以別樣的視角呈現(xiàn)中國(guó)當(dāng)代藝術(shù)發(fā)展的不同線索。“民族共情”作為八個(gè)主版塊之一,圍繞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主題,呈現(xiàn)了川蜀地區(qū)延續(xù)至今的重要文化態(tài)勢(shì)。
中國(guó)作為多民族國(guó)家,豐富的多民族文化和民族交流中產(chǎn)生的能量是形成中華文明的重要推動(dòng)力。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蜀之地,在歷史上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積淀,同時(shí)作為多民族聚居地,四川是中國(guó)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隨著20世紀(jì)以來(lái)新的藝術(shù)形態(tài)的涌入,藝術(shù)的民族問(wèn)題成為許多藝術(shù)家思考的重要內(nèi)容。從20世紀(jì)30~40年代的旅邊潮開(kāi)始,西南地區(qū)成為藝術(shù)家關(guān)注“邊地”的重要區(qū)域,這既是國(guó)內(nèi)藝術(shù)家廣泛關(guān)注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開(kāi)始,也是川蜀地區(qū)參與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進(jìn)程的例證。
新中國(guó)成立之后,隨著西藏和平解放與川藏線開(kāi)通,成都愈加成為漢藏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錨點(diǎn),以民族文化共情為土壤,無(wú)數(shù)行走在川藏線上的內(nèi)地與藏地藝術(shù)家,用他們的作品記錄了這一宏大的文化交流潮,同時(shí)在多元民族文化滋養(yǎng)下,他們的許多作品又成為中國(guó)藝術(shù)發(fā)展的重要?jiǎng)幽堋T凇懊褡骞睬椤卑鎵K中,藝術(shù)家們的創(chuàng)作雖然圍繞這一核心主題,但具體的敘述內(nèi)容和藝術(shù)語(yǔ)言又各有不同。
作為早期進(jìn)藏的代表藝術(shù)家,韓書(shū)力用他幾十年如一日的深耕延續(xù)著自己對(duì)于民族文化交流的眷戀。吳長(zhǎng)江、于小冬、李新建都是20世紀(jì)80年代進(jìn)藏創(chuàng)作的代表,或長(zhǎng)期駐藏,或多次成行,藏區(qū)成為他們創(chuàng)作的代表性內(nèi)容,在長(zhǎng)期與藏區(qū)交流的過(guò)程中,逐漸形成各自更具特色的風(fēng)格。同樣表現(xiàn)朝圣的藏民群體,袁武以單幅個(gè)體的方式進(jìn)行創(chuàng)作。田黎明則用如詩(shī)一般的繪畫(huà)語(yǔ)言表達(dá)了對(duì)中國(guó)文化中恬淡自然的美學(xué)理念的追求。長(zhǎng)期以軍旅身份生活在西藏的藝術(shù)家臧躍軍,對(duì)西藏文化有著獨(dú)特的執(zhí)著,作品充滿了濃郁的藏地文化風(fēng)格。馬琳以出色的光影構(gòu)建藏地題材,圍繞現(xiàn)實(shí)的真實(shí)和精神的幻化之間的平衡。王兵深入藏區(qū)游歷,繪畫(huà)以不大的尺幅,記錄了真實(shí)的見(jiàn)聞,線條與色彩可見(jiàn)藝術(shù)家深厚的版畫(huà)創(chuàng)作功底。劉商英多次深入西藏阿里、內(nèi)蒙古額濟(jì)納旗、新疆羅布泊和阿爾金山等地進(jìn)行野外現(xiàn)場(chǎng)繪畫(huà)項(xiàng)目,將繪畫(huà)與身體行為并行,以苦行的方式融入自然,與自然對(duì)話共鳴的作品。張洹在旅行中以多媒體形式輯錄了一路西行的人文之旅。熊文韻長(zhǎng)達(dá)4年持續(xù)往返于川藏和青藏公路,圍繞自然與環(huán)境的主題,呈現(xiàn)了一場(chǎng)特殊的公共藝術(shù)形態(tài)。楊越巒以鏡頭記錄自己在青藏高原的見(jiàn)聞。李青稞描繪四川彝族生活,兼工帶寫(xiě),用中國(guó)傳統(tǒng)工筆人物畫(huà)傳達(dá)女性細(xì)膩而溫暖的情感。黃潤(rùn)生同樣聚焦少數(shù)民族的生活,將感性抒發(fā)與理性傳達(dá)融洽地呈現(xiàn)出來(lái)。
民族文化的交流從來(lái)不是單向的,除了不斷有藝術(shù)家通過(guò)川藏線汲取創(chuàng)作靈感的同時(shí),在這種多民族的交流中,出現(xiàn)了一大批在大的民族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少數(shù)民族藝術(shù)家,他們的作品突破了傳統(tǒng)民族藝術(shù)形式和內(nèi)容的固有形態(tài),呈現(xiàn)出繽紛的形態(tài),使得這一多民族藝術(shù)交融共情的潮流更顯宏大壯美。
藝術(shù)家噶德將油畫(huà)的表現(xiàn)方式與藏地的巖畫(huà)、壁畫(huà)等風(fēng)格結(jié)合,在層次的變化中展現(xiàn)圍獵畫(huà)面的節(jié)奏,以斑駁的視覺(jué)效果,訴說(shuō)畫(huà)面背后厚重的歷史沉淀;巴瑪扎西則以水墨的層次來(lái)糅合畫(huà)面中的文字和圖像,以非真實(shí)的組合,穿插線條,呈現(xiàn)頗具現(xiàn)代感的水墨探索。藝術(shù)家邊巴從早期的架上作品逐漸擴(kuò)展表達(dá)手法,回歸故園語(yǔ)境,是對(duì)傳統(tǒng)生活生產(chǎn)方式的懷念以及藝術(shù)化的留存。次仁朗杰、德珍夫婦以架上連環(huán)畫(huà)的方式,描繪四川甘孜、阿壩地區(qū)加絨藏族關(guān)于青稞的傳說(shuō),內(nèi)容豐富且可讀性強(qiáng),借鑒傳統(tǒng)色彩的畫(huà)面搭配使其呈現(xiàn)熱烈醒目的效果。
在現(xiàn)當(dāng)代藝術(shù)發(fā)展的歷程中,四川能夠成為不可忽視的陣地,“民族共情”提供了特殊且重要的創(chuàng)作土壤。同時(shí),正是這些頗具分量的“民族共情”作品的出現(xiàn),又進(jìn)一步帶動(dòng)了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風(fēng)潮,共情、共融、共生成為這一風(fēng)潮下頗具代表性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