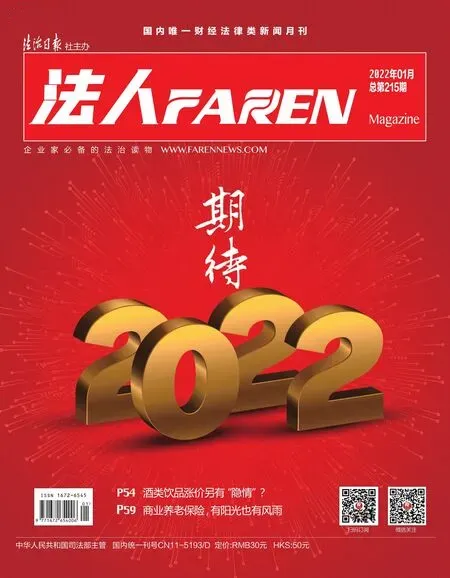醫者仁心:理性與感性的平衡
李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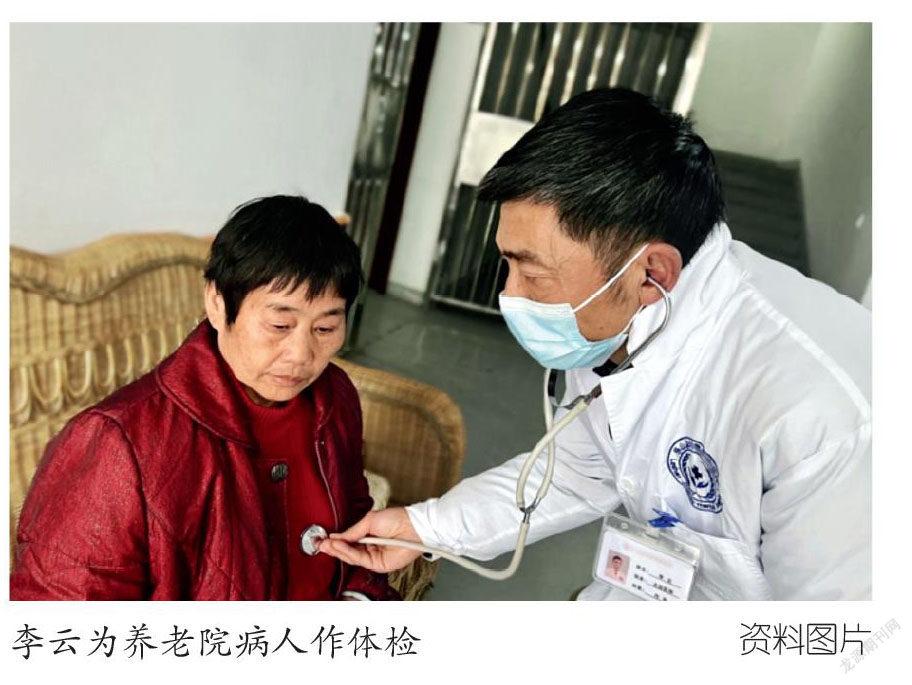
和平年代,醫務工作者站在“生死場”最前沿,嫁接著生命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時間悄然走進2022,忙碌的他們為給病患帶來更多從容應對未來的力量,少有閑暇憧憬剛剛到來的新年。
1月1曰,《法人》記者聯系到3位在不同醫院、不同科室,卻肩負著相同責任的醫務工作者,試圖體會他們的“十字人生”。
是醫者,也是患者
2022年1月1月,汪喜順接到記者采訪電話時,剛結束了一臺手術。“昨天24小時值班,今早又完成了一臺急診手術。”他的聲音略顯疲憊。
作為首都兒研所的骨科醫生,幾乎每天都能見到清晨5點的北京,是汪喜順的工作常態。他笑言:“家離單位22公里,晚出發10分鐘可能就會晚到半小時,耽誤不起。”
汪喜順從事兒童肢體畸形矯正工作。但孩子們往往無法說清癥狀,而且有時哭鬧不止,醫生只能依賴于家長的描述和縝密的體格檢查,無形中增加了處置難度。“兒童骨科患者,很多都是急性肢體骨與軟組織損傷,需要醫生及時明確損傷部位,通過有效輔助檢查作出準確診斷,采取有效處理措施。”汪喜順坦言,“家長心急如焚,我們也會跟打了雞血似的忙得不可開交。”
2021年,汪喜順與同事接診過一位出生僅9個月卻患有先天性腓側半肢畸形的嬰兒,大家都在心底暗自埋怨命運對小病患的不公。在連續進行了數次手術后,治療告一段落。“孩子一歲多時,她的父母發來照片,我們看到她如今能借助支具筆直站立,心情難以言表,覺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2022年是汪喜順從醫的第8個年頭。“我熱愛這個職業,因為我曾經也是一名嚴重腸胃炎和鼻竇炎的患者,得到了醫生護士無微不至的照顧,從此人生有了方向,原本喜歡文學的我最終棄文從醫。
不忘初心,一年300多臺手術
十幾年前,盧炯在報考研究生時,毅然選擇了普外科中最為復雜的專業之一一膽道外科。談及當年的初衷,已是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肝膽外科醫生的他告訴記者:“膽道疾病的病因紛繁復雜,病情變化多端,作為醫生,要敢于承擔,敢于挑戰。
作為外科醫生,手術幾乎占據了盧炯的大部分時間。“我每天早出晚歸,不是在手術,就是在門診,平時還要抽出時間完成科研及教學工作。最忙的時候,連續一個星期,回家時孩子都已經睡熟了。2021年,他一共主刀做了300多臺手術,最長一次持續了7個多小時,“不吃不喝也沒上廁所,結束之后感覺身體已經被掏空了。
盧炯十分推崇醫生特魯多在墓志銘上鐫刻的那句名言: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這3個詞像3級階梯,升華出醫生的境界。豐富的醫患溝通經驗讓他體會到,一位醫生不僅要在學識、技術上擁有很高的造詣,人際溝通能力也十分關鍵,“手術做得再好,如果患者精神垮了,也很難達到預想的治療效果。”
2022年,盧炯最大的期待是能在肝膽胰微創手術方面取得更大進步。“醫學在不斷發展,醫生也需要不斷學習來提高自己的診療技術,只有做到精益求精,才能給患者帶來更多的福音。
竭盡全力,留住生命
退休半年后,李云被四川省樂山市一家醫養結合的養老院聘為內科醫生。與他之前診治的地方病患者和高寒疾病患者不同,現在他面對的多是器官功能衰竭的老者,是患上阿爾茨海默病的病患,是癱瘓多年的耄耋老人。
“從事老年病治療,必須是’多面手'大部分老年病患,都會把醫生當作是包治百病的’神醫’,覺得醫生是他能抓住的最后那根救命稻草。李云回憶,2021年,一位患有支氣管哮喘疾病的老人在搶救之際氣喘吁吁地說,“李醫生,今天我把命交給你了……”而平時這位老人從不求人。“能說出這句話,可見在生命攸關時,人是多么無奈和無助。他感慨地說。
每天上班,李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房。“每當看到幾十個床位都是滿滿的,我就坦然了,因為一個都沒少。但如果突然看到一張床空了……”說到這里,李云沉默了。
和同行聚在一起時,總有其他科室的醫生自豪地說,“我治好了很多病人”然而,從事老年病治療的李云只能說:“我的治愈率幾乎為零,卻延續了他們的生命。
(責編白馗美編劉曉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