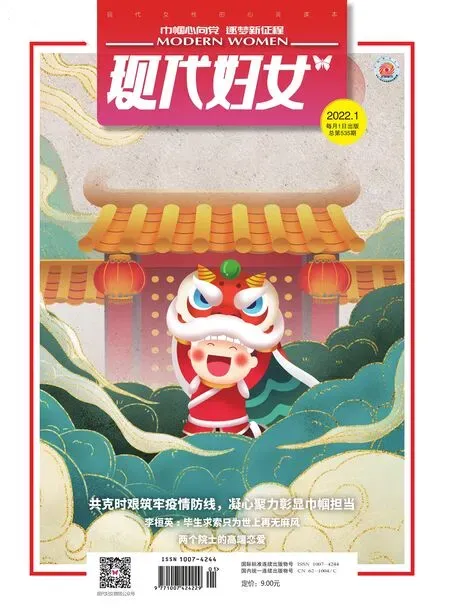尹學蕓:只有默默耕耘,作品才能熠熠發光

作家莫言在其公眾號上更新了一篇題為《我小時候都讀什么書》的文章。文中分享的關于讀書的童年往事令人印象深刻。
莫言說,那時候既沒有電影更沒有電視,連收音機都沒有,在那樣的文化環境下,看“閑書”便成為最大樂趣;看第一本書《封神演義》是為同學拉了半天磨才換來的半天讀書權。他還在文中分享了因為癡迷讀書把羊餓得狂叫,頭發被火燒焦而渾然不知,兄弟之間爭書看等細節,以及《青春之歌》《破曉記》《三家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書籍帶給他的影響。
似乎每個成名作家或文學愛好者都有相似的“書蟲”童年。天津市作協主席、作家尹學蕓同樣經歷過兒時的書海漂流。
“我們小時候能看到的書非常有限,當時也不知文學為何物,反正就是對文字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癡迷,只要看到書就想著趕緊把它讀了。”尹學蕓說,“那時候讀了很多故事,但是真正能讀懂、能記住的卻是有限的,不過是多一些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的談資罷了。至于海量閱讀對自己在創作和人生走向方面的影響,可能更多是潛移默化的。”
身經百戰的讀者,此時早已嘴角上揚,這不就是翻版黃蓉么?不光可以保著自己的男人不死,還能去外邊打裝備、教武功提升自己男人的等級。故事如果按照流程發展下去,那么又是一個古靈精怪的少女,幫助自己家的傻男人走江湖的故事了。只是,并非所有人都是黃蓉,能夠不嫌棄郭靖傻,像我們的丁珰就嫌棄死了好嘛。
尹學蕓出生在天津薊縣(現為薊州區)一個偏遠村莊,似乎與文學隔著不小的距離,但是小村與小城的經歷恰恰成了她在文學上獨有的、標簽式的寶貴財富。
一般人關于童年的記憶往往是碎片化的,很難連貫到一起。尹學蕓說:“如果沒人問起,有些記憶甚至很難被激活。”因為采訪,尹學蕓又一次回到記憶深處,重新審視童年時期能和文學搭上邊兒的印跡。愛唱戲、會看話本、會喊夯號的爺爺;愛聽收音機、重教育、常把“只要想讀書,讀到哪,我就供到哪”掛嘴邊的父親;還有常帶書回家的哥哥姐姐,這是尹學蕓能夠想到的為數不多的“家學淵源”。
尹學蕓喜歡故事,對爺爺的話本和父親的收音機總是興趣濃厚,但是更吸引她的還是哥哥姐姐從外面帶回來的書。有一次姐姐帶回來一本說是“少兒不宜”的書,藏起來不給她看,她就跟姐姐斗智斗勇,翻箱倒柜,最后在一只舊棉鞋里翻出了《青春之歌》。書本的臭蓋不住故事的香,尹學蕓偷偷摸摸讀得津津有味。哥哥從城里帶回來一本名叫《沸騰的群山》的書,因為天明就要帶走,姐姐前半夜看,她后半夜看,把厚厚的一部書囫圇吞棗地看完,她說:“也不知道能記住啥,只要見到文字,就想看進眼睛里。”就這樣,一本接著一本讀,尹學蕓的童年時光被文字和故事充溢,讓她顯得不同。
與(3)阻(3)注(2)縷(3)樹(6)鼓(2)暑(1)渚(1)俎(1)苦(4)醑(3)舉(3)主(3)故(3)具(1)許(4)吐(1)睹(1)賦(2)股(1)露(3)度(3)素(2)絮(1)誤(3)舞(1)譜(1)鑄(1)羽(2)遽(1)據(1)渡(2)趣(3)付(1)富(2)霧(1)駐(1)暮(3)訴(1)戶(1)悟(1)
歸根結底來看,能夠保證房地產開發企業繼續在行業中生存下去的仍是顧客,因此唯有拿出令顧客滿意的開發項目,才能夠確保自己的房產品可以創造出經濟價值。基于此,顧客層面的指標設計將會對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帶來直接性影響,同時也可以直接反映出房產品的市場占有率。房地產開發企業需要對現階段的市場情況進行摸底,其中包括房產品的產量、房地產面積、客戶購買率、客戶增長率等等。同時還需要綜合分析顧客對所購買房產的滿意度,檢驗自有房產品的價格比、交房準確率、交通情況、設施完善度、退房率、投訴率、房屋抗震等級、消防設施密度以及服務及時率等,針對這些指標來與實際情況展開對比,找出薄弱之處,及時加以改進。
中國的錢幣歷史悠久,經過春秋戰國貝、刀、布、圜流通,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錢幣的形式統一為方孔圓形,而且對錢文有了統一的規定,這樣的錢幣在中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的清末民國初年。秦以后的中國貨幣通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幣材多用銅、鐵等賤金屬;錢幣圖飾不用人物或動物圖案而用文字;技術上采用范鑄或翻砂澆鑄制成;形式為圓形方孔;錢幣上的文字字體變化多,有楷、行、草等不同書體,因字體的不同,而形成對錢;銘文多記幣值、年號及地點等。
對文字著迷的人通常也會對周遭的事物充滿好奇。很難想象一個花季少女會對農村生產隊的農業勞動滿懷憧憬。而剛剛高中畢業的尹學蕓撒了歡兒地沖向了農村生產隊。她說:“玉米熟了,掰下來要用筐背上車,一位比我大三歲的女孩累得哇哇大哭,我也累得不行,但是咬牙堅持了下來。”這樣的經歷帶給尹學蕓的不只是生活經驗,更重要的是,它鍛造了尹學蕓面對困難和低谷絕不輕言放棄的毅力。
尹學蕓的創作大概從小學就開始了。她每天要給小幾歲的弟弟講故事,哄他睡覺,她把聽來的、讀來的故事雜糅在一起講得繪聲繪色,故事不夠了,她就天南海北地編,書里的張三,道聽途說的李四,腦子里突然蹦出來的王五,組合在一起就有了新的故事。這樣的故事一次次把弟弟帶進了夢鄉,也讓尹學蕓從編故事中獲得了一種令人著迷的成就感。學校開始寫作文之后,老師布置一篇作業,她經常收不住能寫上三篇,而且寫著寫著就“跑偏了”,編起了故事。
工作后的尹學蕓曾輾轉薊縣多個部門,還曾下鄉掛過職,最終留在了縣文化館。她用幾十年的時間,從不同角度,用腳步丈量、用文字“解剖”一座城和一座村莊,在一個小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看著形形色色的人,聽著各種各樣的事。她的筆沿著她的足跡,刻下有血有肉的小說主人公和鮮活的故事。盡管經歷了很多年的默默耕耘,但她一旦破繭起舞,展現出的就是夏花般的絢爛。
2014年,她的作品《士別十年》等逐漸在文壇大放異彩,繼而迎來了佳作井噴期。2018年憑借中篇小說《李海叔叔》獲得魯迅文學獎之后,她的新作《青霉素》等仍在不斷為文壇帶來驚喜。有人說她的成功讓基層創作者看到了光。她說:“只有讓作品發光才能反過來把自己照亮。”
文學評論界注意到尹學蕓的小說中常出現“罕村”和“塤城”,這兩個地名幾乎構建起一個完全的、自足的尹學蕓文學世界。她的小說跨越鄉村與城市,涉及底層疾苦、體制生態與知識分子紛爭,是典型的“社會小說”。在看似不算宏大的篇幅中,于日常中見真知,刻畫了生存環境中的世道人心。尹學蕓寫的都是她熟悉的人和事,她在塑造人物,人物也在陪伴她前行。
“寫完一部作品很長一段時間,筆下的人物在感覺中揮之不去。他們就像生活中的某個人,讓你惦記,讓你心心念念。會在散步時如影相隨,有與他對話的欲望。他們也在跟著時代一起成長。”尹學蕓體悟道。她已經習慣了與筆下的人物共處,甚至在心情不好的時候,還會從他們那里尋求心理慰藉。近幾年,尹學蕓時常會翻看過往的一些沒有寫完的殘篇,有些氣韻尚存,人物和故事能夠重新激活;有些人物在電腦里“躺”了許久,拿出來已經隨著時代變了模樣。她深有感觸地說:“寫作是一件辛苦的差事,同時又有它令人著迷的地方。”尹學蕓留心著“罕村”和“塤城”以及外面的世界,持續創作出更多的發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