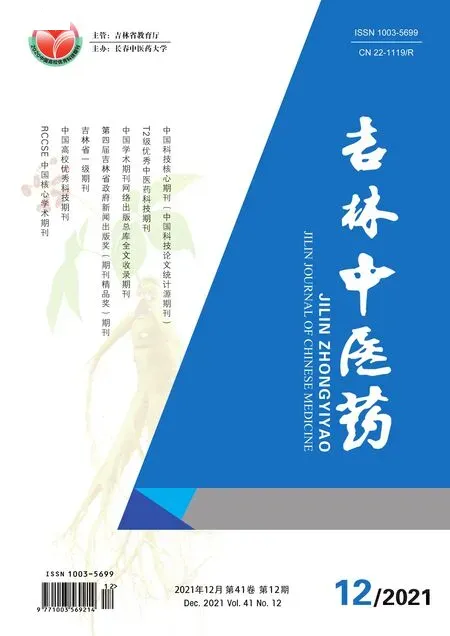王行寬從肝論治心脹經驗
范建民,姚福勝,田 晶,張 穩*
(1.湖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長沙 410007;2.湖南中醫藥大學,長沙 410208)
全國名中醫王行寬教授是湖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終身教授、主任醫師,是全國第二、三、四、五、六批名老中醫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教師,是湖南省名中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中醫學中的心脹與現代醫學的擴張型心肌病相對應,屬于心血管系統疑難病之一,其致死率高,可導致患者在短期內生存質量迅速下降。西醫對擴張型心肌病以對癥治療為主[1-2],中醫治療心脹歷史悠久,經驗獨到[3-5]。王行寬從事中醫藥臨床工作多年,擅長各類型疑難雜病的治療,對心脹的論治有其獨到的見解。本文論述王行寬從“痰、瘀、郁”病機立論,運用“雜病治肝,肝心同治”思想論治心脹的經驗。
1 病因病機
中醫學中的“心脹”是古人“以形正名”得出病名的代表[6]。王行寬認為,心脹發病與六淫、飲食、情志、勞逸、稟賦等病因相關。基本病機為邪毒上逆犯心,致心之氣營耗傷,心絡、心肌瘀阻,痰、瘀、郁駁雜而致心體脹大,最終引起心之元氣虛衰。各種發病因素犯逆于心,致使心之氣營虧損,心屬火,脾屬土,火生土,心之氣營受損,必傳之脾,致使心脾同損,正如《醫碥·五臟生克說》云:“脾之所以能運水谷,氣也,氣虛則凝滯不行,得心火以溫之,乃健運不息”[7]。因此本病初起多表現為脾氣不運、痰濕內生,久則脾陽虧耗、運化無權。隨著病進,心之氣營進一步損耗,心主血,肝藏血,心的行血功能有賴于肝之氣機條暢,或因心陽不足,心陽失于溫煦,心之鼓動乏力,可致心絡瘀阻,或使全身血脈瘀滯,可發為胸痹心痛,或心陽不能溫煦脾陽,脾失健運,痰濕內生,可致痰瘀互結。疾病后期,心之氣血陰陽俱虛,久病使肝氣郁結,肝木不疏,心血不運,血脈瘀滯,脾腎陽虛,痰飲內生,痰瘀郁相互兼夾為患,嚴重者心陽虛脫,陰陽離決危及生命。
心脹病性屬本虛標實。本虛為心陽、氣營耗傷,心失所養;標實為痰濕、血瘀、氣郁等相兼致病,而“痰、瘀、郁”參與了心脹的整個發生發展過程。正如前文所述,心脾同病致使痰飲水濕內生,心肝不調使血運瘀滯,而“脾胃為氣機升降之樞紐”,肝脾不調也可導致氣機變化失常,均可導致心體脹大,發為心脹。心脹發病病位主要在心,但涉及肝、脾,“心-肝-脾”三臟失調是導致心脹病情變化的關鍵,而“肝”作為聯系心、脾的樞紐,其地位顯而易見,見圖1。

圖1 心脹“痰、瘀、郁”“心-肝-脾”理論關系
王行寬認為,肝之主疏泄,多包括舒暢、舒展、調達、宣散、疏通等綜合功能,不僅僅局限于氣機條暢,還涉及血液運行、物質及水液代謝、精神活動等方面。正如《明醫雜著》所言“肝氣通則心氣和,肝氣滯則心氣乏”[8],肝木得疏,氣機得順,則心血得運,脾濕得化,因此王行寬主張“雜病治肝、肝心同治”的觀點,治療心脹時多用疏肝,調肝之法治之。
2 分期論治
關于脹病的論治,《內經》中有“無問虛實,工在瀉疾”“審其脈,當瀉則瀉,當補則補”等說法,主要提及的是心脹的針灸療法。但“審其脈”又指出疾病變化多端,不能拘泥于形式,要根據疾病病位以及證候的虛實論治[9]。在心脹辨證中,王行寬結合臟腑辨證,認為“痰、瘀、郁”的不同可以反映疾病不同階段,并根據“痰、瘀、郁”病機與病情發展過程的先后及關系,將心脹分為三期。治療上,王行寬主張以“標本同治”為主要治則,治本以“益氣養營”為主,治標以“疏肝理氣,豁痰化瘀”為主。
初期,患者多有胸悶,心悸,輕微氣促,困倦乏力,納差口渴,大便稀溏,兼舌淡,苔白膩或黃,脈濡等表現。此期主要為邪毒犯心,脾不健運,痰濕內生。各種因素犯逆于心,致使心陽、氣營輕微受損。根據“五行生克”理論,心屬火,脾屬土,火生土,心陽虛,則脾不燥、土不運,脾生痰濕。此期病人多癥狀輕微,主要以邪氣犯心癥狀,兼夾心悸,輕微氣促等心陽、氣營耗傷癥狀,同時伴有納差,乏力等脾虛痰濕表現。辨證為外邪犯心,痰濕內蘊,治法為疏解外邪,化痰祛濕,選方多以柴芩溫膽湯為主方,組成藥物多有:柴胡10 g,黃芩10 g,法半夏10 g,竹茹15 g,枳實10 g,陳皮10 g,茯苓10 g,生姜3 片,甘草5 g。柴芩溫膽湯中柴胡疏解半表半里之邪,又能疏肝解郁,兼之升舉脾胃陽氣;黃芩清熱解毒燥濕,又兼解表之力,主降。兩藥同用,一升一降,一疏一解,相輔相成。該方又能疏調肝膽氣機,理肝之陰陽,體現“肝心同調”之意。若表證明顯,可合用銀翹散加強清熱解毒之力;若熱勝陰傷,可加用沙參、麥冬、玉竹、生地黃等養陰清熱;若胸悶且痛,合用瓜蔞、薤白、丹參、桃仁等加強豁痰化瘀;咳吐黏痰可合用浙貝母、桔梗等加強清肺化痰。
王行寬認為,心脹初起病情隱匿,容易失治誤治,又因外邪易損傷后天脾胃,易發生傳變。此時應根據表證征象或痰濕邪毒的嚴重程度不同,分別予以加強解表或加強化痰祛濕解毒之力。而臨床中,患者因發現不及時或失治誤治或反復受邪,往往病情加重,隨著病進,進一步耗傷心陽,致使心陽虧損,出現心之鼓動乏力,血脈瘀滯等表現,轉為中期。
中期,患者多有胸悶痛,心悸氣短加重,夜間為甚,甚則喘促不能平臥,肢冷汗出,面舌晦暗,口唇、爪甲紫紺,或兼下肢浮腫,大便稀溏,舌淡或淡暗,苔白膩,舌邊或有瘀點,舌下系帶瘀滯,脈細澀等表現。此期主要為心陽虛耗,痰瘀內阻。此期已病進,邪氣久耗,心陽、氣營進一步虛損,推動血脈之力不足,脈絡瘀滯,或肝木不疏,氣滯血瘀。因此,心陽虧耗,則氣促乏力,端坐呼吸;推動乏力,血脈瘀阻,則見唇甲紫紺;不通則痛,可見胸痹心痛,夜間為甚。辨證為心陽虧虛,痰瘀阻絡,治法為溫陽通脈,豁痰祛瘀。選方多為桂甘龍牡湯合血府逐瘀湯加減;組成藥物多有:柴胡10 g,桂枝6 g,川芎10 g,赤芍10 g,當歸10 g,桃仁10 g,紅花6 g,牛膝10 g,枳殼10 g,炙甘草5 g,龍骨15 g,牡蠣20 g。若痰濕內蘊明顯,胸悶咳痰較重,可合用瓜蔞、法半夏、竹茹、陳皮等藥豁痰寬胸;兼見水腫,喘息不能平臥可合用五苓散,加用炒葶藶子、蜜麻黃利水消腫,宣肺平喘;若寒象明顯,加用附片、肉桂、山茱萸等溫陽通脈。
心脹中期病情已極重,多數患者此期確診擴張型心肌病,或伴有心臟結構改變,病情多不可逆,隨著痰瘀久積,心陽耗傷加重,可致陰陽兩虛,甚至由于久病勞神,四處求醫,患者氣郁難解,大多數伴有精神情志改變。轉為后期,臨床也以該期患者最多見。
后期,患者多有心悸喘促,不能平臥,胸悶痛極重,頭暈,唇色紫紺,納差,惡心煩嘔,口干欲飲,夜寐極差,或徹夜不眠,膽戰心驚,四肢厥冷,時或二便失調,兼下肢水腫,舌淡胖,舌邊齒痕或夾瘀點,苔薄白或黃,脈細欲絕等表現。主要為氣陰兩虛,肝木不疏,痰瘀互結。心主藏神,肝主疏泄,久病勞神傷氣,情志不遂,氣郁難解,兼脾陽虛衰,痰瘀互結,病情危重。心陽極虛可見氣促難平臥,虛汗不止,心煩不安;肝木不疏,可見動則易驚,神思恍惚,夜寐夢擾;痰瘀互結可致胸悶痛,心悸,唇色紫紺;心腎陽虛,則見水腫,四肢厥冷。辨證屬氣陰兩虛,肝木不疏,痰瘀夾雜。治法為益氣陰,疏肝木,豁痰瘀,寧心神。選方多用自擬心痛靈III號方合生脈散加減化裁,組成藥物多有:白參10 g,柴胡10 g,郁金 10 g,麥冬15 g,五味子5 g,川黃連4 g,瓜蔞皮10 g,法半夏10 g,當歸10 g,白芍10 g,柏子仁10 g,茯神 10 g,丹參10 g。心痛靈III 號主要為小柴胡湯去人參、甘草、大棗等補益溫燥之品,取其疏肝理氣之效;合小陷胸湯,取理氣寬胸,化痰散結之功;生脈散補益心之氣陰;柴胡配白芍、當歸,調肝體而養肝之用,梳理肝之氣血;柏子仁、茯神功能養心安神,丹參活血化瘀。全方共奏益氣養營、疏肝解郁、豁痰化瘀、寧心安神之功。若寒象明顯加用桂枝、黃芪等藥加強益氣溫陽之效,或合用春澤湯取“通陽不在于溫而在利小便”之意;痰濕較甚可加枳實,陳皮,竹茹,茯苓理氣化痰;寐差,精神不振可加茯神、酸棗仁、制遠志等安神之品;若水腫明顯,可合用五皮飲淡滲利濕;若喘不息,可合用炒葶藶子、蜜麻黃、杏仁等宣肺平喘。
3 病案舉例
易某,男,34 歲,2017 年11 月6 日初診,主訴:心悸氣喘4 年,加重伴雙下肢水腫3 月余。刻見:心悸氣促,難平臥,時胸悶痛,全身乏力,勞累尤甚,唇色紫紺,下肢腫,喜冷汗出,惡心煩嘔,口干黏膩,納差,夜寐夢擾,小便少,大便稀溏,舌淡胖,舌邊齒痕,苔薄白,脈細弦。4 年前于當地醫院完善冠脈造影示:1.左冠優勢型;2.左前降支中段心肌橋,另見全心影擴大。造影診斷:冠脈心肌橋,全心增大。心臟彩超示:1.全心擴大,左室順應性減退。2.左室射血分數減低(26%)。西醫診斷:擴張型心肌病。中醫診斷:心脹,證屬氣營兩虧,肝木不疏,痰瘀互結;治則:益氣營,疏肝木,豁痰瘀,寧心神。藥用心痛靈III 號方合生脈散加減:白參10 g,黃芪20 g,當歸10 g,白芍10 g,麥冬15 g,五味子5 g,柴胡10 g,川黃連5 g,瓜蔞皮10 g,法半夏10 g,丹參15 g,枳實10 g,茯神15 g,澤瀉15 g,三七3 g,柏子仁10 g,炙遠志6 g,炙甘草5 g,共14 劑,每日1 劑,水煎早晚分服。
2017 年12 月20 日二診:藥后相安,心悸氣促、乏力顯減,胸悶痛偶發,雙下肢水腫較前消褪,仍夜寐夢擾,易汗出,口干喜飲,二便調,舌淡胖,舌邊齒痕,苔薄白,脈細弦。原方湊效,再擬益氣養營,疏肝理氣,豁痰化瘀,佐安神定悸,上方加桂枝8 g,酸棗仁10 g,30 劑,煎服同前。
2018 年4 月25 日三診:藥后生活耐量較前明顯增加,期間院外自行取原方服用,堅持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刻見:胸悶痛、心悸氣促不著,寐可,雙下肢不腫,微汗出。復查彩超:1.全心擴大,左室順應性減退;2.左室射血分數減低(37%)。患者久病,氣營虧虛嚴重,再加熟地黃10 g,養陰扶正。
患者隨訪至2019 年10 月,病情基本穩定,日常活動可,胸悶痛、氣促、心悸等癥狀不明顯,夜寐轉可,汗出可,精神情志較前明顯改善,并可進行輕微體力勞動。
按:患者青年男性,久病擴張型心肌病,病機為陽氣暗耗,氣營虧虛,病程日久,肝木不疏,痰、瘀、郁相互搏結,阻滯心絡為患,為心脹中后期。依據王行寬“雜病治肝,心肝同治”思想,患者屬心脹病,初診病程4 年,由于久病,患者情志抑郁,肝木不疏,氣機失調;又因疾病耗氣傷陽,推動乏力,血瘀阻滯心絡,則見胸悶痛、氣促,動則加劇;心陽虧虛,心失溫煦,則心悸怔忡,寐差;心陽虧耗,脾失健運,痰濕內生,則納差;陽虛不能斂汗,可見冷汗出;心藏神,肝藏魂,心陽失煦,肝木不疏,則寐差,夢多。其治療全程按“益氣營,疏肝木,豁痰瘀,通心脈,寧心神”的治則。選方為心痛靈III 號方合生脈散加芍藥、當歸等養血調肝之品,以及合用遠志、茯神、柏子仁等養心安神之品;加用黃連,以“小陷胸湯”之意加強豁痰寬胸之效,同時加用三七,加強活血化瘀之功;又加澤瀉,組成“春澤湯”以“利小便通心陽”。二診時,患者藥后相安,但仍寐差,汗出,口干,原方中加用桂枝,功能溫陽調營,也能組方“枳實薤白桂枝湯”,加強祛痰散結之力;酸棗仁安神斂陰,止汗安神。三診患者諸癥悉除,但王行寬遵循“未發以扶正氣為主,既發以攻邪氣為急”的原則,繼續用原方加熟地黃補陰扶正,并以益氣養陰、利水溫陽為后續調護。
4 討論
王行寬認為,心脹發病多為邪毒上逆犯心,致心之氣營耗傷,心絡、心脈瘀阻,痰、瘀、郁駁雜而致心體脹大,最終引起心之元氣虛衰。辨證上,王行寬結合痰瘀郁病機不同,將心脹分數三期,活用小柴胡湯、柴胡陷胸湯、柴芩溫膽湯、瓜蔞薤白半夏湯等方,并創制心痛靈III 號方合用生脈散加減治之,療效顯著。在心脹論治中,王行寬重視肝的功能,全程重視疏肝補肝,體現“肝心同治”的思想。
王行寬結合多年臨床經驗及古代文獻研究,總結出“多臟調變,雜病治肝”的學術思想,且習用“隔臟而治”的方法[10]。辨證上常以五臟為基礎,重視“肝”的作用。在心病論治中,王行寬又特別指出“肝心同病,心痛治肝,心肝同治”的思想。從五行理論中講,肝屬木,心屬火,木生火,肝失疏瀉,心則首先受累。王行寬推崇《明醫雜著》中“凡心臟得病,必先調其肝腎二臟。腎者心之魂,肝氣通則心氣和,肝氣滯則心氣乏,此心病先求于肝,清其源也”之理[11],基于“損其心者,調其營衛”“肝主疏泄,條暢氣機”“心主血,肝藏血”等理論,提出“肝心共主血脈”的觀點[12],認為肝的功能失常,往往可導致心脈運行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