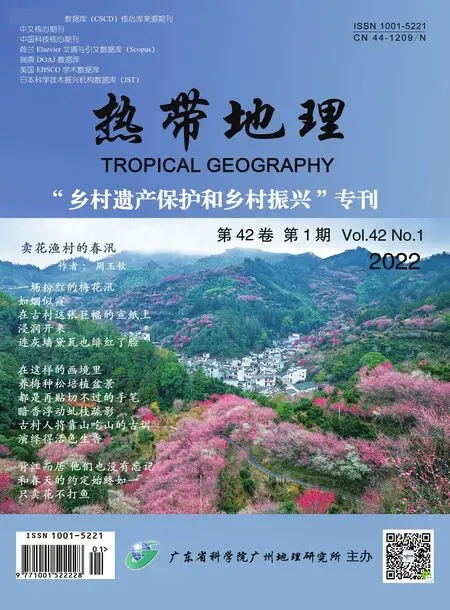多元權力主體實踐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間再生產
——以貴州肇興侗寨為例
董寶玲,白 凱,陳永紅
(1.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西安 710119;2.貴州師范大學國際旅游文化學院,貴陽 550025)
民族村寨,有別于大眾旅游目的地,或因神秘奇異、原真古樸、剽悍粗獷的民族風情而吸引游客,或因云山霧繞、恬淡愜意、逃世隱逸的詩性畫卷而賦魅鄉村。在民族村寨,具有鄉村性與民族性的自然與人文景觀重疊交錯,似乎成為人們對詩意棲居和田園生活的向往之地,也近乎成為旅游者踏尋鄉村、發掘鄉趣、尋覓鄉愁的理想場所。但不可忽視的是,在旅游發展的影響下,資本涌入和治理結構改變,產生了多元主體介入旅游地、勞動力流入或流出、土地重置利用、民族村寨景觀變化加劇等情況,使旅游化的村寨呈現地方全球化(晏雄,2019)、鄉村紳士化(何深靜等,2012)、旅游商業化(吳驍驍 等,2015)、民族現代化(許洪位,2018)等特征。空間社會關系也經歷了旅游化再生產,呈現疏離與親和、沖突與協商、嵌入與讓渡等特點。空間再生產過程中外顯的矛盾與沖突,內隱的協商與和解在旅游現象形成的社會事實中不斷涌現、不斷重置、又不斷被消解,成為一個交錯并置、多重雜糅的社會現象(郭文等,2012),成為后鄉村時代需要識別、抽取、引導、修復的社會問題。
在貴州肇興侗寨,物質空間是容納多元權力主體、村寨景觀符號的場所。社會空間是承載退讓與妥協、公信與威權、讓渡與周全等社會關系的容器。意義空間則成為裝載文化慣習、價值觀念、民族情感的環境。空間的再生產不僅是對物質空間與社會空間的再生產,也是對意義空間的再生產(洪世鍵等,2016)。在再生產過程中,旅游化的民族村寨按照“物質-關系-情感”的發展邏輯,經歷著“經濟社會轉型-旅游地空間再生產-空間變遷和重構”的螺旋式演進過程(黃劍鋒等,2015)。在該進程中,空間的社會功能與經濟功能不斷被解構,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和象征意義不斷被重構(白凱等,2014),在發展中呈現出空間社會化、鄉村城鎮化、旅游再地化(孫九霞,2020a)等特性。
隨著權力主體結構的變化,不同主體對空間的解讀往往因利益和立場的不同而存在差異,一些表面上看似基于經濟利益的空間實踐,在本質上是不同主體對空間新秩序的觀念表達和權力斗爭。這些權力斗爭作用于不同的空間,在多元主體的分階段約束與分群體調和下,帶來肇興侗寨空間的表征、表征的空間與空間的實踐的不斷變化,產生空間溢出效應與空間收斂效應。為厘清地方全球化背景下,旅游化發展給民族村寨帶來的多重空間效應與影響,本文采用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結合的方法,以肇興侗寨為例,從空間再生產研究視角出發,探討以下問題:一是蘊含在物質空間中的多元主體的結構演變特征;二是包含在社會空間中的多元主體的社會關系與處事原則;三是隱含在意義空間中的原住民的文化慣習與記憶情感。以期拓展空間再生產研究的要素與內涵,為民族村寨旅游化深入研究提供實證案例,為村寨旅游地發展前景研究擴充人本素材。
1 概念與研究回顧
1.1 空間生產與再生產
空間是物理的場所,是先于人的認識而存在的物質實體,也是權力的容器,是社會中各種力量關系相互作用的地方(Foucault,1977),還是情感的載體,是人類社會物質、情感以及文化藝術要素的投射(海德格爾,2006)。Lefebvre(1991)批判把空間僅僅當作場所或容器的觀點,認為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在此基礎上,Lefebvre(1991)從空間生產的角度提出了空間三元論,認為空間的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與表征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是闡釋空間運作過程、包含要素與形成機制的解釋框架。其中,空間的表征對應構想的空間(conceived space),是由管理者、規劃師、科學家等建構起來的符碼化的空間,是權力主體自上而下的政策、規訓與管制,以空間使用秩序、規劃文本、藍圖等形式呈現;表征的空間對應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是居民或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和體驗的空間,也是居民自下而上對規訓、管制等的適應、讓渡、協商和抵抗。空間的實踐對應感知的空間(perceived space),體現社會中不同主體與空間的互動,承載著不同主體對空間的回憶、情感、想象與依戀。
空間的再生產發端于學者們運用空間生產理論分析社會問題與實踐時對社會現象、社會制度與社會關系的深層思考。在工業化、全球化與現代化背景下,在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對于空間再生產的研究應不再局限于資本的重組,權力的再構與關系的重塑等社會現實問題,而是應拓展關注多元主體的價值觀念、集體記憶、文化自覺、制度規約、地方認同(何明等,2017;蔡曉梅等,2018)等社會感知與情感問題。
1.2 旅游空間再生產
為厘清旅游情境下不同區域旅游空間的再生產方式與呈現形式,學者們從不同空間視角闡述了旅游發展對社會經濟文化結構的影響。部分研究認為,旅游地空間生產與再生產會驅動空間紳士化、加速旅游地商業化(張娟等,2017)、加速地方性的消弭(孫九霞等,2017),給旅游地制造群體分層與社會矛盾(劉濤等,2010),造成人情關系的淡漠與疏離(金光億,2018)。也有研究認為,旅游空間的再生產有利于增強資本的流動性,有助于緩解現代性背景下城市生活的焦慮,有利于物質文化的保存與修復,在一定程度上能滿足旅游者尋覓“鄉愁”的需求(孫九霞等,2021),增強當地人對自身文化與身份的審視、對風俗習慣的認知(孫九霞,2020a),有利于鄉村精神文化的調適與再造(孫九霞等,2020b)。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旅游產業逐漸從城市拓展到鄉村,成為地方政府高度重視,民眾廣泛參與,外來群體不斷涌入、資本持續作用的地方產業類型和地域發展選擇。在旅游業向鄉村不斷拓殖與滲入的過程中,鄉村物理空間在資本、利益團體的作用下或不斷更新或得以保存,在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打造之路上不斷探索;鄉村的社會空間在內群體與外群體的相互作用下出現維系、漸變和裂變等問題,成為評判旅游地鄉風文明與否、治理有效與否的主要因素;鄉村的意義空間則在旅游地主客互動中發生疏離與回歸,讓旅游空間再生產相較于囊括資本、生產、權力、階層、生活和社會等維度的旅游空間生產而言(郭文等,2012),要素更加復雜,視角更為抽象,涵蓋了旅游引導下多元主體間的情感表達、文化認同、規約調適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典型民族村寨交互并存,不斷演替,呈現出表征的地域性與表現的日常性。因此,從“物質-關系-情感”的邏輯視角審視旅游空間再生產過程,聚焦物理、社會與意義的空間,可在一定程度上豐富鄉村旅游地空間再生產研究的人文意蘊,拓展地方特征與民族個性在旅游空間的解釋維度。
1.3 民族村寨旅游空間再生產
民族村寨區別于一般的鄉村旅游地與社區,主要以單一族群的聚族而居或多個民族的交融雜居為主,常因保留了完整的村落景觀、絢麗多彩的民族文化、神秘奇異的民族習俗等吸引大量游客,既滿足了游客求新、獵奇、逐異的消費需求,也帶動了村寨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轉型。
有學者從文化再生產視角出發,明確了地理空間是旅游情境下主客互動的場域,認為民族文化空間是經由地理、文化與旅游要素相互疊合生成的(桂榕等,2013),這延展了地方文化對旅游空間的詮釋維度;也有學者從儀式空間的符號性和社會性視角出發,刻畫了儀式空間再生產過程中社會秩序與社會關系的變遷(孫九霞等,2020c),深化了旅游化的民族村寨社會結構與網絡關系變化的機理分析;還有學者從神圣空間的地方性視角出發(郭文等,2018),探尋旅游化過程中神圣空間的非正義性與村民身份認同的非延續性,揭示了旅游資本化導致的村寨社會分化和村民權益的低權能化(郭文,2019),拓展了對旅游空間再生產研究中村民權益與權能變化的解讀。既有對民族村寨文化空間、儀式空間與神圣空間的解析,多以“資本-權力-關系-利益”的在地化呈現為切入點,從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價值信仰、處事態度以及群體社會關系著手透視村寨商業化、資本化的演進歷程,分析民族村寨社會關系、村民權益、村寨空間變化的動因。本研究在延續該思路的基礎上,除考慮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關系表現外,還將視角更多地聚焦在民族村寨意義空間的旅游化建構上,將多元主體間的關系網絡、情感表達、規約調適等納入空間再生產考量范圍,探究肇興侗寨生產關系與生活方式變化、群體關系與行為準則變化的外顯表征與內隱動因。
2 案例地概況與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況
肇興侗寨,距離貴州省黎平縣城70 km 左右,轄肇興上寨村、肇興中寨村和肇興村3 個行政村,截止2019年8月,全寨共有1 100余戶6 000余人①數據來源:黎平縣旅游發展有限責任公司統計數據。,均為侗族,是全國最大的侗族自然村寨,有“千戶侗寨”之稱(圖1)。肇興侗寨景區內有5座鼓樓和風雨橋,受漢文化影響,5 座鼓樓按當時儒家奉行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命名,分別代表5個房族,當地人對其以“團”相稱,即仁團、義團、禮團、智團、信團。過去5 個團邊界明顯,現在界限已分不清,融為一體,成為肇興大寨。

圖1 貴州省黎平縣肇興侗寨區位Fig.1 Location of the Zhaoxing Dong Village,Liping County,Guizhou Province
肇興“頭銜”眾多。其鼓樓群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紀錄、是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國家4A 級旅游景區、中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2018年春晚貴州分會場。肇興侗寨旅游發展始于上世紀80 年代的發現期,經歷90年代的急速增長期和歷經21世紀00年代的提質轉型期。截止目前,肇興景區經歷了貴州世紀風華公司的入駐、村民委員會的集體參與、黎平旅游發展有限責任公司的接管兼并、肇興撤鄉并鎮、肇興管委會的成立、肇興鎮政府的搬遷。在肇興旅游化發展40多年中,其空間秩序、治理結構與社會群體等隨權力主體的變更發生歷時性變化。
2.2 研究方法
以貴州省黎平縣肇興鎮肇興侗寨為例,采用田野調查法和深度訪談法,于2019年8月進入肇興侗寨景區,訪談24人(表1),收集整理訪談資料6.35萬字。在調研中通過交朋友的方式取得訪談對象的信任,通過加微信與訪談對象保持長期聯系。同時還注重對行政機構、管委會和企業的展板、宣傳資料進行收集和整理。所有資料都按受訪者“類型+編號”的形式引用。如企業工作人員1,A1;歌舞隊成員2,B2;周邊居民3,C3;經營戶4,D4;本地居民5,E5,標注。

表1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3 多元權力主體實踐下旅游空間再生產過程
空間不僅是經驗形成的事實,也是人們對具體事物的感性認識(劉少杰,2018)。空間亦是由社會建構的,經濟社會的發展轉型催生了旅游綜合功能的發揮。在此過程中,旅游地新的生產、消費、居住、生活、游憩等空間得以再生產,推動著人地關系的演化(黃劍鋒等,2015),該演化的結果有別于空間點、線、面的同質集聚和異質分析,而表現為空間組合更加彈性化、相互形成一種復雜的耦合關系(姚華松等,2010)。映射在肇興侗寨,具體表現為,空間的再生產不僅是物理空間的重構,還是社會空間的重塑與意義空間的再構(圖2)。旅游活動發生于肇興侗寨物理的空間,經交往、實踐形成新的空間社會現象和新的空間社會關系,以規劃、約束管制、景觀符號形式隨權力主體的變化而產生物理空間的形變;以沖突、抵抗、躲避、協商、妥協、讓渡等形式再現與再構社會關系空間;以節事活動、傳統慣習、鄉約民俗、回憶與想象等意義空間的形式呈現侗族同胞的文化與精神家園。

圖2 肇興侗寨旅游地空間再生產過程Fig.2 The process of spatial reproduction of Zhaoxing Dongzhai tourism destination
3.1 物理空間的重新規劃、規制與表征
物理空間的變化可反映多元權力主體的更迭。物理空間作為容納多元權力主體的載體,每種占主導地位的權力主體會依照自身的權力、利益和立場去改寫、塑造和標識物理空間,從而達到表征其功能、價值與意志(黃劍鋒等,2015)的目的。在肇興,空間的表征作為構想的空間,受地方政府、管理機構、規劃者等的知識和意識形態所支配,在空間再生產中可從權力主體的更迭、當地居民與周邊居民群體的流動性、空間秩序的重構、管轄權能的分配、景觀符號的再塑上窺見(圖3)。

圖3 物理空間的規劃、規制與表征Fig.3 Planning,regu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hysical space
3.1.1 變遷與安適:權力主體的更迭與人口的回流 肇興侗寨旅游業的興起推動著多元主體進入原本只屬于社區居民的空間,通過制定新的規劃改寫空間,通過自身的權限和方式分割、使用、管理空間,在空間再生產中以物質呈現與人員流動的形式控制、支配和使用空間,促成人地關系的演變,背后滲透著不同群體的空間支配與選擇邏輯。通過調研獲悉,目前,景區主要有當地政府、黎平縣旅游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景區管委會、社區居民、周邊居民、外來經營戶六類主體。上世紀90年代,隨著旅游發展的不斷作用和持續發力,肇興侗寨行政主體、管理體制、管理模式不斷變遷,權力結構的變遷引發物質空間的歷時性改變,具體表現為:
2003—2008年,肇興鄉政府、肇興侗寨村民委員會與貴州世紀風華公司簽訂《肇興景區開發經營合作協議》,該公司開始進駐肇興,負責景區的旅游開發與管理運營。世紀風華公司進駐之初為肇興侗寨旅游業發展引入了資本、注入了活力。目前,景區西面廣場、亭、榭、廊、水車、觀光道、觀光稻田等旅游公共設施和田園景觀在政府和貴州世紀風華公司的協作下得以規劃設計和建成使用,初步形成旅游公共基礎空間。但2008—2013年,貴州世紀風華公司由于經營管理不善,瀕臨破產重組,因企業的不當管理引發的社會民生問題驅動地方政府出面干預肇興景區的重組與運營,而貴州世紀風華公司逐步被黔東南州政府籌建的肇興旅游發展有限公司兼并和收編。
2013年肇興旅游發展有限公司成立,該公司屬于州級國有獨資企業。因借力黔東南州政府的支持和融資渠道的廣泛加持,規劃管理范圍更大,吸納接收的當地勞動力更多,創造就業機會的民生服務性質大于營利獲益性質。“公司在建立初期,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公司也通過銀行貸款、企業合作等擴展融資渠道。在建設時,肇興景區被規劃為規榪服務區內,2013年我們做了步道、網線、展示空間、寨門、鼓樓、花橋的建設、服務區停車場硬化、涼亭的建設、園林綠化等,下一步我們會將景區向高鐵服務站延伸,以此創造更多的商業空間。公司有400 多人,吸納了負責市場運營、保安、保潔的大半當地人,這是我們作為國有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以旅游發展促進當地人就業(A1)”。“景區內的肇興國際酒店以及原來的糧倉現在是公司的國有資產,由我們負責經營管理,景區糧倉已被改建為小型商鋪,由公司統一招租(A2)”。
肇興景區管委會成立于2013年,為黎平縣正鄉級派出機構,主要負責景區內房屋建設審批管理工作、車輛進出管理、商鋪進駐管理、村容村貌整治與維護、消防安全管理等,管委會是地方政府為促進旅游可持續發展、維持旅游地秩序、維護當地人與旅游者權益而設置的景區監察管理機構,意在實現對空間的統一規范管理,避免空間沖突與地方矛盾的發生與升級。
肇興鎮政府改建于2013 年,由原來的肇興鄉改鎮演變而來,轄區范圍有22 個行政村,主要負責轄區內的民生事務與行政事務,較少干預肇興景區旅游的發展。其鎮政府原所在地現為肇興景區表演場,為擴展肇興景區發展空間及適應發展需要,鎮政府已搬遷至距高鐵線1.3 km 處。為促進當地旅游業的發展,權力主體會讓位于旅游發展而做出空間置換的讓步,可見當地發展旅游業的決心與信心,其背后透露出鎮政府希望通過旅游發展促進地方社會發展而做出的空間妥協。
當地居民因占據不同空間而從旅游發展中獲得了不均等利益,但相較外出務工面臨背井離鄉的窘境而言,當地人本著就業不離家的原則駐守家鄉。“旅游業發展起來后還是會有矛盾的。沿街沿河有房出租的人就富了。沒房出租的人家就到商鋪、酒店做服務員。我們這里多數人都贊成發展旅游,最起碼很多人不用外出打工了(E4)”。“肇興大部分人在景區打工,因為家里有地要種,有老人孩子要照顧,只要生活要求不高,找口飯吃沒問題的(C1)”。“現在可以在這里當環衛工或者打臨工。雖然工資少一點,但工作穩定,活也輕松(E2)”。
當面臨離鄉不能兼顧家庭以及留鄉務工可以兼顧家庭的對比選擇時,肇興成為周邊居民選擇離家不離鄉的權宜之地,在肇興打工也成為周邊居民的權宜之計。“肇興周邊來這里打工的比較多,跑外地打工照顧不了老人和小孩。住在這里,離家近,有事可以請假或調班回家(C1)”。“畢業后待業在家,打算一邊實習,一邊備考。在這里教團散客制作蠟染,拿實習工資,能時常回家(C2)”。
外來經營戶則瞄準級差租價、免稅政策、景區商機等而紛紛進駐肇興,給原來二元結構的空間增添了更多群體,加速了旅游地的商業化。“嫂子是肇興人,哥和嫂因在縣城上班,家里房子空置,就便宜租給我做生意,在這里開店不收稅(D2)”。“當街門面費用高,費用要8萬多一年,這里除了不允許占道經營外,沒有其他規定,沒有稅收,要不然我早就關門歇業了(D4)”。根據調研統計,外來商戶主要來自廣東、湖南、四川、北京及貴州凱里等地,以經營旅游紀念品、干貨鋪、特產鋪、茶葉鋪、超市、客棧、酒吧、餐館等為主,當地人多將一樓商鋪出租,二、三樓房間留用,因大多數當地人在地就業,肇興未出現大規模的空間置換,有利于村寨景觀的保存與鄉風民俗的延續。
3.1.2 規制與約束:管轄權能明晰與村寨原貌維護 為實現民族村寨旅游地的良性發展,在減少沖突、維持秩序的責任驅使下,管理機構通常會制定相應的地方性規章與規定,以重新劃定物理空間的租賃使用范圍。其他主體也在接受與適應旅游地相關規定的情況下,厘清各自的權責與權能,明晰各自的權利與權益。在肇興,景區經營權、所有權和管理權“三權分置”,權責明晰。景區經營權屬旅游發展有限公司,主要負責景區的經營管理和市場開拓,除有肇興國際酒店和糧倉的管理租賃權外,無權干涉景區內居民房屋和土地的使用和租售。為統一侗寨的建筑風格,肇興國際酒店的建設嚴格遵循侗寨房屋的樣式設計。私人房屋與集體空間的所有權屬于當地居民和各團鼓樓,當地居民除需遵守房屋層高和外形的規定外,可以自行處置和變更房屋的功能和性質。各團有各自不均等的集體商鋪、廣場、河道、林地以及鼓樓等,可用于對外租賃以獲得各團集體資金。景區管理權屬地方政府和肇興侗寨管委會,主要負責房屋改拓建審批和景區秩序的制定和維護,如商戶不準占道經營、統一商鋪牌匾、車輛出入景區限時、景區物價監督、受理游客投訴、規定賣菜時間和區域等。
在此過程中,由于地方性規章與規定的出臺早于物理空間的形變,在肇興幾乎看不到三層以上的商住樓;旅游發展公司與居民住戶的空間劃分也因征地賠償處理與當地勞動力吸納等措施前置在先而未出現大的沖突。權責與權能的明晰,有利于村落基本原貌的維護,防止村寨景觀產生旅游化裂變,使村寨物理空間在面臨全球化沖擊下基本保留了原真性印記。
3.1.3 符號與注解:標識性景觀的錯位建構與表達 Cosgrove(1998)認為景觀是集體文化和象征意義的沉淀物,是經由不同主體建構的主觀視覺空間,以符號化的景觀形式展現,承載著建構主體的價值觀念,具有意義傳遞的功能(Anderson et al.,2002)。在肇興,符碼化的旅游景觀在2018 年春晚分會場集中呈現(圖4)。

圖4 肇興侗寨符碼化的旅游景觀Fig.4 Coded tourism landscape of Zhaoxing Dong Village
在建構主體-地方政府的視角下,具有侗族元素的鼓樓舞臺架的搭建,意在突顯和傳達具有標識性特征的地域民族元素;苗族牛角頭飾型景觀的建造,意欲突顯貴州主體少數民族——苗族的典型特征;象征時代速度的復興號高鐵模型的搭建,則想表達民族地區搭上時代發展的快車,與時代共榮共進的理念。它們是建構主體基于自己對地方元素與社會發展的認識而對地域文化景觀進行的符號化提取。但當地人并不認為建構的符號化景觀能起到彰顯地域形象特征的作用。對他們而言,象征宗族文化的鼓樓,屬于公共游憩空間的風雨橋、侗族婦女發髻、侗音侗話等才是民族的符號化象征。對游客而言,這些建構的符號景觀在與原真性自然人文景觀保留較好的肇興景區相形之下,顯得既矯揉造作又格格不入。致使本應成為旅游吸引物的符號變成與當地居民民族特性不相符,與游客審美喜好不相宜的刻板符號。可見,在民族村寨旅游地景觀符號的提取與建構過程中,不可低估游客的辨識水平與評價能力,也需考慮原住民對宗族意識、民族觀念、價值取向與地方認同的共情性。
3.2 社會空間沖突的調適、調和與消解
表征的空間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間,也是居民被支配的日常生活和被管理的生活空間,居民在與多元主體的空間相互作用過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社會關系,該關系投射出居民的生活策略、文化道德體系與為人處世哲學(圖5)。

圖5 社會空間沖突的調適、調和與消解Fig.5 Adjustment,reconciliation and resolution of social space conflict
3.2.1 退讓不退出:居民的伺機而動與空間的調和使用 在肇興,弱勢群體在面臨空間管理者的管制與約束時,會運用自身的靈活性與流動性特征,采取“退讓而不退出”(斯科特,2007)的空間生存與弱者抵抗策略(孫九霞等,2014),來消解管委會的日常管制,并在此過程中通過自我約束來與空間管理者達成分時段空間利用與管理默契,既避免了各方抵觸情緒的產生,又維系了弱勢群體的生計問題,還兼顧維護了管理者的工作職責。
管委會明確規定,在肇興景區早上8點后不允許在主街上擺攤賣菜,于是賣菜的攤販伺機而動,錯開管制時間沿街售賣,或在管委會驅趕時利用挑菜擔子的靈活性與自身對當地空間的熟悉度,快速躲避與隱匿到巷道中,避免與管理者產生正面沖突。同時為了維護賣菜生計,賣菜攤販在其群體內達成空間使用約束,如規定爛菜葉子不亂丟,保持所占領地的干凈整潔等,以最大程度地減少與管理者的矛盾,也為日后錯峰使用空間謀生留有余地。
3.2.2 公信與威權:寨老協調下社會關系的鞏固與凝聚 在肇興,鼓樓這一象征族群和宗親孝悌關系的空間充當著當地人社交與人情往來的媒介。在長期形成的族群社交關系中,當地人非常看重社會交往的群體參與性與人情世故的粘連性,十分重視寨老在族群中的公信與威權,遵循寨老分派的各類事務,信任寨老的議事能力和合理使用集體資金的能力。寨老這一存在于體制外產生于族群內的人物和組織,對于維系族群內部團結、處理族群內外糾紛、鞏固群體社會關系和凝聚族群向心力等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得到當地居民的支持和認可。
鼓樓既是當地人休憩的空間,也是議事的空間,更是代表各鼓樓親緣關系的空間。“每一個鼓樓代表一個同根的家族,平時會去鼓樓下棋唱歌玩耍、有大事大家會到鼓樓商議(E1)”。
寨老是各團的組織基礎和居民地方話語權的代表,負責聯絡其他鼓樓,組織安排各類活動。“每座鼓樓都有一個寨老,寨老必須是本鼓樓的人,是大家選出來的,你信任他你就選他。寨老一般操持月也②月也,即兩座鼓樓或兩個村寨之間以集體作客,互邀歌隊唱歌,邀請侗戲班演戲等形式的相互走訪。、谷雨節、蘆笙節等活動(B3)”。“寨老主要代表鼓樓去議事,寨老也要遵從大家的意見(E7)”。寨老也是負責分配集體收益、維護族群內部團結、鞏固群體間社會關系的威權人物。“我們和智團鼓樓有共同的地,比如源泉超市就是信團和智團共有的資產,租出去的錢就是分給信團、智團兩座鼓樓,我們信團鼓樓還有好多棟沿街的集體所屬房子租出去之后,一般這些錢都是分到鼓樓,然后經過寨老商議,鼓樓就拿這些錢來與其他鼓樓組織比賽,做蘆笙,聚餐之類的,我們不用自己掏錢(B2)”。在肇興,以血緣親緣為基礎的互助合作關系,增強了以人情關系進行的社會交往,強化了社會粘連度。“紅白事是大家一起來幫忙,不計報酬(E4)”。
寨老這一在剛性管理制度之外存在的柔性管理組織,通過日常空間實踐既拉近了當地居民的社會關系又保證了當地社會網絡結構的相對穩定,在他們的親身實踐下,表征的社會空間充滿了人情味與煙火氣。
3.2.3 讓渡與周全:當地居民的待客之道與處事哲學 旅游必然帶來“我者”與“他者”的空間碰撞(周尚意,2017),激烈時會帶來沖突,緩和時能達成諒解。在少數民族旅游村寨,東道主作為本地文化的持有者(Boissevain,1996),多通過節事開展、舞臺表演的方式增強目的地吸引力和增進主客互動。游客往往抱著追求“文化差異”的動機前往“他者世界”(Qian et al.,2012)。這一方式往往給目的地帶來多種壓力,一是外來游客的大量涌入造成的空間使用壓力和日常秩序維護壓力。二是極少數游客不道德行為舉止造成的主客沖突。三是外來資本進入民族村寨帶來的不同利益相關者矛盾處理壓力。當面臨這些群體或個體問題時,肇興居民本著“來者都是客”的原則來處理空間中的關系問題。從當地居民對失態游客的態度、對失序秩序的約束、對失范經營戶的協助上能感受侗族居民的待客之道與處事哲學。
對于失態游客,當地人通常采取迅速逃離的方式避免與游客的正面沖突。“游客的素質也有好有壞,我們唱歌或者表演完收工時有些游客就會不管告示牌,跑到后臺跟我們拍照。只要說話禮貌客氣,我們都會高興地配合他們合影,但是有個別游客舉止態度輕佻,喜歡勾肩摟腰的與女演員拍照,這種情況我們一般會迅速閃開,盡量避免和游客正面沖突(B1)”。
對于失序的空間秩序,當地人以張貼巨額罰款為警示與威懾,規范游客的行為。“允許用瓢舀水喝,禁止在井邊洗手、頭、拖把、衣服,禁止把手伸入井水里,禁止小孩在井邊玩水,違者罰款500~1 000元③數據來源于肇興景區內告示。”。“鼓樓范圍禁止停放一切車輛及倒垃圾,堆雜物,違者按鼓樓規定罰款500元④數據來源于肇興景區內公告。”。“也沒有真的罰過誰的款,一般看見不遵守規定的人,當地人嘴上指責一下就完了,而且大家看到這么大金額的罰款,也基本上不會違規(E8)”。
對失范的經營戶,當地人會協助其處理復雜難題。2019年8月調研期間,信團鼓樓附近一家廣東茶葉商因用電不慎引發火災,火災導致其所租賃的房屋被全部燒毀并波及隔壁店鋪,給自己、房東以及隔壁租戶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利益牽連甚廣。在此情形下,房東基于對外來經營戶付租能力和續租時間的考量,主動擔當調解人,出面洽談受損各方的賠償及房屋修繕事宜,使得一度緊張的鄰里關系和租賃關系得到緩解,受損的各方也在這次“資本預付”(郭文,2020b)的相互讓步中獲得了延遲性空間互惠,讓旅游化的空間展現出更多人本主義色彩,對維護利益共同體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3.3 意義空間的重新詮釋、漸變與回歸
空間的實踐,是人們對世界的感知(莊良等,2019),傳統村落的精神文化根植于原始村寨,通過節慶、儀式、慣習等得以體現,與空間意義的構建緊密相連(孫九霞等,2020c)。在肇興,當地居民對節事、文化的情感注入,對文化慣習的傳承、對懷舊物質載體的感情釋放與回歸,使他們無意中參與了意義空間的再生產,讓傳統民族村寨變得更有人文意蘊、更富民族特性、更具鄉土氣息(圖6)。

圖6 意義空間的重新詮釋、漸變與回歸Fig.6 reinterpretation,gradual change and regression of meaning space
3.3.1 節事與社交:文化慣習的傳承與傳播 馬林諾夫斯基(2002)認為節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的“幸福感”及“歸屬感”,和睦愉悅的集體活動更容易形成“重群文化”(郭文等,2020a),強化共同的價值觀和信仰(錢晶晶,2012)。在肇興,民族故事與非遺侗歌的舞臺化與商業化展演雖被部分研究者所詬病,但當地人卻在參與演出的過程中獲得收入保障,在這種文化慣習中找到親和感與歸屬感,并在政府加大對非遺傳承保護的助力下,自覺而主動地將這種文化慣習傳給下一代。“旅游帶動了就業,讓很多人有事做,我在歌舞隊每個月拿固定工資,參加篝火表演還能拿加班工資,侗族大歌、蘆笙都是我們當地的寶(B4)”。“肇興的民風民俗保存得很好,比如我們平時交流都用侗語。侗歌我們從小就跟著父母學唱。如今我們是年長的教歌,年輕的唱歌,年幼的學歌(B3)”。
康納頓(2000)指出:“所有的儀式都是重復性的,而重復性必然意味著延續過去。”在儀式的重演中,必然伴隨著社會記憶的再生產,每一次的儀式重演就是一次記憶的再生產(丁華東,2019)。在旅游發展語境下,六月六、谷雨節、蘆笙比賽等節事活動經歷了資本和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現代性協商,既保留了原真性,也在被游客凝視的過程中增強了當地人的民族自信。在年復一年的節事活動參與中,當地人不斷審視自身文化的獨特性,重新定位其文化價值,使抽象的文化精神空間在時代發展中不斷演繹和創新,延續著民族文化的活力與魅力。“肇興的旅游事業必須依托民族文化讓它活起來,民族文化搞不好怎么發展旅游,怎么吸引游客(B2)”。“經常唱(侗歌)了才能傳承下去,不參加比賽就會生疏。我們幾個經常在一起唱就會配合默契,大家的關系相處得很好。有時就算沒有商家找我們演唱,我們自己也會演,唱侗歌本身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希望通過我們演唱把肇興的旅游事業發展下去(B3)”。
3.3.2 觀念的漸變:鄉約的承繼發揚與自洽 鄉約的漸變能體現當地居民日常空間實踐中的自然觀、世界觀和道德觀的漸變,具有“心-物” 自洽性(郭文 等,2020a)。在與現代力量的角逐中,鄉約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地方結構環境的變化作出調整,與社會發展達到協調和自洽。肇興侗寨日常生活實踐中遵循的鄉約,隨著民族村寨旅游發展進行現代性調適。這種調適有助于對當地人的價值觀念進行集體引導,有利于文明鄉風的培育與鄉約的延續。在肇興,鄉風鄉約的承繼發揚體現在當地居民對鼓樓、花橋維護的變化上,對信團戲臺的磋商使用上。
在旅游發展影響下,肇興侗寨的標識性景觀-鼓樓、花橋的修繕與維護從過去的投工投勞演變為現在的集資修繕。當地采用集體議事后共同決定維修資金如何使用的做法,減少了內部分歧,鄉約的約束效力得到了當地居民的自覺承繼。“以前鼓樓和花橋的維護是由各家出工出力,不要報酬。現在鼓樓的維修是本鼓樓自己出資,這些都是大家集體議事的結果,沒有人對這筆錢的使用有異議(E4)”。屬于信團的戲臺目前出租給外來經營戶,但在信團開展大型活動時,信團居民仍能隨時使用已出租的戲臺,該鄉約的調整使多方受益(圖7)。“我們的戲臺出租出去了,但是在我們開展活動的時候,商家可以隨時讓我們使用戲臺的二樓,既不耽誤我們開展活動,也能吸引大量游客圍觀,還給商家帶來許多人氣和財氣(E8)”。

圖7 被出租后可磋商使用的信團戲臺Fig.7 The stage of xintuan that can be negotiated after being rented
3.3.3 回憶與想象:人-物情感的釋放與回歸Cresswell(2014)認為,人與地方積極的情感聯系往往是通過具體景觀、敘事和對特定意義的符號感知來實現的。展示物品是連接過去與現在的介質,是對歷史的想象、重新詮釋以及轉換(羅易扉,2016),承載著人們豐富的情感(馬天等,2019)。
肇興侗寨博物館展示廳,以舊物展陳的方式建立起“人-物”的時空對話,這種以物品為載體的情感建構,激發了游客對村寨的想象,喚起了當地人對過去生活的回憶,這種將鄉村空間的歷史脈絡與鄉村生活方式置于特定場所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鄉村文化空間的歷史內涵,激活了人們的懷舊情感,讓民族旅游地更富鄉土性人文意義。
肇興侗寨信團的兩棟“老屋”,經政府的“文物化”保護,成為了當地人追憶過去、述說現在與向往未來的情感中介。“你看信團鼓樓邊上的這兩棟老房子,政府說要完全保留它當初的樣子,弄成‘文物’,所以現在這兩家一點都不能動。現在的房子大都是翻新和重修的,所以保留一兩棟老房子是應該的。特別是對我們老年人而言,希望以后可以告訴子孫,我們過去住的老房子就是這樣(E11)”。Amedeo(1993)認為,場所和空間像人本身一樣能引起情感的響應,能夠引起響應的場所包括房間、屋舍、鄰里以及城市等。布迪厄(2017)則將住宅視為傳統和文化延續的載體,視為居住者基本文化實踐技巧習得的場所。在肇興,游客與當地人經由展示廳與信團“老屋”的物質連接,建立起對過去、對鄉村的想象、回憶與追憶,承載著物質與精神感情的空間賦予肇興更多的原真、質樸等目的地魅力。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沿用空間生產理論,聚焦民族村寨的旅游化空間再生產過程、梳理民族村寨空間中“物質-關系-情感”的關聯,得出以下結論:
1)物理空間在權力主體的更迭下得以重新規劃,旅游業在民族村寨的發展,促進了當地勞動力的回流,讓肇興成為當地人就業不離家、周邊居民離家不離鄉的權宜之地。權力主體管轄權能的明晰有利于減緩商業化對村寨原真性的侵蝕。而標識性景觀的建構需契合村寨的景觀環境氛圍與侗族同胞的族群印記,才能避免成為游客與當地人心中的刻板符號。
2)對于包含復雜網絡的社會關系空間,在面臨空間管理者的管制與約束時,弱勢群體采用退讓而不退出的策略謀取生計,通過維持攤位整潔的自我約束行為與空間管理者達成分時段空間利用與管理的默契。寨老則利用自身的公信力來維系族群內部團結、處理族群內外糾紛、鞏固群體社會關系。面對失態的游客、失序的秩序、失范的經營戶,當地居民采取迅速逃離、張貼巨額罰款等方式威懾,主動擔當調解人進行調和,以最大程度地消解空間沖突,促進旅游地和諧發展。
3)對于反映侗族文化慣習與心態價值觀念的意義空間,節事活動的廣泛參與有助于增強當地人的文化記憶與自信。商業化演出帶來的穩定收入推動了當地人文化傳承的自覺性。在面對因集體收入變化帶來的空間關系變化時,當地人通過適時改變鄉約,去適應旅游業的發展,這種調適有助于文明鄉風的培育與延續。當地建立的展示廳、文物化保護的“老屋”共同建構起了鄉土與懷舊情感安置與釋放的空間。
盡管旅游發展影響下的肇興侗寨存在諸多社會問題,隱含不少社會矛盾,但多元權力主體在達成利益同享、正和博弈、和諧共生的共識下,在對當地旅游業發展趨勢與發展潛力進行評估后,會在多方斡旋、多類組織協調、多重關系考量下,做出各自的空間安排、空間妥協、關系讓步與情感調適。尤其對于處在發展期與上升期的民族村寨而言,在面臨沖突、對抗、矛盾時,多元權力主體會出于對利益的共同性與社會關系的粘連性考慮,做出符合當地旅游發展,符合自身容納限度的調適與讓步,以此適應因旅游發展帶來的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與意義空間變化。此類旅游空間再生產過程經肇興侗寨案例地實踐證明,多元權力主體間的協商與妥協對于塑造現代鄉土文化、維護原真性鄉村風貌、體現少數民族風情、發揚鄉村人文道德價值等有積極的助力。因此,自上而下的政策在民族村寨的落地,需充分考慮民族地區的特性,各民族迥異的秉性,民族地區自組織的有效性。多元權力主體需調和利用這些特點,方能產生旅游發展的涓流效應與乘數效應,助力民族村寨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與美麗鄉村的繁榮振興。
盡管本研究就肇興侗寨物理的、社會的與意義的空間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抽離,但旅游地鄉村空間再生產是隨時間發展動態演變并受外部政策環境沖擊較大的長期實踐。本研究囿于調研時間的前置,未就疫情常態化背景下民族村寨旅游地的各類結構、關系、情感的變化進行跟蹤調研。今后,疫情常態化背景下基于案例地的持續跟蹤,以及鄉村空間旅游業的脆弱性及恢復性對居民流動性的影響等拓展研究或將彌補本文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