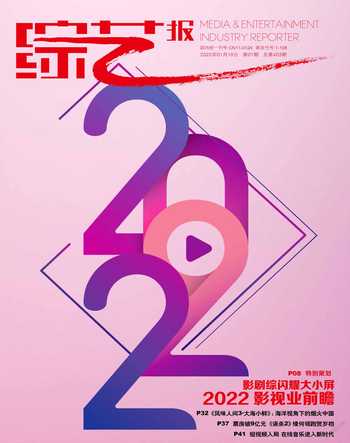新聞人“單打獨斗”的時代來了
方世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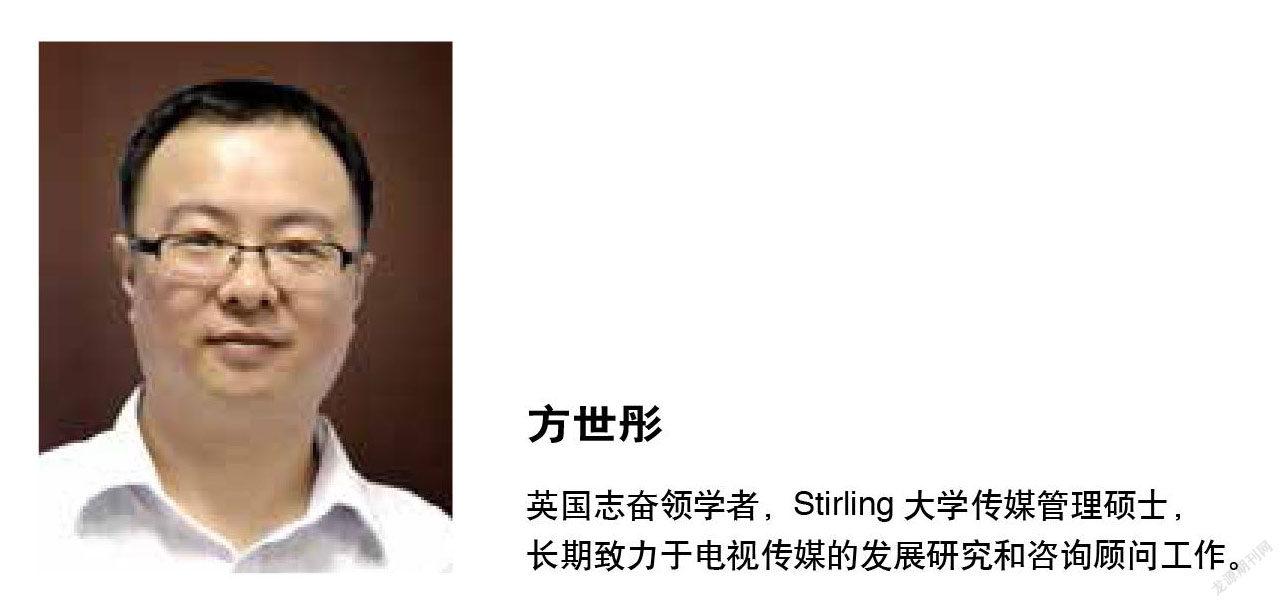
英國志奮領學者,Stirling大學傳媒管理碩士,
長期致力于電視傳媒的發展研究和咨詢顧問工作。
融媒改革并非簡單的設備更新換代,更是人才戰略的升級迭代
多年前,我應邀到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參加講座,介紹當時在全球興起的具備多任務能力的VJ(Video Journalist)——全能記者。時至今日,各地媒體正面臨融媒轉型,但很多機構的運營機制、制播人才還是沒有太大變化,我們有理由在2022年于變局中開新局。
全能記者并非新名詞。曾經的全能記者指的是那些既可以寫國內新聞,也可以寫國際新聞;既可以做一般新聞報道,也可以做深度調查報道……沒有完不成的報道,沒有寫不出的稿件的新聞達人、業界翹楚。融媒時代,全能記者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曾有新聞人戲言,“肩上扛著攝像機、胸前掛著照相機、口袋里裝著手機、背包里是無線上網本、手上拿著錄音筆……他們既是記者、編輯,也可能是播音員、主持人;既可以為報紙工作,也可能服務于電視臺、網站、電臺……他們是全能記者,是記者中的戰斗機。”
融媒時代最大的特征是去中心化,我們過去習慣的層級制度,在移動互聯網的沖擊下逐漸變得扁平,新聞和消息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層層上報。在這樣的變化下,“單打獨斗”的新聞人才成為各家新聞機構的重要生力軍,就連電視臺這樣重裝備、強調團隊作戰的單位,也開始培養和扶持能夠單打獨斗,即獨立完成“采編播”全流程的全能記者。
20世紀80年代,輕便的索尼超8攝像機的問世,帶動了一批喜歡自拍的獨立視頻記者的出現;隨后,衛星電視新聞的全球覆蓋,也造就了一批活躍在全球“熱點地區”的獨立記者;當下,5G和高性能手機的普及,更是為全能記者創造了完備的技術條件(一部手機就可以完成“采編播”流程)。
十年前,我到美國參觀NAB展會(全美廣播電視設備展覽會),那時4G剛剛興起,蘋果手機才開始普及,廣播電視設備廠家就已經開始推出在手機上剪輯影片的應用了。時至今日,國產視頻剪輯軟件已相當普及,甚至在應用中引入很多人工智能技術,讓高清節目制作變得愈加容易。
近年,直播業高速發展,5G的普及讓越來越多的人加入直播大軍。以前,我覺得做直播的都是帶貨銷售、追逐熱點事件或是旅拍的人,但是現在的直播做到了隨時隨地,各種內容應有盡有。大約4年前,我和團隊用專業的4G圖傳設備做了一次過春節吃家宴的直播,很隆重,也讓親友很是羨慕。2022年春節,相信會有更多的家庭在社交平臺上開著直播吃團圓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發,更是加速推進了直播在人們工作生活中的主流地位。對于以直播為生的媒體機構來講,如何讓眾多專業人才、專業內容在百姓的直播狂潮中脫穎而出,成為重中之重。
2021年爆紅的抖音博主“張同學”所發表的作品,吸引了許多專業人士研究其拍攝和剪輯方法,不少人斷言“張同學”是科班出身,他背后有個強大的團隊。然而,真相卻讓人大跌眼鏡,“張同學”只是一個35歲的普通農民,所謂的“強大制作團隊”只有他一人,而他全部的設備就是一部手機。一人一部手機,制作出令專業人士都印象深刻的視頻作品,“張同學”的案例值得新聞機構反思。
融媒時代,鳥槍戰勝大炮不再罕見,媒體機構要放棄大炮思維,積極應對變革浪潮。國外有些電視臺已經和手機廠商合作,定制專門為記者配備的全媒體采訪手機,這樣的專業設備價格并不高,但是因為配備了專用的App和軟件,使其更容易在與自媒體的競爭中搶占先機。融媒改革并非簡單的設備更新換代,更是人才戰略的升級迭代。在手機可以折疊,可以發文字、發圖片,可以錄音、攝像,還可以通過人工智能應用配音、配字幕的5G時代,一部手機就能搞定的事情,我們為什么還要堅持讓一堆一般人學不會、用不了的專業設備,阻擋記者成為“采編播”一體,可以應對全平臺、全任務的全能型記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