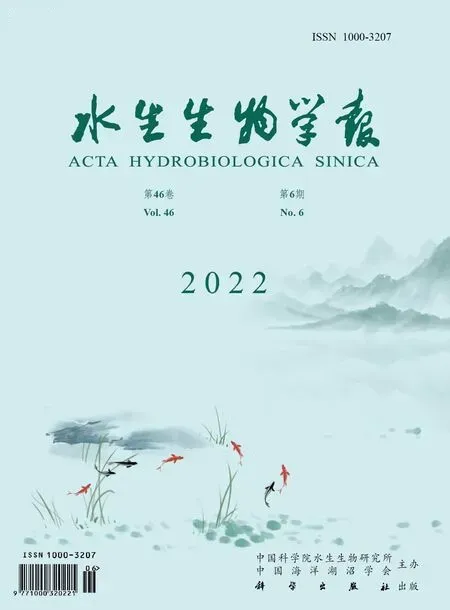動物個性和行為集:概念、測試和分析
李思平 張 東 段 明
(1.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東海水產研究所,上海 200090; 2.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漢 430072)
一個學科的發展,方法和理論同樣重要。要了解動物個性研究發展史,必須循著動物個性研究和行為生態學理論發展兩條線。有關動物個性研究發展史,Whitham 和Washburn[1]已做了比較詳細的回顧,國內也有簡要綜述[2]。動物個性研究史大致可分為五個期:
(1)萌芽期: 19世紀末,人類個性研究剛剛起步,此時尚無動物個性的實驗研究,但對動物有生物學意義的個體差異有了初步的認識。比較心理學家的早期研究主體傾向于個體,而不是物種的行為規范。雖然尚未明確動物的個性(Personality)概念,然而有關動物的性格(Temperament)、行為傾向和性格特征的描述性語言顯示了動物個性研究的萌芽。
(2)啟蒙期: 諾貝爾獎獲得者,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Pavlov Ivan Petrovich,1849—1936)可能是第一個將動物個性融入動物研究的科學家。巴甫洛夫在研究狗的消化和條件反射過程中,發現了狗的個性特征[3]。雖然他并未正式地采用“性格”“類型(Type)”“體質差異(Constitutional difference)”等后來用于個性研究的名詞,但他基于神經系統并借鑒人類性格對狗性格的非正式分類[4],為動物個性研究提供了基礎框架,是20世紀少見的動物個性研究的重要成果。
(3)起步期: 此階段以4個先驅性探究工作為標志。第1個杰出貢獻是Crawford Meredith[5]1938年發表的《幼年黑猩猩行為等級量化表》(A Behavior Rating Scale for Young Chimpanzees),這是第一篇動物個性的探索性文章。遵循巴甫洛夫的動物個性研究理論,Crawford對觀察個體的行為差異進行了實證調查,并對研究對象的行為進行了連續的22個等級劃分,歸納出行為等級量化表,該量化表是動物個性研究的第一個量化指標。第2個杰出貢獻是Billingslea[6]1941年對不同品系小白鼠(Mus musculus)的個性差異進行了短期研究。當時動物個性研究幾乎空白,其成果堪稱卓越。第3個杰出貢獻是Hebb[7]1949年的“黑猩猩的性格(Temperament in Chimpanzees)”。Hebb[7]似乎發現了動物個性的核心內容: 一個可靠的、能夠衡量整個生命周期(至少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穩定的物種內個體差異指標。但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動物個性”研究幾乎銷聲匿跡。
隨后,20世紀70年代,Buirski Peter、Plutchik Robert和Kellerman Henry[8—11]三位科學家合作開發并改編了一個適用于人類(Homo sapiens)、橄欖狒狒(Papio anubis)、黑猩猩(Pan troglodytes)和海豚(Delphinidae)的個性評定量表。該量表使用情緒特征指數(Emotions profile index,EPI),成功地突破了動物個性研究的物種界限。
(4)發展期: 20世紀70年代后期,Stevenson-Hinde等[12—14]發表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動物個性研究成果。她發展了現在仍在使用的馬丁利問卷(Madingley questionnaire),通過對個體每個成分的總體平均值進行標準化分析,使研究者能夠通過個體偏差得到個性特征。因為這種新穎且重要的方法,Stevenson-Hinde被視為該領域的先驅[15]。20世紀90年代,借鑒人類個性等級量化方法,黑猩猩的個性研究又發展出了“五因素模型+優勢度”(Five factor model+dominance)方法。
(5)相對成熟期: 20世紀90年代后,動物個性研究快速發展,并在越來越多的學科,包括心理學、基因組學、行為生態學、定量遺傳學、神經內分泌學等領域取得了巨大進展,衍生出很多研究思路,并在交叉學科中起到重要橋接作用。
從上述歷史回顧可以看出,動物個性研究方法基本遵循人類個性研究。然而,作為行為生態學的研究范疇,動物個性理論是隨著行為生態學理論的發展而不斷進步。本文正文將對理論概念和相應的研究方法做比較系統地介紹。
行為生態學的核心概念是適應性,Krebs和Davies等[16,17]提出行為生態學應該更加聚焦于行為本身,以適應性作為核心概念框架,并提出了一個精確的先驗預期: 行為進化應該是為了將個體適合度(Fitness)最大化。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行為生態學領域的共識仍認同最優模型,該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釋決定行為進化的基本收益、利弊權衡及限制,簡單且準確性很高[18]。依據最優模型理論可導出一種假設,即動物行為要么圍繞著一個單一的適應性最適值而變化,要么行為變化是集中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共存的保守性進化策略上的[19]。然而,行為生態學的最新研究挑戰了這一觀點,并提出了一個可以闡釋行為(包括解釋次優行為傾向)變化的新概念,即動物個性[20]。隨著20世紀70年代行為生態學家對個體差異的重要性進行了深入探究,如三刺魚(Gasterosteus aculeatus)面對捕食者時的御敵行為和侵略性呈正比[21],大批行為生態學科研工作者證實了動物個性的差異,并開始探究個性在生物進化、種群動態和群體分工等問題中的重要作用。
經過近20年的研究,動物個性已成為行為生態學的前沿及核心內容,研究對象廣泛涉及哺乳類、嚙齒類、鳥類、兩棲類、魚類、甲殼動物及軟體動物等[22]。雖然動物個性研究在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顯著發展[20,23—26],但仍有一些混淆需要厘清。如不同時期的動物個性概念存在較多含義且易混淆[27],盡管這些概念和定義在字面僅有細微差別,但不同領域的科研工作者在定義上存在分歧。鑒于動物個性研究始于多學科交叉復雜的發展史,動物個性的測試方法在不同時期、不同研究對象中也存在較大差異[20,28]。此外,行為數據龐大復雜且多樣,分析也是挑戰性很高的工作。因此,有必要對動物個性中涉及的概念、測試和分析方法進行梳理,否則,這些混淆可能會導致錯誤地標記特征,并且錯誤地闡釋結果,不利于動物個性理論的發展。在此,我們綜述了動物個性的定義和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問題,并總結了成功應用的研究方法,以提高未來動物個性研究方法的標準化程度。
1 概念
個性(Personality)和性格(Temperament)皆源于人類個性研究。由于人類個性的復雜性,個性心理學家對個性的定義長久未達到統一; 性格被認為是一種與個性密切相關的結構,在某些情況下,使用“性格”似乎純粹是為了避免使用“個性”一詞。早期動物個性研究對象皆為哺乳類,因而很自然地借鑒了人類個性研究的概念、理論和方法[7,29]。因此,動物個性也長期沒有嚴格的定義[30]。此外,應對方式(Coping style)[31]和行為集(Behavioral syndrome)[23]也用于表示動物個性。雖然這些概念有一些差異,但有關行為的核心內容皆統一于“個性(Personality)”定義[32]。
針對“動物個性”的不同表述,Stamps和 Groothuis[32]進行了系統總結,并給出了比較嚴謹的定義:隨著時間的推移,動物在不同情境下所表現出的持續一致的行為個體差異,即在不同環境中,個體在不同生活史階段的行為表現具有一致性。對不同物種的研究發現,“個性”具有三個關鍵特征: (1)差異性(Difference),即個體在行為上存在差異; (2)持續一致性(Consistency),即個體的行為差異在不同時間和情境下保持穩定; (3)相關性(Correlation),即某些行為特征(例如,大膽、攻擊和探索行為)間存在關聯性[24,33]。其中“差異性”指的是個體間的行為差異; “持續一致性”指的是個體行為的可重復性[20,34]; 而“相關性”指某些行為特征(如大膽、侵略性和探索性)往往在個體之間存在關聯,與行為集(相關聯的協變行為的集合)[20,31]概念一致。根據定義,個性研究不能僅僅以在某個時間點某種情境下的行為數據作為依據,應該涵括對不同時間點下同一個體相同行為的重復性(Repeatability),這樣才能更加準確地對個體的行為進行分析和評估[35]。
“個性”概念和“行為集”一致,但反之卻有差異。行為集關注點在于不同環境和不同活動狀態(如: 攝食、交配、反捕食、親代撫育、競爭和擴散)下各種行為特征的相關性(即將各相關行為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側重于生態和進化[23],為整合生態、生理、遺傳和進化手段在行為研究中的應用搭建了有效的橋梁。行為集涵蓋以下三種情況下行為特征的相關性: (1)相同環境下不同活動的行為特征(例如: 在相同生態條件下攝食活動和交配活動的行為特征); (2)在不同環境下同一活動的行為特征(例如: 在捕食者存在和不存在條件下攝食活動的行為特征); (3)在不同環境下不同活動的行為特征(例如: 在捕食者存在條件下攝食活動和同類爭斗的行為特征)。
個體在面對壓力時表現出一致的行為差異[36,37]。因此,Koolhaas等[38]用“應對方式”來表述“隨著時間和情境的推移,個體表現出的一組連貫的行為和生理應激反應,是某一特定類群的特征”。“應對方式”依據個體在不利環境和壓力下的行為和生理應激反應將個體分為三大類群: 積極應對(Proactive)、消極應對(Reactive)和中間型(Intermediate)[39]。而“性格”則更關注于個體特征本身,是個體在不同條件下由于其神經系統的生物學差異而導致的行為類型的不同,是“個性”的基本組成部分[2,40,41] 。
就各定義研究的側重點而言,“個性”定義強調了某一行為的一致性,常應用于心理學領域(尤其是早期用于哺乳動物的個性研究); “行為集”則偏重于不同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多在行為生態學領域廣泛使用; “應對方式”則突出了行為和生理的聯系,還包括神經內分泌[17],在生物醫學研究和農業科學研究中應用較多[39]。
個體間的行為差異通常以非隨機的方式沿特定的軸分布[42,43],即所謂的行為軸(Behavior-axis)。行為集包括五個動物個性軸: (1)害羞-大膽(Shyness-boldness); (2)探索-回避(Exploration-avoidance);(3)活躍性(Activity); (4)攻擊性(Aggressiveness);(5)社交性(Sociability)。其中最重要的是害羞-大膽軸,其他四個特性都與此有關。例如,食蚊魚(Gambusia affinis)的大膽個體具有較強的探索能力,且更活躍[44]; 褐鱒(Salmo trutta)的探索性與攻擊性呈正相關[45]。然而,實際研究不能僅限于此五個行為軸,應該關注可能出現的新的行為特征及其關聯性[43]。
在量化行為集時,至少需要對個體的兩種行為進行觀測(最好是在不同活動狀態或不同情形下)。根據觀測數據,可以量化一個行為集的兩個不同方面: 個體本身行為和個體間行為的一致性。個體本身行為一致性指任何一個特定的個體傾向于在不同觀測中表現出一致的行為(例如個體的攻擊性)。個體間行為一致性是指個體間行為差異的一致性(例如攻擊性等級順序的一致性),在統計學上表現為行為相關性。如果在相同活動狀態和相同環境下重復觀測同一個行為類型,行為一致性稱為重復性[46]。此外,為了更好地分析動物的行為集特征,最好一并測量相關的特征(例如形態學和神經內分泌特征)和表現(例如攝食率、交配成功率和存活率)。很多行為在不同狀態或環境下具有相關性,鑒于動物一生中的活動狀態和面臨的環境的多樣性,通過綜合分析行為集數據,可有助于我們理解不同行為的相關性對總體適合度的益處,使我們對動物一生的行為有更全面的認知。
2 個性測試
2.1 個性測試需要考慮的要素
測試個性,首先要考慮采用何種測試方法。目前個性測試方法有3種: 主觀個性評估法(Subjective personality ratings)、行為編碼法(Behavioral coding)和實驗法[47—51]。主觀評估法采用多項評分,例如在觀察基礎上對包含多個個性軸維度進行定性描述,此法借鑒于人類個性研究,多用于高等動物(如靈長類)研究中; 行為編碼是根據預定的行為譜(Ethogram)記錄特定個體的行為[48,52]; 實驗評估是記錄個體在實驗條件下的行為類型,以評估有限數量個性軸的變異性,如大膽性、攻擊性或社交性[24,53]。
主觀評估法需要觀察者提供量化的、動物習性主觀評價報告。應該多人觀察,且測試需要在多個時間點進行。如恒河猴(Macaca mulatta)的“活躍性”[54],通過對其行為的開放評價整理出25個形容詞。主觀評估法主要揭示了研究對象具有心理學意義的行為,是一種快速有效的研究個體行為的手段。事實上,主觀評估法信度很高,主觀性并不很高[55]。
在設計行為編碼法實驗時,則需要預判研究對象可能發生的行為反應,并進行量化。同時,需要在相同條件下進行多次重復觀察。如Mather和Jennifer等[56]在研究不同情境下章魚(Octopus rubescens)的活躍性時,通過行為編碼法對章魚預期的行為對活躍性進打分: 在喂食條件下,章魚噴射協助撲向獵物,活躍性記為2; 如使用吸盤觸手緩慢移向獵物,活躍性記為1; 而當章魚經過獵物時才發生捕食,此時活躍性記為0。White等[57]對野外環境下黃雀鯛(Pomacentrus moluccensis)的大膽性進行測試時,對黃雀鯛在鉛筆猛刺下的行為進行了量化: “0”表示受到驚嚇前后即發生躲藏,較少出現; “1”表示受到驚嚇后撤到庇護所,超過5s后才出現,并嘗試攝食; “2”表示受到驚嚇時不躲藏,而是繼續探索或攝食。此外,Li等[58]對中華絨螯蟹(Eriocheir sinensis)的打斗激烈程度進行了評分,以判斷其攻擊性。此類方法要求測試的行為表象顯著,且要具有重復性,能夠揭示行為和環境之間關系[59]。
實驗法則針對研究對象特定的個性設計實驗進行測定。如雄性地毯巖蜥蜴(Iberolacerta cyreni)的活躍性和冒險性分別通過其在新環境中移動的總距離和進入新環境的潛伏時間作為行為參數[60]。魚類個性的研究多使用實驗法,如通過對新物體的反應和攝食行為分析吻海馬(Hippocampus reidi)的大膽性[61]; 通過捕撈刺激和網隔中的反應篩選不同個性的牙鲆(Paralichthys olivaceus)[62]; 新物體測試下虹鱒(Oncorhynchus mykiss)接近新物體的反應時間區分大膽和害羞性個體等[63]。李武新等[64]總結了魚類的探索性研究的標準流程: 記錄實驗魚進入新環境中一段時間內的包括潛伏時間、游泳速度、游動時間、游動路程等可量化的行為參數,當該魚的潛伏時間越短、游泳速度越快、游動的時間和路程越長則表明該個體的探索性越強。研究人員不同程度地組合這些方法開展個性研究。行為生態學家常在實驗過程中對自然狀態下的行為進行編碼,結合實驗觀測的行為對個性進行評估[49,50]。雖然每種方法各有優、缺點[51],但綜合利用這些研究手段能夠幫助研究人員得到更可靠的結果[49],起碼在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的測試中是如此[65]。
個性測試時第二個要考慮的是情境強度(Situational strength)[50]。行為生態學的情境是指測試條件(例如,溫度或可利用資源)。情境強度是指被測個體的行為受情境影響的程度[50]。較強的情境可能會導致個體間行為差異很小,而較弱的情境可能會讓更多的個體差異顯現出來[66,67]。因此,考慮到由于下限、上限效應(即地板、天花板效應),個體之間可能存在微小的差異,強情境(例如生存溫度的上限或下限)可能不適合行為測試[50]。此外,由于上限效應,在達到上限前某個時間點切斷數據可能會導致對個性的評估產生偏差[68]。例如,魚類的探索性測試是根據魚類探索新物體所需的反應時間來確定的,測試的時間點將決定探索性評估的可靠性。Castanheira等[69]在網隔中測試魚的行為反應以區分金頭鯛(Sparus aurata)個性時,金頭鯛在第1分鐘內的行為得分與前3分鐘的行為得分顯著正相關,如此,網隔中第1分鐘的行為即能可靠地代表金頭鯛的個性特征。
最后,在行為測試中,要考慮個體和情境的相互作用。在行為生態學中,行為反應范式(Behavioural reaction norm,是指個體在給定的系列環境中產生的一組行為表型[70])為理解動物和情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提供一個有用的理論概念框架,其中個體對不同情境的反應使用隨機回歸建模進行分析[71,72]。
2.2 實驗設計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
根據以上概念,動物個性研究需要對行為進行重復測量,才能算是嚴謹的實驗方案[73],這是設計個性測試實驗時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而對個體行為進行單一測量時,如果研究人員僅強調他們的結論是為了反映個體實際行為的平均值(或“個性”),這種研究仍然可以與動物的個性研究相關聯[74]。然而,這種假設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太可能成立,因為行為的重復性(行為學領域的重復性和持續一致性類似,是指隨時間的推移,由個體間差異而導致的行為變化的一部分,是個體間的方差,s2是個體內方差[75])只有0.4左右[76,77],說明對行為進行單次測量在很大程度上只反映了個體本身的行為差異(60%)而不是個體間的行為差異(40%)[78]。有些研究人員可能會認為,“前人實驗已證實某種行為具有重復性了,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們對每個個體的該行為進行單次測量即可代表個性”,這種觀點不合理也不符合邏輯,因為對個體進行單次測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個體表型中不可重復的部分。因此,在開展此類研究時需要謹慎。例如,3個月后再次測試藍鰓太陽魚(Lepomis macrochirus)在捕食者存在時的探索性和活躍性時,其離開庇護所的反應時間和在接近捕食者區域的停留時間具有重復性,而其活躍時間和監視捕食者的時間無顯著的重復性[79]。因此,對于重復性低的指標而言,環境復雜性導致偏差效應的可能性極高,許多動物個性的行為研究中也會存在類似的問題。
有些研究常將動物的個性定義為一種特定類型的行為,無重復測量,僅僅引用Réale等[20]的文章以示理論支撐,此類研究顯然不合適。例如,應對人工圈養條件或新環境下的行為、冒險、大膽或攻擊行為被認為是個性特征。這種方法很難納入行為生態學范疇,因其不涉及針對行為中可重復的個體變化(即“個性”)來解釋適應性意義[80]。此外,有些研究將“個性特征”定義為“可重復的行為特征”,此定義也存疑,這只是將一個標簽(行為)替換為另一個標簽(個性)。只要累積足夠多的數據,所有的行為都是可重復的[81]。將“動物個性”變異定義為“重復觀察下平均行為的個體差異”,這種表述更加直觀,能夠避免概念的混淆。
上述的很多觀點也適用于行為集[73]。簡而言之,行為集是多個行為在重復測量中均表現出的相關性[74]。它本質上代表了個體多個特征均值之間的相關性。因此,需要對每個行為進行重復測量[82]。此外,還需要在不同的分析中測量不同的行為。否則,這種相關性可能僅僅反映了在同一觀察中出現的相互涵括或者排斥的行為類型。據上所述,當行為只測量一次時,兩種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可能主要反映了個體自身的行為變化,而不是個體間的協方差[83,84]。如果個體間和個體自身的相關性均沒有差異,對行為進行單次測量就沒有問題[82,85]。但是,元分析(Meta analysis)表明,這一假設并不成立[74,86]。同樣,如果假設成立,每個個體的每種行為的單一測量對行為集研究可能也有用。
2.3 個性測試步驟
完善的動物個性研究方法應該包括多重特征測試、可靠性測試和驗證測試[19,50,87],并在研究開始時確定研究問題和假設。動物個性研究的方法目標建議如下:
(1)確定測試方法
a.采用哪種方法(主觀個性評估法、行為編碼法或實驗法)。
b.是否真正測量了測試對象的目標特征? 也就是說,測試是否具有情境關聯性?
c.情境強度和上限、下限效應(地板和天花板效應)。刺激是否過強? 在弱情境下,是否存在影響個性的刺激臨界點?
(2)多重測試
對一個特征進行多重測試是建立該特征和測試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所必需的。對研究問題要調查的每個特征,建議考慮以下因素:
a.測試是否具有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指研究者擬就的問題從表面上看跟其研究目的是否相關)?
b.針對這種特征的測試以前是否用過? 以前的研究結果是否表明這些測試也適用于本研究?
c.確定一個主測試方法,并至少還有一個其他的方法,確保每個都可以用來測試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指運用不同測量方法測定同一特征時所得結果的相似程度,不同測試間具有相關性)或區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指在應用不同方法測量同一特征時,觀測值之間的區別程度,兩個測試之間缺乏相關性)[25]。
d.如果測量的是目標性狀,則應該對所選各測試之間的相關性進行明確預測,即在采集數據之前考慮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即聚合和區分效度)。
(3)驗證測試
驗證應包括:
a.可靠性: 是指任何人在不同情境下測得的同一特征的結果具有一致性。其不同于效度,因為測試可能可靠但卻無效。
b.生態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指實驗室觀測的行為是否能反映自然行為[20])。需要說明的是,“生態效度”借鑒于心理學,較適用于高等動物或野外研究比較容易的物種,水生動物由于野外觀測難度大,生態效度驗證難度高。
c.聚合效度。
d.每個測試的區分效度。
為了避免測試每個測量值與所有其他測量值沖突所致的I型誤差(拒絕了正確零假設)[55],可以使用結構方程建模法(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SEM)[34,89]來檢測哪些測量值與其他測量值共同加載。必須強調,兩個測試之間的相關性可能是通過測量同一行為特征而建立,或者測量的特征通過一個潛在的行為集而關聯,這取決于是以個性特征驗證還是以行為集識別為解讀重心。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研究行為集,仔細選擇驗證測試也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因子分析法可能有助于整合相關聯的特征,如大膽-攻擊因子。然后,我們可以就有關測試進行自我提問[90]:
a.這些測試測量的是不同稱謂的同一個特征,還是不同的特征?
b.測試特征重疊度。例如,雖然可以用在開闊區域中移動的距離來表示探索性,但這個指標可以同時測量活躍性,當用它來測量探索性時,是否應該控制活躍性?
c.針對所測動物個性特征的所有測試是否都必要? 如果測試未現預期的結果或關聯,則考慮所做的假設是否合乎邏輯。
3 統計分析和結果報告
常見的表達動物個性的參數有距離、時間、頻率、比例等。其中距離數據、時間數據的理論分布類型為正態分布,頻率數據為泊松分布,比率數據為二項分布。最重要的是,動物個性和行為集研究應該包含行為的重復性[82]和變異系數[91]。選擇合適的行為集數據分析方法,從統計學上更加精準的闡釋個性,探究、詮釋行為變異的交互影響因子等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不滿足分布假設時(如非正態分布),常選擇非參數分析統計方法。但非參數分析方法忽略了與進化論密切相關的關鍵參數(例如,重復性、遺傳性和皮爾森相關性)[92],研究價值因而會大打折扣[83]。折中的方案是使用參數分析(如混合效應模型Mixed-effects models),其與固定效應模型(Fix-effects model)相比,優勢在于引入了隨機因子,對于動物個性研究而言,可以將實驗開展時間等因素作為隨機因子加以控制,從而得到更加可靠的結果或隨機化程序來推導零分布。最新研究表明,混合效應模型對分析不符合分布假設的數據極為有效[93]。
混合效應模型包括線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LMM)、廣義線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GLMM)、廣義可加混合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ixed model,GAMM)。這三種模型的核心差異在于所處理的數據類型不同: 一般線性模型適用于正態分布的數據; 廣義線性模型適用的數據服從指數分布,例如頻率數據和比率數據;可加模型本質是多段回歸曲線的組合[94]。一元混合效應模型(Univariate mixed-effects model)包含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參數值及其不確定性(例如,95%可信區間),有助于理解結果并進行后續的元分析,同時還有助于解釋每個成分的方差并估算(調整后的)重復性[96,97]。迄今為止,研究行為集最佳的方法是利用廣義線性混合模型,其能夠對多個重復測得的數據指標進行擬合[35]。當使用這種分析方法時,需要在文中展示個體自身和個體之間的方差、協方差和相關性,從而能夠對整個矩陣結構進行元分析[35,98],并在生物層面進行比較[72,99]。如上所述,由于個體間的相關性涵括了試驗中的額外方差(偏方差)和協方差,因此個體間的相關性最能代表行為集[100,101]。研究者有時也會使用其他的統計方法來分析行為集,但由于這些分析方法會使結果發生偏差,在實際研究中并不太適用[100]。然而,廣義線性混合模型需要足夠多的數據量,它只適用于大數據集的分析。
在動物個性研究中,常常以多個指標衡量某一個性特征,由此產生了多變量分析的問題,這是混合效應模型所解決不了的,由此引出多元統計分析方法,而其中最常用的是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102,103]。PCA可以將同一觀察期間或測試分析的多項行為指標匯總為單個指標或潛在變量,以此代表個體的主要行為。然而,PCA方法不適用于對重復測量的數據集進行分析[104],當然也不能分析成分間的關系。因此,在采用這種數據降維方法時必須極為謹慎。一種比較適用的方法是通過對相同試驗中(個體自身和個體之間)的行為進行重復測量,分析不同行為的相關性矩陣,然后提出一個具代表性、呈正態分布且與PCA主成分或者潛在變量協相關性最強(如負荷量)的行為指標[105,106]。總而言之,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只有對行為進行重復測量或多種試驗時,PCA才能用來表示“行為集”或“動物個性”。除PCA分析方法之外,多元分析還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驗證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主坐標分析(Principal coordinate analysis,PCoA)、非度量多維標度分析(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NMDS)等降維方法[103],雖然這些分析方法在動物個性研究中并不常見,但并不代表其不適用于動物個性分析,選擇分析方法時還應結合行為數據特點和研究目的進行適當適合的選擇。
行為集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大規模個體層面的相關性或方差-協方差矩陣。此時,當涉及多變量的因果關系時,更合適的統計方法是結構方程建模法[107,108]或類似的多變量方法,如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或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109],因為特定協方差結構(如基于文獻)的特定先驗假設(Priori hypotheses)可以通過測試和正式比較發現最可能的擬合[110,111]。
另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動物的個性測量值(每個個體的平均行為差異),在統計上如何與生理、生態和進化過程相關聯? 常見的方法是首先計算每個個體的平均行為,然后通過另一個模型將其與其他生物變量、生態指標或適合度等進行統計比較。這通常包括對本質上是統計估計的數據進行統計(即stats-on-stats),從而忽略了兩組測量的誤差方差。為了避免偏差或誤解,應盡量使用一元(多變量)混合模型進行評估[112,113]。然而,這些復雜的統計模型不適用于每種數據。因此,對于更為復雜的數據,上述基于頻率統計的方法可能難以分析,需要借助基于后驗分布的貝葉斯等統計方法加以解決。例如,越來越多的研究根據個體間的后驗分布(而不是點估計)來確定備選SEM的相對擬合度[105]或遺傳相關性矩陣[82,114]。這種分析方法雖應用廣泛,但具有主觀性,因此最好與模擬結合使用,以證明其對特定數據集的效用[82,105,115]。
本綜述基于已發表的文獻,總結出了截至目前適用于動物個性研究的最佳統計分析方法。未來應該會有更好、更適用的方法出現,可以盡量避免分析錯誤。當然,我們也應該批判性地審視新方法。
4 總結
隨著科研工作者對動物的個性的深入研究,動物個性研究的在不同學科之間搭建概念性橋梁的巨大理論價值和動物福利及管理等方面的實際應用價值使得其自身的學術地位逐漸凸顯。其中,魚類的個性研究為人們了解其生活史策略、種群動態、物種形成及遺傳變異等方面提供了進化和生態學啟示。本文簡要回顧了動物個性研究的發展史、探討了動物個性概念、研究的實驗設計和統計方法問題,但真正的目的是通過詳細闡釋其概念、分析方法的異同,從而使得研究人員從研究動物個性和行為集的進化生態學實踐中獲得更前沿和準確的生物學見解。通過規范化動物個性研究,為該領域研究人員提供足夠的認識,明確地將動物個性或行為集與所涉及物種的生態學和進化聯系起來,不斷完善行為測試方法和行為適應理論,促進行為學研究的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