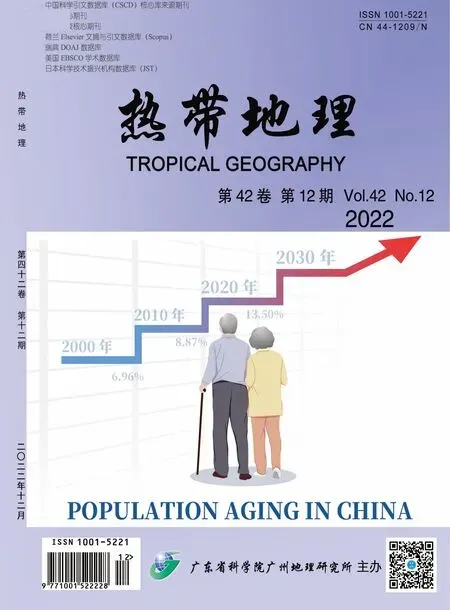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時空格局演化及影響因素
馮瑜滿,梁育填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廣州 510275)
電子信息制造業的高價值重量比和高價值體積比特征使其成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產業之一,同時,其產業價值鏈環節的相互依賴關系使其具有集聚性,呈現區域化特征(盧明華等,2004)。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的區域格局受全球化、國家政策以及本地生產網絡的影響,自20 世紀90 年代珠三角承接國際電子信息制造業轉移后,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經歷了從珠三角轉移到長三角、京津冀地區的變化;近年來,向四川、重慶等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趨勢也逐步顯現(高菠陽等,2015)。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劇烈沖擊了全球經濟,顯著地影響了后危機時期全球生產-貿易網絡和全球經濟增長態勢,并對該階段的全球化導向與策略造成顛覆性的影響,使全球化發展發生轉折而進入新階段。同時,在此之后的全球化脫鉤、貿易保護主義、區域化與本土化、非傳統安全沖突等極大地影響了全球經濟發展和產業格局。美日等發達國家提出“再工業化”戰略,積極推動本國和本地區工業化進程,減緩對外投資步伐,推動全球生產網絡的解構與重構(金鳳君等,2021)。后危機時期,基于成本、技術、生產環節的電子信息制造業全球產業格局被重塑,而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格局、影響因素將產生何種新變化,及其影響因素的空間異質性有何特征,亟待探討。
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電子信息制造業時空格局進行研究,主要集中在:1)分析電子信息產業中某一特定產業的時空演變特征及其內在機制和影響因素。如高菠陽等(2008)、郭建峰(2020)分別對中國彩電產業、電子信息產業中制造業企業時空格局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發現產業在不同時間階段呈現不同的轉移趨勢;2)基于產業鏈、價值鏈分析電子信息產業的時空演變。如Frederick(2016)、康江江(2019)等分別基于全球價值鏈對世界3C產業的時空演變、蘋果手機零部件的全球價值鏈分配特征進行探討,發現中國是供應鏈所有環節的主要出口國,但高價值環節仍主要集中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3)從產業轉移角度分析信息產業的時空演變特征及其影響因素。如高菠陽等(2015)、段美娟(2018)從全球化、國家政策、勞動力成本、技術差異等角度對全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產業轉移進行分析,發現不同因素在區域間存在差異且具有一定空間溢出效應;4)基于區位論理論對城市或區域內部電子信息產業的空間分布特征研究。如盧明華(2012)、余穎(2020)、Luo(2020)等分別采用企業數據對北京、深圳、武漢都市圈的企業空間分布特征進行探討,發現城市的電子信息產業均呈現顯著的郊區化特征。
上述研究為探討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的時空格局演變及影響因素分析提供有益借鑒,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大多研究的空間范圍廣而尺度粗,如全國省級尺度的研究,或是范圍小而尺度精細,如城市內部空間尺度的研究,而城市尺度和縣級尺度的研究較少。一個城市某一行業企業的多寡,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多寡,能有效表征該行業的活力、集聚程度,因此以城市尺度作為基本單元,探討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時空格局具有一定現實意義。其次,對于數據來源方面,多數研究采用官方統計數據中規模以上企業的產值、從業人員等指標反映產業的發展,較少使用企業數據進行分析,且受限于數據,一般將尺度放在省區層面。因此,本文擬采用2009-2018年全國城市尺度的數據,基于基尼系數、空間相關性分析、負二項回歸模型等方法,探討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時空格局演變特征及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以期深入理解后經濟危機時期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的變化及發展趨勢。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方法
1.1.1 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可用于度量收入、經濟發展在空間單元上的不平等,基尼系數取值為0~1,數值越高,表明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空間集聚現象越顯著。公式為(王倩倩,2019):

式中:n為空間單元數,本文n=326;yi、yˉ分別為當年各城市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數量、平均數量。
1.1.2 空間相關性 空間相關性分析采用莫蘭指數分析(陳彥光,2009),分為全局莫蘭指數及局部莫蘭指數,其中,全局莫蘭指數用于衡量空間相關性是否存在,而局部莫蘭指數用于探究空間集聚的位置及范圍,本文結合全局和局部莫蘭指數分析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空間相關性。其中,全局莫蘭指數和局部莫蘭指數的公式分別為:

式中:n為空間單元總數,本文n= 326;Uij為空間權重矩陣,采用高斯核函數、最大KNN 距離帶寬生成;Xi、Xj分別為空間單元i和j的屬性值,即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數量;X為樣本平均數,即每個城市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平均數量。
1.1.3 計量模型與變量說明 自變量新增企業數量屬于離散的計數數據,不符合正態分布與連續分布的特征,因此在計量分析中采用計數模型比線性模型更合適,計數模型包括泊松回歸模型與負二項回歸模型,需根據數據特征對兩模型進行選擇。
使用泊松回歸的前提是假設數據均等分散,即方差等于期望,其基本模型為:

式中:λit>0 為泊松達到率,由解釋變量決定;yit為從參數為λit的泊松分布中抽取;λit的表達式= exp(βi Xit)。
采用Alpha檢驗對樣本數據進行離散程度檢驗,樣本數據方差大于期望,且Alpha顯著(P<0.001),樣本數據呈過離散分布。為修正樣本過離散帶來的問題,采用負二項回歸模型而非泊松回歸,公式為:

同時,樣本數據為2009-2018年面板數據,還需對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進行選擇。因為樣本為中國所有城市,城市分組原本代表總體而非隨機抽樣;同時,本文探討個體城市特征對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需控制個體效應,所以采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適。
綜上,使用個體固定效應面板負二項模型進行參數估計,模型為:

式 中:i表 示 城 市;t表 示 年 份;LABORit、CAPit、RCit、 MARKETit、 INNit、 GLOBALit、 GDPit、TRAFFICit為解釋變量,具體含義見表1。β0為常數項,β1~β8為自變量的回歸系數;μ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表1 電子信息制造業時空演變影響因素的變量名稱及定義Table 1 Variable names and definition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有學者認為地區經濟規模、教育水平、產業發展水平、交通基礎設施等是影響區域制造業企業進入的主要因素(Coughlin et al., 2000; Sutaria et al.,2004);也有學者聚焦城市化經濟、產業聯系等,發現集聚效應是影響企業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Venables,1996;He et al.,2016);此外,制度環境、政策等也是影響中西部后發地區電子信息制造業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畢秀晶等,2011;賀燦飛等,2018)。綜上,從人口、產業、城市3個維度探討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的區位選擇,各變量定義如表6所示。其中,人口維度包括勞動力成本、人力資本豐富程度,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的傳統因素之一;人力資本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核心動力之一,在校大學生數對工業企業主動選擇呈正效應,高效率的企業更傾向于進入人力資本儲備豐富的城市(劉穎等,2016)。產業維度的變量包括產業市場化水平、產業協同集聚程度,產業市場化水平是是地區制度環境和產業政策的綜合反映,涉及到產權制度、競爭性價格制度、市場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王立平等,2006),市場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業自由競爭和地區資源的合理分配,國有企業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區市場化水平;從產業關聯角度分析共享中間投入品對產業空間集聚的效應,產業關聯即產業協同集聚,是指上下游產業在特定空間范圍內的高度集中現象(陳曦等,2018),同一行業內上下游產業集聚的企業越多,地區產業專業化水平就越高,越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外部規模經濟。城市維度的變量包括創新能力、城市對外開放水平、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交通基礎設施水平,電子信息制造業屬于先導性高技術產業(賀燦飛等,2018),產業的發展與升級需要創新驅動,本文采用發明專利授權數目衡量地區創新能力;城市對外開放程度反映該地區與國際市場的聯系程度,對外開放水平越高,區域間要素流動越頻繁,越有利于促進地區產業發展水平的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反應城市實力,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產業活動越活躍,但也有研究表明隨著經濟發達地區產業產品市場飽和,企業為避免趨同競爭會在一定程度上傾向于開辟縫隙市場(符文穎等,2017);由于制造業普遍的生產與消費時空分離現象,交通運輸成本是影響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交通基礎設施水平的改善有利于吸引制造業企業的產業布局(陳曦等,2018)。
1.2 數據來源
電子信息制造業包括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17)(國家統計局,2017)中的計算機制造、通信設備制造、廣播電視設備制造、非專業視聽設備制造、智能消費設備制造、電子器件制造、電子元件及電子專用材料制造7個行業。通過“天眼查”企業數據網站①https://www.tianyancha.com/檢索并下載電子信息制造業相關的企業數據,采用R 4.0 對數據進行清理與處理,將企業按照成立年份、所屬市區、企業經營狀態進行歸類匯總,覆蓋中國1949-2018年326個城市(4 個直轄市、287 個地級市、3 個盟、26 個州、6 個地區)的數據,以此為基礎構建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數據庫。其中,企業狀態分為在業、存續、吊銷、注銷、停業、撤銷、遷入和遷出8種,在業、存續代表企業正常營業,本研究重點在于目前仍正常經營的企業,因此將在業、存續的企業數據作為企業總數數據,而新增企業數據則將所有企業納入。中國電子信息產業利潤總額、主營業務收入、出口、平均用工人數等數據來源于《1949—2009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統計》(工業和信息化部,2011)及2009-2018 年《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統計年鑒》(工業和信息化部,2009—2018)。區位選擇實證分析部分各城市社會經濟數據,包括當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職工平均工資、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GDP、道路面積等,數據來源于2009-2018年《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09-2018)以及EPS中國微觀經濟數據查詢系統②https://www.epsnet.com.cn/index.html#/Index,各城市發明專利授權數目得分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③https://www.cer.pku.edu.cn,各城市電子信息制造業每年新建企業數量以及產業協同集聚程度、市場化水平等指標的原始數據來源于本文構建的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數據庫。
2 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時空格局變化
2.1 電子信息制造業穩步發展,由出口導向轉為內需拉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劇烈沖擊了全球經濟,極大地影響了后危機時期全球經濟增長態勢,使得全球化發展發生轉折從而進入一個新階段。2009 年,隨著世界經濟逐步回暖以及國內相關政策效應(如家電下鄉、以舊換新、3G與TD等等)的顯現,電子信息制造業穩步向好,總體企業數量快速上升(圖1),年均增長率為14.09%;新增企業數量呈波動中上升的趨勢,年均增長率為6.24%。從利潤總額及主營業務收入看(表2),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在2009-2018 年獲得較快的發展,分別由2009 年的1 791 億元、51 305 億元增加至2018 年的6 000億、126 297 億元,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6.31%和11.92%,相較2001-2008 年的18.84%和23.89%,增速呈下降趨勢。

圖1 2009—2018年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數量Fig.1 Number of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18

表2 2009—2018年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運行概況Table 2 Overview of the operation of China'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2009 to 2018
利用出口總額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衡量產業對外依存度,結果發現,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對外依存度由2009 年的57.93% 下降至2018 年的41.25%,表明內需拉動逐漸成為產業發展的重要引擎。但由于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大多處于產業鏈上游、中游環節,在制造技術、制造設備、品牌效應等方面仍與世界其他電子信息制造業強國存在一定差距。同時,產業依存度仍處于較高水平,導致產業受世界經濟局勢的沖擊較大,如2018年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電子信息制造業的利潤總額及主營業務收入下跌明顯,回到2016年的發展水平。
2.2 城市群成為電子信息制造業集中發展區域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城市群將成為全球經濟核心(Fang et al.,2017)。中國五大國家級城市群——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長江中游城市群的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數量及變化特征存在明顯差異(圖2)。珠三角始終是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發展的熱點地區,企業總量、增量均居首位;其次是長三角地區,每年新增企業數量在1 500~2 000 家波動變化,產業發展穩定;成渝城市群與長江中游城市群的電子信息制造業雖然基礎薄弱,但借助后發優勢,呈不斷向好的發展態勢;而相比于其他4個城市群,京津冀地區的發展有所放緩,雖然企業數量不斷增加但其占全國的比重呈下降趨勢。總而言之,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目前已形成由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成渝城市群及長江中游城市群構成的菱形布局及“中部高地”。

圖2 五大城市群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數量(a)和新增企業數量(b)Fig.2 Number of total and newly-increase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the five city clusters
2.3 深圳、東莞等重點城市一直為產業重要集聚區,城市兩級分化嚴重
選取2009和2018年2個時間截面對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總體及新增數量的時空格局演變進行分析(圖3、4),發現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主要分布在胡煥庸線以東地區,集中于東南沿海地區,總體經歷了由沿海發達地區向沿海欠發達地區,由東部地區向中部、西部地區蔓延推進的過程,且近年來電子信息制造業向中部地區、川渝地區擴散的趨勢加速;東北地區大部分城市的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總量、增量均較少,發展滯后,地區發展不均衡。采用基尼系數衡量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城市間的發展差異(圖5),發現城市間兩級分化嚴重,基尼系數>0.7,表明中國電子信息企業的空間分布極度不均衡,馬太效應顯著,但總量、增量基尼系數均呈下降態勢,表明城市間電子信息制造業發展的差異呈不斷縮小、極化增長趨勢有所放緩,這主要受中國實行的一系列區域調整政策推動的影響,包括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戰略等;同時,東部地區面臨的環境問題、制造業成本上升等壓力,也是推動產業逐漸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動力之一,導致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逐步向較不發達城市轉移。

圖3 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總體數量時空演變Fig.3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圖5 2009—2018年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數量和新增企業數量基尼系數變化Fig.5 Gini coefficient of the number of total and newly-increase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18
從十強城市變動的角度分析城市尺度的電子信息制造業時空格局特征(表3),企業總量前十名城市占全國的比例由2009年的52.72%上升至2018年的54.16%,新增數量占比由2009 年的53.88%略微下降至2018 年的50.02%。其中,總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主要包括深圳、東莞、寧波、廣州、蘇州、溫州、惠州、中山、廈門、天津等城市,新增數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主要包括東莞、深圳、廣州、寧波、惠州、溫州、中山、江門、蘇州、梅州等城市,大部分均位于珠三角、長三角及其周邊,表明雖然產業在向中西部轉移,但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是電子信息制造業重要集聚區的性質并未發生實質性轉變,產業空間集聚明顯。其中,深圳一直是總量最多的城市,東莞、寧波緊跟其后;此外,梅州也于2016 年進入前十,這主要得益于珠三角產業轉移、對口幫扶政策。增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主要包括東莞、深圳、廣州、寧波、惠州、中山、江門、溫州等城市,相較于總量排名,東莞排名第一而深圳排名第二,反映近年來東莞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發展勢頭迅猛,一直在追趕深圳,二者的企業總量差距由2009 年的63.57%下降為2018 年15.98%。

表3 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總量和增量十強城市及占比Table 3 Top 10 cities and share of the total enterprises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2.4 城市間電子信息制造業存在明顯空間集聚特征,集聚趨勢不斷增強
結合全局及局部莫蘭指數對2009-2018年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空間相關性進行分析,選取2009和2018年2個時間截面的數據對空間關聯特征進行分析。2009-2018年,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總體數量、增量的莫蘭指數均為正值(圖6),表明區位選擇存在明顯的正空間自相關。其中總量莫蘭指數逐步上升,企業在空間上與相鄰城市的正相關程度逐漸提高;增量莫蘭指數呈波動下降趨勢,表明企業區位選擇呈現擴散趨勢。從局部空間自相關看(圖7、8),高-高集聚區集中于珠三角、長三角及周邊地區,隨著時間推移,珠三角高-高集聚趨勢增強而長三角高-高集聚趨勢減弱,表明珠三角及其周邊地區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空間集聚程度不斷上升,而長三角地區的空間溢出效應逐漸減弱,空間集聚程度下降;高-低集聚區主要為內陸中心城市,包括成都市、重慶市等,屬于近年產業轉移的熱點發展地區;低-低集聚區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區及東北地區,且集聚趨勢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強;低-高集聚區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周邊城市,集聚趨勢隨著時間推移而減弱,表明城市發展的極化效應開始惠及周邊相對落后地區,逐漸形成涓滴效應,區域不斷向協調發展的格局轉變。

圖6 2009—2018年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數量和新增企業數量莫蘭指數變化Fig.6 Moran's I of the number of total and newly-increase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18

圖7 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總體數量局部LISA集聚圖Fig.7 Local LISA cluster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圖8 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增量企業局部LISA集聚圖Fig.8 Local LISA cluster of the incremental number of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3 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區位選擇的實證分析
表4顯示,在全國層面上,企業更傾向于選址在勞動力成本較高、產業協同集聚程度高、創新能力強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而人力資本、產業市場化水平、城市對外開放水平、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對電子信息制造業新創企業區位選擇影響不顯著。其中,勞動力成本在1%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與郭建峰(2020)的研究一樣,其原因可能有:一是相比勞動力成本,企業對勞動生產率更加敏感;二是雖然電子信息制造業有向勞動力成本較低地區轉移的趨勢,但相比之下,企業在勞動力成本較高地區的成立數量、年增長率高于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三是整體上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不斷轉型升級,已由過去位于較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向附加值較高、技術密集型產業。經濟發展水平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這可能是因為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發展在經濟發達地區已經達到產品市場飽和,企業為避免趨同競爭而傾向于開辟縫隙市場。在長三角地區,企業傾向于選址在產業市場化水平高、創新能力強、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好的城市。其中,產業市場化水平在5%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在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制造業市場化水平越高越能吸引新企業的進入,主要是因為市場化水平越高的地區,越有利于企業主體高效地參與到各類合作競爭中,在開放自由的制度環境下企業間的交流能更好地促進“知識溢出”,從而實現產業的不斷發展與創新(劉君洋等,2021)。創新能力在10%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在長三角地區,在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下,企業更傾向于選址在創新水平高的城市以獲得知識溢出,從而支持企業的過程升級、產品升級等。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在10%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交通基礎設施條件好的城市對電子信息制造業的進入具有吸引力,長三角地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公路網絡完善,交通運輸便利,企業依然對傳統的區位因子——交通基礎設施條件敏感(徐維祥等,2019)。這表明不斷完善與提升城市交通基礎設施水平,有利于提升城市對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的吸引力。

表4 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的負二項回歸模型估計結果Table 4 Result of the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of the location choic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在珠三角地區,僅有勞動力成本因素通過顯著性檢驗,勞動力成本在5%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企業對勞動力成本不敏感,傾向于選址勞動力成本高的城市。珠三角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比較成本優勢促進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發展,而在經濟全球化、新型城鎮化、產業轉型升級等背景下,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問題使得珠三角原本粗放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丁俊等,2016),而從模型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目前珠三角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發展不再追求勞動力成本最低,逐漸由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為技術密集型企業。
在京津冀地區,企業傾向于選址在勞動力成本高、交通基礎設施條件好的地區。勞動力成本在10%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與珠三角類似,表明京津冀地區的電子信息制造業也在產業轉型的壓力下逐漸轉為技術密集型企業,對勞動力成本因素不敏感。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在5%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在京津冀地區,電子信息制造業傾向于布局在交通基礎設施條件好的城市。交通基礎設施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先行基礎,而環京津貧困帶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與京津冀核心地區差距較大(劉浩等,2017),因此,應加強完善京津冀地區交通基礎設施水平以提升該地區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競爭力。
在長江中游城市群,勞動力成本的系數為正,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為負,表明企業傾向于選址在勞動力成本高、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城市。由于長江中游城市群作為承接沿海地區產業轉移的排頭兵,企業對傳統生產要素如土地價格、勞動力成本敏感,傾向于選址在地價水平較低的經濟較不發達城市;同時,由于長江中游城市群以承接勞動密集型的電子信息制造業為主(鄭艷婷等,2018),企業除考慮勞動力成本外,還需考慮勞動生產率,因此導致企業偏向于選擇在勞動力成本較高的城市。
在成渝都市圈,企業傾向于選址在產業協同集聚程度高、產業市場化水平高,但創新能力較弱且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其中,產業協同集聚程度在5%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在產業轉移的推動下,成渝都市圈逐漸成為中國制造業重要集聚區,而重慶、成都2個極核城市以及綿陽、瀘州等次中心城市又是城市群內部的發展熱點區域,產業集群明顯,產業協同集聚程度高,對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的區位選擇具有較強吸引力。創新能力、經濟發展水平在10%置信水平上顯著為負,是由于成渝城市群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人均地區生產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工業仍以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為主,技術密集型、高技術產業比重較低(肖金成等,2019),企業對創新的需求不高;同時,這些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對土地價格因素較敏感,傾向于選擇土地價格較低的經濟較不發達地區。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以全國城市尺度的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為研究對象,基于基尼系數、空間相關性分析、負二項回歸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數據庫以及相關城市統計年鑒數據,對2009-2018年中國電子制造業的時空格局及影響因素進行探討。研究發現:
1)中國電子信息企業總體數量穩步上升,每年新增企業數量波動上升,整體行業發展迅速,但受國際形勢影響有所波動,產業發展存在一定不穩定性;產業逐步形成由五大城市群構成的菱形布局及“中部高地”,珠三角、長三角地區領跑,長江中游后發優勢不斷凸顯;中部及川渝地區城市發展迅速,而東北地區陷入發展困境,城市兩級分化嚴重,十強城市排名穩定,且大部分均為南方城市;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表明,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的總量及增量均存在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自身城市對相鄰周邊城市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表明,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總體和新增企業的分布情況都呈現類似特征,即高-高集聚區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及周邊地區,高-低集聚區主要為內陸中心城市包括成都市、重慶市等,低-低集聚區集中在西部地區及東北地區,低-高集聚區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周邊城市。
2)總體而言,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更傾向于選址在勞動力成本高、產業協同集聚程度高、創新能力強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而人力資本、產業市場化水平、城市對外開放水平、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對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不顯著;創新能力對企業區位選擇存在異質性,長三角地區的企業偏好創新能力高的城市而成渝地區則偏好創新能力較低的城市,可能是因為落地長三角的企業主要為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而落地成渝地區的主要為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在京津冀、長江中游地區為正效應,可能是因為京津冀地區的電子信息制造業也在產業轉型的壓力下逐漸轉為技術密集型企業,對勞動力成本因素不敏感,而長江中游城市群作為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承接地,當地勞動力成本低于沿海地區,相比于勞動力成本,企業對勞動生產率更敏感;產業協同集聚程度在成渝地區為正效應,表明在產業轉移的推動下,成渝都市圈逐漸成為中國制造業重要集聚區,產業協同集聚程度逐漸提高,吸引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的落地;產業市場化水平在長三角、成渝地區為正效應,表明兩地的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在區位選擇時對當地市場化水平較敏感;經濟發展水平在長江中游、成渝地區為負效應,這主要是中國產業轉移相關政策導向的結果;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在長三角、京津冀為正效應,表明即使在交通網絡完善的發達地區,企業依然對城市交通基礎設施水平敏感,提升城市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有利于促進產業進一步發展。
本文在城市尺度上對全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的時空格局刻畫、企業區位選擇分析等方面做出了相應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可為理解后經濟危機時期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的時空變化及機制提供參考。但基于研究的嚴謹性和學術貢獻,仍然存在一定不足,包括受限于數據完整性,無法從企業異質性角度進行分析;未將企業根據所處的生產環節劃分為上中下游企業或根據其生產滿足的需求劃分為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生產型企業、出口型企業等展開深度研究。因此,未來可以針對上述不足,進一步從企業異質性的角度對企業區位選擇進行分析,并對電子信息制造業產業鏈不同環節進行分析,從而更深入地理解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的時空格局演變。
4.2 建議
隨著產業的快速發展,電子信息制造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在國際環境壓力不斷加大的背景下,為進一步提高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發展水平,促進產業結構不斷升級以及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中、西部地區及東北地區應加強城市產業配套能力的提升。東部地區電子信息制造業產業轉移不能僅考慮勞動力成本、交通運輸成本等傳統因素,應更注重對承接地綜合制造成本的考慮。因此,為吸引東部地區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產業轉移,中、西部地區及東北地區應不斷提升自身產業配套能力、地區綜合發展水平,充分釋放消費潛力,從而實現城市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促進當地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2)位于城市群地區的城市應不斷提升創新能力、產業市場化水平、勞動生產率、產業集聚水平,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夯實產業基礎能力,發揮市場優勢,抓住5G、智能語音、計算機視覺等新興產業的市場機遇,推動中國電子信息制造業向高質量發展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