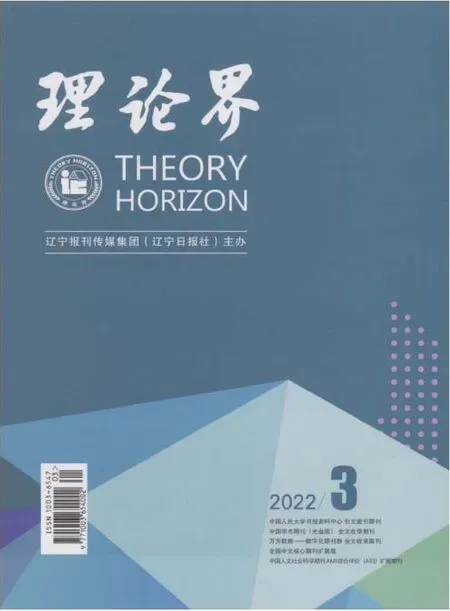日常經驗的現時化:社會秩序的凸顯與文化觀念的復現
張東贊
人類為了生存,需要通過勞動去利用自然,適應自然,經驗在此基礎上不斷積累,智慧也隨之不斷向前發展,從而能夠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一個時代中本體的存在,對存在發生的根源、發展的過程和動力有更真切的認知。〔1〕在共時層面,“常”既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角,也是人與外在世界達成的一種平衡,是社會生活中自然的狀態。奧斯卡·克勒指出,在文化本性問題上,必須做到不把穩定性歸因于人的“本性”和不把歷史歸因于人的演化,而把穩定性理解為歷史業績,這種業績只有在演變中做出來。歷史不是由眾多不可重復的奇特事物以及具有威力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構成的,而是由日常生活中許多常規習慣和相關行為模式等一系列重復性結構組成的。地方性的習俗、個人習慣各以其不同的社會生活秩序跟一個包括方方面面的系統的功能要求、法則和決策交織在一起,從而逐漸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秩序。〔2〕其中,節日與儀式化的活動將前人所傳承的經驗呈現于日常生活中的時間與空間領域。正是這些日常生活中“常”構成了人們生活的社會環境,促進了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交往與信息的傳遞。
一、節日與儀式活動:時間秩序和空間秩序
人不是反社會的獨眼巨人,更不是無私的蟻群,而是具有群居屬性的“社會動物”。現代生物學認為,人類沒有經歷所謂的“隔離期”,人類的靈長目先驅早已開發出廣泛的社會與政治技巧,促進合作的功能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是一種生存本能。公共組織在人們中間自然形成,只是不同的環境、思想和文化,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合作方式。〔3〕人只有在與他人的不斷交往中才能不斷發展與凸顯自身個性,加深自我認知。因此,趨同與遵守秩序成為人們交往的重要原則。社會秩序是交際正常進行以及群體正常運轉的重要保證,離開秩序,整個群體將會變成一盤散沙。〔4〕秩序隱藏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人們生產生活中重要經驗、智慧的積累。
從詞源義上看,“秩”和“序”的概念義反映的都是人們最基本的生活領域。《說文解字注》:“秩,積也,積之必有次敘成文理。是曰秩。”“秩”原指人們收割后禾粟儲存的一種自然形態,它所隱含的“次第”是事物自身所固有的。《說文解字注》:“序,東西墻也。釋宮曰:東西墻謂之序。堂上以東西墻為介。禮經謂階上序端之南曰序南。謂正堂近序之處曰東序、西序。”“序”所指的東西墻是古人室前階之“堂”左右兩邊的墻,作為建筑部分的“序”也就成了主客及他人登堂、依年齡或者尊卑安排座席的標記性設施,因而有了“次第”之義。“賓升,立于序內,東方。”(《儀禮·燕禮》)
在漢語語境里,“秩序”蘊含著物隨其自然,人隨其倫理而排列的意思。〔5〕人們對“秩序”的認知主要來源于自身所處的日常生活環境,是人與周圍環境互動的結果。心理學相關研究發現,認知主體在信息處理的方式上具有自動信息處理和控制信息處理兩種不同機制。〔6〕其中,自動信息處理主要是用來應對認知主體所熟知和習慣的事物,無需意識的特別注意,人們運用以往相關知識信息在不知不覺中作出反應。控制信息處理則是人們在面對比較復雜的問題時所進行的一種自覺而有意識的信息處理機制。〔7〕因此,當人們感知存在于生產生活中的某種秩序時,可以通過控制信息處理機制來對優先凸顯的文化信息進行接收、提取、對照、評價并作出一系列相關反應。時間秩序與空間秩序是群體成員在社會生產生活中所共同享有的經驗財富。法國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認為,“過去并非自然生成的,而是由文化創造的,它可以在群體成員的社會交往及文化層面以特殊形式呈現出來,從而將群體記憶擴展到社會建構的層面”。〔8〕在社會學家那里,“過去”不同于“歷史”,過去不可能完全消失,必定有證據流傳于當世,它是人們集體建構的結果,歷史始于過去不再被經驗的地方。一般來說,傳統終止,社會記憶消失后,歷史才開始。歷史不會重演,但過去卻可以重現。
節日作為群體“過去”的一種現時化載體是人們對社會生活秩序的重要認知,它將人們日常生活中昏暗的存在重新照亮,把人們日常生活中忽略而變得平淡的秩序重新擦亮,讓人們對生活的日常產生一定的審美距離,從而可以再次體驗到前輩所留下的經驗。〔8〕以乞巧節為例,乞巧節作為古代重要節日所凸顯的是農耕社會中男耕女織的生產生活方式。通過節日的周期性循環,“男耕女織”的文化觀念得到不斷傳承,從而有利于農耕文明的“穩定、和諧”。節日的周期性讓人們對時間產生一種心理期待,人們對時間有了不同的心理感知。這種期待讓節日所承載的文化觀念再次進入人們的生活之中。再如重陽節,每年農歷九月初九,人們通過一些活動來表達對天、地、祖先的感恩,同時也以求達到消災避難,長壽的美好愿望。在這種敬老的儀式活動中,孝意識以人的內時間意識的深長得以延續,內時間意識或者生存時間意識的發達,表明人與他人和世界打交道的時機化或中道化的能力。〔9〕時間秩序的凸顯對于維持群體成員之間的關聯有著重要的作用,成員之間共享的重要群體回憶有利于增強群體的凝聚力。
空間秩序表現為群體成員在生產生活中所凸顯的聯結方式。這種秩序可以血緣、宗教或者其他關系為紐帶,其實質是一種社會關系。以華夏文化中的“社“為例,“社”除了作為人們跟土地溝通的媒介之外,還是人們跟祖先聯結的重要紐帶,它作為一種公共空間是理性和宗教之間激發出來的產物。理性與宗教之間激發的辯論在某些“空間”與“既定時機”現身,在這樣的時空中決定了“相遇的規則”。“社”不僅是一個建筑,還包括在該場合中進行的某些儀式化活動。“唯為社事,單(殫)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禮記·郊特牲》)對于這些在某些特殊場合中進行的儀式性活動來說,它們具有建筑性、實體性,就像是一塊脆弱的織布,人們總是能夠予以重拆,儀式的角色就如織線一樣,將整個看似松散的絲線編織在一起,編織出美麗的布。〔10〕空間秩序存在的重要目的就是打造對話的場所。對話而不是對抗已經是被歷史所證明的有利于人類發展的行為。在一定的空間內可以保證群體成員將社會距離拉進到同一個物理距離之中,從而使個人利益導向的社會合作的親屬選擇以及互惠利他這樣兩條路徑更加容易實現。〔11〕
二、社會日常生活中秩序的凸顯與文化自覺
人類首先要成為一個“知道者”才能成為一個“決定者”,然后成為一個“行動者”。〔1〕“知道者”能夠對自己生活的時代有深刻的體會,這種體會主要是對時代價值觀念以及存在的問題有較清楚的認知,對文化乃至社會的發展規律有較清楚的把握。社會生活秩序在群體成員中的凸顯是文化自覺的重要表現形式。當人們對某種文化行為進行反思的時候,被建構的“過去”則處于被激活的狀態。根據理性在文化不同階段的作用將文化的發展分為混沌階段、蒙昧、覺醒以及自覺等幾個階段。混沌階段,人們對于周圍的主體和客體是不分的,無法從客體中分離出來,也就談不上對客體自覺的審視。人與人之間是無對關系,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是人們要處理的主要矛盾。文化蒙昧階段,人們將主體與客體進行了區分,對于未知世界往往采取一種妥協態度,進行偶像崇拜。群體與所崇拜的神祇之間存在一種休戚與共的關系,這種關系非但沒有使群體成員之間變得疏遠,反而成為一種最為牢固的紐帶。〔2〕文化覺醒階段,人們對自己的行為特點以及文化觀念有了一定的認知。在群體成員眼里,神祇并非萬能的,群體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力量。文化自覺階段,人們自覺反思自己的文化,把文化觀念的傳承作為維持群體秩序的重要手段。文化符號在群體成員之間的不斷被重復是社會生活秩序凸顯的重要表現形式。節日和儀式化的活動作為重要文化符號是文化自覺的重要突破口。在古代社會,統治者將其統治意志植入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之中,節日所凸顯的社會秩序是統治集團意志的體現,目的就是激活并維持統治者所倡導的一種社會秩序。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基于自身的努力,通過與時代與環境的交往活動來產生智慧,這種智慧又存在于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日常交往之中。
人類所具有的認知能動性以及文化自覺性使其能對文化環境進行自由選擇、適應、調整和塑造,不斷創造出新的生產和生活秩序以服務于整個群體。一般來說,文化自覺的動力主要來自群體內部的統治需要以及群體外在環境的變化等兩方面。對群體而言,文化自覺是群體經驗的進一步總結與繼承,也是一個群體凝聚力的重要保證。在文化的自覺的問題上,智者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起到連接作用,上可以影響決策者,下可以影響百姓。西漢董仲舒從同統治者的立場闡述了“一統”(疆域、政治、理論)的文化觀念,其本意是為劉氏天下的永久統治提供理論依據,卻為后世兩千余年的帝制利用儒家學說,并弱化儒家學說的人文性與實踐性開了頭。董仲舒的做法既符合了人類構建社會的根本規律,也繼承了三代以來的民心,對后世的發展有很大好處。文化自覺的作用還在于應對異質文化的沖擊,任何文化只依靠自身的調節和自發的成長是不行的,必須在自己文化基礎上吸收異質文化的精華,唯其如此,文化才能前進,國家才能發展。〔12〕任何偉大的文化,當其遭遇其他異質文化的嚴重的挑戰時,都會反思自身的文化觀念及理論,對照古今,重新闡釋,建立新的秩序以適應新的變化。經此應戰、適應,一個民族的文化將會重獲生命力,繼續前行。
自亨廷頓1993年發表《文明的沖突》以來,各國學者乃至決策者都更加關注不同文明之間沖突的可能性,而忽略了文明所面臨的挑戰。成中英將文明挑戰中所包含的正面因素稱為文明的理性,他指出,“每一種文明傳統多有其所以建立與傳承之道。此道即所謂生活與行為的價值目標與準則,也是一套思維方式與評價方式。依此目標與準則,一個族群可以生存、發展與繁榮下去;以此目標與準則,此一族群形成一種特色的文化”。〔13〕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人們更多的是享受全球化帶來的共性,而對自身文化的獨特性漸漸喪失了真切的體驗,逐漸淡忘了歷史對我們的啟發,忘記了我們文化的根源。文化的根源其實就蘊藏在日常生活之中,人們因太熟悉而不去重視。我們看世界是認識環境,只有認識環境才能更好地認識自己,我們反思自己是認識自己的歷史與根源。〔1〕文明是那些懂得文明所依賴的原則的人以及那些愿意為文明的維持、發展獻身的人努力的結果。人們只有維護大家所共同創造的規則與秩序才能守護自身的文化家園,生態家園與意義家園。〔14〕
三、儀式活動的重復性與文化觀念的現時化
社會資本是維系群體正常運行的重要手段,它是指人與人之間社會交往的密度與黏性。根據“社會資本”理論,人們通過密集、廣泛的社會交往培養參與精神、組織能力、責任意識、契約習慣乃至信任。〔11〕儀式性的活動通過聚集人群的參與從而實現不同成員的社會交往,人們之間交往的密度與黏性在這種儀式性活動的影響下得以提高。以黃帝祭祀大典為例,2020 年3 月26 日上午,庚子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鄭市舉行。大典仍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諧”為主題,主旨則為“長江黃河共戰疫,軒轅黃帝佑中華”。拜祖大典有著嚴格的規范和既定的流程,具體為:盛世禮炮、敬獻花籃、凈手上香、行施拜禮、恭讀拜文、高唱頌歌、樂舞敬拜、天地人和、圣火祈福。根據相關統計,截至3 月26 日10 時15 分,全網綜合點擊量已突破22.1億人次。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這種儀式化的空間已經擴展到虛擬的網絡空間。網絡上留言最多的則是“偉大的祖國繁榮昌盛,人類早日戰勝疫情!”〔15〕通過這種盛大的儀式化行動,群體所共享的文化觀念再一次被植入到群體成員的意識中去,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提升人們交往的黏性。人類在創造自己的時候,必須創造一種環境與一種秩序。這種社會秩序作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包含了所有的規范、價值、機構、世界觀和人生觀,人就是在這種環境與秩序中生活和活動的。文化的這種獨特性與約定俗成性相對于個體而言就會變成隱藏不可見的東西。〔8〕正是這種隱藏不可見的東西引導著群體成員有條不紊地生活,為群體成員營造合適的社會環境。在人們自己所創造的社會環境中,群體所共享的文化觀念就成為成員之間交往的黏合劑。當這種共享的文化觀念不斷復現于群體成員之間時,成員之間交往的密度就可能進一步增高,從而提升群體的社會資本。
文化觀念的復現客觀上創造出一種文化空間,讓生活其中的成員不斷接收該環境所傳遞的相關文化信息,在形式上打破了時間的一維性,讓時間秩序和空間秩序找到了很好的結合點:重復。重復不僅使儀式活動再次呈現,還讓文化觀念變得更加清晰。人們的生活也因此變得有章可循,有效降低了生活中的一些不確定感。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埃文思-普理查德在《努爾人》一書中,論述了努爾人的年齡等級制度,即每四年一群新的成年男子就要參加一個入會儀式,埃文思-普理查德將年輕人的這種進步稱為“結構時間”,對于這種結構時間對個人的影響,他描述道:“季節和月歷的變化一年一年的重復著,以至于站在任何一個時間節點上的努爾人都會知道在他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樣子,并能預測并計劃他以后的生活。一個人結構性的生活好像已經被安排好了,有秩序地進入不同的時間段,以便他可以預見他在這個社會體系中注定要經歷的地位的整體變化。”〔16〕重復是人類生存的一種重要技能,它讓人們在其熟悉的領域取得成就感,并且避免在同一事務上浪費時間,從而可以騰出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新領域。〔8〕同時,重復還可以避免人們的行動路線無限延長,通過重復,人們的行為模式再一次得到辨認,從而被當作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認同。
人們周期性的行為活動把一個經過群體反思過的“過去”復現出來,并保持一種活躍的狀態。作為文化觀念和文化符號的聯接部分,并非所有文化行為都凸顯一定的文化觀念。按照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頻率,文化活動大體可以分為習俗性、偶連性和循環性等幾種類型。〔17〕對于習俗性活動,人們對文化信息的處理主要采用自動信息處理機制,即個體聽任情緒反應并按照慣例行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往往對內部與外部的諸多信息視而不見。行為活動背后的文化觀念處于一種未被激活的狀態。偶連性的活動也只有在把群體的活動作為觀察對象時,才能發現其中所反映的文化觀念。梁漱溟曾經明確指出國人在紀律習慣方面上的問題,“在開會場中,中國人還當在他家里一樣,耳目四肢只為其個人所用,不曾意識到團體的要求,妨礙公務而不自知,更為習見不鮮”。梁漱溟指出:“習慣是環境的產物,這與其生活的環境息息相關。”〔18〕在面對該類文化活動所負載的文化信息時,認知主體往往采用控制信息處理機制。在這個過程中,認知主體實現了從群體無覺知的狀態轉向群體有覺知的狀態,即群體成員對于當下的經歷和現實給予更多的意識和關注,是一種積極主動的認知方式。〔7〕
重復使文化觀念在時間層面上的疊加得以在空間上進一步凸顯,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文化觀念的鮮活性。在沒有文字的社會中,重復是文化意義傳承的重要手段。在有文字的社會,節日和儀式性活動相對于文本來說,仍然具有其自身優勢。一般來說,文本所傳承的文化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往往要借助注釋者的注釋才能復活,這往往讓文化觀念囿于狹小的范圍,而一旦文本停止使用,它便不再是文化概念的載體,而變成了文化觀念的墳墓。對于表音文字而言,有些文本隨著語音的變化而無法解釋,尤其是當大量不計其數的文本出現超出了一個時代所能記憶和銘記的限度。有些文本將被塵封在資料庫而變成了空殼,有些文本因無法解釋而成為陌生的、遺忘的角落,文字所記錄的文本幾乎與未知的東西沒什么兩樣。〔8〕與文本不同,節日和儀式性活動具有廣泛的群體參與性。
節日側重時間秩序,華夏文化傳統節日的產生、發展、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們農耕社會中具體實踐的感悟及心路歷程。華夏文化的傳統節日經歷了由虛到實、從嚴肅到娛樂化的過程,這與人們重視當下的現實生活的價值理念分不開。儀式活動側重空間秩序的凸顯。對于儀式活動來說,它的本質就在于還原曾經有過的社會秩序,并將其重現。對于沒有文字的社會來說,每一次儀式的舉行都與前一次吻合,由此在一定的空間內形成了時間循環往復的觀念。〔8〕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的行為活動隱含著測量的過程。時間的循環往復給人們回顧過去提供了參照點。發生在過去某個時間的事件就有可能成為人們比較參考的對象。當不同的“過去”充當其他事件的參照點時,這些充當參照點的“過去”就由人們建構成一種秩序,同時也體現文化的發展歷程。
四、社會生活日常秩序:“過去”經驗的重要表現
文化對感知的影響體現在客觀實際轉換為經驗實際的過程。魏斯頓(D.Westen)在心理感知與客觀實際之間的關系上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自然賦予我們絕妙的感官樂器,把雜亂的噪音創制為美妙的音樂,而經驗則教導我們如何彈奏。”〔19〕在這里,經驗將生活中事物賦予一定的秩序,而不是雜亂無章的東西的拼湊。文化對感知過程的影響可以從感知的選擇、組織和闡釋三個階段來看。選擇是一種本能的適應性活動,人們在生產生活中依據環境的變化選擇不同的生產生活秩序。比如,從采集游牧階段發展到農耕社會,人們對于榜樣標準就要進行重新調整:從勇敢武力變為勤奮協作。這種選擇不是偶然的,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經驗的總結。在游牧社會里,崇尚武力會帶來更多的食物,但是在農耕社會崇尚武力則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的因素。在中國的傳統觀念里則有“止戈為武”的闡釋。文化對感知組織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群體成員所共同享有的“過去”往往會成為人們對當下事物感知的參照,并把當下事物納入其過去的經驗之中形成群體記憶,進而形成一定的社會生活秩序,所以人們的生活中總會保留過去的影子。人對自我的經驗總是經由他人而獲得的,是個人對群體中他人的社會屬性的認同而進行自我反思,正如我們如果不借助鏡子就幾乎無法觀察自己的臉頰一樣。這種反射—投射中包含著意識與反思結構,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完成對過去經驗的一種體驗。〔8〕
記憶總是由社會的范疇以及我們無意識地投射在自己的記憶中的東西共同決定,個人記憶無法脫離群體,這些社會范疇決定了記憶的選擇與交流。人們不論對節日還是儀式性活動之間信息的交互傳遞都不是個人情感純粹的感知,而是過去的群體記憶與當下社會環境共同作用于個人的結果。〔20〕文化對闡釋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群體成員基于自己的核心觀念對所感知的事物進行闡釋,優先凸顯某些觀念,并試圖通過一些手段將這種觀念傳承下去,從而繼續維持群體秩序,保證組織的正常運行。認知主體在實際生產生活中習得的文化意義好比過濾器,可以將客觀實際折射為經驗實際。〔6〕為更好地利用過去的經驗,人們還要將這些經驗實際進一步轉化為生活秩序,最后將這些生活秩序以一定的形式固定并傳承下去。奧爾森(M.Olsen)指出,社會結構的存在需要某種程度的秩序化,這種秩序化包含個體、社會和文化三個層面。其中,個體的秩序化是使個體在認知、情感等在內的心理過程具有連貫性和穩固性,從而增強個體的安全感,降低個體在面臨陌生環境時的恐懼感。社會秩序化則是群體成員在交往過程中共同享有文化觀念、群體回憶以便形成帶有模式特征的行為。同時,對文化行為進行共同的闡釋,享有并傳承為群體所認同的生產生活秩序。〔21〕
五、余論
全球化是一種新知識的象征,本身也是經驗文化,它給全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情況,也讓不同文化接觸變得更加頻繁。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風險社會理論的倡導者烏爾里希·貝克指出,全球化的發展把風險帶到了世界各地。如果說階級社會的推動力可以用“我餓”來概括,而在全球化的風險社會中集體性格則可以用“我怕”來概括。〔22〕解除群體的恐懼心理,文化是必由之徑。認清本民族文化的特點,掌握文化發展的趨勢,繼承和傳承優秀的傳統,從而保持群體自身的穩定性,可以有效降低社會的風險性。只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觸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與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原則。我們必須喚醒過去的回憶,喚醒頂天立地的良知精神力量,從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