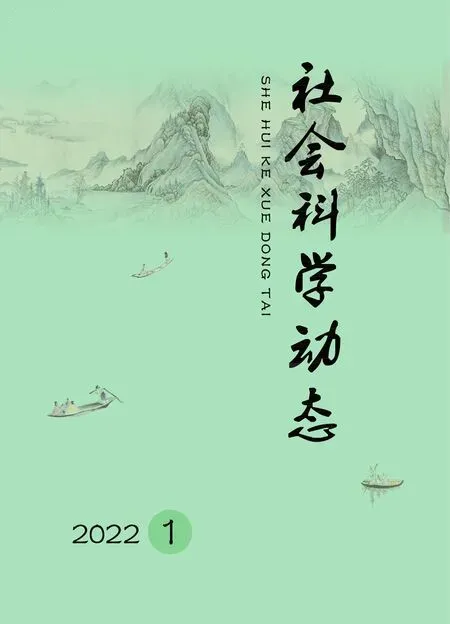大智眼界 大愛情懷
——試論馮天瑜先生的湖北武漢區(qū)域歷史文化研究
涂文學
武漢是一座建城歷史悠久、空間布局獨特、極富個性魅力的城市。在這座由鋼筋水泥搭建起來的近代歷史舞臺上,幾乎每隔幾年都要上演一出驚天動地的歷史活劇。武漢是一座充滿活力的商業(yè)大都會, “十里帆檣依市立,萬家燈火徹宵明”,九省通衢,萬商云集, “貨到漢活”,明清為 “天下四聚”之一,晚清更被外人譽稱為 “東方芝加哥”。然而長期以來,武漢的這種歷史地位被嚴重低估,至少在史家的眼中和筆下是如此。民初湖北方志大家王葆心在其所著 《續(xù)漢口叢談》中就不勝感慨:“近日有為 《上海小史》者,其旨則專詳見今。因淞滬大埠,自來紀述良多,且云間一郡,明季清初,此類記鄉(xiāng)土里俗之書尤多,美備之余,無庸賡述。漢口則記者寥寥。”①時至當下,專力于武漢歷史與文化研究的 “學院派”仍然寥如晨星,遠不如上海、廣州、北京甚至天津、成都、重慶的本土城市研究學者之眾,著述之豐。但值得慶幸的是,在為數(shù)不多的關(guān)注武漢城市歷史與文化研究的學者中,能夠有馮天瑜先生這樣的文史大家,以造福荊楚鄉(xiāng)梓、復興武漢文化的歷史使命感,40 年甘之如飴地奉獻著自己的學術(shù)智慧,獨樹一幟引領(lǐng)湖北武漢區(qū)域歷史文化研究的方向,為湖北武漢區(qū)域史研究積累了豐厚的學術(shù)資產(chǎn)。
一、事件史:工業(yè)化、城市化、城市現(xiàn)代化與辛亥革命 “城市起義”
馮天瑜先生對湖北及武漢區(qū)域史研究肇始于辛亥武昌起義的研究。
辛亥革命首發(fā)于武漢,這場改寫中國乃至亞洲歷史的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由于是 “唯物史觀的一個絕好的例證”, “明白地指出了將來的中國的去向”,并且 “因為濃郁的地方色彩,對熱愛鄉(xiāng)邦的人們更有著特別的魅力”,因此引起馮先生的 “十二分留意”,從此便有了持續(xù)40 年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史研究。對此,馮先生在1985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辛亥武昌首義史》的序言中曾有詳細披露: “這段史事濃郁的地方色彩,對熱愛鄉(xiāng)邦的人們更有著特別的魅力。三烈士紀念碑、彭劉楊路、首義路、起義門、閱馬廠湖北軍政府舊址、拜將紀念碑、蛇山頭黃興銅像等首義勝跡,是我們這些 ‘老武昌’從幼年時代起便經(jīng)常留連徜徉的處所;至于首義先烈的故事,連同其中包蘊著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則通過前輩的講述和書本上的文字,如同 ‘潤物細無聲’的春雨,滋潤著我們的心田。正是這一切,使我形成了對武昌首義的惓惓情懷,它驅(qū)使自己從致力史學工作之始,就有意研究這段悲壯而又曲折多致的歷史。”②
通覽馮先生關(guān)于辛亥革命研究的系列成果,我們發(fā)現(xiàn)他對于武昌首義的研究有著獨特的視角,作為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歷史事件,馮先生理所當然地對事件始末進行了詳實系統(tǒng)的研究,其中對某些史事的細節(jié)還有精細獨到的考證甚至精彩形象的描述。但我們感興趣的是馮先生以辛亥武昌首義為基點,以 “長時段” (地理時間)和 “中時段” (社會時間)視野契入湖北武漢區(qū)域史、經(jīng)濟史、社會史及文化史的研究。即通過晚清湖北武漢區(qū)域經(jīng)濟、社會、文化狀貌的述寫,不僅探討了辛亥革命在武昌首義并首勝的背景和原因,而且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作為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 “城市起義”的性質(zhì)。區(qū)域史與事件史的綜合、交叉研究視野,賦予馮先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歷史縱深感和學術(shù)理論高度。他認為晚清已經(jīng)進入了傳統(tǒng)社會的總結(jié)時期,此時專制社會出現(xiàn)了解體的征兆,近代社會也已曙光微露,故而研究辛亥革命不應拘泥于事件本身,還應關(guān)注到當下所處的歷史時期,城區(qū)風貌、社會形態(tài)、文化狀貌等時空背景因素,進而發(fā)現(xiàn)推動辛亥首義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形成與發(fā)展的誘因。通過漢口城市空間形態(tài)的變化、武昌城市空間形態(tài)的拓展、漢陽城市空間形態(tài)的發(fā)展,勾勒出近代武漢城市空間演變的特征;他不僅描繪出了武漢近代都會的景觀與樣貌,更通過城市的工業(yè)化發(fā)展及現(xiàn)代化進程,獨辟蹊徑地提出 “城市起義”概念,創(chuàng)見性的揭示出 “工業(yè)化” “城市化”道路的發(fā)展路徑,促成武昌首義事件發(fā)生的內(nèi)在因果聯(lián)系。
事實上,早在20 世紀70 年代末期,馮先生已將對于辛亥革命的單一事件研究,轉(zhuǎn)而邁向更深層次的多元環(huán)境探討,即從區(qū)域史的角度切入并展開,著重關(guān)注 “首義之區(qū)”的城市經(jīng)濟、社會文化及背景特征,探尋辛亥革命事件背后更為深層次的歷史文化與空間交錯之影響③。在 《湖北成為辛亥革命 “首義之區(qū)”原因初探》一文中,馮先生指出,辛亥革命絕非 “始于意外”的偶然成因,而是“先聲奪人”的歷史進程之必然結(jié)果。這一觀點駁斥了對于 “湖北地處形勝,控扼九省,故登高一呼,應者云集”的論調(diào),凸顯出區(qū)域特征的重要性。湖北武漢在內(nèi)陸地區(qū)能在中國早期現(xiàn)代化進程中 “先聲奪人”,既與近代漢口被迫開埠開放、外力楔入有關(guān),同時更得益于張之洞 “湖北新政”使湖北武漢成為工業(yè)化、城市化、城市現(xiàn)代化獲得長足發(fā)展,從而為辛亥革命爆發(fā)創(chuàng)造思想與論和經(jīng)濟社會條件。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英、法、俄、德、日、美等國相繼侵入湖北,開商埠、辟租界、設(shè)銀行、辦工場、辟航道、筑鐵路,逐步控制湖北武漢經(jīng)濟、金融、交通等,改變了武漢地方社會固有的社會經(jīng)濟生態(tài),這個深處堂奧、風氣古樸的內(nèi)地省份,一變而為 “商賈輻輳,白皙人種聯(lián)翩并集”的列強 “勢力圈競爭之中心點”, “鎖國時代之楚”,變成 “門戶洞開之楚”,湖北的社會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動。④
馮先生敏銳洞悉道:辛亥前夕的湖北,不僅是黨人慘淡經(jīng)營的基地,也是清廷統(tǒng)治脆弱的一環(huán)。正是由于地處 “九省通衢”的獨特優(yōu)勢,加之無獨有偶地成了 “三不管”地帶,才使西方勢力順理成章地大舉滲透湖北地區(qū),而西方勢力滲透湖北武漢的結(jié)果,便是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武昌首義。對此,馮先生有深刻剖析:
從19 世紀中葉至辛亥革命前,帝國主義列強對湖北無孔不入的滲透,給人民帶來的苦難當然是十分深重的,與此同時,也造成了西方殖民者所不曾料想到的結(jié)果。
世界上最古老最堅固的帝國,因受了英國資本家紡織品的影響,八年來已處于社會革新的前夜,這種社會革新對于文明無論如何應有非常重大的結(jié)果。我們歐洲的反動派,在最近的將來勢必向亞洲逃跑,一跑跑到中國的萬里長城,跑到這個最保守的堡壘的門口,那時候,安知他們在那里不會碰到“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大字呢?馬克思、恩格斯在19 世紀中葉對于資產(chǎn)階級革命不可避免地將在中國發(fā)生的天才預見,被中國近代歷史,特別是辛亥革命史所證明。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這場革命是在西方列強經(jīng)濟侵略的刺激、影響下發(fā)生的。特別引人注目的,恰恰是列強滲透的中心之一——湖北,成為辛亥革命的 “首義之區(qū)”。
這是歷史的辯證法所使然!⑤
城市化的進程是一個蛻變的過程,往往伴隨著痛苦的記憶與屈辱的歷史。中國民族資本在甲午戰(zhàn)爭后出現(xiàn)了一個短暫的高峰,此時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活動正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在馮先生的詮釋中,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初具規(guī)模的地區(qū),一是江浙,二是廣東,三是湖北。作為首義之區(qū)的武漢,在19 世紀末,其現(xiàn)代經(jīng)濟產(chǎn)生、成長具有自身的特點,這便是官辦發(fā)展速度快、企業(yè)規(guī)模大、投資額度高、技術(shù)設(shè)備先進、自成體系、工人數(shù)量多。在官辦工業(yè)和外資企業(yè)的帶動刺激下, “湖北作為一個深處堂奧的內(nèi)地省份,自然經(jīng)濟開始解體,并隨之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新的經(jīng)濟形勢”⑥。商品市場的擴大、勞動力市場的出現(xiàn)以及貨幣財富積累,民族資本形成。盡管由于地域與時代的關(guān)系,對于武漢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經(jīng)濟實力不能做過高估計,但是“由于漢口作為一個傳統(tǒng)商業(yè)社會廣泛存在的商人階層,城市功能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之后新加入的工業(yè)資本家、金融資本家、自由知識分子和大量的產(chǎn)業(yè)工人等,一個具有現(xiàn)代城市共同體意識的新型市民階級萌生了,他們在推動城市轉(zhuǎn)型,參與社會革新,反對專制政治,推動民主進程方面發(fā)揮了主導作用”⑦。近代工業(yè)與民族資本大發(fā)展的區(qū)域背景,加之張之洞 “種豆得瓜”辛勤耕耘的結(jié)果,新興階級和知識階層與具有近代色彩的軍隊交相輝映,清朝最后的命脈也就被革命黨人攥在了手里。誠如馮先生所言,辛亥革命的爆發(fā)與武漢所處的區(qū)域環(huán)境及歷史文化息息相關(guān),湖北革命黨人具有與清軍主力一決雌雄的實力,也絕非偶然。
當現(xiàn)代化的車輪碾過清朝腐朽的軀殼時,工業(yè)化和城市化也隨之展現(xiàn)其偉力與魅力。武昌首義終于在清朝統(tǒng)治薄弱的環(huán)節(jié)但卻是工業(yè)化、城市化最發(fā)達的近代都會——武漢爆發(fā)。正是這發(fā)達的都會賦予作為 “城市起義”的辛亥革命不同于中國以往任何革命和起義的階級特性和時代特性。馮先生對辛亥武昌首義 “城市起義”的定義精準而獨到,對區(qū)域工業(yè)化、城市化及城市現(xiàn)代化與辛亥武昌首義“城市起義”之間因果關(guān)系的探析系統(tǒng)且深刻。無論是從武昌起義發(fā)生背景,還是革命方式、革命主體,武昌首義都可堪稱典型的近代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城市起義,或曰城市市民革命。城市起義首先必須發(fā)生在城市,而且是近代工商業(yè)較為發(fā)達,新的市民階級較為成熟的城市。辛亥革命中,具有代表性的兩次起義是廣州起義和武昌起義,而廣州和武漢都是近代以來開埠通商后,現(xiàn)代工商業(yè)得到較大發(fā)展,城市功能現(xiàn)代轉(zhuǎn)型較為充分的城市。城市革命的目標在于建立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使包括資本家在內(nèi)的廣大市民階級獲得管轄治理城市乃至參與國家政治事務的權(quán)利。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在革命的方式上,城市中的市民階層既可選擇和平改良如游行罷工、議會談判、協(xié)商調(diào)停、和平請愿等,也可采取武裝起義;既可以選擇君主立憲,也可以建立民主共和。改良與革命、立憲與共和之間并無實質(zhì)區(qū)別,都只是資產(chǎn)階級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已,在近代中國,上述手段都曾被城市資產(chǎn)——市民階級采用過。曾經(jīng),立憲派的和平運動氣勢不輸革命派,李提摩太評價資政院彈劾軍機大臣: “吾輩居中國四十年,一旦得目睹此景象,殊堪驚訝。吾輩今日所見者,與前日所想望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土耳其、葡萄牙之兩大革命尚不能比。”⑧但當現(xiàn)實粉碎了他們的幻想后,最終都主動參加了革命,選擇了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激烈形態(tài)——城市武裝起義。此外,革命的主體必須是城市市民階級,包括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小商販、城市貧民和資產(chǎn)階級等,武昌起義的領(lǐng)導和參與者雖然是文人、士兵與下層軍官,也就是所謂 “秀才造反”。新軍這個群體實際上是當時城市市民階級下層的集合體,革命爆發(fā)后,城市市民階級上層——商人、工業(yè)資本家、金融資本家以各種形式積極參與、支持革命,形成強大合力。武昌起義作為一場現(xiàn)代城市市民革命與傳統(tǒng)的農(nóng)民起義相比,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梁啟超嘗言: “暴動事業(yè),無論在何國,無論在何時,其必出于嘯聚,必為無機的群眾。”⑨但作為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城市起義的武昌首義,絕非無組織無準備的 “嘯聚”,其參加者也絕非 “無機的群眾”,而是有著明確的革命理論綱領(lǐng)和建立民主共和的目標,有著較為嚴密組織體系和行動路線圖,不是舊式會黨或梁山泊那樣的綠林山寨,而是具備現(xiàn)代政黨性質(zhì)的革命團體,其維系成員的紐帶不再依靠江湖義氣、血緣關(guān)系,而是依靠實現(xiàn)民主共和的革命信仰,發(fā)動和號令起義的也不是簡單迷信的揭帖、口號,而是民主、自由、人權(quán)等近代資產(chǎn)階級啟蒙思想主張。武昌起義是在留學生、革命黨人長期艱苦的思想啟蒙和輿論發(fā)動下爆發(fā)的,這些革命者推崇法國大革命,鼓吹暴力革命,宣揚民主自由,服膺天賦人權(quán),辛亥革命前的武漢,儼然已是新文化運動中心和新思想策源地。
從早年與賀覺非先生合著 《辛亥武昌首義史》中對武昌首義爆發(fā)背景和原因的探討,馮先生就指出: “這一切則無法用 ‘偶然性’一言以蔽之。當我們考查19 世紀末葉以來湖北出現(xiàn)的新的經(jīng)濟土壤、新的社會階級和社會思潮,追溯湖北革命黨人在長達十年的期間,遵循孫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lǐng),在鄉(xiāng)邦所作的英勇而堅實的努力,便會發(fā)現(xiàn),武昌首義決非一只從云端掉下來的幸運之果。”⑩到2011年辛亥革命100 周年推出洋洋80 余萬言的《辛亥首義史》 (與張篤勤合著),提出辛亥武昌首義為“共和旗幟下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義”的新論斷,他指出: “處于中國內(nèi)陸貿(mào)易最高地位的漢口,兼具中心都會、地區(qū)都會、地區(qū)城市、較大城市的功能。在這樣的近代中心城市爆發(fā)的辛亥首義,在三個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上開創(chuàng)先機: (一)以武裝暴動擊碎兩百余年清王朝的統(tǒng)治機器,終結(jié)沿襲兩千余年的專制帝制。 (二)以湖北軍政府建立和 《鄂約法》頒布,昭示了近代意義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樣。 (三)辛亥武昌起義、湖北軍政府成立舉起取代清政府的旗幟,而多數(shù)省份也紛紛宣布 ‘易幟獨立’,導致中央集權(quán)的清朝瓦解……這些既破且立的環(huán)節(jié),都留下種種未竟之業(yè)和令人嗟嘆的遺憾,然其首創(chuàng)性價值卻可昭日月。20 世紀初葉發(fā)生在東方大國的辛亥革命,與17 世紀的英國革命、18 世紀的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戰(zhàn)爭、19 世紀日本明治維新,在推動社會近代轉(zhuǎn)型方面的勞績,是可并輝千秋。”?馮先生經(jīng)過筆耕不輟近40 載的研究與沉淀,對辛亥首義的革命屬性尤其是區(qū)域工業(yè)化、城市化、城市現(xiàn)代化與作為 “城市起義”的辛亥首義之間的因果互動有了質(zhì)的升華。跟隨馮先生的腳步,可以看出近代武漢從漢口開埠到武昌首義及武漢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城市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等歷史演進的根本路徑,而城市起義 “發(fā)生在武漢這一較為后起的腹地都會。這次城市起義從醞釀、爆發(fā)和取得相當程度的成功,皆植根于近代城市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積淀”?;“城市化是現(xiàn)代化的基本內(nèi)涵之一。現(xiàn)代城市借助工業(yè)文明的偉力,通過現(xiàn)代社會系統(tǒng)將人群組織起來,使個體的、分散的人的能量得以回合、放大與升華。”?“作為九省通衢的武漢,自19 世紀中葉以降,從中古式鎮(zhèn)崛起為華中首屈一指的現(xiàn)代都會,聚集了由機器工業(yè)、現(xiàn)代商業(yè)及交通、新式學堂和現(xiàn)代傳媒組合成的巨大物質(zhì)——精神力量。人稱辛亥首義為一次 ‘新軍起義’又稱其為一次 ‘城市起義’,它所憑借的正是現(xiàn)代都會聚集的巨大能量。”?因此,工業(yè)化、城市化及城市的現(xiàn)代化是辛亥革命之因,而武昌首義推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又是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結(jié)出的時代之果。
二、人物傳:時勢造英雄與英雄造時勢
馮先生持續(xù)40 年的區(qū)域研究除了 “事”——辛亥武昌首義外,另一個關(guān)注點便是 “人”——張之洞。一人一事,構(gòu)成其湖北武漢區(qū)域史研究的兩大側(cè)翼。
張之洞是集晚清重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為一身的影響中國近代歷史的關(guān)鍵性人物。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為人生之 “三不朽”,而張之洞恰巧在此 “三不朽”方向均有所建樹。身處中國近代“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轉(zhuǎn)型動蕩時代,張之洞 “立德”衛(wèi)道,忠君愛國,清廉自守,堅守傳統(tǒng)儒學道德的最后底線;作為學者和思想家的張之洞,學養(yǎng)厚重,思想深邃,其 《書目問答》 《勸學篇》皆為傳世佳構(gòu),他提出的 “中體西學”學說, “匯通中西、權(quán)衡新舊”,成為近代國人處理中西文化關(guān)系的指導思想和基本遵循;作為政治家的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施行 “湖北新政”,建工廠、修鐵路、興文教、練新軍、辦市政,治鄂18 載,使武漢由一個傳統(tǒng)政治軍事中心和以內(nèi)部循環(huán)為主的商業(yè)市鎮(zhèn)崛起為富有國際影響力的近代大都會。
馮先生對張之洞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他出版的三部張之洞傳記中,一是1985 年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張之洞評傳》,二是1991 年與何曉明合著、由南京大學出版社納入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 《張之洞評傳》,三是2020 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張之洞評傳》。從這三部關(guān)于張之洞研究成果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馮先生對張之洞研究的前后側(cè)重,即前期側(cè)重于對作為思想家張之洞的研究,近些年則在保持對張之洞思想和學術(shù)研究的同時,加重了對其作為政治家——洋務殿軍張之洞 “湖北新政”的研究分量,凸現(xiàn)張之洞督鄂18年對湖北武漢區(qū)域現(xiàn)代工業(yè)化、城市化的重大貢獻,尤其是 “湖北新政”的 “種豆得瓜”,導致辛亥革命爆發(fā)的客觀效應。這種前后變化,我們從1991 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張之洞評傳》和2020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張之洞評傳》的章節(jié)安排即可一目了然。南大版 《張之洞評傳》 “生平篇”共8 章,其中僅第五章 《“勞歌已作楚人吟”》評述了張之洞督鄂事跡;而湖北人民版的《張之洞評傳》 “生平篇”為9 章,較南大版僅增1章,但記述張之洞督鄂章節(jié)卻增加至3 章,占了生平篇1/3 的篇幅。
在最新版的 《張之洞評傳》中,馮先生系統(tǒng)梳理了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施行 “湖北新政”的種種實績,并給予實事求是的客觀評價: “總督湖廣、暫署兩江的18 年間,張之洞全面展開其洋務事業(yè),成為洋務派晚期的最大代表。他慘淡經(jīng)營的‘湖北新政’,以創(chuàng)實業(yè),練新軍,興文教,造成一種聳動朝野視聽的格局,產(chǎn)生全國性影響,清末各省推行 ‘新政’皆取法于湖北。張之洞的勢力亦‘由武昌以達揚子江流域,靡不遍及’”。?
關(guān)于興辦實業(yè),馮先生指出: “19 世紀末20世紀初,張之洞在湖北興辦的幾家近代化機器工廠,就規(guī)模和設(shè)備水平而言,都在國內(nèi)居領(lǐng)先地位,甚至可以與外國企業(yè)一爭雄長。如漢陽鐵廠所用高爐和貝色麻煉鋼爐,其技術(shù)性能都屬19 世紀晚期的上乘設(shè)備,連當時的東方強國日本尚不能望其項背。”?在開拓鐵路和電信事業(yè)方面,盧漢鐵路的修建,幾乎與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經(jīng)歷共始終。該時期張之洞在慈禧的支持下,成長為與李鴻章相頡頏的洋務派又一巨頭。?張之洞積極籌設(shè)電報局,主要出于政治軍事上的需要,在客觀上對民間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也有助益。在武漢三鎮(zhèn)設(shè)置電話線,1900 年在武昌、漢口設(shè)電話局,1904 年成立電話公司,是為全國官督商辦電話的創(chuàng)始。在興辦機器工業(yè)方面,漢陽鐵廠的修建雖然屢經(jīng)周折,走了許多彎路,但終于在19 世紀90 年代建設(shè)成中國以至亞洲第一家現(xiàn)代化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日本的第一家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1901 年才開始投產(chǎn),比漢陽鐵廠晚了7年。 “當時的西方人和中國官方站在不同角度都意識到:建成現(xiàn)代化鋼鐵聯(lián)合企業(yè),對增強中國的國力具有重大意義。”?除了漢陽鐵廠外,創(chuàng)辦軍事工業(yè)——湖北槍炮廠,是張之洞督鄂的另一政績。“湖北槍炮廠于光緒十六年 (1890)在漢陽大別山(龜山)北麓動工興建,光緒三十年 (1904)改名湖北兵工廠,光緒三十四年 (1908)定名漢陽兵工廠。這是中國第一座具有完備系統(tǒng)的大規(guī)模軍火工廠, ‘植中國軍械之初基’……湖北兵工廠就其規(guī)模和技術(shù)水平而言,確乎在當時居全國軍事工業(yè)之冠, ‘較津局既逾數(shù)倍,較滬局亦復加多’。”?張之洞創(chuàng)辦的湖北紡織官局 (紡織絲麻四局),雖然在資金、設(shè)備、管理諸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但卻起到了 “略分洋利”的作用。就規(guī)模而言,武昌織布局為中國最大織布廠之一,名列全國紡織廠前茅。張之洞為了發(fā)展棉紡業(yè),力圖用長絨優(yōu)質(zhì)洋棉取代短絨劣質(zhì)土棉,曾進口一批美棉在武昌附近種植,可惜未能得到推廣。他在湖北開設(shè)的繅絲局為華中地區(qū)最大的機器繅絲廠。對于張之洞興辦之官辦企業(yè),馮先生歸納了六大特點:一是發(fā)展速度快,二是企業(yè)規(guī)模大,三是投資額度大,四是技術(shù)設(shè)備先進,五是自成體系,六是體制陳舊,經(jīng)濟效益差。?在充分肯定張之洞興實業(yè)的巨大成就的同時,馮先生也花了不少筆墨直陳弊端,如漢陽鐵廠在工廠選址、煤鐵資源勘察開采等失誤,他認為,“并不僅僅是由張之洞主觀指導失當造成的,也與落后、守舊的客觀環(huán)境帶來的障礙直接相關(guān)。”?張之洞以防止權(quán)益外漏為由興辦漢陽鐵廠, “然而,實施的結(jié)果卻是一再虧本。”究其原因, “大而言之,當然要歸結(jié)于西方列強經(jīng)濟侵略和宗法社會、專制政治對近代工業(yè)的桎梏。正如時人評價的:‘官督商辦之工業(yè)幾乎無不失敗,即其變相之商辦工廠,因官習未除亦百弊叢生,鮮克生利。其失敗原因有二:一、信任官紳萬能,不重專門人才;二、依賴外人過甚,工程大權(quán)遂為外人所專攬。’但這種總體性的原因,尚需通過對張之洞一手操辦的鐵廠、槍炮廠、布紗絲麻四局的內(nèi)部情形進行考察方能具體理解。”?這些具體原因,馮先生歸納為: (1)以官府衙門方式管理大機器生產(chǎn); (2)對洋款、洋員依賴日益加深; (3)工人生產(chǎn)和生活狀況悲慘等等。種種原因中,馮先生著重強調(diào)了兩點。一是以官府衙門思維和作風興辦與管理近代機器大工業(yè),往往違背市場規(guī)律。以紡織工業(yè)為例, “歐美各國走向工業(yè)化,大都是從發(fā)展輕紡工業(yè)開始積累資金的,但清末中國,由于統(tǒng)治者 (包括張之洞這樣的洋務大吏)迫于國防危機,違背經(jīng)濟客觀規(guī)律,優(yōu)先發(fā)展洋務軍工,輕紡工業(yè)一再為軍工輸血,套上沉重的枷鎖,以至步履維艱,奄奄一息。其結(jié)果不僅阻礙紡織業(yè)的發(fā)展,而且導致整個工業(yè)因資金匱乏、比例失調(diào)而無法正常運行,而布紗絲麻四局招商承辦后,便 ‘起死回生’,欣欣向榮,誠如 《湖南實業(yè)雜志》所指出的: ‘鄂省紡紗、織布、繅絲、制麻四局,前因官辦虧耗,租與粵商韋子封 (韋應南)之應昌公司承辦,獲利甚巨。’該公司接辦四局后,每年向政府納租銀10 萬兩。這個對比昭示了一條真理——宗法帝制的政治結(jié)構(gòu)是發(fā)展近代工業(yè)的大礙,這些實業(yè)項目的興建過程和內(nèi)部狀況,相當?shù)湫偷恼宫F(xiàn)半殖民地中國官辦近代事業(yè)的特征”。?“張之洞興辦實業(yè)的坎坷經(jīng)歷告訴人們,病入膏肓的專制官僚政治,是中國建立近代化大機器工業(yè)的制約和障礙。”?二是 “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的工業(yè)化運動只引進技術(shù)和人才而忽略先進管理制度和現(xiàn)代化理念,產(chǎn)生出官辦及官督商辦企業(yè)成了怪誕的混合體——技術(shù)設(shè)備是現(xiàn)代化的,經(jīng)濟體制則是衙門式的。 “二者極不協(xié)調(diào),死的拖住活的,過去的拖住現(xiàn)在的和未來的。從西方引入的先進生產(chǎn)技術(shù)無法施展其威力,生產(chǎn)一直不景氣,至20 世紀初葉,更走到窮途末路,或停產(chǎn)倒閉,或交商承辦,幾乎一一中道夭折。”?張之洞總督湖廣、暫署兩江的18 年 (1889—1907),興實業(yè)是其洋務新政的基礎(chǔ)性工作,此間他的實業(yè)建設(shè)以官辦為主,兼及襄助民營工商業(yè),均取得聳動視聽的成就,特別是創(chuàng)建的漢陽鐵廠 (后演為冶萍公司)、湖北槍炮廠 (后演為漢陽兵工廠)、布紗絲麻四局,其規(guī)模和技術(shù)水平都在國內(nèi)乃至亞洲處領(lǐng)先地位。然限于政治體制、財經(jīng)困窘和對科技的認知水平,興實業(yè)可謂舉步維艱, “荊天棘地”,往往經(jīng)不起價值法則的檢驗,成功與挫折兼具。但張氏的實業(yè)踐履畢竟為中國近代經(jīng)濟的發(fā)展奠定初基,其成功經(jīng)驗與失敗教訓皆可垂之青史。張之洞在經(jīng)濟上有成有敗:一方面奠定華中地區(qū)近代工業(yè)初基,促進工商業(yè)發(fā)展;另一方面官辦企業(yè)弊端叢生,虧損連連,難以維系?。
關(guān)于編練新軍,1896 年張之洞開始大規(guī)模編練新軍,經(jīng)過數(shù)年努力,編成一鎮(zhèn)一混成協(xié)湖北新軍,即陸軍第八鎮(zhèn) (鎮(zhèn)統(tǒng)張標)和暫編第二十一混成協(xié) (協(xié)統(tǒng)黎元洪),其中第八鎮(zhèn)官702 員,兵10520 名;二十一混成協(xié)官288 員,兵4612 名。這是僅次于北洋六鎮(zhèn)的第二支強大的新軍。新軍“新”在何處?馮先生從四個方面予以概述:其一,裝備和訓練,全為洋式。 “一切操練章程,均按西法處理,連一切行軍應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購備。”其二,淘汰老弱和兵痞,對入伍士兵有一系列較嚴格的要求。其中新軍文化素質(zhì)較高尤引馮先生贊賞: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要求入伍士兵粗通文字,這使新軍的文化水準較之以往任何軍隊明顯提高。1905 年湖北新軍在黃陂募兵,入伍的96 人中,就有12 個廩生,24 個秀才。知識青年在士兵中占如此高的比例,是以往任何舊式軍隊所沒有的。士兵構(gòu)成成分這一變化,不僅使得現(xiàn)代化軍事技術(shù)的掌握成為可能,而且新軍士兵也有了接受新的社會政治思潮的知識基礎(chǔ)。這一點對晚清政局的影響十分深遠。”?其三,軍官多由軍事學堂出身者擔任“非武備學堂出身的,不得充將弁。張之洞是這一政策的倡導者之一”。由此催生出現(xiàn)代軍事教育,張之洞在武漢興辦湖北武普通中學堂 (1901)、湖北將弁學堂 (1902)等近代軍事學校,并選派軍事學堂學生赴日留學,培養(yǎng)出吳祿貞、藍天蔚等著名軍事將領(lǐng)。其四,不僅對士兵進行忠于朝廷的政治灌輸,也進行一定的技術(shù)訓練,即 “治兵之道,首在訓兵,其次練兵”。在張之洞苦心經(jīng)營、銳意編練下,仿效德日的湖北新軍成為清末最新銳的新式陸軍,在幾次各地新軍 “秋操”中皆名列前茅,成為各省編練新軍的楷模。?盡管湖北新軍有上述諸多 “新”特點,但囿于張之洞 “中體西用”思想指導,現(xiàn)代化新式裝備湖北新軍,骨子里仍然是舊式武裝。 “張之洞建立新式軍隊的努力,限于仿效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shù),并未著意創(chuàng)造近代化軍隊所必須具備的一系列社會前提。在 ‘中體西用’思想的指導下,張之洞建立近代國防的措施,可以形成某些引人注目的外觀,但在不觸動舊有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官僚制度的情況下,這支用近代化武器裝備起來的軍隊,仍然是一支帝制武裝。”?
關(guān)于文教事業(yè),張之洞致力于書院改制,將科舉應試之舊式書院如經(jīng)心書院、兩湖書院、江漢書院改制為或與學堂近似 (經(jīng)心書院),或略涉 “西學” (江漢書院),或向新學堂過渡的近代高等學堂 (兩湖書院)。大力興辦各類學堂,先后興辦了各類實業(yè)學堂,如礦業(yè)學堂和工業(yè)學堂 (1892)、湖北自強學堂 (1893)、湖北方言學堂 (1898)、湖北方言商務學堂 (1891)、湖北算術(shù)學堂 (1891年)、湖北農(nóng)務學堂 (1898)、湖北工藝學堂、湖北駐東鐵路學堂 (1896)等,師范學堂包括湖北師范學堂(1902)、兩湖總師范學堂 (1904)、湖北師范傳習所 (1903)、支那師范學堂 (1905),普通學堂包括湖北初等小學堂 (1904)、湖北五路高等小學堂(1904)、湖北文普通中學堂 (1903)、湖北文高等學堂、湖北存古學堂 (1907)等,婦幼學堂包括湖北敬節(jié)學堂 (1904)、湖北育嬰學堂 (1904)、湖北女學堂 (1906)等。派遣游學生,其方針是 “西洋不如東洋”,因而主要向日本派遣游學生, “據(jù)粗略統(tǒng)計,達數(shù)千人之多,為留日學生數(shù)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創(chuàng)辦圖書館、報刊等文化設(shè)施,其于1904 年創(chuàng)辦的 “學堂應用圖書館”即湖北省圖書館前身, “為中國最早成立、最先對外開枚的省級公共圖書館。”?馮先生認為,在張之洞 “湖北新政”興辦的諸多事業(yè)中,文教是最為成功的: “張之洞主持湖北新政,政治上難稱成功——它沒有,也不可能挽救清廷政制頹勢。在經(jīng)濟上則有成有敗——一方面奠定華中地區(qū)近代工業(yè)初基,促進工商業(yè)發(fā)展;另一方面官辦企業(yè)弊端叢生,虧損連連,難以維系。而在文教事業(yè)上,卻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果。其在湖北創(chuàng)辦的一系列近代文教設(shè)施,對湖北以至整個華中地區(qū)影響深遠……”?
張之洞督鄂18 載,于湖北武漢早期現(xiàn)代化功莫大焉。1909 年,病中的張之洞對人談起自己在湖北推行 “新政”時頗為自負,認為 “實堪自問”。在張之洞卓有成效的努力下,武漢開始了從傳統(tǒng)的政治中心和商業(yè)市鎮(zhèn)向現(xiàn)代化的國際性工商業(yè)城市功能的轉(zhuǎn)型。
首先, “自相挹注”的近代工業(yè)體系建立,武漢成為中國早期工業(yè)化運動的發(fā)祥地。張之洞督鄂前,武漢除了有一些外資工廠外,民族工業(yè)完全空白,但至辛亥革命前夕,武漢工業(yè)實力已躍居全國前列,工廠總數(shù)和某些經(jīng)濟指標曾一度超過上海。當時全國官辦和官督商辦工廠共46 家,武漢工廠占其中的24%,而上海則只占10.87%。武漢的紡織工業(y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在國內(nèi)獨占鰲頭,1892 年紗錠總數(shù)占全國的40.9%,1893 年占比更高達77.1%。楊銓 《五十年來中國之工業(yè)》說: “……漢口之鐵政局,武昌之織布、紡紗、制麻、繅絲四局,規(guī)模之大,計劃之周,數(shù)十年以后未有步其后塵者。” “當三十年前,能預測現(xiàn)今商戰(zhàn)之潮流,急謀中流之砥柱,篳路藍縷,慘淡經(jīng)營,以作武漢工業(yè)之先導者,厥為張文襄公之洞之功。雖張氏好大喜功,博而不精,然其燭照幾先,氣魄雄厚,有足稱焉。且張氏創(chuàng)辦伊始,銳意以振興工業(yè)為己任,造端宏大,不圖茍簡,如漢陽鋼鐵、兵工二廠,遠采德國之制,誠東亞第一之大規(guī)模,他若紗麻絲布四局,雖至今稱為武漢第一等大工廠可也。夫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張氏能不避其難,而好為其難,此種魄力,實足以開一時之風氣,而樹工藝之基礎(chǔ)。”?正是由于張之洞這種 “開風氣之先”,武漢的早期工業(yè)化運動獲得了長足發(fā)展。張之洞督鄂前,武漢民族資本主義工業(yè)完全空白,但到1911年,武漢已有民辦企業(yè)122 家。行業(yè)涉及機械制造業(yè)、造船業(yè)、榨油業(yè)、火柴業(yè)、服裝業(yè)、面粉業(yè)、食品加工業(yè)、木材加工業(yè)、磚瓦業(yè)、肥皂業(yè)、玻璃業(yè)、棉織業(yè)、煙草業(yè)、造紙業(yè)、化工業(yè)、制革業(yè)、水泥業(yè)、碾米業(yè)、制藥業(yè)、制茶業(yè)、建筑業(yè)、印刷業(yè)、麻織業(yè)和水電公用事業(yè)等。這些私營民族工業(yè)雖不一定都是張之洞直接扶植的,但與張之洞推行的獎勵工商業(yè)的政策有聯(lián)系。”?
其次,武漢成為全國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兩湖地區(qū)的文化中心, “文化湖北” “文化武漢”異軍突起。湖北曾經(jīng)是楚文化的發(fā)祥地,其文化與學術(shù)在中華文化發(fā)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惟楚有材,于斯為盛”。但是,宋元尤其是明清以來,湖北文化卻急劇衰落,文化的實用主義傾向濃厚,學術(shù)名流鮮見。 “湖北素稱文藪,本朝文章,首推熊劉,則仍以時文掩其實用。粵匪(對太平天國的誣稱——引者注)寇攘以來,郡邑涂炭,文獻凋殘,雖經(jīng)克復,而急功近名之士,又思剽竊浮艷以博榮名,問以先正制藝之法,不能舉其名,況六經(jīng)精義乎。”?身兼學者和官僚兩重身份的張之洞任湖廣總督后,十分重視文化和教育, “查自強之策,以教育人才為先;教戰(zhàn)設(shè)方,以設(shè)立學堂為本”?。 “湖北地處上游,南北沖要,漢口、武昌為通商口岸,洋務日繁,動關(guān)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緩。”?因此,他把興辦教育作為其洋務新政的重中之重,湖北武漢一改過去文化落后的局面,成為全國學界注目的焦點,學府林立,人才輩出。 “其在湖北創(chuàng)辦的一系列近代文教設(shè)施,對湖北以至整個華中地區(qū)影響深遠,湖北省的現(xiàn)代大、中、小學教育的雛形,形成于張之洞督鄂期間,武漢大學、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武漢科技大學、湖北省圖書館等重要文教機構(gòu),其淵源都要追溯到張氏業(yè)績。至于從所辦各類新學堂及所派遣的留學生里,更涌現(xiàn)出大批對近代歷史發(fā)生重大影響的改革者和文化人……這里只需提一提普為兩湖書院、武備學堂、文普通高等學堂等校學生黃興、宋教仁、吳祿貞、藍天蔚、董必武、李四光即可。”?
其三,市政建設(shè)成就斐然, “東方芝加哥”聲名鵲起,蜚聲海外。張之洞對現(xiàn)代城市功能有某種自覺的認識,在他的努力下,1899 年夏口廳正式成立。至此,陽夏正式分治,漢口成為有獨立行政權(quán)力的城市,它標志著漢口作為一個獨立的現(xiàn)代城市終于脫離了傳統(tǒng)社會的母體而獲得了新生。在張之洞的有效治理之下,漢口華界的城市規(guī)劃和市政建設(shè)開始起步。1904 年,張之洞主持興建漢口后湖長堤, “1905 年在漢水沿岸筑起一道水墻,繞過平原直到隕水。長14 英里,耗資白銀一百萬兩。目的在于防止周圍地區(qū)免遭洪水襲擊,在此之前這一地區(qū)每年免不了洪水一劫。這一工程已經(jīng)完工,只不過還有一些水閘尚待興修。”有了這道屏障,就可以填高地基,擴建馬路,拓展城區(qū)范圍。實踐證明,后湖長堤修筑后,對漢口的發(fā)展具有改變城市版圖的意義, “涸出田十余萬畝,澤國皆劃為市廛”?,使上至舵落口,下至丹水池的一大片土地露出水面,從此,東北濱江,西南臨漢水,西與北則以后湖長堤為界的新市區(qū)形成了。后人評論說:“總督張之洞,見鐵路外的土地荒廢了太可惜,就在鐵路外另做了一道堤,把漢口的面積擴大了20倍。堤修成后,堤內(nèi)成了良田,人民感激張之洞的功德,稱呼堤為張公堤。”?張之洞將修馬路作為“利民富國之要政”予以高度重視,鑒于 “舊時省城街道仄狹,歲久不修,遇雨或積水或泥淖難行”?,于1905 年在武漢三鎮(zhèn)設(shè)立 “馬路工程局”,是為現(xiàn)代市政機構(gòu)之濫觴。1907 年,漢口老城墻被拆除并在原址上修筑了華界第一條馬路——后城馬路,漢口的商業(yè)區(qū)與居民點向東北方向延伸,逐漸形成了今六渡橋、花樓街、黃陂街、新堤街、半邊街 (統(tǒng)一街)、歆生路 (江漢路)、三民路、濟生馬路、大智路、輔堂街 (友益街)等新的街道,漢口的鬧市區(qū)也逐漸轉(zhuǎn)移到六渡橋和江漢路一帶。張之洞還注意城市公用事業(yè)的建設(shè),水電、電話、公用交通等都開始起步,城市面貌發(fā)生重大改觀。張之洞為維護利權(quán),鼓勵商戰(zhàn),在漢口開辦商務公所,仿照外洋勸工場舉辦湖北土特產(chǎn)交易會, “這顯然是一種鼓勵民間工商業(yè)發(fā)展的開明措施”。他 “十分注意振興實業(yè),發(fā)展商品經(jīng)濟”?,任內(nèi)有設(shè)立漢口商務局、籌設(shè)商學商會、創(chuàng)辦兩湖勸業(yè)場、設(shè)商場局等重大舉措,在其—系列重商興商政策推動下,武漢由一個傳統(tǒng)內(nèi)貿(mào)商業(yè)市場成功轉(zhuǎn)型為國際商貿(mào)大埠。1867 年,漢口間接外貿(mào)額僅3000 萬海關(guān)兩,1901 年達1.35 億海關(guān)兩,增加了1 億多海關(guān)兩,“長江沿岸之商場除上海以外,其交易總額無一能凌駕漢口者……其地實為南北交通之咽喉,商業(yè)之繁榮。”?漢口成為僅次于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外貿(mào)口岸,被人稱之為 “東方芝加哥”: “與武昌、漢陽鼎立之漢口者,貿(mào)易年額一億三千萬兩,夙超天津天津,近凌廣東,今也位于清國要港之二,將進而摩上海之壘,使觀察者艷稱為東方之芝加哥 (美國第二大之都會)。”?
從某種意義上言之,張之洞是和湖北武漢的早期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連在一起的,沒有張之洞的 “湖北新政”,就沒有近代湖北武漢的崛起。當然,除了張之洞個人能力和魄力之外,天時地利也格外惠眷張之洞,自太平天國運動之后,湖北有近50 年沒有發(fā)生戰(zhàn)亂和大的自然災害,對于經(jīng)常受戰(zhàn)爭和天災困擾的武漢來說,晚清近半個世紀的風調(diào)雨順,安定祥和,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發(fā)展機遇。武漢九省通衢,在近代沿海沿江開放格局中,以長江為孔道,形成了滬——漢連動、對外開放的總格局,武漢成為內(nèi)地 “唯一出海口”,張之洞主持修建京漢鐵路通車后,漢口輸出額增加,武漢交通樞紐地位和商業(yè)勢圈得以進一步強化和擴展。 “時勢造英雄”與“英雄造時勢”,在晚清的湖北武漢、張之洞之間極其偶然地結(jié)合起來了,成就了張之洞,成就了湖北,成就了武漢。
張之洞 “湖北新政”意想不到的結(jié)果是催生了辛亥武昌首義這枚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之碩果。關(guān)于張之洞的 “湖北新政”與武昌首義之關(guān)系,歷來議論頗多,早在武昌起義爆發(fā)后不久, 《申報》即有評論指出: “張之洞者,平日以頑固見稱,所以舉動皆以忠君守舊,為新學派所吐棄者也。不謂其所培養(yǎng)之人才、經(jīng)營之事業(yè),如湖北軍隊、如漢陽兵工廠等,均為革命軍之預備,使革命力量頓增數(shù)倍于疇昔。”?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探訪首義之區(qū),看見張之洞新政遺跡,幽默地稱 “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革命家”。張之洞的學生張繼煦作 《張襄公治鄂記》更明確指出張之洞的湖北新政是 “種豆得瓜”:“抑知武漢所以成為重鎮(zhèn),實公二十年締造之力也。其時工廠林立,漢漢殷賑,一隅之地,足以聳動中外之視聽。有官錢局、鑄幣廠,控制全省之金融,則起事不虞軍用之缺乏。有槍炮廠可供戰(zhàn)事之源源供給。成立新軍,多富于知識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領(lǐng)導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學生也。精神上、物質(zhì)上,皆比較彼時他省為優(yōu),以是之故,能成大功。雖為公所不及料,而事機湊泊,種豆得瓜。”?在馮先生看來,張之洞 “湖北新政” “種豆”是因,使作為城市起義的辛亥武昌首義具備起精神和物質(zhì)條件, “中國歷史上多次發(fā)生農(nóng)民起義和貴胄奪取,然而這些暴烈的事變,雖導致 ‘改朝換代’,卻并未觸動社會形態(tài)的基本面,地主經(jīng)濟與宗法君主專制政治一仍其舊。而辛亥革命則另成格局,它引發(fā)國體、政體的更化,是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性民主革命。這樣的革命,只有在近代文明達到一定程度的條件下方有可能發(fā)生。而20世紀初葉中國的某些地區(qū),如辛亥首義爆發(fā)地湖北武漢,便大體具備此種條件。”?而辛亥首義正是工業(yè)化、城市化結(jié)下的 “城市革命”之果。
對于張之洞主辦湖北新政的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之二律背反的矛盾情況,馮先生在 《辛亥首義史》中有深刻分析:
“種豆得瓜”的辨析, “徒資逆用”的責難, “豈非天哉”的無可奈何,從不同側(cè)面反映出 “湖北新政”主持人張之洞思想行徑陷入“二律背反”——張氏操持“新政”,目的在于維護清王朝和綱常名教,但 “新政”創(chuàng)辦的近代工業(yè)、近代軍事、近代文教,卻一并轉(zhuǎn)化為綱常名教的異己力量。
他組訓的新軍、培養(yǎng)的知識分子更成為大清皇朝的掘墓人。張之洞大刀闊斧地引進 “西用”,無不對 “中體”發(fā)生解構(gòu)作用。由張氏推進的近代城市文明 (興學練兵,設(shè)廠制造),竟成為 “城市起義”的動力。戊戌年間,張之洞連康梁變法都不容忍,當然更加痛惡革命,但這位文襄公的新政業(yè)績在客觀上卻助推了革命的發(fā)生。
曾經(jīng)入張之洞幕府20 余年的辜鴻銘(1856—1928),言風趣,喜調(diào)侃,晚年發(fā)表過蘊含機鋒的妙語: “民國成立,系孫中山與張香濤的合作。”實際上,孫中山、張之洞系對立營壘的兩路人,哪有 “合作”之可能?然而,兩人事業(yè)卻有相通、相應之處,張氏的 “湖北新政”,為孫氏領(lǐng)導的辛亥革命奠定了物質(zhì)基礎(chǔ)和人才基礎(chǔ),故從此種言之:民國成立,是孫、張合作的結(jié)果。?
辛亥革命之所以爆發(fā),有著深刻的城市文化背景。商埠的開放,近代工業(yè)的創(chuàng)立,西方思想的輸入等因素,打破了傳統(tǒng)社會內(nèi)循環(huán)的商業(yè)格局,動搖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文化思想,并產(chǎn)生了一批具有現(xiàn)代屬性的商人、實業(yè)家及知識分子;同時傳統(tǒng)社會的士紳階級也在分化,人們要求擺脫封建專制政治和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文明的桎梏,追求發(fā)展經(jīng)濟的新技術(shù)和西方民主制度的現(xiàn)代城市文明。盡管張之洞在武漢實施的 “新政”,其主觀目的是維護傳統(tǒng)的 “道統(tǒng)”和 “君統(tǒng)”——綱常倫理和專制帝制,但在既定事實上,卻導致了武漢傳統(tǒng)城市功能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與社會階層、階級心理的變化,客觀上營造了發(fā)生城市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政治和經(jīng)濟環(huán)境。因此,無論在實踐和還是理論兩方面,張之洞都可以被看作舊時代、舊制度和舊文化的終結(jié)性人物。歷史也確實通過張之洞,給洋務運動甚或清朝的專制統(tǒng)治徹底畫上了句號。
張之洞督鄂與其施行的 “湖北新政”,既給湖北和武漢區(qū)域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 “前無古人”之歷史頂點,同時因為 “湖北新政”基本屬于 “強人政治”型的個人政治行為,也使 “后張之洞時代”出現(xiàn)“后無來者” “不如時昔”的尷尬局面。是故,馮先生在 《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序言中指出: “中國早期現(xiàn)代化是在自身社會條件遠未成熟的情形下,因外力逼迫,由政府自上而下發(fā)動的,故這是一種 ‘強政府、弱社會’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 “上海、天津、武漢之所以成為晚清現(xiàn)代工商業(yè)的三鼎足,除三地特定的區(qū)位優(yōu)勢、西洋勢力的滲透等因素外,與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的坐鎮(zhèn)直接相關(guān)。中國的早期現(xiàn)代化與軍政強人的活動關(guān)系密切,以至人存事興,人亡事衰,現(xiàn)代化進程不斷發(fā)生大起大落以至中斷。這是政府大力干預的現(xiàn)代化所要付出的代價。張之洞離鄂,武漢在全國的地位漸降,張氏本人有此預言,以后的歷史進程也證實了這一點。武漢早期現(xiàn)代化的成敗得失與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洋務后期巨擘張之洞干系甚深,人們?yōu)榇耸①潖埵系墓祝珡埵显谖錆h早期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巨大個人作用,已埋藏著武漢早期現(xiàn)代化坎坷性的伏筆。” “武漢的早期現(xiàn)代化在19、20 世紀之交成就斐然,頗聳動中外視聽,成為現(xiàn)代化 ‘后發(fā)優(yōu)勢’的一個例證,而其間包蘊的種種弊端,又制約著武漢的進程。在此后近一個世紀,武漢的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又續(xù)有發(fā)展,其規(guī)模與水平非張之洞督鄂時可比,但就在全國的地位而言,20 世紀初葉以后的武漢則要發(fā)出 ‘不如昔時’之嘆。”?武漢在近代的崛起與塌陷,既受制于中國早期現(xiàn)代化總體格局,同時更與張之洞與 “湖北新政”所深藏著的種種流弊不無干系。馮先生基于對歷史史實深入挖掘所展開的充滿辯證思維的哲理之論, “洞悉文明轉(zhuǎn)型的種種不可抗拒的規(guī)律”,給我們以深刻的歷史啟示:由于中國社會轉(zhuǎn)型漫長而曲折,依靠個人權(quán)力和個人魅力推動現(xiàn)代化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實而長期存在。張之洞作為湖北武漢早期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開拓者,不僅未能建立一套旨在規(guī)范和引導行政官員領(lǐng)導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政治體制,反而身體力行維護和強化 “人治化”的專制體制,使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與延續(xù)失去了政治保障,導致其開創(chuàng)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 “人走政息”。從這個意義上言之,張之洞對湖北武漢20 世紀前半葉現(xiàn)代化進程的某種 “斷裂”應負不可推卸之責。盡管將湖北武漢比較優(yōu)勢風光不再的原因一股腦兒推到張之洞身上有苛求古人之嫌。但是,由于張之洞是主持一方政務的封疆大吏而非一般布衣百姓,由于 “湖北新政”不是一種傳統(tǒng)的政治行為和個人行為,而是對區(qū)域乃至全國發(fā)展具有轉(zhuǎn)折意義的政治—社會事件,因此,張之洞 “應負其責”該是應有之義。歷史一再表明,只有走出 “強政府、弱社會”和 “人治” “權(quán)治”體制循環(huán)怪圈,依靠體制機制而不是仰賴個人權(quán)力和魅力,建立和健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政府與社會相互聯(lián)動的現(xiàn)代化體制機制,區(qū)域乃至國家現(xiàn)代化發(fā)展方能走出困境,步入坦途。
三、文化史:源遠流長的荊楚文化與異軍突起的江漢人文
馮先生長期研究中華文化史,在傳統(tǒng)文化宏觀研究的架構(gòu)上,長江文化與荊楚文化是其關(guān)注的重要內(nèi)容。
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是中華文明的兩大發(fā)祥地,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文明并不比黃河流域時間晚、水平低,就農(nóng)作物產(chǎn)生的時間而言,還略早于黃河流域。進入鐵器時代的秦漢魏晉,此階段的長江流域文明的總體水平顯然落后于黃河中下游區(qū)域。從三國時期長江流域的吳、蜀與黃河流域的魏國勢力鼎足看來,此階段的長江流域文明仍然在進步之中,發(fā)展水平與黃河流域不遑相讓。兩晉之際與中唐以后,文化中心逐漸南遷,長江流域進入其文化發(fā)展的繁盛期。兩宋以后,完成了經(jīng)濟、文化中心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轉(zhuǎn)移。?馮先生認為長江和長江文化具有 “水” “通” “中”三大特點:一是淡水富集,二是水運通衢,三是文明中心。關(guān)于 “文明中心”,馮先生指出: “如果說中國的自然地理中心在黃河上中游,那么經(jīng)濟地理、人口地理中心則在長江流域以武漢為圓心,1000 公里為半徑劃一圓圈,中國主要大都會及經(jīng)濟文化繁榮區(qū)皆在圓周近側(cè)。居中可南北呼應、東西會通、引領(lǐng)全局,近年遂有 ‘長江經(jīng)濟帶’發(fā)展戰(zhàn)略的應運而興。長江經(jīng)濟帶覆蓋中國11 個省市,包括長三角的江浙滬3 省市、中部4 省和西南4 省市。11省市GDP 總量超過全國的四成,且發(fā)展后勁不可限量。回望古史,黃河流域?qū)χ腥A文明的早期發(fā)育居功至偉,而長江流域依憑巨大潛力,自晚周疾起直追,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與北方之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龍鳳齊舞、國風—離騷對稱、孔孟—老莊競存,共同構(gòu)建二元耦合的中華文化。中唐以降,經(jīng)濟文化重心南移,長江迎來領(lǐng)跑千年的輝煌。近代以來,面對 ‘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長江擔當起中國工業(yè)文明的先導,改革開放的先鋒。未來學家列舉 ‘21 世紀全球十大超級城市’,依次為:印度班加羅爾、中國武漢、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中國上海、泰國曼谷、美國丹佛、美國亞特蘭大、墨西哥昆坎—圖盧姆、西班牙馬德里、加拿大溫哥華。在可預期的全球十大超級城市中,竟有兩個 (武漢與上海)位于長江流域,足見長江文明世界地位之崇高,發(fā)展前景之遠大。”[51]
根據(jù)長江文化的歷史源流,馮先生進而切入對荊楚文化的縱深考察,他分別從宗教文化、思想學術(shù)、以及人物特征等方面進行了分門別類的分析研究、系統(tǒng)地探討了湖北地區(qū)思想文化發(fā)展的特點與規(guī)律。
馮先生認為,湖北在思想上的百花齊放與人才輩出之格局,都同荊楚大地的區(qū)域特征不無關(guān)系。荊楚文化在空間上的分布,大致包含今兩湖及河南、安徽、江西部分地區(qū)。而在時間上的區(qū)隔則主要包括先秦荊楚文化、早期荊楚文化、近世荊楚文化和當代荊楚文化四個階段。以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先秦荊楚文化而論,其主要成就在于莊子的散文和屈原的詩歌,浪漫主義是他們共有的色彩, “楚人愛國忠君、念祖、好巫翕然成風。”而自秦漢以來至東漢末年,早期荊楚文化因地處南北軍事要沖、行政體制的地理分割,已呈現(xiàn)出多元文化大融合的趨勢。隨著宋代經(jīng)濟中心的轉(zhuǎn)移,儒釋道進一步融合催生出理學,近世荊楚文化也就此孕育出 “湖湘學派”,以其經(jīng)世致用的學風代代相傳,爾后更是在近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轉(zhuǎn)型過程中,發(fā)揮了積極重要的作用。[52]雖然鼎盛時期的楚文化影響遍及大半中國,但湖北作為楚文化的發(fā)源地,是楚文化核心和精華之所在。對此,身為楚人的馮先生不無自豪地指出: “湖北又是楚文化的發(fā)源、繁盛之地。楚國文化,作為南方文化的代表,與中原文化相頡頏,自成一派,上起殷商,下迄秦漢。而湖北,作為楚文化之重鎮(zhèn),從古至今,未嘗衰替。從上古的郢都,到中古的荊州,到近古的鄂州,再到今天的武漢,始終為國家、民族興衰的一大關(guān)樞之地。”[53]
馮先生認為,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春秋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的百家爭嗚的局面,百家按地區(qū)性可分為南北兩派, “荊楚學派是南派的代表,它主要活動在楚國境內(nèi)。湖北是楚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故涌現(xiàn)出一大批出類拔萃的思想家。”[54]
——湖北上古的楚郢文化,尤其是1978年隨州 (今隨縣)曾侯乙墓編鐘的出土……充分展現(xiàn)了楚都郢城作為歌舞之都、音樂之都的藝術(shù)魅力,代表了當時樂律的高水平。湖北上古漆器的工藝研究……如江陵九店楚墓出土的方形彩繪銅鏡、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編鐘上的髹漆銅人、荊門包山方形銅鏡等,都一展漆器藝術(shù)的風采。
——湖北是“楚辭”文學的興盛地,屈原的 《離騷》 《哀郢》 《招魂》等楚辭名篇傳誦至今……湖北民間盛傳的上古伯牙、鐘期的古琴臺,也早已成為中國古代知音文化的代名詞。
——東漢時期,荊州已經(jīng)成為墨客騷人、飽學經(jīng)師的薈萃佳地。當時荊州刺史劉表麾下,人才盛極一時。余波延及六朝,荊州文化獨樹一幟。東漢文人禰衡在江夏創(chuàng)作 《鸚鵡賦》 “文無加點”的故事,早已成為一個傳奇。當年偌大的一個小洲,卻因之而名傳千古。多少年過去了,人們?nèi)匀荒钅畈灰选F渲凶钬撌⒚氖翘拼揞?《黃鶴樓》詩。宋代嚴羽稱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 《黃鶴樓》為第一”……李白一生足跡踏遍了大半個中國,在湖北居游時間最長。他多次在荊門、江陵、襄陽、江夏一帶游歷,留下上百首詩文,不少為經(jīng)典名篇。如 《早發(fā)白帝城》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渡荊門送別》 《襄陽歌》 《與韓荊州書》 《上安州李長史書》 《上安州裴長史書》等。李白詩云: “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武漢由是有 “江城”美名。
——在唐代,湖北涌現(xiàn)了不少名家,古今稱羨。有著名的 “文選學”世家李善、李邕父子,江夏人。李善是公認的 “文選學大師”,完成 《文選注》60 卷,他開創(chuàng)的 “選學”,至今仍然為臺、鄂等省的眾多專家所重視。其子李邕,有 “書中仙手”美名,唐代著名書法家,其 《李思訓碑》 《岳麓寺碑》等書法造詣,飲譽至今。同時期還有著名的唐代邊塞詩派的代表人物江陵人岑參、唐代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襄陽人孟浩然、晚唐散文家襄陽人皮日庥、“世客荊州”的小說家段成式等。
——湖北的安陸、黃州等地,是唐宋文學的重要陣地。唐代大詩人李白曾經(jīng)在安陸成家立室,娶前宰相安陸許圉師孫女為妻,前后在安陸居住了十余年,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文。到了宋代,安陸宋庠、宋祁兄弟,名噪一時。宋庠官居相位,刊印 《陶淵明集》等,影響甚巨;宋祁奉命和歐陽修撰寫 《新唐書》。宋氏兄弟的詩文創(chuàng)作,開拓出湖北文學之大局。同時,安陸人鄭獬,參與歐陽修的文學革新運動,為進士第一,累官翰林學士,權(quán)知開封府,以經(jīng)學聞世,亦名噪一時。黃州,古稱齊安,唐宋時多為大臣貶謫之地。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 《齊安秋日》說: “齊安荒僻地,平昔放逐臣。”唐武宗會昌年間,大文豪杜牧被貶任黃州,創(chuàng)作了不少相關(guān)的詩文。到宋代,大文豪王禹偁被貶謫到黃州、蘄州,也有不少作品傳世。最引人注目、成就最大的,是大文豪蘇軾。他曾經(jīng)被貶謫到黃州長達四年,正是蘇軾文學創(chuàng)作的高峰期,也是他文學風格發(fā)展成熟的重要時期。他的前、后 《赤壁賦》 《記承天寺夜游》 《念奴嬌·赤壁懷古》 《東坡八首》 《寒食雨》等著名作品,都創(chuàng)作于這一時期。此外,北宋大文豪歐陽修也是在湖北成才的。
——元明以后,湖北的文化實力已躍居全國前列,在經(jīng)學、文學等領(lǐng)域,更是人才濟濟,雄霸天下。以經(jīng)學大儒而論,元明時期,湖北先后有趙復、郝敬等著名經(jīng)學家,備受臺灣等地區(qū)經(jīng)學研究者的重視。趙復為元代著名經(jīng)學大儒,安陸人,深受忽必烈等元朝皇帝的禮遇和重視。趙復自稱是朱熹的私淑弟子,他傾一生之力,將北宋關(guān)學 (陜西)、洛學 (河南)的影響延伸到河北,為河北之學興盛作出重要貢獻,在宋明理學發(fā)展中地位顯著。郝敬為明代萬歷十七年進士,京山人,有 “窮經(jīng)巨擘”美譽。郝敬的經(jīng)學貢獻,黃宗羲 《明儒學案》稱其 “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jīng)之士,先生實為巨擘”,足見郝敬在整個明代經(jīng)學中的地位和實力。
——以地域和家族而論,明代中后期,湖北學風大熾,人才鼎盛。黃安 (今紅安)三耿(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麻城二周 (周思久、周思敬)、二梅 (梅國楨、梅之煥),公安三袁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俱名噪一時。明代中后期的湖北文學,有執(zhí)全國文壇之牛耳的盛勢。嘉靖年間, “后七子”之一的吳國倫,湖北興國 (今陽新)人,與當時的文壇盟主李攀龍、王世貞齊名,時人有 “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 (王世貞),則西走興國 (吳國倫)”之稱。萬歷年間,著名思想家李贄在黃安、麻城等地,定居達15 年之久,講學著書,傳播新思想,對晚明湖北文化影響極大。公安 “三袁”,深受李贄思想的影響,掀起一股引領(lǐng)時局的文學創(chuàng)作潮流,他們高舉明代中葉以來的個性解放思潮,倡導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取得了很高的文學成就,至今為人稱頌。公安派之后,湖北竟陵 (今天門)派崛起,以竟陵人鐘惺、譚元春為代表,他們繼承公安派的文學新變旗幟,形成 “幽深孤峭”的藝術(shù)風格,對后世影響也很大。
湖北文化發(fā)展源遠流長,高潮迭起,在思想學術(shù)、文學藝術(shù)諸領(lǐng)域涌現(xiàn)了不少杰出思想家和文學家,為古代中國思想史貢獻了湖北智慧。馮先生認為湖北古代思想有包容性、思辨性、否定性三大特點。關(guān)于包容性,湖北古代主體思想雖然受老莊思想影響至深,但因善于融合百家之說,構(gòu)造荊楚學派之論。湖北思想家縱覽群書,博采眾長,包容百家,形成湖北學術(shù)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關(guān)于思辨性,重義理,善思辨,是湖北學術(shù)思想史的一大特點。荊楚老莊學派、兩漢荊州新學、南北朝至隋唐的湖北佛學以至近代江漢新學,都偏重哲理與思辯,具有比較突出的思辨性。關(guān)于否定性, “湖北歷代主要思想家們在哲學思想們在哲學思想方面,一般以講 ‘否定’為主這是老莊哲學思想的繼承和延續(xù)老子講 ‘無’,是一種否定,莊子講 ‘無無’,更是徹底的否定,荊州新學開玄學之先河,也是講否定。佛學論 ‘空’,更是徹底的否定。哲學上以‘否定’論見長,形成了湖北古代哲學思想的基本特點。而否定論可以導致革命性,也可以導致 ‘無為’性,因此,湖北地區(qū)往往成為新舊思想大交戰(zhàn),革新與守舊相沖突的 ‘競爭最劇烈之場’,就不足為奇了。”[55]
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實施素質(zhì)教育的大背景下,學習科學的研究得到廣泛重視。我把“興趣對學習的影響”作為研究的主攻方向,研究興趣教學,探討用怎樣的方法策略引起學生有興趣地學習。隨后,承擔了全國教育科學“八五”“九五”“學生學習現(xiàn)狀調(diào)查與指導”及“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會學習研究”等課題研究。這一時期的研究,使我不僅積累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也從研究過程的管理上積累了較豐富的經(jīng)驗。
古代湖北不獨思想學術(shù)成就斐然,名家輩出,而且在宗教乃至醫(yī)藥、茶道諸領(lǐng)域也取得了引領(lǐng)中華文化的驕人成就:
——湖北是我國道教的重要發(fā)源地。早期道教之一的五斗米道,在三國、兩晉時期活躍于湖北境內(nèi)。221 年,孫權(quán)遷都鄂州,改鄂州為武昌,尊崇道士介象,供奉南岳師祖,改龍蓋山為南岳山,此為湖北最早的道教圣地。
——湖北也是我國佛教的重要發(fā)源地,與佛教的淵源甚深。早在東漢年間,佛教已經(jīng)傳入湖北,并且形成有寺有僧的格局……湖北是禪宗的重要發(fā)祥地,祖庭所在地。湖北江陵名剎當陽玉泉寺,即為隋代天臺宗創(chuàng)始人智顗創(chuàng)建。智顗禪師,在玉泉寺創(chuàng)立天臺一宗。到了唐代,禪宗四祖道信禪師在黃梅雙峰山,創(chuàng)建正覺寺,弘法30 余年,傳衣缽于五祖弘忍 (黃梅人);弘忍傳承衣缽后,又在黃梅創(chuàng)建五祖寺。湖北黃梅,因此被后世公認為禪宗祖庭,以及禪宗的策源地。弘忍圓寂后,其弟子神秀在當陽山玉泉寺大開禪法,開創(chuàng)北宗禪,與六祖慧能的南宗禪并峙,開禪宗南頓北漸之風。禪宗作為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經(jīng)過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在湖北黃梅的傳法,已成定局,五祖之后,形成各家宗派。湖北為什么能出現(xiàn)一批著名的佛學家,并成為 “南方佛教的中心地區(qū)”?馮先生這樣道出原委:“佛教思想為什么能夠在湖北迅速傳播,并出現(xiàn)一批著名的佛學家呢?除了政治、經(jīng)濟方面的原因以外,人文傳統(tǒng)和地理條件也是重要的原因。先秦時期,湖北是楚國的中心,故道家思想流行。漢初,以道家思想為基礎(chǔ)的黃老之學在全國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魏晉玄學也發(fā)端于湖北的荊州新學。佛教思想在不少地方與道家思想、玄學思想相近,故入華初依附于道、玄。湖北的文化傳統(tǒng)使佛教在那里很容易找到結(jié)合點。一從地理條件看,湖北地處中國中部,從西北入華的佛學和從海南入華的佛學常在湖北碰撞、交流,這就使湖北聚集了一大批著名佛僧,佛學極一時之盛也就事非偶然了。”[56]
——中國是茶文化的故鄉(xiāng)……而湖北,是茶文化研究的重鎮(zhèn)。全世界第一部茶葉專著,最著名的《茶經(jīng)》,由唐代湖北竟陵人陸羽撰寫。 《茶經(jīng)》一書,首次系統(tǒng)地向世人展現(xiàn)了茶葉生產(chǎn)的歷史、源流、現(xiàn)狀、生產(chǎn)技術(shù),以及飲茶技藝、茶道原理等,推動了中國茶葉技術(shù)的向外傳播。陸羽因而受到后人的尊重,被譽為 “茶圣” “茶神”。
——中國的醫(yī)藥學在全世界也是獨樹一幟的。對于中醫(yī)藥學的重視和研究,湖北更是獨占鰲頭。明代湖北蘄春人李時珍的 《本草綱目》,標志著我國古代中醫(yī)藥學領(lǐng)域的重要突破。 《本草綱目》在明代各類本草藥籍的基礎(chǔ)上, “集諸家之大成”,記載植物近2000 種,動物460 多種,礦物260 多種,以及物理、化學、天文、地理、農(nóng)業(yè)、氣象等方面的系統(tǒng)知識,在我國科技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被西方的科學家達爾文稱譽為 “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57]
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一樣,荊楚—湖北文化在經(jīng)歷古代既有輝煌、繁盛之后,在19世紀中葉以后,邁入了近代轉(zhuǎn)型期。馮先生認為,荊楚文化 “這當然是中國文化整體近代轉(zhuǎn)型的一翼,但又有其地域性特征”。[58]
關(guān)于荊楚文化近代轉(zhuǎn)型的時間節(jié)點,馮先生認為其 “遠源固然可以追溯至漢口鎮(zhèn)晚明以降的崛起,然其正式起步,則在清咸豐、同治之際,即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這較之東南沿海晚了20 年,但較北方和西部,又呈 ‘捷足先登’之勢”。馮先生特別強調(diào), “我們討論荊楚文化的近代轉(zhuǎn)型,必須正視與東南沿海的 ‘時間差’,以及與西部相比的先進性,從而準確把握荊楚地區(qū)在全國近代文化格局里的第二梯級位置”[59]。
何為荊楚文化近代轉(zhuǎn)型的 “地區(qū)性特色”?馮先生總結(jié)歸納出三大特點,一是漢口開埠、西力東侵的外鑠性特色;二是 “湖北新政”、國家和政府的先導性、主動性作為;三是風云際會、古典與現(xiàn)代交織的瑰麗色彩。關(guān)于 “外鑠性特色”,馮先生指出,1861 年漢口開埠尤其是江漢關(guān)設(shè)立后,漢口逐步成長為水陸交通樞紐,華中最大的貨物集散地, “貨到漢口活”的說法遍傳遐邇,武漢 “九省總匯之通衢”的功能得到充分發(fā)揮,帶動了長江中游商品經(jīng)濟及近代工商業(yè)的發(fā)展。至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漢口的對外貿(mào)易額居全國第二, “駕乎津門,直追滬上”, “這樣的經(jīng)濟土壤,培植了近代文教事業(yè),武漢漸次成為華中首屈一指的文化中心。總之,19 世紀60 年代初漢口開埠,是荊楚社會及文化近代轉(zhuǎn)型的正式起點。這正昭示了荊楚文化近代轉(zhuǎn)型的外鑠性特色。”[60]
“荊楚文化近代轉(zhuǎn)型的又一重要特色,是官府主動性,政府行為是轉(zhuǎn)型的先導性動力。”馮先生認為,張之洞督鄂前,湖北的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在全國充其量只是位居中游的一般性省份,但在張之洞湖北新政的大力推動下,湖北不僅 “從一個中等發(fā)展水平的內(nèi)地省份,迅疾躍升為全國近代化進程的排頭兵”,而且開始了荊楚文化從傳統(tǒng)到近代的轉(zhuǎn)型與跨越。張之洞便是這種轉(zhuǎn)型的主要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張之洞本人經(jīng)歷了從清流黨到洋務大吏的跨越,這正是文化轉(zhuǎn)型在同一個歷史人物身上的戲劇性展現(xiàn)。” “轉(zhuǎn)型前后的張之洞的文教舉措有明顯差別……1889 年總督湖廣,已儼然洋務殿軍,其文教興革與20 年前意趣迥別。”由于張之洞力推 “中體西用”、會通中西的文教新政,湖北武漢文風丕變,人才蔚興, “洋務運動末期 (19 世紀90 年代)和清末新政 (20 世紀前10 年)20 年間的湖北文教興革,是荊楚文化近代轉(zhuǎn)型的直接導因。僅從近代文化的載體——近代知識分子的成長而論,都與這一時段新學堂興辦及留學生出洋熱潮相關(guān)。由封疆大吏張之洞推動的湖北文教興革,使這個較封閉的華中省份一躍而為人才輩出之處。”[61]
由于湖北武漢獨特的地理位置, “同東南沿海相比,近代北方和西北較為封閉、落后,而長江中游諸省,尤其是湖北、湖南 (也即 “楚地”),正處在較開化的東南與較守舊的西北的中間地帶,借用氣象學語言,這里恰置濕而暖的東南風與干而冷的西北風交匯的 “鋒面”,乍暖乍寒,忽晴忽雨。如果說,整個近現(xiàn)代中國都卷入 “古今一大變革之會”,那么兩湖地區(qū)更處在風云際會之處。同時也由于荊楚文化悠久的傳承和厚重的積淀,使得轉(zhuǎn)型期的荊楚—湖北文化中西雜揉,古今交織。于是形成荊楚文化近代轉(zhuǎn)型的第三個特點:古典與現(xiàn)代交融,融鑄古今、會通中西。 “這種時代的風云際會,又養(yǎng)育了湖北學子的深沉哲思,為現(xiàn)代荊楚文化染上古典與現(xiàn)代交織的瑰麗色彩。熊十力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又目睹民國政治的腐敗,退而論學,窮究天人,完成了整合儒釋的大建構(gòu),對中國現(xiàn)代哲學有重要貢獻。聞一多兼涉文史,其新詩蘊涵格律詩韻致,其楚辭、詩經(jīng)研究借助芝加哥社會學派方法,融鑄古今、會通中西,展現(xiàn)了轉(zhuǎn)型時代學人的風范,昭示了現(xiàn)代荊楚文化的特殊魅力。”[62]
在湖北武漢區(qū)域文化的研究中,馮先生于近世荊楚人物著力尤多。
湖北 “地靈人杰, ‘惟楚有材,于斯為盛’:炎帝辟草萊、創(chuàng)農(nóng)耕,嘗百草、救蒼生;楚莊王成就春秋霸業(yè),不飛則已,一飛沖天;香草美人孕育屈原 《離騷》,絕唱千古;出塞昭君、中興劉秀、智慧孔明、傳禪弘忍、放達孟浩然,皆一時俊杰;茶圣陸羽、書家米芾、活字畢昇、藥師李時珍,競獻越代發(fā)明;張居正一條鞭法、譚鑫培須生演藝、黎元洪都督軍政府,堪稱創(chuàng)舉”[63],但是,相對全國尤其江浙甚至江西而言,兩宋以后晚清以前,湖北人才尤其是學術(shù)思想名人并不多見。古來即流傳“惟楚有材”之說,但指的是先秦,漢唐以迄明清的湖北,其實并非人才茂盛之區(qū)。梁啟超 《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指出: “湖北為交通最便之區(qū),而學者無聞”, “湖北為四戰(zhàn)之區(qū),商旅之所輻集,學者希焉。”這是對清末以前湖北人才情形的概括。[64]但這種狀況在晚清發(fā)生根本改觀,湖北人才異軍突起,獨領(lǐng)風騷,成為近代中國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
近代湖北人才蔚興,當以武漢和鄂東為甚。“作為 ‘九省總匯之通衢’的武漢,近一百多年來從中古式的軍政重鎮(zhèn)和商貿(mào)集散地,崛起為華中地區(qū)首屈一指的現(xiàn)代都會,在經(jīng)濟、政治、文化諸方面放射出較大能量,得益于時代風云際會間的群賢畢至,才俊薈萃。”[65]馮先生認為,近代武漢人物(包括旅居武漢的外籍人士)有三大特點:第一,政治類人物密集;第二,經(jīng)濟類人物未成大氣象,實業(yè)多虎頭蛇尾;第三,文化類人物巨匠紛呈。[66]
馮先生認為 “這顯然與武漢近世以來數(shù)度成為全國政治中心直接相關(guān)”。武漢作為辛亥首義之區(qū)和大革命中心, “是早期國民黨人和共產(chǎn)黨人的重要發(fā)祥地之一。湖北籍元老居正 (廣濟)、陶希圣(黃岡)等都是從武漢登上政治舞臺的。武漢籍著名共產(chǎn)黨人則有惲代英、蕭楚女、李求實、項英等;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3 人中,有五位鄰近武漢的湖北人——董必武 (黃安)、陳潭秋 (黃岡)、包惠僧 (黃岡)、李漢俊 (潛江)、劉仁靜 (應城),他們卻曾在武漢求學、任事,都有長期旅居武漢的經(jīng)歷”。[67]
武漢歷來為工商大埠,商賈云集,但本籍商界成大器者寥寥,稍有作為者,也多半有始無終。馮先生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奇特現(xiàn)象。 “張之洞治鄂期間興辦的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絲布紗麻四局曾是中國乃至東亞領(lǐng)先的現(xiàn)代工業(yè)項目,都因內(nèi)外原因而未獲健全發(fā)展,其主辦者蔡錫勇等人也無緣成長為強勁的歷史人物。武漢著名商號 ‘曹祥泰’創(chuàng)始人曹南山父子的日用百貨制造業(y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曾興盛一時,抗日戰(zhàn)爭間則跌入低谷;裕大華集團徐榮廷、蘇汰余20 世紀初葉頗有拓展,之后卻飽經(jīng)磨難,屢遭挫折;號稱 ‘地皮大王’、自詡 ‘創(chuàng)造了漢口’的劉歆生,其房地產(chǎn)事業(yè)于清末民初勢頭甚健,不久則一再敗績,地產(chǎn)大部典賣;創(chuàng)辦震寰紗廠的劉鵠臣兄弟,創(chuàng)辦第一紗廠的李紫云,軋花業(yè)巨頭周文軒,建立民營機器廠的周仲宣,商界聞人賀衡夫、周蒼柏等,也都是企業(yè)初創(chuàng)有成,一度頗具規(guī)模,終因戰(zhàn)亂、天災、政治變故或自身經(jīng)營不善而一蹶不振,甚至全然倒閉。通覽武漢工商業(yè)者的傳、錄,并加以綜匯,便可勾勒出近世民族資本崎嶇坎坷的發(fā)展軌跡。”[68]其實,就經(jīng)濟類人物而言,近代武漢還有兩個奇特現(xiàn)象,一是漢口作為商業(yè)重鎮(zhèn)卻沒有形成有勢力有影響的“漢幫”,二是近代武漢缺少工業(yè)巨擘。
筆者2004 年9 月在接受 《長江日報》記者訪談時,曾以 《武漢文化現(xiàn)象三問》為題對此發(fā)表過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與馮先生的上述觀點不無契合之處。 “在近現(xiàn)代武漢有名的民營大企業(yè)中,創(chuàng)辦者和投資人本地人寥寥。如漢陽周仲宣等的周恒順機器制造廠,武昌徐榮廷等的漢口裕華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武昌裕華紗廠),江夏人李紫云等的漢口第一紡織公司 (武昌一紗廠)和祖籍山西生于漢口的劉子敬等的震寰紗廠等,除裕華紗廠外,經(jīng)營都不成功,后來大都租給外商或?qū)崬橥獾厝私?jīng)營。漢口燮昌火柴廠和既濟水電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是浙江寧波府鎮(zhèn)海人宋煒臣;漢口福新面粉五廠和申新四廠是榮德生的長婿李國偉;漢口最大的機器廠揚子機器廠是僑商顧潤章、王光等合資創(chuàng)辦的,宋煒巨也有投資;承辦漢陽鐵廠的是以盛宣懷為首的上海商人集團;最初承租布紗絲麻四局 ‘商辦’的是在漢口做茶葉生意的廣東商人韋紫封,本地商界沒人出來承租,其后的承租者和主要出資者也大多是外籍人。”此一現(xiàn)象,連當時駐漢日本領(lǐng)事水野幸吉也有察覺: “在漢口這樣的商業(yè)集中之地,有財力的商人,主要來自廣東、寧波等地,反而湖北本地人,經(jīng)營的商業(yè)規(guī)模較小。工業(yè)尚處于幼稚階段。”[69]究其原因,筆者以為與漢口 “轉(zhuǎn)輸貿(mào)易”商業(yè)形態(tài)形成的投機和急功近利的碼頭文化有關(guān)。 “武漢獨特的地理位置,使武漢商人熱衷于商業(yè),而對投資工業(yè)企業(yè)無興趣,極大地影響了武漢城市經(jīng)濟格局,甚至對政治活動也帶來影響……張之洞投資工業(yè)勸募資本的時候,漢口商人響應并不積極, ‘力微識近,大都望而卻步’。地方志書也談到本地士大夫與商人 ‘諱談洋務’。正是這樣一種社會文化氛圍,造成張之洞在武漢無商可招,只能官辦。”[70]
關(guān)于武漢學術(shù)文化人物,馮先生指出,由于武漢兼具腹地城市和對外通商口岸的雙重身份,是新舊文化沖突融會的聚焦點,其特定的學術(shù)土壤培育了一批學貫中西、影響達于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名人。他列舉出歷史地理學家楊守敬,書法家張裕釗,哲學家熊十力、湯用彤、徐復觀、殷海光,地質(zhì)學家李四光,化學家張子高,文字學家黃侃,文學家聞一多、胡風、曹禺,考古學家李濟、黃文弼,藏書家徐行可,法學家張知本,方志學家王葆心等湖北文化名家,論析他們與武漢的淵源關(guān)系:“他們大都在武漢鄰近縣份的鄉(xiāng)間發(fā)蒙于私塾,又到武漢進入新式學堂或改制書院,接受新文化洗禮,不少人從武漢出國留學,學成又曾執(zhí)教、治學于此。武漢確乎養(yǎng)育了一批現(xiàn)代文化巨子,熊十力‘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哲人超識,徐復觀的堅毅果決,殷海光孤行獨往的求索精神,聞一多的奔放和勇于犧牲,胡風九死不悔的堅強個性,以及這批文化人共有的 ‘開放進取’與 ‘保守執(zhí)著’相輝映的雙重內(nèi)蘊,都與江漢交匯處特定的文化氛圍緊密相關(guān)。”[71]馮先生的意思是,正是武漢作為現(xiàn)代城市新思想策源地和新文化薈萃地的城市功能,同時也由于荊楚—江漢地區(qū)多元開放、銳于拓新、敏于哲思的文化秉性,為近代學人的成長提供了溫潤的氣候,肥沃的土壤,形成近代湖北文化異軍突起、人才輩出的可喜局面。
武漢因為現(xiàn)代都市吸引并聚集了大批政軍英豪、工商巨子、文化名流,而偏于湖北東隅的鄂東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這里曾經(jīng)產(chǎn)生了許多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進程的風云人物。 “將軍縣”紅安和 “教授縣”蘄春,一文一武,可謂雙峰并峙,堪稱奇觀。馮先生的區(qū)域文化研究中,對鄂東學術(shù)文化名家輩出現(xiàn)象多有關(guān)注,其中尤有價值者是對鄂東文化人才興盛原因的深入探究。
閱覽徐復觀先生 (1903—1982)的 《中國藝術(shù)精神》 《學術(shù)與政治間》諸書,每震其窮觀極照、心與物冥的博大氣概。展讀與徐復觀相先后的熊十力、湯用彤、殷海光諸先生的論著,也能感受到一種貫穿古今、匯通中外的浩然之氣和特立獨行的精神。在研習上述先生宏著之際,想到他們都是湖北人,而且都是鄂東人,如熊十力 (1885—1968)、殷海光(1919—1969)黃岡人,湯用彤 (1893—1964)黃梅人,徐復觀浠水人,均屬湖北東部黃岡地區(qū) (隋唐稱黃州,元稱黃州路,明清稱黃州府)。進而又聯(lián)想到鄂東的另外一些近世鄉(xiāng)賢,如地質(zhì)學家李四光 (1889—1971)、政治史兼經(jīng)濟學家王亞南 (1901—1969)黃岡人,文字學家黃侃(1886—1935)、文學家胡風 (1902—1985)蘄春人,詩人聞一多 (1899—1946)浠水人,方志學家王葆心 (1867—1944)羅田人,邏輯學家汪奠基 (1900—1979)鄂城人。他們都堪稱某一文化門類領(lǐng)風騷的一代巨子。在一個省份的東隅,于半個世紀間涌現(xiàn)出如此眾多的全國性乃至世界性文化名人,可謂一種罕見現(xiàn)象。[72]
地理位置偏僻、并非經(jīng)濟繁庶區(qū)的鄂東何以短時間內(nèi)出現(xiàn)人才 “井噴”的 “罕見現(xiàn)象”?馮先生引章太炎 “視天之郁蒼蒼,立學術(shù)者無所因,各因地齊、政俗、材性發(fā)舒,而名一家”的觀點,從鄂東特定的地理方位和政教風俗諸方面做了詳細剖析。鄂東雖然偏于湖北東隅,但 “吳頭楚尾”的文化交流融通優(yōu)勢, “剛強的性格,激越的思緒,浪漫的情感”的民情特點,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熊十力、徐復觀、聞一多、胡風等人。這些人的品格塑造都與鄂東民風的熏陶有關(guān),它們又是這些文化大師學術(shù)品性、創(chuàng)作風格的有機構(gòu)成部分。鄂東人“開放進取”與 “保守執(zhí)著”二者兼?zhèn)涞碾p重性格,在熊、徐、聞、胡諸人的文化事業(yè)中也深有體現(xiàn)。
鄂東向來尊文重教。馮先生以他的親聞親見為例,論述這種鄉(xiāng)俗民風對近世鄂東文化人的潛移默化: “這里有問津書院等書院傳世,保持著尊師重教傳統(tǒng),有 ‘愛子重先生’的民謠流行。筆者幼時曾多次從先父那里聽到這樣一則故事:抗日戰(zhàn)爭期間,原在武漢任教的父母親返回黃岡山區(qū)避難,有兩年在鄉(xiāng)間教私塾,得到鄉(xiāng)民的廣泛敬重,甚至當?shù)氐耐练祟^子李顯軍,每至春節(jié)都要前來送禮拜年,見到父親,納頭便拜,可謂 ‘盜亦有道’,這正是鄂東尊師重教傳統(tǒng)的一個側(cè)影。另外,鄂東,特別是徐復觀的故鄉(xiāng)浠水,有藏書傳統(tǒng),明清以來,浠水外出做官、經(jīng)商、游學的人,都給家鄉(xiāng)贈書,這形成一種不成文的規(guī)則。故至今浠水博物館還藏有大量明版、清版線裝書,筆者曾前往參觀、閱覽。以筆者見聞所及,一個縣級博物館藏有如此數(shù)量的古籍,浠水為僅有之例。由此推想,清末民初,在浠水的鄉(xiāng)村、集鎮(zhèn)間,藏書數(shù)量一定可觀,讀書風氣也必然隆盛。浠水及鄂東諸縣,還興辦族學、村學、家塾、門館,民間有集資辦學、尊師重教的深厚傳統(tǒng)。這無疑是鄂東近世人文興盛的基礎(chǔ)。徐復觀等先賢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又得到新式教育的洗禮,加上個人天資與努力的結(jié)合,終于成就為一代文化大師。此為鄉(xiāng)邦之榮,中國之幸!”[73]
在馮先生看來,鄂東文化人才興盛既是兩宋以來中國經(jīng)濟文化重心南移,長江中下游漸成人文繁盛薈萃之區(qū)的大趨勢使然,同時更得益于張之洞“湖北新政”興文教,使湖北迅速崛起為長江流域乃至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給鄂東學人提供了接受現(xiàn)代教育,走上中國乃至世界文化殿堂前所未有之新機遇。此乃近世鄂東大批量涌現(xiàn)具有地域特色、民族氣質(zhì)、世界影響的文化學術(shù)大家之主要原因。
湖北乃至鄂東近世人文薈萃,更直接的動因是張之洞督鄂期間開端的文教興革,使湖北的文化教育水平居于晚清各省前列,鄂籍學人出國留學人數(shù)也名列各省前茅。前述現(xiàn)代湖北文化名人大都是張之洞督鄂期間興辦的新式學堂或改制書院培養(yǎng)出來的,或由其派遣出國留學。如王葆心曾就學兩湖書院;張知本曾就讀兩湖書院,又以官費赴日本留學;黃侃由張之洞親自指示,資助官費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張子高 (1886—1976)曾就學武昌文普通學堂,后赴美留學,入麻省理工學院;李四光曾就讀路高等小學堂,又被選送日本東京弘文學院學習;黃文弼 (1893—1966)就學漢陽府中學堂;聞一多曾就讀武昌兩湖師范附屬小學,后留學美國。如果說,曾國藩 (1811—1872)及其湘軍把湖南山鄉(xiāng)的農(nóng)家子弟帶上全中國舞臺,為近世湖湘人文之盛奠定基石,那么,張之洞開端的文教興革及大規(guī)模留學生派遣,則使湖北學子走上中國乃至世界文化殿堂,徐復觀正是行列中人。如果他無此機遇,可能只是終老浠水一鄉(xiāng)紳或者私塾先生。[74]
四、區(qū)域史觀:大智眼界與大愛情懷
馮先生視野宏闊、立意高遠,其區(qū)域史研究,既不就事論事,也不孤立看人,而是從整體環(huán)境著手,由宏觀入微觀,聚焦于區(qū)域與時代背景之下的人與物、史與事的相互聯(lián)系,進而使區(qū)域不再是空洞的存在,反因獨特的事件及代表性的人物而鮮活豐滿,從而在描繪區(qū)域政治、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演進的歷史軌跡的同時,揭示區(qū)域文化鮮活生動的個性特征。馮先生的湖北武漢區(qū)域史研究是有系統(tǒng)的區(qū)域史觀做指導和觀照的。
(一)整體史觀
整體史觀又稱全球史觀,是將人類社會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一種史觀。整體史觀或者全球史觀的關(guān)鍵不在于是否談論了 “整個世界”,而在于是否把研究對象置于普遍聯(lián)系的 “世界”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言之,馮先生可謂深得整體史觀的精髓。他在把湖北武漢區(qū)域社會與文化置于中華文化的背景下來考察,比較分析中國文化和湖北荊楚文化的共性與個性。在馮先生的區(qū)域文化研究構(gòu)架中,中華文化—長江文化 (南方文化)—荊楚文化 (湖北文化)三個層次雖然都有不同的涉及,但其重心在彼此之間的影響和互動。他認為,湖北兼有 “北雄南秀”的文化特征,荊楚文化不僅有百折不撓的 “九頭鳥”精神,還因南北文化交匯與近代中西文化的互通,融創(chuàng)出 “敢為人先,追求卓越”的湖北佬精神。近代以來, “碼頭文化”更是構(gòu)筑了大武漢雄闊的城市性格,也形成了開放與包容的市民文化精神。故而他將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進行比較,又將荊楚文化與各區(qū)域文化進行比較: “回望古史,黃河流域?qū)χ腥A文明的早期發(fā)育居功至偉,而長江流域依憑巨大潛力,自晚周疾起直追,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與北方之齊魯文化、三晉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龍鳳齊舞、國風—離騷對稱、孔孟—老莊競存,共同構(gòu)建二元耦合的中華文化。”[75]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共同組成南方文化,區(qū)別于北方文化的雄渾、謹嚴,其文化性格為清奇、靈動。正所謂 “北峻南雄,北肅南舒,北強南秀,北塞南華”,用陽剛和陰柔將北南文化特性區(qū)別開來。[76]馮先生以整體史觀觀照近代鄂東文化異軍突起、名家輩出的文化現(xiàn)象,從兩宋以來經(jīng)濟文化重心南移,長江中下游成為文化繁盛之區(qū) (宏觀)到鄂東為 “吳頭楚尾”的荊楚文化與吳越文化交錯融會之區(qū) (中觀),再到鄂東偏于湖北東隅獨特地理位置和政教風俗 (微觀),三個層面,揭示了近代鄂東學術(shù)文化繁榮的宏觀歷史文化背景、中觀區(qū)域交流融通、微觀重教尊文民風浸潤等多重生成機制,是為以整體史觀研究區(qū)域文化典型案例,經(jīng)典之作。
(二)環(huán)境史觀
環(huán)境史觀是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和觀照人與環(huán)境關(guān)系的發(fā)展和演變的歷史觀,其中地理環(huán)境影響人類生產(chǎn)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和法律、區(qū)域文化和國民性格是其重要內(nèi)容。孟德斯鳩是 “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始作俑者,他在 《論法的精神》中用6 章篇幅詳論 “法與氣候性質(zhì)的關(guān)系”,指出 “不同氣候下的不同需求,促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導致不同的法律”[77]。孟德斯鳩十分注重氣候?qū)φ沃贫群头伞裥愿竦挠绊懀J為 “有些國家的酷熱氣候使人身體疲憊,精神萎靡,只有借助懲罰才能讓人履行艱苦的義務。在這些地方,奴隸到對理性的沖擊相對小些,由于奴隸主懶待君主,奴隸也懶待主子。那里的民事奴隸制與政治奴隸制并存”[78]。孟德斯鳩把他的這個理論用于考察中國專制政體,認為 “專制政體盡管其性質(zhì)而到處都一樣,但是,由于狀況、宗教觀點、固有的想法、受到遵循的慣例、人的氣質(zhì)、風俗的不同,差異還是很大的。”[79]“中國的氣候出奇地有利于人口增殖。那里的婦女生殖力之強為世界所僅見。最殘忍的暴政也不能抑制人口增長……中國的君主只能抱有尼祿的那種愿望:但愿全人類只有一個首領(lǐng)。暴政歸暴政,氣候?qū)⑹怪袊娜丝谠絹碓蕉啵⒆罱K戰(zhàn)勝暴政。”[80]孟德斯鳩認為,因為南方氣候炎熱而北方氣候寒冷,所以南北方人的性格迥然有別。他以中國為例對此觀點予以證明: “中國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勇敢,朝鮮的南方人也不如北方人勇敢。”[81]
孟德斯鳩把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文明的影響程度極端化、絕對化,理所當然的不被馮先生所認同。馮先生曾作 《地理環(huán)境與文化創(chuàng)造》專文對之予以批判,指出: “地理唯物論強調(diào)氣候、地形等自然條件對人類歷史文化的影響,與 ‘神創(chuàng)說’和 ‘智力決定論’等唯心史觀相背反,包含著若干合理的、有價值的思想成分,然而又有直觀化、簡單化的偏頗,特別是當?shù)乩砦ㄎ镎摫煌葡驑O端,擴張成 ‘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時則有若干重大失誤。” “‘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把地理環(huán)境全然看作人類社會的外力,認為是自然環(huán)境這種外力決定著社會的進程、左右著人性和文化的特征。事實上,地理環(huán)境并不是簡單作為一種外力影響人類生活的。人類通過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日益把地理環(huán)境轉(zhuǎn)化為人類社會內(nèi)部不可缺少的因素。在這一意義上,可以把地理環(huán)境稱作 ‘人化了的自然界’,或者稱作 ‘社會—地理環(huán)境’。人類歷史的變遷和文化類型的形成,是作為社會的人依托于物質(zhì)存在創(chuàng)造出來的,并非由地理環(huán)境外在賦予。”[82]因此,馮先生指出,在人地關(guān)系上, “有必要復歸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觀點,既高度肯定地理環(huán)境對歷史文化的深遠影響,又揚棄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堅持文化生成的主體客體辯證統(tǒng)一的觀點。”在肯定地理環(huán)境一定程度上影響歷史文化的基礎(chǔ)上,馮先生進一步探討了 “地理環(huán)境究竟在怎樣的意義上、經(jīng)由哪些中介,方作用于人類的歷史進程和文化創(chuàng)造”。
理清了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歷史發(fā)展和文化創(chuàng)造的影響途徑與主要中介后,馮先生進一步探討了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物質(zhì)生產(chǎn)方式、經(jīng)濟——社會關(guān)系尤其是風俗習慣、性格面貌的影響。關(guān)于地理環(huán)境影響國家、民族、區(qū)域文化類型,馮先生指出: “地理經(jīng)由物質(zhì)生產(chǎn)方式這一中介,給各民族、各國度文化類型的鑄造奠定了物質(zhì)基石,各種文化類型因而都若明若暗地熏染了地理環(huán)境提供的色調(diào)。” “地理環(huán)境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的風俗習慣、性格面貌,但這種影響要通過人們自身的活動實現(xiàn)。”而且這種影響并非線性和直接的,表面而暫時的,“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文化創(chuàng)造的影響是真實而側(cè)面,持續(xù)而深刻的,但這種作用主要又不是立竿見影的。在通常情況下,地理環(huán)境只為文化發(fā)展提供多種可能性,至于某種可能性以某種形態(tài)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性,則取決于人類的選擇。”[83]
馮先生以 “地理環(huán)境經(jīng)由一定的中介影響歷史發(fā)展和文化創(chuàng)造”的環(huán)境史觀觀照湖北武漢區(qū)域歷史和區(qū)域文化,從地理——人文的自然與文化生態(tài)角度系統(tǒng)地探討了區(qū)域發(fā)展和文化創(chuàng)造的生成機制,肯定地理環(huán)境對歷史和文化的巨大影響,認為人類的社會因素 (經(jīng)濟的、政治的、心理的)具有強大的選擇能力,使人類可以在同一自然環(huán)境內(nèi)創(chuàng)造不同的文化事實,并進而考察地理環(huán)境為中華民族提供了怎樣的可能性,以及中華民族如何在這些可能性中做出自己的選擇,創(chuàng)造出獨具風格的文化類型[84]。具體到湖北及武漢,馮先生從湖北自然地理和自然氣候出發(fā),引申歸納出湖北自然——人文生態(tài)類似氣象學 “鋒面”特質(zhì),這一生態(tài)特征因為對湖北武漢區(qū)域文化和民俗影響至大至深而被馮先生反復提及。在 《湖北省志人物志稿》前言中,馮先生認為, “同東南沿海相比,近代中國的北方和西北較為落后、保守,在一個長時間, ‘北洋勢力’是近現(xiàn)代中國反動陣營的代名詞。而地處長江中游諸省,尤其是湖北、湖南,正處在較開化的東南與較封閉的西北的中間地帶,借用氣象學語言,長江中游處在濕而暖的東南風與干而冷的西北風相交匯的 ‘鋒面’,因而氣象因素繁復多變,乍暖乍寒,忽晴忽雨。如果說,整個近現(xiàn)代中國都卷入了‘古今一大變革之會’,那么,兩湖地區(qū)更處在風云際會的漩渦中心……湖北在20 世紀初葉崛起為僅次于上海的工商業(yè)基地,繼而成為辛亥革命首義之區(qū)、大革命心臟地帶、土地革命的主戰(zhàn)場之一,便是有力的實證。”[85]地理區(qū)位上九省通衢,為中國經(jīng)濟與文化之中心,自然氣候方面濕暖與干冷交匯,文化風尚上的東西對沖、南北交匯,形成湖北武漢不東不西,既南又北, “沒有特點就是特點”的“雜糅”特征。馮先生對近代湖北文化地理特征的生動形象概括,成為他研究湖北武漢近代轉(zhuǎn)型和文化創(chuàng)造的邏輯起點。
縱觀馮先生的湖北思想史、湖北人物尤其是鄂東人物研究,一個突出特點是都強調(diào)地域因素對思想形成及發(fā)展產(chǎn)生的深刻影響。早在1990 年代初,馮先生與友人主編 《湖北歷代思想家評傳》中即注意到對中國思想學術(shù)人物研究, “不滿足于從宏觀的社會存在、傳統(tǒng)資料兩因素的影響來研究歷史思潮,還要求結(jié)合地區(qū)條件、人物經(jīng)歷等因素對其進行更加細微更加具體的考察,這無論從研究領(lǐng)域的拓展上,還是從方法論的科學化而言,都是一個大的進步”。[86]馮先生認為,盡管中國古代思想學派和思想家思想學術(shù)體系生成機制復雜多樣,但包括地理環(huán)境在內(nèi)的 “地區(qū)條件”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人所共知,中國以學術(shù)流派眾多著稱于世,非但在 “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時代如此,即使在秦漢以后獨斷論盛行的時代,中國學術(shù)的多極潛質(zhì),以及與此直接相關(guān)的學派之爭卻未曾一日止息。造成這種情狀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章太炎曾分析道: “視天主郁蒼蒼,立學術(shù)者無所因。各因地齊、政俗、材性發(fā)舒,各名一家。”他把地理環(huán)境 (“地齊”)、政教風俗 (“政俗”)、人才素質(zhì) (“材性”)三者共同視作學術(shù)派別形成的因素,這是一種比較完備的看法。而結(jié)合地區(qū)條件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正是對這幾重因素綜合考察的科學方法。這里們說的地區(qū)條件當然包括自然環(huán)境,但更重要的是指社會環(huán)境、文化風氣方面的地區(qū)特點,即兼顧 “地齊”與 “政俗”兩個側(cè)面。每個時代的思想,都是這個時代生產(chǎn)斗爭、階級斗爭的反映。每個時代的生產(chǎn)斗爭、階級斗爭都要在特定的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中進行,這個特定的自然—社會環(huán)境因地區(qū)而有差異性,這就給思想發(fā)展帶來了地區(qū)特點。每個時代的思想,又深受傳統(tǒng)思想資料和文化風氣的影響,而傳統(tǒng)的思想資料和文化風氣因地區(qū)而不完全相同,這也是產(chǎn)生思想地區(qū)性的重要原因。另外,思想的發(fā)展一定要通過思想家的主觀思維來實現(xiàn)。每個思想家都生活在一定的地區(qū)里,他們的思維方式、性格特征都受到特定的 “地齊”和 “政俗”的影響,其學術(shù)活動總有一定的地區(qū)范圍,這就使每個思想家的思想體系或多或少熏染上地方色彩。凡此種種,便是我們應當結(jié)合地區(qū)條件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的原因。[87]
(三)長時段史觀
自覺運用 “長時段理論”研究辛亥武昌首義和武漢城市歷史發(fā)展演進,是馮先生湖北武漢區(qū)域史研究的一大特點。馮先生認為,傳統(tǒng)的辛亥首義研究僅僅將其看做一個 “短時段”的事變,顯然有諸多欠缺,需要將其置于整個近代社會轉(zhuǎn)型的全過程,超越單一 “事件史”范疇,方能準確把握辛亥革命的生成機制、革命性質(zhì)及其歷史地位: “法國年鑒學派第二代的代表學者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 《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中提出歷史研究 ‘時段’理論,即區(qū)分地理時段 (長時段)、社會時間 (中時段)、個體時間 (短時段),又將三者分別稱為 ‘結(jié)構(gòu)’ (structures)、‘局勢’ (conjunctures)和 ‘事件’ (evenements)。主張重視地理時間 (‘結(jié)構(gòu)’)、社會時間 (‘局勢’)對歷史進程的深遠影響,個體時間 (‘事件’)為結(jié)構(gòu)和局勢所左右。而傳統(tǒng)史學較多注目于 ‘個體時間’,主要用力于重大政治事件、外交活動、軍事征戰(zhàn)等 ‘短時段’事變的研究,這顯然是有缺欠的。今日我們作辛亥首義史考辨,必須超越狹隘的政治史觀,將視野投射到近代社會轉(zhuǎn)型全貌,從結(jié)構(gòu)、局勢、事件的辯證關(guān)系探索這一歷史事變的生成機制。”[88]借鑒法國年鑒學派布羅代爾的歷史研究“時段”理論與恩格斯晚年提出的 “歷史合力”論,馮先生認為短時段 “首義”事件造因于中長時段社會變革,辛亥首義是由革命黨人與立憲派、從清朝離析出來的漢官、袁世凱集團、清廷滿洲親貴、西方列強等多種力量相互博弈的產(chǎn)物。故而馮先生回到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中去,由微觀入宏觀, “考察19世紀60 年代漢口 ‘開埠’以來,尤其是考察張之洞總督兩湖、主持 ‘湖北新政’以來20 年間的社會變動,考察興實業(yè)、辦文教、練新軍等諸多近代化事業(yè)造成的經(jīng)濟、社會及觀念形態(tài)的深刻演化,還要考察辛亥首義之后錯綜復雜的政情演繹與社會變遷,從而在既宏闊又精微的歷史視野下,辨析辛亥首義史的起承轉(zhuǎn)合”[89]。馮先生還以 “長時段”理論武漢城市史,提出極具創(chuàng)見的 “武漢城市市齡四段說”。他認為,武漢城市史的階段性發(fā)展,可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以盤龍城的 “城垣建筑”為武漢市歷史起點。第二個層次是以國家確定行政建制,為城市定型的重要標志。今武漢地區(qū)定為縣、郡治所,以西漢肇始,距今2100 年左右,而郡治置于今武漢市中心區(qū),則始于三國吳,距今約1700 年左右。第三個層次以武漢地區(qū)的市鎮(zhèn)經(jīng)濟與工商業(yè)開端為近代化標志,大約成于明朝成化年間,距今大概600 年的歷史。第四個層次以19世紀中葉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的漢口開埠,確立武漢轉(zhuǎn)型為現(xiàn)代都會的歷史門檻。[90]為研究武漢城市史提出了新思路,頗具方法論意義。
近40 年來,馮先生的湖北武漢區(qū)史研究持續(xù)不輟,時有佳作。這既緣于他濃烈的鄉(xiāng)邦情結(jié)、家國情懷,他把對家鄉(xiāng)的大愛之情寄托于書齋里,濃縮于筆墨中,同時也基于一種學者使命感,學術(shù)重在經(jīng)世,學問貴于應用,馮先生用自己的智慧為生民謀福祉,為鄉(xiāng)梓獻良策。因是觀之,馮先生并不是關(guān)在象牙塔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桃園之人,方外逋客,他的區(qū)域史研究有著極強的當下意識、參與意識和使命意識。
一是當下意識。馮先生曾經(jīng)研究過晚清經(jīng)世實學,對實學家譏刺時政、詆排專制、倡言變法、變一味考辨古史為 “寫當前活的歷史” 的當下指向和功用價值表示肯定和贊許,藉此明確地表達了自己既追求學術(shù)內(nèi)在圓滿,又為現(xiàn)實提供歷史借鑒的價值追求。馮先生是心憂天下、情系鄉(xiāng)邦的學者和思想家, “傳統(tǒng)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為現(xiàn)實而學術(shù)的文化基因深植于他的靈魂”[91]。他的湖北武漢區(qū)域研究與晚清以來的經(jīng)世實學一脈相承,植根學術(shù),直指當下。一方面,他的純學術(shù)的歷史著述基于強烈的經(jīng)世意識,包蘊著對于當下區(qū)域經(jīng)濟、社會與文化發(fā)展的歷史智慧和有益啟示;另一方面,他的不少文章和演講以嚴謹務實的歷史研究與敏銳深邃的學術(shù)智慧為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及文化建設(shè)提供理論支撐。如馮先生以長時段視角審視大武漢發(fā)展戰(zhàn)略,為武漢成為中部發(fā)展支點提供歷史依據(jù)和理論支撐。他認為,以長時段結(jié)構(gòu)性觀照,武漢擁有成為中部發(fā)展戰(zhàn)略支點的自然稟賦;以中時段局勢性觀照,武漢具備成為中部發(fā)展支點的深厚的歷史積淀;以短時段事件性因素而論,近代湖北多次領(lǐng)受戰(zhàn)略支點安排。自然稟賦、歷史積淀、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機遇,賦予湖北武漢良好而深厚的發(fā)展條件,湖北武漢應當從歷史中找回自信,抓住機遇,復歸其位。 “近代湖北曾是文明領(lǐng)先之區(qū),后因帶際戰(zhàn)略安排,一度落后,當下正進入復歸其位、更上層樓的時候。而實現(xiàn)這種提升,自然稟賦、歷史積淀是基礎(chǔ),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正確抉擇和主觀努力則是關(guān)鍵……一切都有賴湖北民眾及其領(lǐng)導,憑借自然優(yōu)勢、歷史積淀,作出正確的進路選擇,持續(xù)地、堅忍不拔地奮力拼搏。”[92]
二是參與意識。馮先生對于湖北武漢的文化事業(yè)總是滿懷熱情,傾力參與。20 世紀80 年代以來,馮先生參與湖北武漢地方志編纂工作,在省、市副總纂位置上一干就是40 年。先生嘗言: “1986 年主持地方志工作的密加凡同志曾說,馮天瑜是當時擔任 《湖北省志》最年輕的副總纂,一晃40 年過去,我現(xiàn)在是最年長的副總纂了。”他不當掛名副主纂,主持編纂了 《湖北省志·人物志》和 《武漢市志·人物志》,數(shù)十載如一日,兢兢業(yè)業(yè)的為地方史志編纂貢獻著自己的心血與智慧。對于省市重大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活動,只要省、市政府邀請,他都積極參與。2014 年,武漢市開展 “武漢——2049”遠景戰(zhàn)略規(guī)劃活動,受武漢市委、市政府之邀,馮先生給全市領(lǐng)導干部作了 《2049 大武漢前景芻議》報告。回顧3500 年建城史,展望2049 年大武漢,馮先生描繪彼時的武漢將以中國中部首席一線城市,崛起為宜居、高品質(zhì)的世界級大都會。2049 年的大武漢,當由道德淳美、遵紀守法、氣度恢弘的市民決定其城市精神。孫中山制定 《建國方略》,以 “心理建設(shè)”列于首位,次論實業(yè)計劃和民權(quán)初步,此可謂先哲之睿見。我們的2049 設(shè)計,不可見物不見人,而應將新市民的鍛造列為首要任務,須將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落到實處,促成全體市民德業(yè)雙修。我們的愿景是:2049年的大武漢 “天更藍,水更清,路更通,人更雅”,這 “人更雅”尤其切中要處,環(huán)境美、人文美的大武漢有賴文雅、優(yōu)雅的市民建設(shè)與呵護。這帶給人們無限美好的企盼: “武漢形勢之優(yōu),得滔滔萬里的揚子江之賜,古人識此,今人更當舉起 ‘長江文明’旗幟,以之聚集力量,引領(lǐng)潮頭。以 ‘締造從江漢起’的氣派,做 ‘江漢朝宗’文章,建設(shè)活力大武漢,正逢其時,而又時不我待!”[93]
湖北省和武漢市每年都舉辦 “臺灣周”,馮先生不僅寫作 《湖北省在對臺工作中獨特的思想文化資源》長篇文章,為 “湖北武漢臺灣周”提供文化支撐,而且應省委省政府之邀,成立武漢大學臺灣研究所,并親任所長。在研究所成立儀式上的致詞中,馮先生表達了他建設(shè)一個特色鮮明的臺灣研究所,為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和中華民族復興貢獻智慧和力量的決心: “省里和學校要我參與組建研究所,實在是力不能企,出于 ‘布衣憂國’之思,勉為其難,愿與諸同仁攜手共進,用心建設(shè)一個貢奉實績、特色鮮明的武大臺灣研究所,為中華文化復興、為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略盡綿薄。”[94]
三是使命意識。正是由于深懷 “布衣憂國”之思,也由于濃烈的鄉(xiāng)邦情結(jié)和家國情懷,使馮先生的區(qū)域文化研究深藏著復興鄉(xiāng)邦文化歷史使命感。在他看來, “湖北不獨能代表長江文化,并能溝通黃河文化。如山東、河南,只能代表北方文化,不能傳播南方文化于北方。湖北則容納黃河文化,而傳播于長江一帶。一面自己產(chǎn)生文化,一面又為文化的媒介者,因其溝通南北,能令二元文化調(diào)和。在歷史上看來,不能不說湖北所供獻及遺留的功勞是最大的。”然而近代以來,湖北走出來的學者多,研究湖北的學者卻不多。幸而如今能有馮先生這樣的名家,作為武漢的學者,關(guān)注家鄉(xiāng)、關(guān)注城市,把大愛融入對城市、區(qū)域的研究,對武漢的發(fā)展寄予厚望。這份歷史的責任與承擔,恰恰是對梁啟超1922 年演講的有力回應:作為 “中國文化的樞紐”,“湖北不惟綰轂南北,而且居東西要衢,文化上應負調(diào)融之責任,使東南西北各部均得以貫通無阻。”馮先生心系武漢發(fā)展,近年來多次撰文,四處演講,為武漢的發(fā)展鼓與呼, “近代以來,面對 ‘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長江擔當起中國工業(yè)文明的先導,改革開放的先鋒。未來學家列舉 ‘超級城市’概念,并在其預測的未來二三十年內(nèi)的世界十大超級城市中,長江流域的武漢和上海入列,足見長江文明世界地位之崇高,發(fā)展前景之遠大”。[95]他不遺余力地吁吁保護曇華林、漢正街、江漢路、漢口租界等城市老建筑、老街區(qū),維護城市歷史的文脈。他關(guān)心武漢當下城市文化建設(shè),提出城市中除了一些公共的大型博物館,還要關(guān)注和發(fā)展棲息在民間的各種小型的、專題的、有特色的民間收藏館、博物館。文化遺產(chǎn)無處不在,有價值的遺產(chǎn)珍藏在我們生活的很多地方,要善于發(fā)現(xiàn)。特色街道、里份的保存、維護、修整和文化價值的弘揚,也非常重要。[96]他呼吁廣大市民要熱愛武漢,要有城市自信: “我覺得武漢有很多優(yōu)點,豪放、義氣,但有一個毛病,武漢人喜歡指責武漢。我并不反對武漢人批評武漢,但拒絕不熱愛。我去過中國甚至世界上的其他城市,有的比武漢小很多,但市民說起自己的城市,都是褒獎,充滿著熱愛之情。我覺得武漢要把這樣的民風、民氣好好轉(zhuǎn)變,這絕不是要掩飾武漢的缺點,武漢的毛病。但是我們要熱愛武漢,要對武漢未來的發(fā)展前景充滿信心。這一點上,我們不僅傳媒要做工作,包括我們武漢城市設(shè)計者要做很多工作來提升。”[97]殷殷之情,溢于言表。這種對武漢的大愛,讓馮天瑜先生的區(qū)域史、區(qū)域文化研究不再是一個個方塊字堆積起來的冰冷的無機物,而充滿著愛的情懷,愛的溫度,溫暖著城市,溫暖著這座城市里的每一個人……
注釋:
① 王葆心: 《續(xù)漢口叢談》卷1,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 頁。
②⑤⑩ 賀覺非、馮天瑜: 《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2、22—23、8 頁。
③ 馮天瑜: 《湖北成為辛亥革命 “首義之區(qū)”原因初探》, 《江漢論壇》1980 年第 4 期。
④ 馮天瑜: 《辛亥革命前列強對湖北的滲透》, 《江漢論壇》1985 年第6 期。
⑥???????[88][89] 馮天瑜 、張 篤勤: 《辛 亥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61、8、17、49、49、56—57、49、102、9、9 頁。
⑦ 涂文學、高路: 《武昌起義的城市革命特性》,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紀念辛亥革命100 周年紀念學術(shù)論文集》第2 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版,第1167 頁。
⑧ “譯電”, 《民立報》宣統(tǒng)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⑨ 梁啟超: 《暴動與外國干涉》,載張枬、王忍之編: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 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8 年版,第282 頁。
????????????????????馮天瑜: 《張之洞評傳》,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75、95、78、84-85、91、84、96、75、102、101、146、123—124、128、126、142、145、146、146、107、146、107—109 頁。
? 申報館: 《最近之五十季》。
? 馮德材: 《武昌新建經(jīng)心書院記》, 《湖北文征》第11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678 頁。
?? 趙德馨主編: 《張之洞全集》 (三),武漢出版社2008 年版,第412、135 頁。
???[英]穆和德等: 《近代武漢經(jīng)濟與社會——海關(guān)十年報告——漢口江漢關(guān)(1882—1933)》,李策譯,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3 年版,第104、104、104 頁。
? 徐煥斗: 《漢口小志》,民國四年 (1915 年)漢口后花樓盤銘印務局, 《商業(yè)志》第6 頁。
?[69] [日]水野幸吉: 《中國中部事情:漢口》,武漢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5 頁。
? 《意想以外之時局》, 《申報》1911 年 11 月 4 日。
? 張繼煦: 《張文襄公治鄂記》,湖北通志館1947年刊印,第7 頁。
? 馮天瑜、陳鋒主編: 《武漢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導言》,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5 頁。
? 明海英: 《訪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馮天瑜》,《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 年9 月6 日。
[51][75] 參見馮天瑜: 《長江文明館獻辭》,長江文明館編: 《長江之歌 文明之旅》,長江出版社2015 年版。
[52][95] 吳濤、張巍: 《匯聚大河文明 共謀未來可持續(xù)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2018 大河對話”國際論壇綜述》,《文化軟實力研究》2019 年第4 期。
[53][57] 馮天瑜: 《湖北省在對臺工作中獨特的思想文化資源》,2013 年11 月21 日內(nèi)部講演稿。
[54][55][56][87] 馮天瑜、宮哲兵、張武: 《重視區(qū)域思想史的研究——兼論湖北歷代思想發(fā)展的軌跡和特點》,《湖北社會科學》1993 年第12 期。
[58][59][60][61][62][64] 馮天瑜: 《荊楚文化的近代轉(zhuǎn)型》,《光明日報》2004 年 5 月 25 日。
[63] 馮天瑜: 《〈湖北名人〉序》, 《湖北社會科學》2012 年第 4 期。
[65][66][67][68][71] 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武漢市志·人物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3、2、2—3、3 頁。
[70] 涂文學: 《文化漢口》,武漢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39—440 頁。
[72][73][74] 馮天瑜: 《湖北英俊人物》 (內(nèi)部講稿)。
[76]《返本開新尋大美——荊楚狂歌序》, 《美術(shù)之友》2007 年第 1 期。
[77][78][79][80][81] 孟德斯鳩: 《論法的精神》上冊,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12 年版,第279、292、249、151、320—321 頁。
[82][83][84] 馮天瑜: 《地理環(huán)境與文化創(chuàng)造》, 《理論月刊》1991 年第 1 期。
[85] 馮天瑜主編: 《湖北省志·人物志稿》第1 卷,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 年版,第3 頁。
[86] 馮天瑜等主編: 《湖北歷代思想家評傳》,武漢出版社1997 年版,第1—2 頁。
[90][97] 馮天瑜: 《武漢:近中古重鎮(zhèn)到近代大都會》,中信建筑設(shè)計院 “無界講堂”第一講。
[91]鄒賢敏: 《真學者——我談馮天瑜》,載《中國文化探究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9 頁。
[92] 馮天瑜: 《中部發(fā)展戰(zhàn)略支點的長時段思考 (論綱)》 (內(nèi)部講稿)。
[93] 馮天瑜: 《2049 大武漢前景芻議》, 《文化發(fā)展論叢》2013 年第2 期。
[94] 馮天瑜: 《在武大臺灣研究所成立會上的發(fā)言》,2013 年 5 月 25 日。
[96] 2019 年11 月3 日,馮天瑜出席武漢市政府、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共享遺產(chǎn)委員會主辦的 “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論壇”,做了題為《面向公眾的遺產(chǎn)研究:新時代的文化遺產(chǎn)學術(shù)研究與公眾普及》的主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