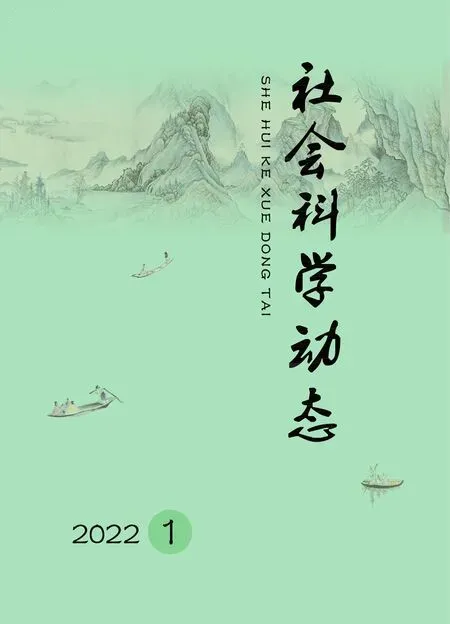監護制度下未成年人隱私權保護之困境及協調
費 宇
一、未成年人隱私權與監護制度的沖突困境
(一)理論設計:監護人作為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者
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新陳代謝、世代更替的過程。作為社會的新成員,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皆處于不成熟的狀態,他們缺乏足夠的經驗和理性判斷能力,以避免作出于己不利的選擇。圍繞著未成年人這一特殊主體,民法設置了種種特別規則,其中,監護便是使未成年人順利過渡到成年階段、成為合格社會分子的基本制度。根據我國 《民法典》的規定,父母監護人的監護義務圍繞著 “撫養、教育和保護”三個方面展開。具體而言,為滿足未成年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監護人向未成年人提供衣食等生活必需品,監護人是未成年人生命維系及健康保障的第一責任人。從社會層面上看,人類本性與社會規則并不時常相合,人非生來便適合在集體中生活。①未成年人的社會化可以被視為克服自身生物本能的過程,需要監護人以教育為手段,促使其理解和遵守在社會生活中生存所必需的一系列社會規則。否則,未成年人難以由一個生物意義上的人轉變為社會生活中的一份子。此外,未成年人是脆弱的,法律假定監護人是未成年人利益的最佳保護者,確定了監護人負有 “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之職責。
就未成年人的隱私權而言,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監護人作為未成年人保護者的思路都得以被延伸。在外部關系中,監護人承擔著未成年人隱私事務處理者的角色。如根據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31條的規定, “個人信息處理者處理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的,應當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同意”。由此可見,監護人就他人利用未成年人隱私信息之行為享有同意權。
在內部關系中,立法者給予了監護人知悉未成年人隱私的權利。根據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63條的規定,監護人對無行為能力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記、電子郵件或其他網絡通訊內容享有代為開拆或查閱的權利。在學術界,學者們基本上皆對 “監護人可以限制未成年人隱私權”這一結論表示贊同,但論證的路徑存在差異。第一種觀點是從限制即保護的角度出發,認為未成年人缺乏社會經驗,危險應對能力不足,行使隱私權時可能會身處險境,因而需要加以限制。②第二種觀點以監督未成年人為視角,認為 “未受監控的兒童有更大的風險從事有問題的行為,包括吸毒、吸煙、酗酒、輟學、早孕等。”③第三種觀點則認為監護人的知情權是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所必須具備的權利④,即對于未成年人相關情況的知悉是監護人履職的前提。綜上所述,無論是在外部關系還是內部關系中,無論是基于立法還是理論研究,監護人作為未成年人保護者的角色都得到了承認。
(二)實踐現狀:監護人時常作為未成年人權益的侵害者
在實踐中,監護人時常以未成年人隱私權侵害者的角色出現,未成年人隱私權與監護職責的履行存在沖突,沖突的表現形式主要有:第一,知悉隱私型沖突。如在實踐中,有未成年人因不滿父親在家中安裝攝像頭而報警⑤,也出現過一位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因日記被父母翻看,而將父母狀告至法院的事例。⑥第二,披露隱私型沖突。此類沖突最典型的表現便是監護人在社交媒體中的 “曬娃”行為。我國對此尚無民事或刑事審判的先例,但有一些國家的法院已就此作出回應。如在葡萄牙,法院要求一對夫婦不得在社交網絡上披露其12 歲女兒的照片或者任何能夠確認她身份的信息。⑦在波蘭,因將2 歲兒子的不雅裸照發布至Facebook 上,法院判處一位父親3 個月的監禁。⑧對 “曬娃”行為,有學者指出, “這也許是父母慶祝孩子生命的一種方式,但另一方面,沒有人知道它對孩子將來的影響。”⑨此類報道屢見不鮮,由此可見,監護人對未成年人隱私信息的披露,不僅涉及到侵權責任成立與否的問題,還可能關乎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
根據我國 《民法典》的規定,監護人的范圍不僅限于與未成年人存在血緣關系的父母,還包括其他近親屬、有意愿的個人或組織等。需要注意的是,父母監護與其他監護人的監護存在本質上的不同。父母與子女血脈相連,由此生發出來的情感大多具有純粹無私的屬性。除去極端的情況,父母在履行監護職責時總是出于愛意,盡管有時方法有誤、程度失當。有別于父母監護人,其他監護人和未成年人之間的關系缺乏此種純粹利他的因素,監護人侵權的案件更容易在非父母監護的情形下發生。如實踐中,就出現過一名繼父長期性侵14 歲的繼女,并將其裸照發布在群聊之中的事例。⑩故此,對于父母監護人與其他監護人不能等量齊觀。
(三)沖突實質:個人自治與保護性他治的固有矛盾
如前所述,在理論的構設上,監護人是作為未成年人保護者的角色出現的。不可否認,監護人是維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最有力群體,但有時,監護人也會轉換為未成年人隱私權的侵害者。對此,有學者指出, “未成年人隱私權與監護知情權,與一般權利沖突不同,其保護的法益具有同一性,權利沖突只是表象。”?但問題在于,既然未成年人隱私權與監護制度指向的法益是統一的,二者之間為什么還會存在齟齬?這是由法益保護的不同路徑決定的,即自治與他治、個人主義與家長主義之間的沖突。隱私權建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若以自決的角度觀察隱私權,則它是 “他人所享有的就其具有私人性質的事務作出自我決定的權利”?。在人際關系中,隱私權具有決定他人能否進入自己的私人生活、調整與他人關系親疏遠近之功能。可以說,隱私權是最能體現和保護個人自治的民事權利。
未成年人是尚未成熟的人,需要監護人的保護,但從另一角度上看,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個發展的過程,隱私權在此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隱私是一道屏障,將不屬于 “我”的外在世界與 “我”相分隔,如此,未成年人才得以感受到自我的存在。 “只有當 (孩子)理解到有一個 ‘不屬于自己’的世界的時候,自我感才會開始產生。”?在有所隱藏、有所保留的過程中,未成年人不斷認識到了 “我”是有別于他人的獨立個體,“我”才能夠成為獨一無二的 “我”。隱私權關乎未成年人自治能力的培養。由于生理和心理的不成熟,未成年人對外界難免存在依賴。然而出于保護隱私的需求,未成年人有動力逐漸去除自身的依賴性,轉而嘗試自我抉擇。一本上了鎖的日記即為例證:一方面,日記內容的形成體現了未成年人獨特內心世界的建構;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有意識維護其隱私的行為彰顯了未成年人自治能力的提升。
監護制度則展現了家長主義 “為了保護行為人的利益而限制行為人的自由”?之取向。家長主義的實質是一種保護性他治,在保護的過程中必然會損害被保護主體的 “自治”權利。在實踐中,出于撫養、教育和保護的需要,監護人必然會對未成年人的隱私權加以限制,即使后者對此往往頗有微詞或試圖反抗。如為了了解未成年人的學習狀況,監護人必然要知悉其成績排名,或觀察其學習狀態。未成年人精神狀態出現嚴重問題,為了解其心事,監護人需要查看其日記。未成年人徹夜不歸,監護人當然有權調查其近期交友狀況及行動軌跡。
以監護制度限制未成年人的隱私權,體現了如下假設:第一,未成年人的自治能力不足,難以維護自身利益,需要他人的保護;第二,法律 “假定父母擁有孩子所缺乏的成熟、經驗,以及做出人生艱難抉擇的判斷能力”?,監護人是未成年人整體利益的第一保護者;第三,未成年人就其隱私權享有的自治利益須讓位于未成年人的整體利益。綜上,未成年人隱私權與監護制度的沖突,在本質上系個人自治與保護性他治的矛盾。此外,監護人常常忽略未成年人自主能力的發展性,未能及時放寬對于未成年人隱私權的限制。法律以十八周歲作為行為能力完備的界限,而不對行為能力作出個案的判斷,此乃維護法的確定性之考量。出于生活經驗的總結,1 歲與17 歲的未成年人當然不能等同看待,監護職責履行的限度應當是動態變化的。舉例來說,同樣是洗浴一事,監護人可以為嬰兒洗澡并知悉其身體隱私,以便更好地照顧他們。但是,隨著未成年人性別意識的強化,若無特殊情況,異性監護人已然不適合為未成年人洗澡。
二、未成年人隱私權的權利救濟困境
(一)監護人行為的合法性難以判斷
監護人監護行為的合法性往往難以判斷。其一,關于監護職責的履行界限問題。如前所述,監護人的權利容易被濫用,一些監護人往往過度探知和披露未成年人的隱私。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監護人有必要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狀況知情。在實踐中,不乏監護人對未成年人不聞不問的極端情況。2015年,貴州省曾出現四名留守兒童共同服藥自殺的悲劇。這四名兒童系兄妹關系,此前已有自殺未遂的經歷,但沒有得到父母的重視。?監護人忽視會對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心理學界的研究表明,忽視型的教養以低要求、低反應為主,監護人既不關心未成年人的健康與成長,也不會規范他們的行為思想及對其提出要求。在此模式下長大的未成年人,會發生不良的心理特征,如自控能力差,做事缺乏耐心等。相比于其他未成年人,他們患抑郁癥的風險更大。?此外,監護人忽視也是青少年產生自殺意念的重要因素。?從結果避免的角度看,恰恰又是因為忽視,監護人無法察覺到未成年人的不良情緒,難以阻止極端事件的發生。其二,監護人和未成年人一般是家庭成員關系,他們之間存在大量的共同隱私,如家族病史、收養關系等,這便增加了判斷行為合法性的難度。而且,基于共同生活的關系,家庭成員往往無須特意刺探,便可以輕易知悉彼此的隱私。其三,對監護人行為合法性的判斷,往往需要考慮倫理情感的因素。在我國,任何類型的監護人都無法因監護人身份而獲得報酬,監護職責的履行往往基于愛和責任,即便有時監護人的行為失當,但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出于對未成年人的關愛所致。
(二)司法救濟手段難以得到應用
當監護人實施隱私侵權行為時,司法上的救濟手段鮮有應用。從訴訟程序的啟動上看,原因首先在于訴訟代理人的缺位。未成年人系無訴訟行為能力之人,當其權益受到侵害時,有賴于監護人代為提起訴訟。而若監護人為侵權人,侵權之訴則難以被提起。有鑒于此, 《民法典》第36 條規定,若被監護人嚴重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則其他具有監護資格的人、居委會、學校、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等個人和機構可以申請撤銷監護人的監護資格。但問題在于,與體罰等可能產生外部痕跡的行為不同,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的隱私侵權是一類具有隱蔽性、日常性的行為,縱使立法者可以設置諸多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機構,但它們也很難深入至家庭內部。另外,未成年人普遍缺乏主動尋求權利救濟的意識,也加劇了司法救濟程序啟動的難度。
司法救濟手段的應用與家庭自治的觀念相沖突。監護關系大多脫胎于家庭領域,自古便有 “法不入家門”的說法。家庭自治觀念有其自洽的一面:其一,家庭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則的延伸,而后者的實質恰恰在于,私法領域的法律關系由平等的個人決定,國家只有在當事人不能解決之時才予以干預。?家庭是私之又私的領域,擁有在處理家庭內部事務時的自由,國家不得任意干涉,這是對家庭自決的尊重。其二,家庭內部問題具有復雜性和非理性的特點。它往往與倫理、情感相互纏連,并不單純是一個法律問題。所謂 “清官難斷家務事”,即是如此。家庭自治強調矛盾的自我解決,節約社會治理成本。其三,從效果上來看,法律途徑不一定是處理每段家庭糾紛的最優選擇。每個家庭的運行都有其內在的規則,此種規則盡管不一定合理,但一定被家庭成員所習慣,法律規則的適用會打破這種自洽性。其四,我國自古有 “家丑不外揚”、“厭訟”的觀念,家庭糾紛的對簿公堂,有時會對家庭關系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結果適得其反。
(三)缺乏恰當的監護人責任承擔方式
理論上講,在監護侵權行為發生后,監護人可能作為侵權行為人,或是基于監護人身份,而承擔兩種不同類型的責任。前者由于司法救濟程序的啟動困難而難以得到應用;對于后一種情況,目前的懲戒措施主要有制止、批評教育、訓誡、責令限期改正。上述措施在實踐中難以真正達到糾正監護人行為的效果:一方面,對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是“沒有牙齒的法律”,懲戒措施的剛性和強制性不足;另一方面,只要監護人的觀念沒有發生根本性轉變,監護關系還在存續,監護權利濫用的情形就有可能繼續發生。
我國 《民法典》第36 條規定,當監護人嚴重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時,法院可以撤銷監護人的監護資格。然而,這一懲罰措施很難被應用于隱私侵權的場合。一是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隱私權的行為大多在小處,尚未達到 “嚴重”的程度,不滿足法律規定的適用條件。二是監護資格的撤銷過于嚴厲和絕對,有違比例原則的要求。此外,父母監護的情形下, “父母與子女的血緣關系和親情是無法替代的。對于監護人在其職責履行中的問題,干預措施必須恰如其分,否則會適得其反。”?不分行為輕重而一味地撤銷監護人的監護資格,可能對未成年人造成更大的痛苦與傷害。
三、未成年人隱私權與監護制度沖突的協調之策
(一)堅持兒童最大利益原則
在處理與未成年人有關的事務時,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是一項最基本的原則。該原則在 《兒童權利宣言》中被首次提出,并因1990 年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的生效而成為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原則。 《兒童權利公約》載明, “關于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該原則在我國 《民法典》、 《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中得到了貫徹。以兒童利益為本位是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的核心理念,至今已成為主流的社會共識。但放眼人類社會,在相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兒童總是不被人們 “看到”。在歐洲中世紀時期,一旦兒童的體力勉強可以自立,他們便立刻被混入成年人的隊伍,成為低齡的成年人。兒童與成年人一樣地工作,一樣地生活,他們與成年人穿一樣的服飾,被畫作微型的成年人。?
近代以來,人們才逐漸意識到需要將兒童和成年人區分看待,盧梭在 《愛彌兒》一書中指出,“最明智的人致力于研究成年人應該知道些什么,可是卻不考慮孩子們按其能力可以學到些什么,他們總是把小孩子當大人看待,而不想一想他還沒有成人”?。從17 世紀末開始,學校代替學徒制成為教育的主要方式,兒童不再與成年人混在一起。?家庭成為家長與孩子之間情感交流的必要場所,孩子在家庭中逐漸占據中心地位。與 “發現并保護兒童”觀念在教育學界的先行不同, “區分兒童并給予他們特殊保護”在實定法中的出現顯然是遲延的。從對待兒童犯罪者的方式上看,立法者并沒有及時意識到兒童在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方面的天然不足,他們對兒童缺乏惻隱之心,對兒童犯下的罪行嚴懲不貸。自19 世紀中葉以來,歐美國家終于意識到了兒童與成人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并通過法律手段的實施,給予兒童特殊的保護。1959 年,聯合國 《兒童權利宣言》首次提出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此乃文明的重大進步。它使得兒童雖為不掌握話語權的弱勢群體,仍可受到以其利益為本位的充分保護。童年時代也終于 “被看作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成為一個超越社會和經濟階級的理想。”?
回到監護制度上來,監護人監護職責的履行,須以兒童利益最大原則為出發點, “評估兒童面臨的日常風險,并就保護兒童的最適當和合理方式作出選擇。”?故此,家長主義干預模式下監護人對于未成年人隱私權的限制,實際上是在對未成年人各項權益進行整體權衡后作出的選擇。作為一項原則,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具有概括性,需要在個案中具體衡量,這需要運用利益位階排序的方法,兩利相權取其重。具體而言, “生命和健康應當被置于首位”?,優先于未成年人的隱私權。這是由于生命權與健康權是自然人從事各項活動,實現自身人格尊嚴與幸福的基礎,失去了生命與健康,其他權利無從行使。如父母為了尋找丟失的兒童而向公眾公開其身體特征,再如父母告知醫生其孩子的遺傳病史、飲食起居等私密信息。上述情形中隱私利益的犧牲是出于保護生命健康權的需要,根據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監護人的行為并無不當。
在實踐中,最難判斷的是監護人日常性的撫養、教育行為與隱私侵權行為之間的界限。這是由于,監護人在獲取未成年人隱私之前,無法對其內容進行準確預測,而只能基于邏輯及對未成年人的固有了解,推測其可能遭遇某些風險。對此,應當在堅持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的前提下,允許監護人基于合理懷疑,限制未成年人的隱私權。即便最后從結果出發,證明監護人的限制系虛驚一場,監護人也可得于免責,以此來保障監護職責順利履行。
(二)區分未成年人的不同發展階段
未成年人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雖然法律將18 周歲作為自然人取得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時間節點,但是這不意味著未成年人在此之前一直生活在搖籃里,一應事務皆由監護人包辦。在未成年人成長的過程中,監護人應當逐漸減少對于未成年人的限制,給予他們越來越多的自主空間,以期使其成為一個真正獨立成熟的個體。
如前所述,兒童這一主體是被 “發現”的,童年這一概念是被社會建構的。以年齡為界限區分未成年人的不同發展階段,也實屬一種人為的擬制,需要符合在某一特定時期內,社會成員普遍接受的對某一事物的看法。本文根據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規律、未成年人參與社會生活的時間節點,參照心理學界的觀點,將未成年人的成長階段劃分如下(以下年齡段的下限包含本數,上限不包含本數):嬰兒期 (0—2 歲)、幼兒期 (2—6 歲)、學齡兒童期 (6—12 歲)、青少年期 (12—18 歲)。
在嬰兒期,未成年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他們對身體的控制及對世界的認知極為有限,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因此,監護人有義務持續關注嬰兒的一舉一動,以避免發生損害嬰兒生命健康的危險情況。此外,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看,如果監護人對嬰兒的活動給予密切的注意和情感支持,敏感地回應他們的需要,則可以促使嬰兒形成安全型依戀。?此種依戀有助于未成年人在日后表現出更高水平的自尊、共情能力和社交能力。總之,為了保障嬰兒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監護人需要密切、全方位地關注嬰兒,掌握關于他們的一切情況,這不構成對于未成年人隱私權的侵犯。
在幼兒期,未成年人的語言技能迅速發展,自我概念逐漸建立,他們可以與成人談論重要的個人經驗,開始形成關于自身生活的自傳式記憶。?在這一階段,未成年人對評價自身行為的規則和標準形成了一定了解,尷尬、羞愧、內疚等自我意識情緒開始出現。?因此,監護人在談論一些重大敏感隱私,如身體缺陷時,應當考慮未成年人的主觀感受及被記憶的可能性。但此時的未成年人尚未形成隱私意識,仍不具備處理自身隱私事務的能力。
在學齡兒童期,兒童步入學校這一重要的社會化機構,社會交往活動日益增多。從人際關系的角度看,同伴對于兒童的重要性不斷增強,友誼的判斷標準經歷了由 “他人能否為自己提供愉悅的機會”,到 “他人是否與自己形成親密和忠誠的心理關系”之轉變過程。?在監護的過程中,監護人應當注意給予未成年人發展主觀隱私、發展友誼的空間,對他們不宜進行持續的控制和干預。另外,該階段未成年人的性別意識顯著增強,性別疏離的現象十分突出,一個明顯的證據是,他們的社交圈幾乎皆由同性別的同伴組成。?監護人應當尊重未成年人對異性的敏感心理,盡量避免在異性面前披露未成年人基于性別特質所衍生的隱私,如不宜再帶該階段的未成年人進入異性公共浴池洗浴。
在青少年期,未成年人的身體加速發育,進入性成熟階段,他們的智力和能力不斷趨于成人化。青少年可以在與他人的比較中認識自己,意識到自身是獨立于包括監護人在內的所有他人的獨特個體。?在這一時期,青少年的自我概念發生重大的變化,他們不斷尋求自身的自主性,試圖擺脫對監護人在心理上的依賴,以謀求獨立和自由。他們開始依靠同伴來獲得情緒支持,更加愿意向朋友而不是監護人分享自己的秘密。對此,監護人要保持與未成年人的良好溝通,給予他們充分的自主空間,尊重未成年人的隱私權,將自身的角色定位由干預者和控制者轉為引導者和監督者。
(三)區分父母監護人與其他監護人
從世界范圍內看, “監護”這一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所謂廣義監護制度,系指對一切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人身及財產權益進行監督和保護的制度。就未成年人而言,其包括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及父母以外的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的監護。?從立法預設上看,廣義監護制度將其他監護人等同于父母來看待,實際上降低了保護未成年人的力度。父母與其他監護人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就性侵而言,發生在父母子女中的概率遠遠低于發生在其他監護人與未成年人之間的概率。這一方面是由于父母子女之愛的無私性,另一方面在于父母對子女負有極重的倫理道德義務。
大陸法系國家將親權制度與狹義監護制度并行使用,前者系指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人身及財產權益加以監督和保護的制度,后者的適用對象則為不在親權保護下的未成年人及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成年人。?將親權與監護相互區分的目的,在于法律將以此進行有差別地干預。對于父母,立法者相信他們會更加關心子女的利益,因而采取了放任的態度,相應的親權監督機構也未設立。對于狹義監護制度下的監護人,法律大多是限制主義的取向:監護人監護權的行使范圍小于父母親權。法律設置了監護監督制度,監護人行使監護權須受法院、監護當局或其他監護監督人的監督。?
我國 《民法典》采取了廣義監護的立場,即便形式如此,也應當在實質上對父母監護人與其他監護人加以區分,并以此為基礎建立對其他監護人的監護監督制度。借鑒大陸法系國家的經驗,可以從設置監護監督人、設置行政監護監督機構及完善司法監護監督機制三個方面入手。
(四)建構強制性家庭教育指導制度
當監護人為侵權行為人時,未成年人隱私權的救濟陷入了困境:傳統的司法救濟手段難以得到應用,現有監護人責任的承擔方式難與救濟需求相互匹配。在此種情況下, 《家庭教育促進法 (二審稿)》的公布為困境的破除提供了新的思路。其第45 條規定了監護人受懲戒的兩種情形:一種是通過監護人自身的行為表現出來,即 “不正確實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另一種則通過未成年人的不當行為表現出來,即 “未成年人實施嚴重不良行為或者犯罪行為”。若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在辦案時發現上述情形,可以責令監護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導。對于該決定的性質,一審稿更傾向于賦予其強制性。若監護人違反了該決定,決定機關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對監護人采取警告、罰款、拘留等措施。但在二審稿中,上述措施被刪除,這大大削減了家庭教育指導制度的強制性。
強制性家庭教育指導,在臺灣地區又被稱為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是指基于主管機關的決定,由監護人接受的關于改善家庭教育方式、增進監護人職能的強制性教育活動。根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規定,監護人若存在該法所列舉的監護失職情形,則會被主管機關責令接受四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的親職教育輔導;若不接受輔導或拒不完成時數,監護人將被按次處以罰款,至其參加為止。在英國,親職教育條款被規定于 《犯罪和擾亂秩序法案》中,法院可要求未成年罪犯的父母參加親職咨詢或指導課程,時間最長不超過三個月。強制性家庭教育指導制度在促進親子關系、糾正監護人及未成年人不良行為等方面產生了積極作用。實證研究顯示,2012 年臺灣地區完成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案件共有166 例,其中在半年后再次被通報虐待兒童的有13 例,再犯通報率為7.8%。?
回到未成年人隱私權與監護制度的沖突上來,不難發現,破除困境的關鍵并非在于施以嚴苛的懲戒手段,而是在于能夠實現對監護人觀念的真正轉變。就強制性家庭教育指導而言,它是一種制度性的構設,可以用來作為教化監護人、傳遞正確監護觀念的依托。從家庭教育指導的內容上看,首先應當使監護人確立以未成年人為本位的觀念,并將兒童最大利益原則作為執行監護事務的首要原則。其次,在具體的沖突中,監護關系中的雙方應當堅持雙向溝通原則,建立起彼此之間的信任、尊重和關懷。?再次,監護人需要認識到隱私權之于未成年人的重要意義。隱私權攸關未成年人自治能力的養成, “即使某個孩子現有的自治程度,不能使他單獨行使隱私權,但也應當基于個人自主的理由,前瞻性地尊重孩子的權利。”?隨著未成年人年齡的增長,監護人要逐步放寬對其隱私權的限制,使其就自身事務作出決策。
四、結語
未成年人隱私權與監護制度沖突的和緩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需要相信——在個體意識、隱私意識日益增強的今天,在監護關系日益開明的時代背景下,困境的破除是必然的趨勢。只不過,這種必然需要被賦予時間,需要由法律、教育等多重方式加以引導。可以說,監護關系的協調任重而道遠。
注釋:
① 參見費孝通: 《生育制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年版,第135 頁。
②? 參見李延舜: 《論未成年人隱私權》, 《法制與社會發展》2015 年第6 期。
③? Bryce Clayton Newell, Cheryl Metoyer, Adam D.Moore, Social Dimensions of Privacy: Privacy in the Family,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p.105.
④? 參見劉金霞: 《未成年人隱私權與監護人知情權:和諧、沖突與法律規制》, 《法學雜志》2007 年第4期。
⑤ 參見韓丹東、蘇欣雨: 《14 歲男孩報警稱被父親用攝像頭監控引發熱議 監護權與隱私權爆發沖突咋辦》,《法治日報》2020 年 9 月 15 日第 4 版。
⑥ 參見谷武民、竇俊杰: 《日記被偷看 男童告父母》, 《大河報》2010 年 9 月11 日第A11 版。該新聞報道沒有提及未成年人訴訟能力及訴訟代理人的問題,法官最終以批評教育監護人的方式處理了糾紛。
⑦ 參見張遠南: 《網上 “曬娃”需謹慎》, 《人民日報》2015 年 10 月 13 日第 21 版。
⑧⑨ Anna Brosch, Sharenting—Why Do Parents Violate Their Children’s Privacy, The New Educational Review,2018, 54(4), pp.76-79.
⑩ 參見 《男子性侵14 歲繼女1 年 并將其裸照傳聊天群》, 《央廣網》,訪問時間:2021 年10 月4 日。
?張民安、宋志斌: 《自治性隱私權研究——自治性隱私權的產生、適用范圍和爭議》,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 頁。
?[美]菲爾·艾溫: 《成長的秘密——兒童到青少年期的友誼發展》,黃牧仁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45 頁。
? 黃文藝: 《作為一種法律干預模式的家長主義》,《法學研究》2010 年第5 期。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ham vs. J. R., United States Reports, 1979, p.584.
? 參見汪志球、潘躍: 《畢節4 名兒童服食農藥身亡 貴州專項檢查留守兒童救助幫扶》, 《人民日報》2015年 6 月 13 日,第 4 版。
? 參見馬衡等: 《兒童抑郁癥與父母教養方式、忽視的相關性分析》, 《國際精神病學雜志》2021 年第2期。
? 參見余思、劉勤學: 《父母忽視對青少年自殺意念的影響:自尊和希望的中介作用》, 《心理發展與教育》2020 年第 3 期。
? 參見李軍: 《私法自治的基本內涵》, 《河北法學》2005 年第 1 期。
? 關穎: 《〈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家庭保護的法律缺陷——兼論監護人的教育、監督和懲戒》, 《中國青年研究》2006 年第 5 期。
?? 參見 [法]菲利浦·阿利埃斯: 《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沈堅、朱曉罕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1、3 頁。
?[法]盧梭: 《愛彌兒——論教育》上卷,李平漚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2 頁。
? [美]尼爾·波茲曼: 《童年的消逝》,吳燕莛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98 頁。
?Alison S. Aaronson, Changing with the Times: Why Rampant School Violence Warrants Legalization of Parental Wiretapping to Monitor Children’s Activities,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2001, 9(3), p.822.
? 參見 [美]戴維·謝弗、凱瑟琳·奇普: 《發展心理學:兒童與青少年》,鄒泓等譯,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9 年版,第 404 頁。
? 參見 [美]勞拉·E·貝克: 《嬰兒、兒童和青少年》,桑標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285 頁。
? 參見 [美]戴維·謝弗: 《社會性與人格發展》,陳會昌等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12 年版,第117—118頁。
? 參見雷靂: 《畢生發展心理學:發展主題的視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255 頁。
?? 參見 [美]羅伯特·費爾德曼: 《發展心理學——人的畢生發展》,蘇彥捷、鄒丹等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 年版,第392、16 頁。
?? 參見李霞: 《監護制度比較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16、16 頁。
? 參見夏吟蘭: 《民法典未成年人監護立法體例辯思》, 《法學家》2018 年第 4 期。
? 參見沈瓊桃: 《處罰父母、拯救小孩?臺灣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的結果評估:以兒虐再通報率為指標》,《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018 年第1 期。
?Kay Mathiesen, The Internet, Children, and Privacy: The Case Against Parental Monitoring,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3, 15(4), p.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