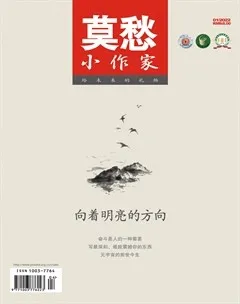一只斑鳩的角色
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斑鳩的鳴叫了。一整個冬天加上一整個春天,斑鳩一直在叫,“咕咕咕”,“咕咕咕”。叫聲有時候柔軟綿長,有時候又急切焦躁。循著聲音找過去,常常是孤單的一只,鼓著頸上的羽毛,站在樹枝上,一叫就是半天,從來不知道疲倦。有時候也看到兩只。一只對著另一只滿懷著深情鳴唱著。一只飛走了,另一只還在那里叫。好像它知道那只一定能聽到,好像它知道那只一定會明白。
整整兩個季節,斑鳩一直停留在我的窗外。它們的聲音并不動聽,鳴唱的詞曲也是簡陋單調,然而這里面卻含著火一樣的熱情。它們執著的鳴唱只是在重復著幾個字:“咕,咕咕。”這是它們的歌,也像是它們的誓言。這種鍥而不舍的重復的鳴叫,竟然不讓人反感。天黑下來,斑鳩回到自己的巢中去休息了,我的耳朵里依然是它聲音的回響。我聽得出來,這種“咕咕咕”的鳴叫,不只是一種簡單的重復,這里面飽含著一種特別的情緒。只要仔細聽,就能聽到一只鳥兒的心思。
夏日來臨,這些每天環繞著我的,或遠或近的鳴唱漸漸消失了。只有在偶爾的時候,才聽到遠處有幾聲。幾聲鳴叫之后,又立即消失在無邊無際的梅雨里,或者風中。我每天還望著窗外,只是原先跳躍在枝頭上的斑鳩不再出現。聽不到它們的鳴叫,讓我感到沮喪。我隱隱約約感覺到,一定發生了什么。
七年前,因為寫一個歌劇,我到貴州的大山里面,去一個侗族的寨子里采訪,然后聽到了一個關于斑鳩的故事。
如果一個女孩愛上一個男孩,她羞于表達,也難以相見。她會養一只斑鳩,一只白色的斑鳩。當黑夜來臨,她把這只白斑鳩藏到自己的衣柜里,然后上床睡覺。她睡著了。斑鳩飛出來,在門外等她。她從夢里走出來,騎在斑鳩的背上,斑鳩展開白色的翅膀,帶她去見心上人。她和他在夢中相會。她在夢中可以盡情地傾吐她的思念。第二天醒來,男孩記得有一只白色的斑鳩飛進他的夢中。他就知道了,有一個女孩在愛他。他會尋找。他總會找到。
在我居住的小村里,只有山斑鳩、珠頸斑鳩,從來沒有見到一只白色的斑鳩。然而因為這個傳說,我對所有的斑鳩都心生好感。可是當夏日來臨,斑鳩漸就漸少了,它們成群地飛走,不知道飛去了哪里,就像要逃離我。
沒有了斑鳩的小村多少有些寂寞。可是我已經習慣了這里,我很少離開我居住的小村,這個小村已經成了我的世界。對此我深感滿足。我當然知道幾公里之外有著熱鬧的小鎮,幾十公里之外有著繁華的都市,可是我已經不喜歡了。我與城市和人群已經產生了隔閡。
疫情無可挽回地使人與人之間產生了距離。起先是因為或長或短的隔離,而后就是一種莫名的焦躁,漸漸使人疏于往來。在一段艱難的寂寞之后,就習慣了,甚至變得歡喜。我喜歡這樣的疏離感。這種無所事事的安靜,把我從一種狂亂的忙碌奔波和粗鄙的快活中拉了出來。我可以坐在陽臺上,一整天什么也不做。看雨從頭頂落下來,又慢慢消失在地平線上。看小河的水渾了又清,清了又渾。看遠處窗口的燈光,亮了又漸次熄滅。我開始記得每一個節氣。芒種之后是夏至,夏至之后是小暑。我以節氣為我生活的節奏。每隔十五天,我會關心什么花又要開放,什么菜正當時令,什么樣的星星到了什么位置。我可以一整天不說一句話,而后在這沉默的寧靜中得到一種從來沒有的自由。
我僻居鄉下,有個大好處,就是不用再參加堂皇的飯局。每一個飯局都有一套特別的儀式,每一套儀式都是某種秩序的體現。只要身處現場,你就要進入這個秩序。雖然彼此之間還在你推我讓,其實你完全了然你的座次。用不著主人示意,世俗人情早就安排好了。入座之后,你就進入了你的角色,你就要扮演好你的角色。有人如魚得水,姿態柔軟地穿梭其間。有人恰到好處地展示著自己的威嚴。有人矜持傲慢,有人放浪形骸。有人酩酊大醉,有人局促不安。也有人惶惑生澀,如坐針氈。沒有一個人會是無緣無故出現的。所以飯局上的每一個人,都不可缺少,每個人都是天生的好演員。你的角色不是主人安排的,而是由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安排,甚至主人也是被它所安排。所有人都只有服從。不同飯局上的座次,就像一串復雜的坐標,準確地標示著你在社會當中所處的位置。一場飯局就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洗禮,同時也是一種溫和的規訓。
座次的排列在生活中隨處可見,有時甚至會顯得極為荒誕。譬如排列整齊的大合影,隆重嚴肅的會議,場面盛大的祭祀,都是在表明某種社會格局。在這個格局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不自然的,都是虛假的,都是社會化的表演者。只是有人入戲,有人不入戲,有人入戲太深。人類社會在演化過程中,發明了一整套儀式。所有的儀式,都是馴化的工具。演員們在這些儀式之中上躥下跳,努力往上提升自己的位置。在這個努力的過程中,人會感到焦躁、快樂和痛苦,同時失去寧靜。于是儀式變成了日常生活,甚至就是整個人生。飯局、祭祀、會議,所有的儀式都在營造一種權力的局勢,局勢一旦形成,就需要一種“犧牲”。有時候是豬牛羊,有時候是人格,有時候是斑鳩。
在我的老家,斑鳩叫野鴿子。它的味道不見得比家鴿或者家雞更好,可是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它竟成了招待貴賓的上等菜肴。鄉下人的心里有著一種頑固的等級觀念。這種觀念在飯局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不只是排座次有著繁復的講究,在食譜上也體現著等級。鄉里來人,都是尋常的酒肉,菜品比村里請客要多,分量也要更大。縣里來人,就要加一個“全烤豬頭”。完完整整一只煮熟的豬頭,生動地裝在一個大盆子里。豬頭首先推到坐在主位的嘉賓面前,請他用刀割第一塊。要是省里來人,就要再加一份“烤野鴿”,形同烤乳鴿的一只斑鳩。根據省里來人的多少,有時也會是兩只或者三只,都放在一只大盤子里。野鴿子烤得皮脆肉嫩,切成小塊,又完好地組裝在一起。主位的嘉賓先動筷子,夾一塊,然后依次傳下去。并不是人人都有。座次排在最后面的人,如果看到盤子空了,要假裝看不到,就像從來沒有過這道菜,臉上一樣的歡歡喜喜。我是完全能領會其中意味的。并不是沒有足夠的野鴿子,只是為了在這個堂皇的場面上,明確分一個主次。有些是你可以得到的,有些是你不能得到的。這個傳統由來已久。大司寇孔丘沒有得到魯國國君春祭時賜予的膰肉,就知道自己被罷免了,只好踏上十四年的流亡之路。一塊祭肉改變了中國的文化史,一只斑鳩又串起了這個文化史。
大群的斑鳩從我的小村里飛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用它作為等級象征的惡習已經傳染到這里。斑鳩既然是野鴿子,它當然不會屈服,它必然會飛走,飛到一個沒有傷害的地方去。可是人們選擇它,恰恰因為它是野的。這個野字,讓人有征服的快感。所以在每次上這道菜的時候,主人一定會向主賓強調,這是野的。人類撕咬啃食野味,其實并不只是貪圖它不一樣的味道,更在于對野性的敵視,或者無望的向往。
斑鳩從我的屋頂上飛過,它看到一個人在陽臺上朝著天空張望。斑鳩飛過它曾經筑巢的小村,它看到小河在流淌,藤蔓在攀緣,小販在村口叫賣。斑鳩飛過了南京城,它看到大街上車水馬龍,小巷里人頭攢動,幾百萬人聚在一起奔波忙碌。斑鳩急速地飛過去,很快變成了一個小黑點,消失在地平線上。對于它來說,一些人聚在一起,就是想用一只餐盤把它端上臺面,然后折斷它的翅膀,讓它不能從一個夢飛到另一個夢。它不愿意。對于一只野鴿子而言,能飛的世界才是一個好世界。
申賦漁:1970年生于江蘇泰興,著有“中國人的歷史系列”《諸神的蹤跡》《君子的春秋》《戰國的星空》等多部作品。
編輯 木木 691372965@qq.com